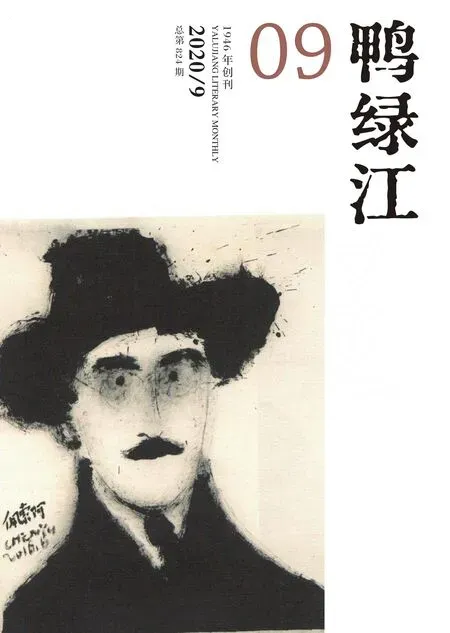《空山》的全球意识与古典精神
2020-11-17薛红云
薛红云
当六角形的雪花漫天飞舞于即将消失的机村上空时,藏族作家阿来的六片花瓣结构的《空山》的第六卷“空山”也画上了最后的句号。这六卷本的《空山》以及相关的机村故事描述的是大山深处的一个藏族小村庄20世纪后50年在外来文化影响下的历史,通过这幅纷繁的历史画卷,阿来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突破了“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的局限,写出了文化的承载者、体现者——人的文学,并以对大自然的审美态度接续上传统文化的美学精神的气脉,从而将高远的全球意识与古典的美学精神完美地凝聚在一起。
一、超越文化局限
一般都把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分为三种形态: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文化,它们分别偏重于政治、伦理、经济,这种分法当然不无偏颇与绝对之处,因为马克思主义文化即主流的政治文化在多年的发展中已然成为中国文化的新传统,并且其中也有现代性的因子,但为了分析问题,本文暂取这种三分法。在机村20世纪后50年的编年史中,20世纪80年代之前,机村也被迫卷入历史变革潮流之中;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改革开放的影响下,机村也或多或少地受到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影响。当偏重于精神与宗教的藏族文化遭遇现代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冲击。正是在这个冲击的过程中,各种文化显示出各自的特点,也显示出各自的局限。这种局限是阿来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以全球意识观照出来的,因为阿来是“把我的故乡放在世界文化这个大格局,放在整个人类历史规律中进行的考量与思想”①阿来.自述[J].小说评论,2004,(5)。
描写50年代中期到“文革”之前这段历史的《空山》第一卷《随风飘散》中,有一段文字很好地表达出当时的政治气候与藏族传统文化的强烈冲突:
“这就是机村的现实,所有被贴上封建迷信的东西,都从形式上被消除了。寺庙,还有家庭的佛堂关闭了,上香,祈祷,经文的诵读,被严令禁止。宗教性的装饰被铲除。老歌填上欢乐的新词,人们不会歌唱,也就停止了歌唱。但在底下,在人们意识深处,起作用的还是那些蒙昧时代流传下来的东西。文明本是无往不胜的。但在机村这里,自以为是的文明洪水一样,从生活的表面滔滔流淌,底下的东西仍然在底下,规定着下层的水流。
生活就这样继续着,表面气势很大地喧哗,下面却沉默着自行其是。”②阿来.空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37页
这段类似于“文眼”的文字鲜明地表达出叙事人对于政治气候与藏族文化的不同态度,其褒贬与倾向在“自以为是的”“表面气势很大地”等感情色彩浓厚的文字中不言而喻。然而,这只是政治文化与藏族文化相遇的开始,慢慢地,“文明”便侵入到“蒙昧”深处。
晚清至“五四”以降,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开始接受西方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只不过面对国家的内忧外患,现代性的观念是以民族国家、民主自由等宏大话语为目标追求的。这种追求在1949年后到“文革”结束也即《空山》前四卷中所描写的历史中,表现出政治文化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的特征。在这种现代性追求下,汉族文化以与传统的决裂形成了自己新的传统。在这种新的传统的影响下,汉族文化更是将宗教信仰指认为封建迷信,是落后的、野蛮的、要从日常生活里清除掉的东西。藏族文化原本是以信仰为主的宗教文化,工作组到来后摧毁寺庙,强令喇嘛还俗,将宗教信仰视之为“封建迷信”,从而揭开了机村世俗化的第一步。世俗化最初的含义便是非宗教化。这也是机村人、藏族文化接受汉族世俗文化以及所谓西方现代性价值观念的第一步。因为发源于西方、从文艺复兴萌发直到启蒙运动建立起来的现代性本身便包含否定宗教、肯定现世、肯定人的自我以及人自身的欲望等世俗化因子,所以即使在政治文化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当伐木场收购猴子等动物时,机村人便不顾禁忌而残暴地猎杀动物。改革开放之后,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理念大规模地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第四卷《荒芜》结尾处,便写到这种以发展为核心的现代性文化在机村人身上的表现:所有人都忙着挣钱,挣大钱,而庄稼却荒芜了。机村人在物质欲望的激励下本能地接受了现代性文化,加入到全球现代化的“合唱”中来。
然而,藏族文化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正如文本中所说,“自以为是的文明”只是“从生活的表面滔滔流淌,底下的东西仍然在底下,规定着下层的水流”,民族的传统、民族的特色不是那么容易消弭的。机村人丰收时仍然会载歌载舞,食物充足时仍然会请各家各户共同品尝。村里有了酒吧这现代文明的标志,却不是现代都市中欲望的滋生地,而是大家“话说当年”的公共空间,不过是取代了以前的广场。村民仍然坚持火葬或天葬,而不愿埋在黑暗的地下,仍然相信神灵而不相信鬼魂,传统的礼节、仪式等不仅没有封存在集体记忆里,当接续上民族文化的根源时,这些集体记忆便转化为现实,把传统在自然的状态下发挥到一个极致。民族的传统不仅仅如生活的潜流,它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奔涌。
藏族文化在受到外来文化影响之前是一种封闭的农业文明,有很多不足之处,如机村的人们只知道听天由命,缺乏改变生活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但强势的汉文化也有其难以撼动的痼疾。第五卷《轻雷》中有一段很耐人寻味的情节:木材检查站站长罗尔依被机村家更秋兄弟撞成了失忆症,不记得受贿,也不记得自己对超载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过去,每天头缠绷带、手拄拐杖,衣冠楚楚地站在站口严格秉公执法,超载的木头全部扣押,而且对司机认真地进行政策教育。不但文本中的司机及同事都觉得他不可理喻,觉得他犯了神经病,连文本之外的我们也忍俊不禁,然而笑过之后,却不禁闻到一股熟悉的气息——那股柏杨所说的酱缸文化的气息。在这里,阿来很幽默地调侃了汉文化一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一段时间里已经成为一种不言而明的现实。这种在藏文化的对照之下显现出的不合理,其实是讲究人情世故的汉族世俗文化与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西方文化交锋之后形成的锋面。这样的一种锋面形成了一种奇特现象,那就是人人都知道某些规章不甚合理,但却没有人不去遵守,人们得过且过,犬儒主义盛行。
而在中国文化的映照之下,西方现代性文化也显示出其局限性。现代性的出现与发展如同机村的新鲜事物——脱粒机一样,呈现其两面性的特征。脱粒机既能以其效率提高人们的生产能力,也会破坏人们的传统生活:集体挥着连枷边打麦边歌唱。这种破坏以颇有寓意的细节写出:当村人在轰鸣的机器声中唱着舒缓的老歌把麦捆输入到脱粒机时,他的一只手臂被脱粒机绞了下来。虽然现代性文化有无可比拟的进步性,其形成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其发展也有符合人的本性之处,但片面地通过刺激人的欲望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无视形而上的终极追求,与工具理性的盛行一道,造成了生存环境恶化以及人成为追求欲望满足“单面人”等,其负面性更是难以忽视。
二、立足“人”的文学
阿来正是看到了各种文化都具有自身的局限性,所以他不把自己限制在民族文化的视角,而是超越了文化的局限,站在人类的立场上来书写自己的民族。阿来很反感“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这种说法,因为这种理论有着明显的民族主义局限,因为无论何时何地中国文化的出发点永远是“民族”,或者说中国文化的归宿永远是“民族”而不会是“世界”。他认为自己所书写的藏族人的爱恨生死其实是全世界各民族共有的观念,因而,他在写藏族的历史与现实的时候其实写的是“地球上生活的主体——人类”。这种文学观念与五四新文学中高举“人的文学”的理论旗手周作人的文学观念庶几相似。周作人曾在1920年的一次演讲中说:“人生的文学是怎样的呢?据我的意见,可以分作两项说明:一,这文学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也不是神性的。二,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①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周作人自编文集·艺术与生活[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9页即“人”的文学应是人性的、人类的、个人的,阿来的《空山》便是这样的“人”的文学。
《空山》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机村人丰富复杂的人性。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机村人的人性、人情、人心在走向上呈现出类似于一个上抛物线的形状。第一卷《随风飘散》中外来的身份不明的桑丹母子如两面镜子映照出机村人性的冷漠,也映照出他们那昙花般闪现的人性的光亮与温暖;第二卷《天火》中外来的救火队丰盛的物质激起了机村人贪婪的欲望,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肆偷窃;第三卷《达瑟与达戈》中伐木场后勤科长的物质引诱,使机村人把枪口对准了与自己和平共处了上千年、有“亲戚关系”的猴群,打破了禁忌后人心变得狂暴,而这一切在第四部《荒芜》中驼背书记的时代水到渠成地走向对物质现实的全面认同。虽然认同物质欲望本身并无大错,马克思尚且预言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但超过一定的限度,如偷窃、滥猎滥杀等,则是人性的堕落、人性的恶。在极端的政治文化影响下,机村的人性发展史也是机村人性逐步堕落、逐渐走低的历史:从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崇信万物有灵渐渐变成贪婪残暴、无所顾忌地将自然界变为牟利的对象,从敬畏神灵、善良怜悯变得自私冷漠、唯利是图,物质欲望的不断膨胀导致的是人性的逐渐堕落。人与人、人与自然界、人与土地的和谐关系都遭到了破坏,人的精神家园与物质家园都面临丧失的危险,这时候人性的走向也到达抛物线的最低点。这一段历史的描写在广义的层面上可以看作是“伤痕文学”,它不仅伤害了人际伦理,如《随风飘散》中桑丹母子所遭受的漠视与冷漠,如《喇叭——〈空山〉事物笔记之六》中广播站长次仁措举报村民“百事通”“收听敌台”,也伤害了藏民善良仁慈的天性。
然而,物极必反,当“文革”结束、改革开始之后,也就是在机村后二十年的历史中,人性开始复苏。第四卷《轻雷》虽然仍然书写村民在金钱欲望的支配下的滥伐,却洋溢着人性的闪光。拉加泽里以其自尊和倔强赢得了双江口镇几位重要人物的喜爱。给他提供木材指标的李老板差点认他当儿子,警察老王说他应当称呼自己“伯伯”,木材检查站的刘站长让他称呼自己“刘叔叔”,本佳称他为“朋友”,虽然这一系列的称呼带有汉文化的鲜明特点,木材生意本身也有诸多不合理、不合法之处,但却让人感到人性的温暖。人际伦理得到修复后,在第六卷《空山》中,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也开始修复。因误伤人而坐牢十二年的拉加泽里回到机村,开始用李老板留给他的钱绿化被伐木场的工人以及机村的村民所破坏的群山。与自然界的日渐和谐,使机村村民接通了与传统的联系,当三千年前的古老村庄出土时,同族同宗的认同感使机村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和谐,“复活了!一个村子就是一个大家的感觉”。人性的抛物线也在机村人手拉手在月亮之下的歌舞中回复到其起点,甚至超过了起点。
以上是简单勾勒出的机村人性的发展曲线。人性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多是因为社会的动荡及外来文化的影响。一般来说,当社会及文化稳定发展时,人性也会正常发展,即便偶有正常波动,也不会有巨大的起伏。另外,即使机村人际伦理达到和谐的最高点,人性也不可能抵达至善,人与人仍然有矛盾,人的各种欲望仍然会伤害人的天性,人仍然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与不足,如鲁迅所深恶痛绝的国民性中的看客心理。在《轻雷》中拉加泽里跟检查站站长罗尔依产生冲突时,“全镇的人有一多半都围了上来”,当没有事情发生时,围观的人们便“像失去了垃圾的苍蝇,轰然一声,四散开去” 。虽然阿来在字里行间也流露出对于这种看客心理的不满,但他并没有如鲁迅一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进而将批判国民性作为自己创作的主题,而是轻轻一笔带过,将其作为人性未达至善的佐证。
然而,正是人性的复杂多变、人的各种未达至善的局限性才真正写出了人作为类的真实性与普遍性。阿来在《写作在别处》一文中提到《蒙田全集》中的一段文字:“我们一般的行动,都是根据我们的心意,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听任一时的风把我们吹向哪儿就是哪儿。”“我们在不同的主意之间游移不定。我们对什么都不愿意自由地、绝对地、有恒心地作出决定。”①阿来. 写作在别处[J]. 青年文学,2001,(6)虽然是写现实生活中人情的无奈时引用的,但把这段文字与《轻雷》中的一段文字相比照,就可以发现更多问题:“好多东西,人家没有自己没有时,谁都不会觉得有什么缺憾。但人家有了,大多数人都有了,你没有,就要日思夜想,不得安宁了。”启蒙时期的法国人在环境中的摇摆不定与20世纪的藏族人的从众心理之间没有质的区别,而机村人对于政治文化的本能抗拒以及对于发展经济的欣然接受,因为现代性对于欲望的肯定更符合人的本性,而这更是人之为人的普遍性。
阿来说:“一个藏族人注定就要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流浪”的含义是居无定所,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这个用词表露出的都是对两种文化的无法认同、不认同或不完全认同。这反而使他在创作时能够超越汉藏两族文化的局限,进而获得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即全球意识,这种意识使他能够放眼世界文化,立足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进行藏地书写。正是眼光的高远,使他在大家都谈论文学、作家的边缘化时仍然对文学抱有宗教般的坚定信念:“我就认为我在中心,认为这个世界就是围绕我的文学在旋转”,认为“这个世界为我而存在”②徐春萍.作家阿来访谈录:重要的是信念不可缺[N].文学报,2007-02-08。而他在藏区生活了三十年的经历,使他“跟这块土地上的人、跟这块土地本身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能够互相感应的这样一个关系”③徐春萍.作家阿来访谈录:重要的是信念不可缺[N].文学报,2007-02-08。这样天人合一般的深厚且灵动的经验积淀,再加上超越性的全球意识以及万物皆备于我的大气,使得阿来的创作具备浓厚的个人风格,也使得《空山》这朵奇葩成为一部“人性的、人类的、个人的”创作。
三、接续古典气脉
当读到白茫茫的大雪覆盖了即将消失的机村时,我不由想到了《红楼梦》结局处那笼罩在天地间的一片白色,一切的荣华富贵、悲欢离合都成为过去,一种文化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一个时代无可挽回走向结束。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限的人生、人事在无限的宇宙时空的对照下形成那种充塞宇宙的悲凉与感伤成为古典文学的高峰,也成为后世文学无法企及与超越的高峰。贾平凹的《秦腔》同样写一个村庄的衰落、一个时代的结束及传统文化的式微,也不脱苍凉的调子,可以说深得《红楼梦》之神髓,却局限于传统儒家价值观念的认同而无法超越。阿来的《空山》在刻画村庄历史的变迁让人产生人世无常的感喟的同时,却没有那份悲凉与感伤。原因何在?一是因为阿来的文学观念是积极的:“小说应该提供一个价值观,而且是积极的价值观。”①易文翔,阿来. 写作:忠实于内心的表达——阿来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4,(5)二是如上文所述,阿来是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来写自己民族的历史的,这种全球意识使他既能超越各种文化的局限,又能汇入传统之流,延续传统文化的气脉。
《空山》结尾处写到了机村人生命意识萌发、族群主体意识觉醒以及寻找到民族文化的传统,洋溢着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与乐观,然而文本之外的阿来并不单纯地乐观,虽然全球意识使他避免为民族文化的受到冲击而吟唱悲歌,但他从小接受的汉文化教育使他看到了所有这一切的有限性:“雪落无声。掩去了山林、村庄,只在模糊视线尽头留下几脉山峰隐约的影子,仿佛天地之间,从来如此,就是如此寂静的一座空山。”无论是机村人的传统还是未来,在自然界的永恒面前都是那么的短促、有限。这与唐诗之冠《春江花月夜》中“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何其相似?!正是在个体生命的有限与宇宙时空的关系问题上,阿来接通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精神的气脉,从而使得整个文本气韵生动,境界阔大。
个体生命与宇宙时空之间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文化方向的基本问题”,而天人互相协调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理想,亦即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基本道路”②张岱年. 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心灵与境界[M].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24页。这种哲学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就是人们在对待宇宙空间时有一种从容的态度,“因为中国人由农业进于文化,对于大自然是‘不隔’的,是父子亲和的关系,没有奴役自然的态度”③宗白华.艺术与中国社会,艺境[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79页,因而向往无穷的自然宇宙,但并不希图控制,能从有限中见到无限,又于无限中回归有限,在悠然自得中形成一种美学的态度、美学的精神。这种美学态度体现在李白的诗中是“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体现在辛弃疾的词中是“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体现在阿来的创作中便是他笔下的自然景物都笼罩着一层氤氲其上的生命气场。在机村,我们闻到空气中弥漫着各种醉人的味道:沃土苏醒时的土香、杜鹃怒放时的浓香;我们看到丝丝缕缕的飞絮在庄稼地上空飘荡,麦苗闪烁着青翠光芒;我们听到轰轰作响的林涛,清脆悠远的鸟鸣……这样一个声色俱全、静中有动的世界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世界,是美的世界、美的源泉:“大自然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活力,推动无生界以入于有机界,从有机界以至于最高的生命、理性、情绪、感觉。这个活力是一切生命之源,也是一切‘美’的源泉。”①宗白华.看了罗丹雕刻以后,艺境[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1—22页这样的世界是极端的政治文化不能抹杀的,是机村人的物质欲望不能消灭的。自然界的这种生生不息之气是哲学化了的生命,它与文本之外的作者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能够互相感应的”这样一个关系。正是这种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暗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和美学精神。另外,虽然民族文化不同,但汉族和藏族都是“由农业进于文化”,滋养阿来的藏族民间文化所崇信的万物有灵和汉族文化对自然的亲和在某种意义上是相通的,所以用汉语书写的藏族作家阿来在有意无意之间便接续上古典美学精神的气脉。
正是这种对待大自然的态度使阿来的创作区别于西方现代性文化、远离政治文化,而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达到精神上的一致。看到各种文化的局限但不虚无地全盘否定而是有所取舍与认同,因而超越性的全球意识与古典美学的认同在他的文本中并行不悖,和谐一致。这种和谐使得阿来的创作能够融入中国文学的传统之流,并以其全球意识为文学传统添加了新的质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