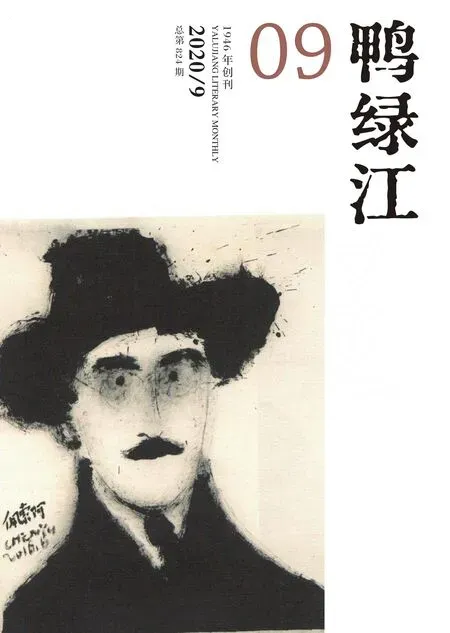摄影师(外一篇)
2020-11-17女真
女 真
住对面的丹丹家搬走了,我不开心。丹丹比我小两岁,我们经常在楼下一起玩。一次我妈不在家,我让她来家里一起看电视,请她吃沙琪玛。我们玩得很开心。
新房客看上去跟我爸年纪差不多。他穿一件有许多兜的马夹,身上鼓鼓囊囊。
我妈说他:“这么大年纪,连老婆孩子都没有,还租房子住,不怎么靠谱。”
好奇害死猫。我本来对新房客不感兴趣,我妈这么一说,我开始注意他了。
他不像我爸我妈准时上下班。他每天背一个黑色大包出门,不知道包里面装了什么。有一天我出门时,他正停在下面的楼梯翻包找东西,瞄见他的黑包里有一片粉色,我吃惊得很。那是丹丹的布娃娃。丹丹搬走时,为什么要把布娃娃扔下?
一个像我爸那么老的男人,他包里装个娃娃做什么呢?他是有个像丹丹那样的女儿,拣了布娃娃要去送给女儿吗?我跟在他后面。他去东面那片小树林。布娃娃挂在树杈上,他围着那个树杈转,手里端着一个黑家伙。我走近了,听见一阵咔咔声。哦,原来他是在拍照。这个人真是怪,不去拍大街上的美女,拍挂在树上的布娃娃。还有一次他去南边一幢有木头窗棂的老房子,那房子要动迁了,白色的“拆”字写在墙上。这个人把布娃娃放在老房子的窗台上,咔咔一通拍。有人围观,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地议论。大概是拍累了,他把娃娃收进包里,往回走。
我跟在他身后上楼,他站在他家门口等我:“你跟着我?”我点头,他又问:“你假期怎么不去补课?”我不告诉他为什么。我爸说小学生补课是浪费钱,男孩子从小应该到处跑、玩。但我还没想多跟他说话,我妈告诉过我,跟陌生人说话要小心。“你想看照片吗?”他蹲下来,让我看相机后面的那个小方框。他教我怎么前后翻看,然后把相机交给我,自己站到楼梯拐弯的窗口去吸烟。奇怪呀,树林、娃娃、房子,明明是绿的、粉的、黑的,但相机里的那些图像,却只有黑白两种颜色。我告诉他:“我有一只斑马,是黑白的。”他笑:“我能看看吗?”我开门回家,翻出小时候的玩具斑马给他看。他拿到手里,问我:“可不可以借给我用几天?”
后来的几天,我跟在他身后去看他拍斑马。他把斑马放在矿石车经过的铁轨、枕木上,放到小河中间的大石头块上。奇怪得很,他拍黑白的斑马时,图像倒是有颜色的了。比如那条小河,河水是红色的。我爸说,是上游的选矿厂污染了河水。我们这里的人已经习惯了看红色的河水,这个人把黑白的斑马和河水拍到一起,就像斑马在流血。
他拍照的间歇,我问他:“你怎么不工作?”
他看我一眼:“这就是我的工作。”
我怀疑他是在哄我。但他把我的玩具斑马拍进彩色照片,还默许我跟着他到处拍照,所以我原谅他了。他可能就是那种喜欢吹牛的人吧。
出事时,我已经开学了。我放学回家,这个人居然正坐在我家沙发上吸烟。他的头上包了纱布,一只胳膊也被白纱布挂起来。我爸陪着他吸烟,我妈把厨房整得叮当响。我想问他怎么了?为什么?他用眼睛瞪着我。他是想在我爸妈面前假装我们不认识吧?我闭了嘴,跟他默默地点下头,去厨房跟妈妈讨肉吃。
他们在客厅里讲话。他什么时候离开的,我不知道。我太困,睡着了。他什么时候从对面搬走的,我也不知道。我上学,不在家。
他没跟我话别。
我爸我妈,偶尔还会说到他。话里话外,他是因为拍照被人打的。好像他拿了什么人的钱,拍矿主和一个女人,被发现了。另一次他们说,他去选矿厂拍照,让人误以为他在偷拍,要去环保部门检举。后来他们又说,他是在街上拍乞讨时,被乞丐头子打伤的。那个小乞丐可能是被拐骗的,也许人家以为他是打拐的。
这个人从我家对面消失了。他拍过的斑马玩具,挂在我的床头。我在想,将来我长大了,当一个摄影师好不好呢?把彩色的世界拍成黑白的,把黑白的东西拍进彩色里,挺好玩的。但我爸说过,男人得养家糊口。靠拍照可以养老婆、养儿子吗?我不敢肯定。所以,有一次我妈问我长大了想做什么,我就没敢说自己想当摄影师。
我其实是不知道摄影师能做什么。
偷窃者
便利店在小区门口。偶尔有过路人进来买水、买烟,大部分光临者是本小区或者附近的业主,有的能叫出名字,叫不上来名字的也面熟。他一人看店,既是老板,也是售货员。媳妇曾说找个帮手吧,他说不必。小店本微利薄,多一个人工,不挣钱了。
如果进库房搬货,或者上厕所、站门口吸烟透气,店里就暂时没人看管。好在,有监控录像呢。很少丢东西。
下午三点多,欢迎光临的提示音有一阵子没响了。他有点困。眼皮正打架时,进来一个头发雪白的老奶奶,他看一眼来人,马上精神起来。
老奶奶穿着灰色羽绒棉袄,身上鼓鼓囊囊。腿脚大概不好,走路颤巍。他在收银台盯着监控画面。老奶奶在小食品那排柜子站了一会儿,可能是眼神不好,头向前探着,眼睛快贴到货物包装上了,反复看来看去,拿了一包苏打饼干塞进口袋。又去调料货架,这次应该是拿了一袋咸菜,还有一包盐。又去了日用品那排货架,把一卷食品保鲜膜揣进怀里。老奶奶在店里磨磨蹭蹭待了大概有半个钟头,走到门口结算处时,并没把塞进怀里和羽绒服口袋的东西拿出来,目中无他,径直向门外走去。
他没阻拦,眼看着她离开。走到她刚才去过的几个货架,把她拿走的东西记在本子上。货是刚理过的,哪种东西少了,他能看出来。
他在等待另一个人来。等待的过程,滋味复杂,但有一点快乐在里面。
晚上八点钟,那个人才来。挑没有顾客的时候进来,是想避人耳目吧。这种事情,毕竟谈不上光彩。
他毕恭毕敬,微鞠躬:“您好。”
来人跟他微微点头,问他:“老太太今天来了?”
“来了。”
他把单子递过去。
“多少钱?”
“算了,不要钱。”
“那哪行。你们是做生意的。”
他拿出计算器,迅速算了下,说:“十九块八。”
来人没掏钱,扫墙上的二维码。当收款成功的提示音响起,来人看了他一眼,说:“走了,谢谢!”
“慢走,管教。”
话一出口,他自己愣住了。多少年没说过这个忌讳的称呼了。这称呼让他想起不堪回首的少年时代。爹病故,妈在街道工厂上班,收入少。假期他带着弟弟捡拾废品卖钱,有一次没把持住,贪心发作,跳进一家围墙有豁口的工厂,往外搬废铁时被抓住。他和弟弟被送去劳动教养。
这个人,就是当年的管教。那时候他还年轻,穿制服,态度严厉,小伙伴都怕他。
昨天晚上,他一下子认出他来。尽管三十多年过去,但管教炯炯有神富有穿透力的目光一点没变。那目光曾经让他胆寒,头几年梦里还见过。夜里醒来,浑身冷汗。管教应该没认出自己。那时他是少年,成年后模样肯定变化很大。如果不看老照片,他甚至想象不出那时候自己长什么样子。管教老了,背稍微有点驼,但基本面相没变化,目光仍旧犀利。双目相接,他身上激灵一下。忍着没让自己张嘴,镇定地听从前的管教讲话:“兄弟,麻烦你点事情。我是这小区新来的住户,家里老母亲老年痴呆,经常办糊涂事。白天我们家里没有人,又不能总拦着不让她出门。万一她到店里来,买东西不给钱直接走,麻烦你不要拦她,拿什么你记下来,我会每天晚上过来结账。麻烦你千万不要喊,如果被看成小偷,老太太面子上受不了,我怕她受刺激。”
管教叫他兄弟。说话的口气里,有一种谦卑让他心动了一下。管教拿出一张照片让他看。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奶奶。
他记得自己郑重地点了头。
现在,他叫他管教了,他能认出自己吗?管教凝视着他,目光凌厉:“你是哪个所的?”
“新生。”
“噢。我在那儿干过五年。你现在挺好?”
“还行。小店,勉强维持。”
“谢谢关照。给你添麻烦了。”
管教忽然不再说话,转身迅速离开。欢迎再来的提示音消失了好一会儿,他还没回过神来。管教走了,他发现自己竟盼着老奶奶再来。他愿意再次看见管教复杂的表情。
但从此以后,他再没见过管教进店,因为老奶奶不再来。
他后悔。把那个称呼藏在心里就好了。
真想把这段奇遇告诉媳妇。话到嘴边,总是又忍下。媳妇只知道他学习不好,没念过高中,不知道他曾经是个偷窃者。那段往事,还是忘了好。老奶奶和管教不来,也是好事。万一哪天媳妇也在店里,遇上老奶奶拿东西不交钱或者遇见管教,他说不清楚。媳妇是个好女人,他得守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