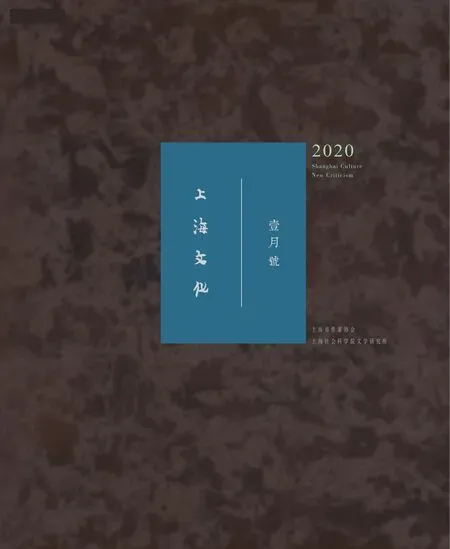仙乡最好诗人住:纪弦与苏州的文学因缘
2020-11-17朱钦运
朱钦运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纪弦作为路易士定居于苏州的时期,对于诗人的整个文学道路和生涯而言,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以及相当关键的意义
位于五卅路上的同益里与相邻的同德里,共同构成了苏州古城内较为少见同时至今保存完好的民国建筑群。这里由一幢幢独栋小楼构成,是上世纪30年代的国民政府财政次长贾士毅和上海滩大佬杜月笙分别出资兴建的。①对于新诗研究者来说,此处更有一段久远的文学往事有待钩沉:1930年代声誉鹊起的“现代派”诗人路易士于1936年7月到1937年8月期间即租住于此。
路易士是纪弦在1933年至1945年间使用的笔名,从他的本名“路逾”而来。纪弦生于1913年,逝于2013年,享年一百零一岁,其一生几与百年中国新诗同步等长,后来更“虬髯客海外称王”般,几十年间,在宝岛台湾延续并重振了源自大陆的现代诗脉。对于创造这个“中国新诗难以想象的事实”②的大诗人而言,仅仅十二年的“路易士”时期,只是他诗国生涯里的一小段前奏般的岁月,住在同益里的一年多时光则更近乎不足道了。
事实上并非如此。通过对他与苏州城之间这段往事的钩沉追溯,本文要揭橥的正是,纪弦作为路易士定居于苏州的时期,对于诗人的整个文学道路和生涯而言,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以及相当关键的意义。标题截取清中后期著名词人周之琦的某阕《摸鱼儿》词中“算福地、仙乡最好诗人住”一句,来形容路易士短暂定居苏州的生涯,更是对他这段时期以苏州为中心、辐射上海与整个苏南地区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活动,有一个暗含的价值判断。
路易士十五岁开始写诗,五年后于扬州编定《易士诗集》并于翌年春自费印刷出版(中和印刷公司,1934)。与此同时,他给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投稿,在1934年5月号有了第一次刊载,从此正式走上诗坛。从此年到1948年11月赴台,十多年间,他的创作和文学活动都相当活跃,给诸多的同辈、同行留下了深刻印象。吴奔星在写于1991年的文章《纪弦的天真与直率》里,如此回忆他与路易士半世纪有余前的交往:
纪弦原籍陕西,出生河北,家住北京,青年时期多在扬州、苏州、上海。他填籍贯往往是扬州,有时也说是上海,我却一直认为他是苏州人。因为1930年代他同我交往时,全家住在苏州。他那时写诗、办诗刊,也在苏州。③
这一小段话,基本概括了路易士定居苏州前的生活轨迹,也涉及到了他在苏州的情况:全家定居于此,在此写诗、办刊。而实际的情况是,整个1930年代里,真正“全家住在苏州”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之所以给吴奔星留下整个1930年代都在苏州的印象,很可能是因为,定居此地的数年前,路易士其实早已和苏州结下了很深的因缘,在此地已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住所——
他在尚未真正于诗坛“出道”的1930年至1933年间,就读于沧浪亭畔的苏州美专,当时著名的油画家和美术教育家颜文樑即是他的校长与老师。正是在就学苏州期间,路易士“文学艺术两开花”,既学美术、办画展,又沉浸于写诗。毕业三年后,他们一家搬到五卅路同益里,弟弟路迈甚至也进了同一所学校学画。文化老人尢玉淇在《姑苏孕育一诗人》一文中,将苏州时期视为路易士创作生涯的开端,并说诗人曾给他来过信,表达了对“使他孕育诗情”的苏州与“水木清华的沧浪亭”的怀念:
住在五卅路之同益里……在1930年到1933年之间,他在沧浪亭畔的苏州美专读书学画……当我进苏州美专的时候,他已经离校了,但他的弟弟路迈还在学校里……这两兄弟都长得很瘦长,恕我不敬,常常使我联想起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先生。……他俩都能诗、能文、能画,路迈还弹得一手好钢琴。④
尢玉淇与路迈同学,认识路易士时,已是1936年路家全家定居同益里之时了。而此前数年,路易士往返于扬州、南京、短暂留学的东京,以及上海和苏州等地,他的创作和文学活动如办刊、出诗集等行为,也都依托于这些地方来展开,其中苏州与上海自然是他的事业的最重要“基地”,《现代》杂志(虽然它维系到1934年就停刊了)及围绕它的作家如施蛰存、戴望舒、徐迟等,则是路易士于苏州美专就读期间到全家定居苏州后四五年间的重要圈子。
据纪弦回忆录所述,定居苏州的更详细的情形是,1936年7月,他从住在北平的三姨家接了短期旅居于彼的母亲和一妹一弟(路易士与创办《小雅》诗刊的诗友吴奔星、李章伯的初次见面,正在这次北平之行),全家正式迁居于苏州,具体地址则是同益里二号。⑤
他如此描述刚刚搬入此地的温馨岁月:
坐落在苏州五卅路同益里二号的江南新居,我很喜欢。这是一幢二层楼半洋式的房子,除了天井太小,其他方面都还令人满意,够我一家人住的了。……楼下客厅里,有一座钢琴,那是属于我二弟路迈的。
同益里和同德里的半洋式小楼的格局,至今依然,和《纪弦回忆录》里的这段描述一样。而新居里的那架属于路迈的钢琴,不止印证了尢玉淇数十年后对路氏兄弟的回忆的准确性,还引发过路易士具体的诗情:
他现在还在读苏州美专二年级。他的同班同学姚应才和全毓秀时常来玩。……姚应才最崇拜贝多芬,他的发式和服装,无一不极力模仿乐圣。他每一次来我家,我都要求他为我弹奏一曲《月光曲》。“升起于键盘上的月亮,/做了暗室里的灯。”我这两行名句,就是为他而写的……
有意思的诗,《月光曲》这首诗的“定稿”直到1999年才完成,文字没有变,但调整成了三行:“升起于键盘上的/月亮。做了暗室里的//灯。”可谓是一首写了六十年的诗,跨度之长堪称罕见。在定稿的《后记》里,纪弦将此诗初稿更详细的诞生缘由及修改的背景讲述了一遍,并为读者补充了这两句诗诞生场景的更丰富的细节——关灯听琴,琴声中想出两句诗,曲终开灯诵出,姚应才非常喜欢,但他们将之视为两句诗而不是一首诗,希望将它以“适当的位置”放在一首较长的诗中。1938年,路易士的这位姚同学与其少校兄长一同阵亡于保卫家乡的战场,而因此痛哭的路易士则决定从此不再听《月光曲》。六十多年后,诗人将当年的两行诗拆成了三行,并不是简单的调整,而有“形式即内容”的用意在,这种“重写”被作者自谓为一种“不完成的完成”,终以此特殊方式了却心愿。⑥
诗的《后记》另外还自陈了一些路易士当时的生活情况:“那时候(1936—1937)我家住苏州,而在上海教书,一方面又创办并主编一份诗刊,苏州上海两头跑,忙得不亦乐乎。”此处对应的这一年间的史实是——
创办并主编一份诗刊,指他与韩北屏、常白、沈洛等苏南诗人组建了“菜花社”,1936年9月开始印行计划每两月出版一期的《菜花诗刊》。除了四位同人外,创刊号的作者尚有吴奔星、李章伯、赵景深、李长之与鸥外鸥等人。同年11月,因嫌“菜花”名称小气,改名《诗志》,出刊至第三期停刊。故《菜花诗刊》只出了一期,即1936年9月号。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期《菜花诗刊》的封底,刊登了一则《路易士全集征求预约户》的“广告”,占据整页,除了一些必要的说明外,征订启事的第一条细则内容是:“直接寄信到苏州五卅路同益里二号本社,信上说明预约若干部数,及预约者之详细通信地址。”⑦所谓“本社”即“菜花社”,是以自己家为办刊地,此则信息或许可以视为1936年路易士迁居苏州后落户同益里的又一佐证,而且是一则强有力的佐证。
与办刊事务相关的另一件是,这一年间,路易士往来苏、沪两地,与徐迟各出五十大洋,支持戴望舒创办了《新诗》杂志,并介入编务。可以说,《新诗》杂志是1930年代中国诗坛最重要的专门性刊物。那么,往来苏沪两地、热衷办刊并支援友人办刊的路易士对当时的诗坛,可谓有一份莫大的功劳。
所谓“在上海教书”,则指路易士在1937年春应聘至上海安徽中学,担任美术教员。他于一年间往来苏、沪两地,编印诗刊,出版诗集,参与文学同人团体的运作,甚为活跃。到“八一三”沪战爆发,始挈家离开苏州避难,往内地迁徙,居停于武汉、桂林、长沙、贵阳、昆明等处,后经河内、海防至香港与戴望舒、杜衡等友人相会,辗转几年后,于1942年香港沦陷后回到上海沦陷区,靠亲友接济艰难度日,还在战争胜利后一度经商,直至1948年赴台。⑧⑨
这期间,在1937年9、10月,路易士一家离开苏州前往内地避难的旅途行进到了武汉,住在汉口。作家胡绍轩当时居于武昌,正筹备《文艺战线》旬刊,听闻纪弦的诗名和行踪,邀他会面,并约了一些作品。⑩路易士在离开苏州后创作的《八月十三日在苏州》,即刊发于《文艺战线》的第三期,这首篇幅不小的诗,基于对当时的回忆,聚焦于“淞沪会战”发生那天苏州城各色人等的反应,是颇为难得的、以诗的方式对“八一三”大战所带来的社会变动进行描绘的“史料”,可谓新诗史中一首别样的、新型的《兵车行》:⑪
(一)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的早晨,/我临窗而坐,/兴奋地/读着当天的报纸,/我看见了上海的毁灭/和中国的新生,/我看见了兽性的跳舞/和正义的翅膀的招展:/我激动着。/当我伏在窗台上,/良久地注视了/那条玩具似地摆设着/一幢幢漂亮的洋房的/整齐的街,和街上/络绎的行人与车辆,/不禁默念着:/“你这江南的名地,/天堂的苏州啊,/有这么一天,你也要/变成灰烬焦土的!”
(二)于是我拿了手杖,/到外面去散步。/我的邻人走过来,/亲热地和我道了早安;/然后他告诉我/马上他就要/离开这座危城了。/他预料日本的空军/早晚要来袭击,/炸弹,机关枪,无法躲避。/他在一个礼拜以前/就拿定了主义,/逃到重庆或成都去,/那里再安全也没有。/他们一共是五个人,/全家撤退:他的太太,/他的少爷,他的小姐,/他自己,和一个娘姨。/他们带了整整/八十件全行李,/衣服和软细,/样样都是必须。/他慰然地叹了一口气:/“这种乱世啊!……”/他还好意地警告着我:/“这里实在是太危险了!”/我点点头,笑笑,什么也没说:/我在想着,他的那幢/化了七千元建筑起来的/西班牙式的小别墅,/是无法携之以俱去了。
(三)公园里寂寞得/有如冬季般,/往日的那些游客们/不知道哪儿去了。/但是大街上却表现得,/异常的骚动和紧张:/搬家,逃难。/一部人力车飞也似地/从我身边掠过,/车上的绅士向我挥着手,/匆匆地说着再见,/我认出了/他便是我的那位/挺阔气的邻人/看他那不安的神色,/似乎连一秒钟/也不敢在这里停留。/难道火山爆发了吗?/洪水淹来了吗?/这些懦弱,可耻的,/自私的东西啊!
(四)晚上,我在门口买号外。/卖号外的是个穷孩子。/“我们打了胜仗啦,/你高兴?”我问他。/他的眼睛里闪耀着/一种喜悦的光耀。/“如果他们打到苏州来,/你逃不逃呢?”/“我不逃,先生,/就是逃也逃不了的!”/多么使我感动的/坚决的口气啊!/接过我手中的铜钱,/他又喊着“号外,号外, /第三次的号外,”/向着前边跑去了。
(五)回到我的楼上来时,/正敲十一点。/而我是兴奋地难以入睡了:/一个思想严重地占据着我。/我于是来回地踱着,/唱着歌,流着眼泪。/我懂得了战争,/懂得了它的全部意义,/并且懂得了其它。/远远的一声汽笛/随着夜风传来——/啊,这时候,我知道/正有满载的兵车/一列一列地离开了车站,/向着前线的东方。/庄严地驶去。
从第一首中对江南名地、天堂苏州的“默念”,到最后一首里的“我懂得了战争,/懂得了它的全部意义”,路易士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完成了他对苏州的怀念。通过阅读这首诗,以及另一首题目为“家在江南”的诗,还有另外两篇散文,胡绍轩则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位情感奔放的诗人是多么怀念已被日本鬼子占领和蹂躏的家乡啊!”
可见,由旁人来看,在路易士当时的诗文里,他早已习惯将苏州当作自己难以割舍的家乡——哪怕后来再没有什么机会重游了。而如今的同益里二号,居住着好几户人家,据打听,此处还是整个弄堂里现在唯一的私有产权房(其他建筑都算老公房),不便入内探访。住在这里的这户人家,乃至整个同益里和同德里的居民,或许都不会知道,远在八十多年前,这里居住过一位(对于日后的新诗史而言)如此重要、发生过长达几十年的持续影响力的诗人。另外,不止诗人的肉身曾留驻于此,这种留驻还以其独特的方式,于兹出发,参与建设、塑造了中国新诗某个时间段的生态与品质。
中国新诗随“新文化运动”而兴起,百年以来,以别具一格的方式,和其他文类与艺术样式一起,共同塑造了现代汉语的文化品格。它的面目和所处文学场域的形成,少不了城市因素的参与。新诗与城市的关联研究——具体到某城对新诗某方面的贡献研究,多集中于北平、上海、昆明、香港、重庆、台北、纽约等城市——这些地方,或聚拢了数量众多的诗人,或形成了形态各异的文学团体,或集中了较多的出版与学术机构,或凝结出了独特的区域生态文化,或在特殊的时间段内承担了文学场域之展开的重要功能(譬如战时昆明的“西南联大诗群”,五六十年代的纽约“白马社”等等)。
而对于苏州古城而言,此地远不缺古典时代的诗人的遗迹,甚至更以建筑中的诗(园林)知名全球——作为人文渊薮的苏州,其区域文化传统(主要是吴文化,当然它还是普遍意义上“江南文化”的代表)既是辉煌的遗产,对于年轻的中国新诗而言,又是一种浓郁的背景和压力;既构成新诗作者的精神背景和文化资源,又在诗人们对这个传统的反叛或继承中,呈现出新诗与古典文化之间的张力。它在中国新诗与现代城市的互动中大概少了些“戏份”,尤其是新诗史的前三十年——
除却间接孕育了陆志韦(少年时代就学于苏州东吴大学)、叶圣陶及郭绍虞(这两位苏州人是新诗早期的作者,但并不以诗人名世)还有袁水拍(籍贯苏州吴县、今吴中区)等几位诗人,新诗史上的第一个社团“中国新诗社”(以该社名义创办的刊物,虽然在上海发行,但刊物内标明的收稿处是苏州甪直,后改为苏州太平巷五十号叶圣陶宅),以及东吴大学学生组建的包含新诗创作的新文学类社团(但影响毕竟有限)外,纪弦“路易士时代”的诗之事业初成的那些岁月,已算是苏州与新诗前半段历史的又一难得关联。
对于纪弦而言,既享年日永,又遭逢这样那样的时代变局,他之生活于不同的城市,自然是漫长人生中的普遍现象。与纪弦相关的城市,多数研究者关注到的,是其间最重要的三个:上海,台北和旧金山(譬如黄一的论文,见本文注释②)。他活跃于沦陷时期的上海,⑫台北三十年间更以“诗坛祭酒”身份自视和为人认同,晚年定居旧金山却依然拥有辐射华语诗坛的巨大影响力。除此三城外,至多再加上他度过了漫长青少年岁月的扬州,但扬州只是承担了纪弦诗人生涯的酝酿期和学徒期。对于为他在诗坛真正起步提供背景、机遇和场域的“根据地”苏州,反而缺乏足够多的关注。
成名于沦陷期上海的作家张爱玲,在1944年8月号《杂志》上发表了《诗与胡说》一文,其中的很多篇幅,谈论和激赏了收录于上海新诗社1937年出版的路易士诗集《火灾的城》中的四首诗。据吴心海的考证,这些诗均创作和发表于搬入苏州前夕,⑬虽然作者后来表示了对这批作品的不满意,但它们已分明显示了诗人的才华与独特性。而《火灾的城》的结集和出版流通,始于作者定居苏州同益里期间——那个最初真正致力于“诗之事业”的阶段。张爱玲说:
路易士的最好的句子全是一样的洁净,凄清,用色吝惜,有如墨竹。眼界小,然而没有时间性,地方性,所以是世界的,永久的。⑭
这样的评判颇有见地,对路易士这一阶段的诗的认识也堪称准确。张爱玲说他的诗没有时间性和地方性,大抵可以理解为,其诗不易为一时一地的格局所限,不受束缚于某种地方性文化。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强调苏州对作为“路易士”的纪弦的诗人生涯之意义,反而显得有些唐突。但任何“世界的”和“永久的”的形成,都依赖于此时此地的每个充满意味的瞬刻,求学苏州的三年和定居苏州的一年,以及遭逢时变的那个八月,这些零星的日日夜夜未必没有潜伏在诗人的灵魂深处,时常如灵感般光顾他的人生。
❶ 沧浪区志编纂委员会.苏州地方志·沧浪区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323。
❷ 黄一.上海-台北-海外:中国新诗现代化的一种路径——百年中国新诗史中的百岁诗人纪弦[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42-51。
❸ 吴奔星.待漏轩文存[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120。
❹ 尢玉淇.三生花草梦苏州[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58。
❺ 纪弦.纪弦回忆录(第一部):二分明月下[M].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1:99.下两段引文与此同一出处,不另注出。
❻ 路学恂,马铃薯兄弟(编选).纪弦诗选集[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306。
❼ 菜花社.路易士全集征求预约户[J].菜花诗刊.1936,1:封底。
❽ 以上三段所述三件事,主要据自纪弦.纪弦回忆录(第一部):二分明月下[M].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1:100-128。
❾ 胡绍轩.现代派诗人纪弦[A].胡绍轩.现代文坛风云录[C].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188-194。
❿ 胡绍轩(1911-2005),初以创作抗战戏剧闻名,1938年还与郭沫若、茅盾等人一道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抗战胜利后,经邵力子介绍,到《武汉日报》任职。据杨川庆.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失踪者”[N].黑龙江日报, 2015-07-08(第12版)。
⓫ 路易士.八月十三日在苏州[J].文艺战线(旬刊).1937,3:36-37。
⓬ 李相银.上海沦陷时期路易士(纪弦)行迹考[J].新文学史料.2014,3:98-104。
⓭ 吴心海.张爱玲激赏路易士诗作来源及初载刊物[A].吴心海.故纸求真[C].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29-39。
⓮ 张爱玲.诗与胡说[J].杂志.1944,5:3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