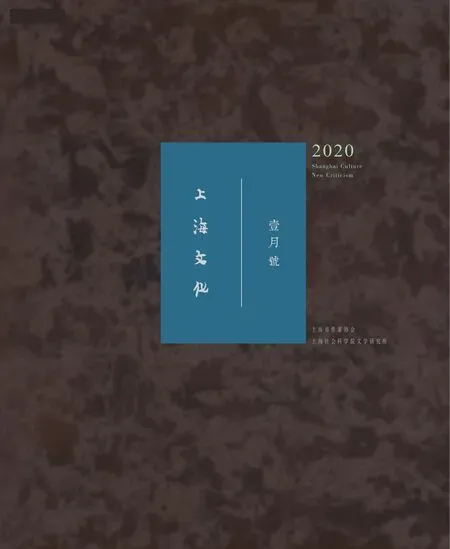“女武神行动”或对高贵精神的拯救
2020-11-17温玉伟
温玉伟
人们如今心绪低迷、愤懑、惶惑。如何给这个民族带来转折,成了每一位有担当的智识精英心中挥之不去的纽结
与国内学界熟悉的中世纪政治史家康托洛维茨(1895-1963)一样,施瓦本贵族家庭出身的施陶芬伯格(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三兄弟也都属于“格奥尔格圈子”的第三代成员,该圈子以具有超凡魅力的大诗人格奥尔格(1868-1933)为核心,团结了年轻一辈有民族使命感的文人和学者,曾在一段时期对于塑造德意志民族精神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格奥尔格和圈内成员眼里,施陶芬伯格三兄弟以克劳斯(Claus,1907-1944)和贝尔托德(Berthold,1905-1944)最有血性。 二人在1944年7月20日暗杀希特勒的行动中失败而先后身死。
三兄弟里年长的亚历山大(Alexander,1905-1964)早年学习法学,经历过第二帝国统治并在魏玛民国成长起来的他,目睹法学家在民主共和国的被动无奈,干脆换专业改修古典学。促使他做出这一决定的关键是,在他看来,古人作品中有一种久违的高贵精神,这种精神曾离德意志人很近,但是自从自由主义在德意志大地蔓延以来,人们反而变得很不“自由”。尤其是德意志民族的“那群人”(即智识精英)似乎被某种东西“禁锢”,曾经高贵的民族精神如今即便不是荡然无存,也可以说奄奄一息。人们如今心绪低迷、愤懑、惶惑。如何给这个民族带来转折,成了每一位有担当的智识精英心中挥之不去的纽结。
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自由民主、欣欣向荣的魏玛民国特别令人神往,“民国热”在我们这里一波接一波,但是在当时某些德意志精英看来,五彩斑斓的百花齐放只是表象,“世界静悄悄地破碎”才是其内核,自由主义盛行的民国迟早将整个民族拖向深渊。德意志民族内忧外患的历史时刻,“作为领袖的诗人”(Dichter als Führer)格奥尔格在其诗教中主张,民族命运的担纲者(Träger),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栋梁或精英群体,应该关注民族的Kairos[时刻],关注德意志民族历史上优异人物身上的高贵精神品质。深受自由主义、虚无主义困扰的年轻一代,在思想深处呼唤格奥尔格这样的精神领袖。
十八岁那年(1923),通过表兄的引荐,青年亚历山大第一次见到崇拜已久的大诗人格奥尔格,而且因富有诗才得到大师的赏识。自此之后,亚历山大对这位大师的忠诚和热情终生不渝。后来,他还与另外两位兄弟聆听了格奥尔格生前最后一次大型诗歌朗诵(《新帝国》),诗人咏唱的诗句——“我把远方或梦之奇迹,带着前往我国的边地”——一生回响在亚历山大的耳际。格奥尔格故去后,施陶芬伯格三兄弟是为数不多获准为其守灵的门徒。1944年,两位兄弟实施暗杀计划之时,亚历山大远在雅典,但他并未因此而摆脱嫌疑。事发后,他随即被召回国,紧接着便身陷囹圄,一年之后方才重获自由。战后,亚历山大在慕尼黑大学教授古代史,直至去世。
在世人眼里,亚历山大首先是古代史家。他于1932年发表的博士论文五百多页,专门疏解拜占庭帝国史家马拉拉斯(Johannes Malalas) 《编年史》(9至12卷),迄今被学界奉为圭臬。为了相关的古代史研究,翻译品达的《奥林匹亚凯歌》和《皮托凯歌》成为他晚年的一项主要工作,当然,他对品达的爱好与“格奥尔格圈子”对这位古代诗人的重视不无关系。作为史家,亚历山大终生未曾忘记大诗人格奥尔格的关切:诗歌-诗人与城邦-国家的关系问题。其实,人们很少知道,亚历山大私下更喜欢强调自己的诗人身份。因为他年轻时就喜爱作诗,史学研究之余写下了不少诗歌作品,比如身后发表的诗集《纪念碑》(Denkmal,Rudolf Fahrner编,Bondi,1964)。
诗歌《前夜》(Vorabend)就出自这部诗集。该诗以对话形式再现了克劳斯与贝尔托德在实施计划前夜的对话,大体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为二者的对话,后半部分为起誓。整个对话由贝尔托德的提问——“这样的行动离我们有多远?”——引起,经过对话和起誓之后,由他对行动的确认而结束——“属于你的是行动”。就该诗的对话体形式而言,显得像是在模仿格奥尔格最后一部诗集《新帝国》中的部分诗歌。值得一提,对于“格奥尔格圈子”而言,柏拉图及其对话体作品意义重大(据研究者统计,四十年间,圈子内共有七位作者写了二十六部与柏拉图相关的作品),对话在圈子内部被视为极其重要的教育形式。
颇为引人注意的是,人们眼中的史学家亚历山大没有拿出看家功夫通过历史书写,而是通过诗歌创作来为两位兄弟“树碑立传”。可想而知,他当时也许想到的是格奥尔格的教诲:比起史家的撰述,诗人的言辞可以更好地保留Tat[行动、事迹],使之免遭遗忘。而且格奥尔格本人和圈中许多成员都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
结构上来看,《前夜》一诗是整部诗集最长和最具戏剧性的一首,承接的是前两组组诗《战场上》和《起义》,在所属的《亡灵书》部分里面是唯一独立的。有研究者注意到,从题目《纪念碑》及其各部分安排——四部分分别为“亡灵书:战场上、起义、前夜”、“囹圄中”、“谣曲”、“梦中的新生”——来看,这部在今天差不多已被遗忘的诗集无疑是为未来的德意志人而作,甚至可以说是为少数能够看到和认识到民族时刻的精英所作。在诗集《第七个环》(Der siebente Ring,1907)中,诗人格奥尔格曾吟唱道,
我远远看到战争的纷乱,它不久便充斥我们的平原。我看到一小群人围住旌旗,其他人什么都未看见。
在1944年那样的时刻,以施陶芬伯格兄弟为首的精英看到了德意志民族的处境:在他们的回忆里,“民族先辈曾与古希腊和十字架(按:即基督教)神圣联姻”使日耳曼人成为西方的发祥地,先辈的高贵精神品质如“来自梦和希望之境的金色光芒”照耀着后人,但这个国家如今是怎样一幅景象呢?“吸血鬼吸榨着民族的血液,它丑陋的扈从前拥后戴。国家被击破的伤口因那毒液和口涎而溃烂”,而那“金色光芒”已成为过去时。
不过,他们看到了转折的时刻,“蝗灾已经落入逼近的暴风雨。它的气数已尽”。诗人在这里用了蝗灾(Der schwarm der schrecken)一词,十分形象地描绘了第二帝国崩溃之后,第三帝国、甚至魏玛民国中的民主状况。代表着“卑劣僭政”的僭主品性卑劣,在人民呼声中上台的他只不过是“吸榨民族血液”的“吸血鬼”,他的统治在怀念高贵精神的他们眼中只不过是被“诅咒唾弃的另一世界”,在“暴风雨”逼近的时刻,精英们所做的决断是,“宣判这个病态夺命无赖的死刑判决”,也就是说,诛杀僭主。我们从德国公法学家施米特二战后的《从囹圄中获救》了解到,这样的行动并不是孤例,他的友人阿尔曼便是其中的一分子(见《两座坟茔》)。
曾几何时,“那时还可抓住[历史]时刻的劝告”,但是当时的精英没能抓住这样的时刻,它的“期限已经截止”。这曾是怎样的时刻呢?第二帝国崩溃前夕,迷恋自由主义的智识精英自愿选择推翻君主立宪制,自行设计宪法并成立民国?抑或是,智识精英在自由主义盛行的民国丧失基本的政治判断,让纳粹钻了宪法的空子,从而断送了自己用心血建立起来的民国?无论如何,错失历史时刻的后果是,“如今,诸领袖的命运就是伏在陌生的轭下,放下常胜的弧形宝刀很多年”。如今在“暴风雨”逼近的时刻,精英们难道还要再次错失吗?
诗人将荣誉同“宝刀”联系起来,似乎只有在抽出宝刀诛杀僭主时,高贵精神在往日的荣光才能再次闪现,德意志先辈优异的精神品质才会得到拯救,这样,“曾经如闪电戡平幽灵般混乱的武器”才有可能“蓦地在我们手中熠熠生光”。在这样的时刻,“在此退却即是懦弱,即是延续到生命尽头最深的痛苦……”因为,倘若不采取行动,那种高贵精神只会像“常胜的弧形宝刀”那样被封存起来,作为领袖的精英的命运只能是“伏在陌生的轭下”,任由卑劣僭主的奴役和屠杀。施米特笔下的友人阿尔曼也将自己算作无所畏惧的一分子,即便他因战争而致盲,但仍参与到拯救高贵精神的行动中来,在施米特看来,这位“失明者更接近上帝”,因为他也属于能够看到关键时刻的少数人。
在这样的时刻,行动者无惧“造物的生存忧惧”,也不“懦弱”,只是心里担心的是“缺少这样的好运:在我们内心目睹未来奇迹般的映照,并唤醒在精神上被禁锢的那群人”。这是行动者针对“那群人”,也就是说少数人(所谓的智识精英)所说的,类似于格奥尔格《新帝国》诗里的“远方或梦之奇迹”,这里的“未来奇迹般的映照”也是对优异之人高贵精神品质的期待,倘若这些少数人在精神上仍然被禁锢在盲目的、不加区分的自由观念,那么,在这样的时刻,民族的转折就会“仍在踟蹰”。“那群人”的行动势在必行。
“那群人”不仅必须行动,而且必须“在当下行动”,这是他们作为“转折的先驱”(der wende wegbereiter)的使命,即便这样的行动“既是幸福又是厄运”,也就是说,对于德意志民族而言,它是Heil[幸福],而对于行动者、这些少数人而言,它是Fluch[厄运],他们“会死,会受折磨”。不过,为了使民族摆脱卑劣僭主的奴役,使高贵精神得到拯救,他们必须承负这样的重担,因为在当下的处境中,只有这些少数宣誓者才是“足够自由的”。当然,这里的“自由”与其说是身体和法律意义上的自由,毋宁说是精神和思想的自由。根据“格奥尔格圈子”所遵循的差序原则(就这一点而言,难怪有人说该圈子背后有尼采的影子),某些人所鼓吹的只不过是“平等谎言”(gleichheitslüge),因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都屈从于自然而然[即天生]的等级”(denn wir beugen uns vor den naturgegebnen rängen)。
在自由平等已经成为普世价值和政治正确的今天,“格奥尔格圈子”的这一主张显得颇为可疑,不过,他们强调的自然等级与纳粹化的种族主义或者物种论远不是一回事。用今天的话来说,“格奥尔格圈子”的成员信仰的是精神上的贵族,其特征是“有高尚思想、有纪律和肯牺牲”——相反,有些出身贵族的人反而由于天生的不自由而沦为了“卑劣僭政”“丑陋的扈从”和“凶残的附庸”。值得一提,诗中“高尚思想”的原文为grossen sinn,是对古希腊文megalopsychia或拉丁文magnanimitas[心高志大]的现代德译,这两个古代词汇也被译为Großgesinntheit或者Hochsinnigkeit,很大程度上类似于柏拉图《王制》中城邦护卫者的德性,这类人恰恰是城邦-国家的担纲者。
在克劳斯和贝尔托德的对话之后便是他们二人的宣誓,通过誓词,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呼吁的是格奥尔格式的“精神同盟”,而这个同盟的承载者则是有着高贵精神的智识精英。“万点星辰”象征了整个民族的成员,而徜徉在其中的“小精灵的身影”则是少数真正自由的精英。宣誓者之所以相信德意志民族的未来,是因为“我们在它的血液里看到力量,它会引领夜色里的民众走向更美好的生活”。可想而知,民族血液里的“力量”不是其他,正是追仿德意志祖先高贵精神的民族担纲者,作为“整个民族的杰出者”,他们的追求必须更为高贵。倘若属于尘世的“物质”代表的是现代民主比较庸俗的东西,那么,他们就得“上升到精神的王冠”,其目标是联合成为一个“精神同盟”。
他们的宣誓这样结尾:“我们联合成为一体的联盟,它以行动和姿态服务于新秩序和未来领袖,它为他们培育所需的斗士”。我们可以看到,行动者理想中的这个精神同盟,并不是一个无主的松散联盟,它有其未来的领袖,有新的秩序,还有为其奋斗的斗士。此外,也许更为重要,它是在对有着高贵追求的智识精英的呼吁,只有用行动才有可能在民族的历史时刻拯救受到岌岌可危的高贵精神。
从亚历山大树立的“纪念碑”上可以清楚读到的是,施陶芬堡兄弟的行动归根到底是为了“唤醒在精神上被禁锢的那群人”。然而,在普世价值充斥文学作品的今天,我们是否还能看清“纪念碑”上用血镌刻的铭文?2008年,美、德合拍的电影《行动目标希特勒》(Valkyrie;亦译为“刺杀希特勒”)上映,以1944年7月20日的“女武神行动”为素材,邀请人称“阿汤哥”的汤姆·克鲁斯主演克劳斯。在美国编剧的诠释下,克劳斯几乎变成美国价值的代言人。从电影一开始的特写中,那位被诗人歌咏的克劳斯竟然变成观众再熟悉不过的好莱坞“超人”,在他深邃的凝视和憧憬中,我们听到这样的内心独白,
作为军官,我的职责不再是拯救我的国家,而是要拯救整个人类……(中文字幕译文)
据说,自2009年在德国上映以来,这部电影在德国的电影市场叫好又叫座。不过,从电影在后来引起的争议中可以看到,毕竟还有少数眼力比较好的德国学者,他们向追慕好莱坞偶像的德意志年轻人奋力呼喊,“德意志的未来呦,这可不是我们德意志人的克劳斯……”
译完这首对话诗作之后,笔者不禁想到中华民族的一位英雄儿女郑苹如(1914-1940)烈士,她曾在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刻,为铲除汉奸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样的事迹可歌可泣。据某内部读物《情报典范人物》记载:
[郑苹如]为顺利执行情搜任务,镇日周旋于日寇高官之间,委身寇雠,曲意求欢,牺牲个人美色换取国家情资,不仅毫无名利,也因与日寇汉奸往来,致家庭遭乡里唾弃轻视,家族蒙羞,门楣无光,惟郑苹如无所悔恨,漠视蜚短流长,此等情操,绝非世俗人所能做到。
那么,我们的民族诗人是否会根据传说中的“旗袍行动”创作一部名为《行动目标丁默邨》或《刺杀丁默邨》的作品?如果有位诗人以郑苹如烈士为主人公创作这部作品——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她在作品中会说些什么和做些什么呢?更为重要的是,那位诗人会不会像亚历山大那样,有能力站在诗歌主人公的精神高度去把握主人公?根据《情报典范人物》的说法,郑苹如烈士的Tat[行动]“绝非世俗人所能做到”,因此,可想而知,去搞创作的诗人绝对不能是“世俗人”,否则,他(或者她)只会以“世俗人”的眼光去理解和呈现这样一位“绝非世俗人”的人,这样一来,英雄郑苹如与其说是被镌刻在“纪念碑”上,不如说是被钉在了耻辱柱。
笔者清楚记得,2007年,因为一部电影的上映,国内曾有学者振声疾呼“某某导演是一个不道德的导演”,但是,这样的呼喊在口沫横飞的谩骂声中显得那么苍白无力……转眼间,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过去,期间,这种“不道德的”似乎已经变为道德和政治的正确。试问,我们的“那群人”是否也在精神上“被禁锢”了?在共和国愈发自由开放的今天,我们能否看到自己身处的时刻?
在这首诗的翻译过程中,笔者请教了系里的几位年轻任课教师,反复斟酌词句之后,他们抓狂地问道:“为什么选择这么一首诗,这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不太好理解啊……”——不消说,对于我们而言理解起来应该也不易,不过,笔者希望通过浅显的译笔和这段说明文字来减轻其难度。
感谢比勒菲尔德(Bielefeld)大学语言文学系安德烈斯(Jan Andres)博士赠文,也感谢格拉纳(Lutz Graner)博士为翻译提供的帮助。
前 夜
施陶芬伯格(Alexander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
温玉伟 译
(贝尔托德 与 克劳斯)
贝
这样的行动离我们有多远?
克
你指的是?
贝
扼在我咽喉的恐惧并不是
造物的生存忧惧。令人折磨的
更为残酷。曾投照在你我头顶
来自梦和希望之境的
金色光芒,这是其一;
如今令你毁弃你的诅咒
唾弃的另一世界的,这是其二。
宣判这个病态夺命无赖的死刑
判决已经做出——不要认为
是颤栗凝住了寰宇的岩浆,
使每个国度的灵魂痛苦
继而被缚。这来自更深的层面。
真正的颤栗就在眼前。
克
颤栗就在眼前,我知道
最深切的渴望是把它驱逐:它
几乎不属我们的职分。我们只不过是:
仍在踟蹰的转折的先驱。
我们缺少这样的好运:在我们内心目睹
未来奇迹般的映照,
并唤醒在精神上被禁锢的那群人。
在当下行动——在当今状态
的环境中——间杂缠绕着
萌芽和凋谢、成长与消亡
勃勃生机疯长的杂草
筛分这样的杂芜对于我们
既是幸福又是厄运。因为属于我们的是行动,
它在纯真花朵的晨梦中
向我们低吟一首新歌——歌曲
如此甜蜜,令人心醉。
那么轻盈那么梦一般远离尘世——幻想者
踉跄的飞翔似乎是我们的命运
那就坚持直到世界
紧紧地颤抖地依偎我们的双手。
吸血鬼吸榨着民族的血液
它丑陋的扈从前拥后戴。
国家被击破的伤口
因那毒液和口涎而溃烂。曾经
如闪电戡平幽灵般混乱的武器
蓦地在我们手中熠熠生光。
在此退却即是懦弱即是
延续到生命尽头最深的痛苦……
是否存在一些烦扰你的,
因为我们对暗杀并无把握?
贝
也有这个,也有这个。
不过我清楚的是,
蝗灾已经落入逼近的暴风雨。
它的气数已尽。让戒鞭制服
迁就它的凶残附庸。荣誉
只在我们抽出的宝刀中发光。只有故国
可作出裁决……不过请告诉我,倘若你失手,将会如何?
克
我们会死
会受折磨……还会如何?
一块烙印,我们的气息烧灼
在凝结的夜之极度黑暗,
在烧尽的火山之烟灰。
在无数因卑劣僭政的疯狂
而随意被屠杀者中间
有十个有百个有千个
他们结为兄弟
为志向献身抛洒热血
为了一个梦——这是正当的梦——
它只向我们民族启示自由。
贝
即便生着,我们的道路
也充满痛楚。期限已经截止
那时还可抓住时刻的劝告。
如今,诸领袖的命运
就是伏在陌生的轭下
放下常胜的弧形宝刀很多年。
克
为了全体而将这样的负担揽在身上,
还有谁像我们这样自由?
贝
你说的在理,我们与此牢牢相联
今晚,夏夜在满月的银光中
熠熠生辉,月儿隆重地落在天际。
小精灵的身影在万点星辰
光泽中徜徉,在松柏间飘荡。
这难道不像从施法的影子里
走出的亲密战友,他们举手宣誓,
“我们相信民族的未来。”
克
“我们在它的血液里看到力量
它会引领夜色里的民众
走向更美好的生活。”
贝
“为了裁断民族活着的运命
我们在精神和行动上
坚定信念,
民族先辈曾与古希腊
和十字架神圣联姻
创造了我们世界的人类。”
克
“就让人人生于其中的民族
正义,成为国家的支柱,
国家确保人人的权利,不过我们蔑视
平等谎言,因为我们都屈从于
自然而然的等级。”
贝
“我们渴望的民族是
扎根祖国大地,靠近自然之力量,
在创造中能从赋予的环境
找到幸福和满足,驱走
无故傲慢、嫉妒、和妒忌的本能。”
克
“就让整个民族的杰出者从物质的地面
上升到精神的王冠,联合起来
以高尚思想、以纪律和牺牲
为神圣的强力树立榜样。”
贝
“我们联合成为一体的
联盟,它以行动和姿态
服务于新秩序和未来领袖
它为他们培育所需的斗士。”
克
那么他们无可指摘地为生而起誓。
贝
他们为服从和献身而起誓。
克
坚定不移地保持沉默
相互之间给予支持。
贝
属于你的是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