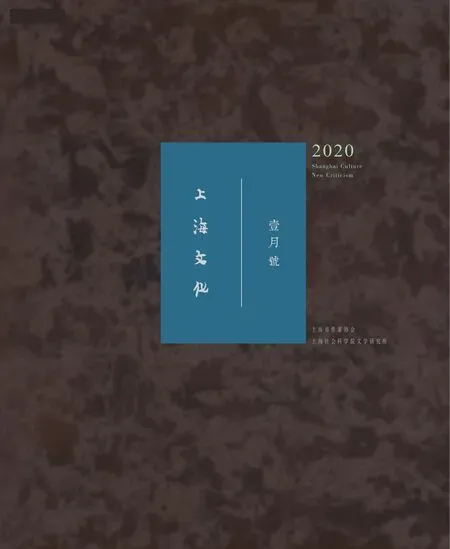瓦尔特·博萨德与罗伯特·卡帕:战争时代的视觉叙事①
2020-11-17皮特普伦夫德
皮特·普伦夫德
葛秀支 译
能够在中国展示沃尔特·博萨德(Walter Bosshard,以下简称博萨德)的作品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凡的经历。自大约二十年前我开始在他的档案中进行研究以来,我有两个愿望:第一,将他的照片带回中国(这些照片大约拍摄于一个世纪前,据我们所知,他在1930年代已经在北京展出!)。第二,与博萨德并肩作战的当时最著名的战争摄影师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以下简称卡帕)作品一起展出。
在我详细介绍展览主题之前,简要介绍一下博萨德。与卡帕相比,他还是一名鲜为人知的摄影师。这样一位拍摄了当时最著名的人物,如圣雄甘地、宋美龄、蒋介石或毛泽东的人,农夫的儿子,1892年出生于瑞士乡村,他怎么会成为一位杰出的亚洲专家呢?
博萨德在瑞士时候曾经作为学校老师接受过相关培训,在一战爆发前几年,就已经工作了。战争结束后,他开始重新寻找新的冒险经历,并前往亚洲旅行,一待就是二十多年。 他是一位伟大的旅行者,也是一位很典型的白手起家的人。他也尝试做一些其他的工作,例如在苏门答腊岛担任种植园经理,或在泰国做宝石商。最终,在1927-1928年,他参加了喜马拉雅山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探险,此次旅行为他成为一位摄影师奠定了职业基础。他被聘为技术经理和摄影师,记录这次探险活动。
1928年,他短暂返回欧洲,办了喜马拉雅摄影作品展并受到国际关注。他拍摄的偏远地区的照片非常成功,当时的领先杂志都渴望获得有关遥远的土地和异国文化的故事。
技术创新和打印技术的发展,改进了当时摄影的制作条件,有一些比较激进的杂志能够开发新的格式,通过摄影作品来描述他们的故事。这种摄影作品以一种更有吸引力的形式展现出来,它比文字更加具有吸引力,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的摄影报道文学是从一九三几年开始的。一些最成功的摄影记者成为新媒体世界的英雄。
在德语地区中,《柏林画报》③引导了这样的潮流。画报以周刊形式发行,在一战前的发行量约有一百万,到了1920年代末则超过了两百万。《柏林画报》杂志委托博萨德报道中国的政治、社会或与战争有关的话题。在1931年到1939年之间,博萨德成为远东地区最重要的西方通讯员之一。
然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全面爆发,博萨德打开了他职业生涯的另一个新篇章。 在1938年他去了瑞士一家非常著名的报纸,负责去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世界的影响,不仅仅在欧洲,还有一些比较远东的地区。1939年,他被任命为瑞士最重要的报纸《新苏黎世报》通讯员,去环游世界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以及在其他大洲偏远地区的影响。博萨德曾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住在椿树胡同三十二号,这是一座四合院,不但是他的住处,也是他的办公室,有洗照片的暗室,还有两名佣人帮他打理。
从那时起,写作对于博萨德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实际上,他的新雇主(《新苏黎世报》④)对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对他作为作家和政治观察员的兴趣比对摄影师的兴趣更大,因为报纸不相信照片是信息的相关传播媒介。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博萨德逐渐失去他作为摄影师和摄影记者的声誉。 1953年,由于在报道朝鲜战争期间发生意外,他的新闻事业突然结束。当时六十一岁的博萨德从板门店(位于朝鲜平壤)的屋顶跳下来时,摔坏了胯部,后来没有完全康复,因此被迫退出了新闻摄影师的职业生涯。 1975年他去世时,大多数人都知道他是写文章的新闻记者,只有少数朋友和同事仍然记得他1930年代做的开拓性工作。博萨德本人也没有野心要在著名摄影师的万神殿中占有一席之地。
现在回到展览本身,我介绍下展览的几个方面。第一:为什么我们要将博萨德和卡帕合在一起做展览?他俩曾是朋友,也曾经是竞争对手,似乎彼此钦佩。⑤更为重要的一点,从历史的视角上来说,我们可以学到一些战争和记忆历史之间的关系,和真相之间的关系,还有对历史的曲解。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其实跟关系是有关的。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论点。但也许更重要的是,通过并列他们的作品,我们可以了解摄影在战争时代的历史与记忆之间,在历史真相或扭曲之间的视觉叙事关系。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取决于视角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它是摄影师的视角,也是今天观察者从不同角度看待所谓的过去文献的视角。
从中国的角度看,世界历史与从欧洲或美国的角度看完全不同。这就是为什么用摄影师的眼光看历史是如此有趣的原因:历史照片总是挑战我们考虑摄影师的观点。相对于我们,摄影师受到的挑战更强。摄影使我们明白,历史记载永远不是客观的,真相也仅仅是视角的不同,可以有不止一个真理。
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取决于视角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它是摄影师的视角,也是今天观察者从不同角度看待所谓的过去文献的视角
我们看到今天的展览,其实不是第一次把我们的视角关注到博萨德身上。在之前的两个展览中,我有机会向中国观众介绍了博萨德。那些先前的项目使我想到他的照片对中国观众来说更为重要。因此,我回到了我们保存在瑞士摄影基金会的档案中,进行了更多研究。博萨德把他的这些底片放在这个箱子里面,我们也对它进行了一些研究。我们还研究如何把它们数字化,希望在更大的背景之下来了解这些。因为底片和最后的成片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必须对它进行一个诠释。
我想从博萨德遗产中保存下来的八千张1931年至1938年间的中国底片中,做一个适合播放的演讲稿,这只是冰山一角,档案总共包括大约两万五千张底片——这是保存下来的,但是更多的已经遗失了。我想用更好的视角展示他的成果,比如这个数据库是在我们自己基金会所持有的,还有在他之前发表过的照片,我发现其实现在市场上还是可以购买到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不仅仅是博萨德拍的照片,还包括他写的很多东西,以及1930年代早期的时候博萨德做的一些工作。我还想以一种更好的方式将他的图像置于历史上下文关系中。在这个过程中,我在德国的一个新闻档案中发现了大量的老照片——这些照片被认为已经遗失了。我非常幸运能找到这些老照片,它们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个对如何来解读博萨德作品非常重要。现在,可以在这个新展览中首次在中国展出这些老式印刷品的精选作品,以及纽约国际摄影中心提供的卡帕的许多老照片。据我所知,这是首次展出,也可能是第一次向中国观众提供观看卡帕老照片的机会,这些照片在过去经常被讨论。感谢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和苏丹教授,他们认可了我对博萨德和卡帕摄影作品研究以及重要性。我很高兴能够在这个享有盛誉的博物馆中展示大量迄今为止从未见过的图像。
展览“沃尔特·博萨德/罗伯特·卡帕在中国”聚焦了从1931到1938年这一时间段,这期间在中国历史上尤为重要。同样,这十年无疑是博萨德和卡帕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时期。对中国而言,20世纪30年代是至关重要的十年。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再到卢沟桥事变、淞沪会战、南京大屠杀等等,日本侵略军从侵占中国东北,蚕食华北,直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试图占领整个亚洲。中国从内战到一致对外,漫长的抗日战争,导致了中国主要城市连续遭遇侵略、数百万中国民众受害。西方世界则隔岸观火,试图在中国人民极力反抗装备精良的日军战争中维护自己的利益。
1938年格外重要,日本侵略军的破坏性行动,使整个世界变得极为紧张。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世界希望能够近距离看到东方人如何来抗争自己的命运,国际媒体非常渴望获得中国的第一手报道。那年的重点报道是“武汉会战”⑥。毫不奇怪,许多外国通讯员,外交官和知识分子聚集在汉口,目睹了长期日本轰炸后这座城市即将倒塌的情况,其中包括卡帕和博萨德。
卡帕是随着荷兰电影制片人乔里斯·伊文斯⑦(Joris Ivens)的摄影组来中国拍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卡帕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与欧洲的反法西斯斗争是平行的。他以理想主义的态度到一线发回令人振奋的报告。作为一名流动的摄影师,他只在中国度过了八个月的有限时间,因为他的电影团队一直在国民党的监督下工作,拍摄任务非常艰巨。他感到过于被束缚,无法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尽管如此,他还是成功地拍摄了许多令人震撼的故事照片。
正如我在开始时提到的,博萨德和卡帕既是朋友也是竞争对手。双方都努力将自己的作品发布在最有影响力的插图杂志上,例如《生活》杂志,博萨德主要通过其代理机构《黑星》,卡帕也和它合作。它们都涵盖了相似的故事,有时甚至是相似的战争场景,但使用的方法却是不同的。在展览中我们会看到,如果将博萨德和卡帕在1938年拍摄的照片进行比较的话,非常具有启发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作品是相辅相成的:卡帕倾向于尽可能走到前线,对特写和“戏剧化的表现”的偏爱尤为明显。而博萨德试图捕捉关键时刻,以便理解动作并传达大量的视觉信息,视线更远。但是有时卡帕和博萨德好像也会改变他们的角色。可能他们也会互相启发,作品相似的主题和背后动机显而易见。这样的图像我们通常以最自然的方式并排展示。我用两个例子说明,例如,他俩都拍摄过1938年在汉口的宋美龄。在卡帕的作品中,突出她向远方凝视的目光,可以看出宋美龄非常坚强。而博萨德对宋美龄刻画更加柔和一些。如果你记得我上文提出的他们使用的不同的摄影方法,或者他们两个各自不同的角色就会发现照片的差异所在。卡帕是在国民政府监视下拍摄的,宋美龄不希望他和共产主义接触,但是博萨德和宋美龄私交很好,像很多人一样,他也将自己在两边的人际关系用在自己的作品中。第二个是,他俩都曾拍过跌倒的战士。不同的是,卡帕拍的这张非常有名,实际证明是一张剧照,摆拍,在照片中,这个士兵已经阵亡,但在博萨德故事中,这位姓陈的士兵,被宋美龄救了下来,并没有死。不管怎么样,通过影像是讲一个故事,所以我们在提到摄影作品真实性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审慎。
卡帕倾向于尽可能走到前线,对特写和“戏剧化的表现”的偏爱尤为明显。而博萨德试图捕捉关键时刻,以便理解动作并传达大量的视觉信息,视线更远
要了解摄影师本人并不认为他们的照片是艺术品,即便他们的图像具有很高的美学和艺术价值,尤其在回顾他们的作品时,两位摄影师都对以下问题感兴趣:摄影如何启发甚至影响复杂的现实,以及如何在杂志上最好地呈现给大众。博萨德和卡帕都利用摄影作为讲故事的手段,在这其中交叉着新闻、事实、信息、情感,甚至小说等元素。
在新闻摄影领域,卡帕当然更倾向于纯摄影,而博萨德是作家兼任摄影师,有时会优先考虑作家的力量。
1938年5月,博萨德成功访问了陕西省北部偏远地区的“红色首都”延安,这里是红军根据地。经过六天的艰苦跋涉,他和美国记者阿奇博尔德·斯蒂尔(Archibald Steele)到达了共产主义的中心,博萨德在这里对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采访。他在给瑞士报纸的一篇大幅报道中,试图捕捉毛泽东的性格和外表。我这里引用他自己的描述:“毛泽东说话掷地有声,简洁,不带任何手势。他讲话时,长长的黑色头发常常落在前额上,他修长灵巧的手总是慢慢地将它捋回去。他一直不断地抽着最便宜的香烟,烟味闻起来像是马粪和德国泡菜的混合物。”博萨德对共产主义学生的组织方式以及他们的培训方式着迷。城市的整洁和年轻人的开朗信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延安是下一代人的麦加城,他们被战争驱逐出学校和家,并期望在这里建立新的信仰联合体。” 抗大的学生生活在窑洞中,这也是他们的避难所。在这里,他们学习理论课程,并准备好对日军进行部署。博萨德像他近年来经常做的那样,还设法制作了一部关于毛和延安的电影——据说这些是毛的第一幅动人影像,1938年展览时候曾经展出过。同时他还拍摄了不少毛泽东的照片。博萨德此次延安之行的杰出成果就是发给《生活》杂志的图画报告。
卡帕也希望实现这个故事,他知道全世界都在等待它,尤其是具有一百万册发行量的《生活》杂志,会将其作为独家新闻发行。当卡帕了解到博萨德的成功时,他感到沮丧和担心,因为他错过了这次机会。他在纽约给他的经纪人信中写道:“博萨德在延安只呆了两天半时间,就是说,他做不了什么事,但即便是做不了,这就足以击倒我了……”实际上,几周后,卡帕回到了家,并没有去延安。另一方面,博萨德返回汉口,设法长时间待在这个城市。他是最后一位离开汉口的西方通讯员之一。他等待这场可怕战斗的最后一幕,见证了日本人如何残忍地侵略这座城市。
不过,卡帕和博萨德之间的竞争并不是太激烈。有时候,他们也会在工作中互相帮助,以全面报道汉口及其周围的战斗,记录日本人对城市的狂轰滥炸。
为此,卡帕和博萨德都尝试使用彩色胶卷。柯达早在1936年就推出了第一款柯达克罗姆(Kodachrome)35毫米彩色胶片,仅仅两年后,就生产出了具有稳定性更强的彩色乳液的幻灯片材料——《生活》杂志的编辑们立即在杂志中使用这种创新技术,用该技术来做彩色图片。1938年夏天,《生活》杂志老板威尔逊·海克斯(Wilson Hicks)送了博萨德一盒崭新的柯达克罗姆彩色胶片。根据卡帕的传记作者理查德·惠兰(Richard Whelan)的说法,卡帕向博萨德借了其中的一部。在此之前,杂志中的彩色图片几乎完全是用于做广告的。
如传奇图片编辑约翰·G·莫里斯(John G. Morris)在关于卡帕的一篇文章中所述,这些有关汉口战役的照片很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本以彩色印刷的战争照片。不过,博萨德的第一张彩色相片已经在两个月前的8月8日的《生活》杂志上出现过。因此,我们不能真正将它们称为“战争照片”,我也不想质疑卡帕是否是战争摄影的先驱者。尽管如此,博萨德可以声称自己拍的毛泽东肖像,再加上两张延安红军演习的彩色照片,也是新闻摄影的重要一步,因为它们标志着新领域——时政报道的第一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很可能是在新闻报道中发表的毛泽东的第一张彩色照片。顺便说一句,博萨德也拍过一些战争的彩色相片,但由于某些原因,它们没有被发布出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新闻摄影时政报道方面),也许博萨德会感到沮丧——但这并没有记录在他的书信中。
1930年代的“中国竞赛”具有多种层次:一是中国内部政治力量之间的角力。二是中国和日本军队之间的角力。三是一场与时间的斡旋。四是不同媒体之间争夺新动态的竞赛。而且,在某些时候,这也是那些必须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在野外,在摄影专业中生存下来的摄影记者之间的私人竞争。他们志在成为能够表达这样故事的第一人。甚至到今天,他们的战地摄影,也影响我们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章节。
❶ 译者按:由瑞士摄影基金会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合作举办的“瓦尔特·博萨德与罗伯特·卡帕在中国”(Walter Bosshard / Robert Capa:THE RACE FOR CHINA)开幕式暨学术研讨会于2019年10月28日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本次展览首次同时展出这两位杰出摄影师作品,以《1931年在南京举行的第一次国民大会》为开端的鲜为人知的一百七十七件原版照片、影像和文献,共分为六个单元展出,分别是:第一次国民大会和日本占领满洲(1931)、西北探险(1933 - 1936)、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1937-1945)、农村动员(1938)、延安之行(1938)、罗伯特·卡帕和瓦尔特·博萨德——来自汉口的平行报道(1938),全面展现了1931-1938年之间,中国南京、北京、上海、东北三省、重庆、青海、山东、内蒙、武汉、延安、徐州等地的风貌。当我们试图用影像还原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悲痛历史时,但这些作品的历史背景却很少被人关注。它们应该被置于国际新闻和摄影报道兴起的大环境下进行解读。例如1938年的“武汉会战”期间,许多外国记者、外交官和知识分子聚集在汉口(瓦尔特·博萨德和罗伯特·卡帕也在其中),见证了日军长期轰炸下即将沦陷的城市。瓦尔特·博萨德和罗伯特·卡帕都试图成为战争中的第三只眼睛。博萨德作为中立国的记者,在残酷的战时状态下自由穿梭于几个对立的阵营之中;卡帕依靠勇气和机智接近冲突的前沿。他们曾是好友,也是竞争对手,不约而同地报道类似的事迹、洞察相同的战争画面。在那个时代,恐怕很难再找到像他们一样如此全面展现1931-1938年中国风貌的摄影师。
❷ Peter Pfrunder,瑞士摄影基金会馆长,策展人。
❸ 《柏林画报》,英文名: Berliner Illustrirte Zeitung,通常缩写为BIZ,是一本周刊,于1892年至1945年在柏林出版。它是第一本面向大众市场的德国杂志。
❹ 《新苏黎世报》是瑞士历史悠久、影响较大的德语报纸。1780年创刊,在苏黎世出版。该报原名《苏黎世报》,1821年改为现名。该报以国际新闻多,分析深入,背景交代详细为特点。在国外派有常驻记者。
❺ 有一张阿奇博尔德·T·斯蒂尔拍摄的照片很能说明,在这张四个人的合影中,卡帕把头靠在博萨德腿上,姿态犹如崇拜偶像般。照片顺序为阿格内斯·斯梅德利,瓦尔特·博萨德,罗伯特·卡帕和埃万斯·F·卡尔松(从左至右)。
❻ 1938年6月到10月,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的一场战役。
❼ 乔里斯·伊文思(1898—1989),荷兰人,世界纪录电影先驱之一,1938年在中国拍摄的《四万万人民》(The400 Million),是他电影生涯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在拍摄片子时,摄影团队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限制和监视,并对他去延安拍摄的要求百般阻挠。在他离开中国前,伊文思设法将一架35毫米摄影机和数千尺胶片赠予将赴延安的摄影师吴印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