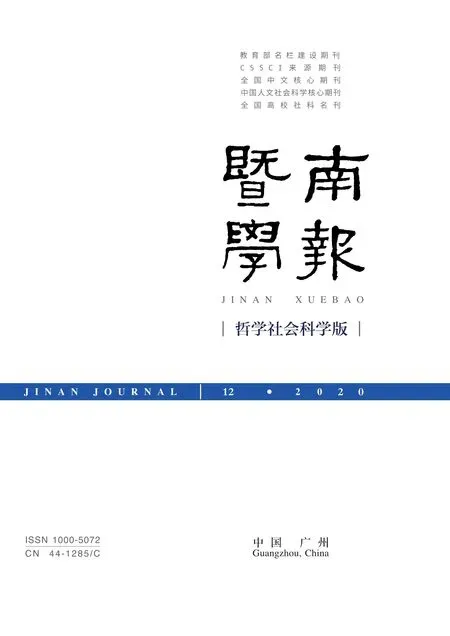居住权的定义与性质研究
——从罗马法到《民法典》的考察
2020-11-17肖俊
肖 俊
一、中国居住权的定义模式及其问题
罗马法以降,居住权一直都是大陆法系基础的用益物权类型之一,由于东西文化差异造成的制度误读,它并没有被东亚各国和地区的法律所接受。(1)“惟东西方习惯不同,人役权为东亚各国所无,日本民法仅规定地役权,而于人役权无明文规定,台湾地区习惯与日本相同,故本法亦只设地役权也。” 台湾地区“民法立法理由书”。王泽鉴:《民法物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4页。当2018年日本法还在继承法改革中谨慎地尝试“配偶法定居住权”之时(《日本民法典》第1028条),(2)2018年继承法修订后的《日本民法典》第1028条:于继承开始时居住在属于被继承人财产之建筑物之情形,合下列各项任一者时,就其居住之建筑物之全部,取得无偿使用及收益之权利。王融擎编译:《日本民法:条文与判例》,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1217页。2020年的《民法典》已经以极大魄力与创新精神在第十四章增设了体系化的居住权制度。因此,与其他传统物权类型相比,我国居住权制度没有台湾地区和日本的相关知识储备可借鉴,这就需要结合大陆法系传统与中国法的特殊性进行研究。《民法典》第366条的居住权定义正是这样一个研究起点。
《民法典》第366条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在现行的用益物权体系中居住权是一种性质独特的权利,它是唯一以建筑物为客体并且受主体生活需求限制的用益类型,第366条通过“合同约定”、“住宅使用”以及“生活需求”这三个要素对其进行界定,但这些要素与既有用益物权理论的兼容性还有待完善,需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居住权中意思自治的边界。第366条规定居住权源于“合同约定”,从权利是由法律行为创设这一点上看,这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从体系上看,则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我国绝大多数的用益物权定义都不包含“合同约定”这一要素,比如《民法典》第331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定义、第344条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定义以及第362条的宅基地使用权的定义。只有地役权的内容才涉及“合同约定”,第372条规定“地役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利用他人的不动产,以提高自己的不动产的效益”,而地役权恰恰是需要通过意思自治来确定权利的类型与内容。在“居住权”这一章中,第367条和第369条也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居住的条件与要求,还可以约定居住权的收益权能。显然如地役权一样,居住权的定义也需要考察物权法定和意思自治的边界问题。
第二,居住权使用权能的界定。第366条通过“使用”权能来界定居住权的权利范围。虽然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是所有权的基本权能,但“使用权”在我国物权法的理论中并没有系统的界定,比如建设用地使用权就包含了土地的使用、收益以及部分处分的权能(《民法典》第344条,第353条),海域使用权包含了对海域的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民法典》第32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23条),甚至宅基地使用权也可能放开出租和抵押的限制(2018年《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在这样的语境中,居住权的使用范围应如何界定,能否扩张到孳息收取乃至于抵押?此外,也有学者提出,对他人房屋的使用并不限于居住目的,例如利用他人房屋储存、置放货品也属于对房屋的使用,但不属于居住权的权利范畴。(3)参见单平基:《〈民法典〉草案之居住权规范的检讨和完善》,《当代法学》2019年第1期,第8页。这都涉及居住权定义中的“使用”的界定。
第三,“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的含义与功能。在规定“住宅的占有和使用”之后,第366条又重申“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这似乎有同语反复之嫌,但与2005年《物权法草案》第180条相比,这又是本次立法新增的元素,显然立法者是有意为之。(4)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第180条:居住权人对他人享有所有权的住房及其附属设施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如何梳理两者关系,发挥其功能,也是分析居住权定义的任务之一。
中国的居住权立法在东亚民法圈中是一个创新,但在罗马法传统中居住权制度有着漫长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为了理解居住权概念,科学地解释《民法典》第366条,有必要以私法史为起点开始研究工作。
二、居住权概念在罗马法中的产生
(一)居住权(habitatio)的产生与意义
“居住”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基本需求,但直到罗马法晚期在法律文献中才出现独立的居住权概念,公元533年东罗马帝国皇帝优士丁尼的敕令(C.3,33,13pr.)首次将居住权规定为一种独立的物权形态。在与使用权、用益权相比较之后,敕令提出居住权是一种有着自身特性的权利(iuspropriumetspecialemnautramsortitaesthabitatio)。在优士丁尼的钦定教科书《法学阶梯》中居住权也是与用益权、使用权并列的独立权利类型。(5)参见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第二卷中第四题和第五题的目录。目录参见徐国栋:《优士丁尼〈法学阶梯〉评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虽然规范意义上的居住权出现得相当晚近,但对他人房屋进行使用收益的法律经验在罗马法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经出现了对他人之物进行使用收益的权利类型“用益权”(usufructus),它包含直接使用(usus)和获取孳息(fructus) 两方面内容。(6)[德] 马克斯·卡泽尔、罗尔夫·克努特尔著,田士永译:《罗马私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300—301页。从共和国时期伟大的演说家西塞罗的作品中可以发现,公元前1世纪的时候用益权的客体已经扩张到房屋。(7)要是一个人能不把田地、房屋、牲畜和无数的金银视为财富,称之为财富,因为在他看来,人对它们的收益(fructus)是轻微的,对它们的使用(usus)是渺小的,对它们的所有权(dominatus)是不可靠的,……那么这样的人该被认为是多么幸福啊! [古罗马] 西塞罗著,王焕生译:《论共和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59页。为了突出“fructus”,“usus”这两个词语所具有的法律含义翻译,略有改动。如法学家乌尔比安所总结的,当一处房屋的用益权被遗赠,那么所有的收入都归于用益权人,无论收入来自于房产或者土地以及其他任何对建筑的利用(D.7,1,7,1)。
用益权全面使用收益的权能架空了所有权的经济内容,为了不给予如此充分的权利,所有权人会明确提出仅给予使用的权利,不能获取孳息。于是在用益权产生之后的一个世纪,法学家承认了一种与用益权结构相似但内容更为狭窄的使用权(usus),只能满足单纯的个人使用不能收取孳息的权利。(8)Grosso Giussepe, Usufrutto e Figure affini nel Diritto Romano, Torino:G. Giappichelli, 1958, p.431.
因此从体系性上看,罗马法一直存在对他人房屋的用益规则,居住权并没有起到漏洞填补的效果,相反可能会引发制度重叠。那么,为什么还有必要创立居住权呢?那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尤其遗嘱制订时,民众往往不会准确地使用法律术语,如“房屋用益权”或者“房屋使用权”,而是直接称为“居住”(habitatio)或者“居住的目的”(habitandicausa),在这一时期“居住”只是一个日常语词,有时居住权人(habitator)在租赁合同中还用来表示承租人。(9)Berger Adolf, The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Roman Law, Philadelphia: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53, p.484.
对于遗嘱中出现的“居住”如何去界定其权利性质,需要法学家进行探索,古典时期的罗马法学家通过类推用益权和使用权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公元533年之前已经出现了居住权,只不过没有独立的名称。
用益权的产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表征物权技术进化到可以区分“物”本身和对物的利用的“权利(ius)”,法学发展来到了一个新阶段。(10)Bretionne Mario, La Nozione Romana di Usufrutto(Volume Primo)Dalle origini a Diocleziano, Napoli: Eugenio Jovene, 1962, pp.35-36.与之相比,居住权在物权技术上并没有新的贡献。它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简化交易和规范统一上,一方面满足民众更为简单直接创设物权的需求,体现法律对习惯的认可和妥协;另一方面,有利于统一规范避免争议,因为不同的学派对居住权的解释会导向多元的法律适用,为了避免不一致的法律适用后果,所有只要与“居住”(habitatio)相关的权利,都一视同仁被看作是“居住权”。因此在著名的敕令C.3,33,13pr.中,第一句话即是“在过去曾有这样的疑问”,而结语则是“为了平息这样的争议,朕以简洁明了的意见消除了所有的疑虑”。
(二)罗马法学家对于“居住权”的观察与解释
虽然罗马法中没有居住权的定义,但是法学家面对居住权所进行的观察与解释,为现代的居住权定义提供了基础。
第一,类推适用使用权。对于非典型的居住权,罗马法学家首先提出类推适用使用权的方法,古典时期的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如果居住权(habitatio)被遗赠,那么所产生的权利完全等同于遗赠使用权。他的老师帕比尼安也持同样的观点,“遗赠使用权和遗赠居住的权利几乎是同样的。因此获得居住权的人不能赠与这一权利,但可以接纳使用人所接纳的同样的人”。在解释中,有的法学家还认为只要出现“居住”这一表述,无论这是和用益权还是和使用权一起,都应该解释为使用权。所以,如果一项遗赠提出“我遗赠给那人以居住为目的的用益权”,那么只有一项居住的权利被遗赠,当然,如果表述为“一项以居住为目的的使用权”,那仍然也是使用权。(D.7,8,10,2)。
也有另一派的法学家主张居住权应该被理解为用益权,权利人可以将之出租(I.2,5,5.),(11)[德] 马克斯·卡泽尔、罗尔夫·克努特尔著,田士永译:《罗马私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307页。但整体而言,主流观点还是支持类推使用权的方法。
第二,居住权特殊的人身专属性。在类推适用使用权规则的同时,罗马法学家还敏锐地感觉到居住权所具有的强烈的人身专属性。帕比尼安提出:“居住权不能被继承,但同时既不因不使用,也不因人格减等而消灭。”用益权本身就具备一定的人身专属性,权利期限默认为终身,不能继承不能转让,但居住权则体现出更为强烈的人身性以及更少的财产性。
首先,居住权不因为人格减等而消灭。所谓人格减等,指的是罗马人所具有的三种基本身份:自由人身份、市民身份以及家庭身份部分或者全部丧失,用现代民法的术语来说,人格减等意味着民事权利能力被剥夺,甚至达到民事死亡的效果。(12)关于“人格减等”的内容,参见徐国栋:《优士丁尼〈法学阶梯〉评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页—123页。所以用益权会随着人格减等而消灭(D.7,4,1pr.),但是居住权不消灭,这意味着即便居住权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完全被剥夺,也能保有居住权。其次,用益权作为所有权的负担,因此用益权会因为权利人长期不使用(nonusus)而消灭,土地是两年,其他物是一年(后优士丁尼改为长期取得时效),但居住权不会因为不使用而消灭,因为它具有维持权利人生活的制度目的,不因为一时不使用而消灭。(13)Rudolf Sohm, The Institutes of Roman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1, p.266.莫德斯丁对此进行解释,他认为居住权遗赠“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事实”(infactopotiusquaminiureconsistit)。(14)参见D.4,5,10.[古罗马]优士丁尼著,窦海阳译:《学说汇纂》(第4卷),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页。如果说,用益权是对于房屋直接利用的权利,那么居住权还包含了人类对居住的需求事实,这使得居住权超过市民法而带有自然法的色彩,某种程度上具有近似于现代社会中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的色彩。
(三)居住权与人役权体系
与居住权一样,“人役权”(servitutespersonarum)这个体系概念也产生于罗马法的后古典时代。“役权”一词在古典法中仅仅意味着土地之间的隶属关系,只有用来表示地役权。而到了罗马法晚期,拜占庭法学家则用这种关系比拟用益权中人与物的关系。用益权只限于个人行使,不能继承也不能出售,于是被看作是一种物隶属于人的现象。它和土地隶属于土地的现象一起构成了一个非常宽泛的役权概念,只要权利人能够利用客体,或者客体具有一种或者多种的用途都可以被看作是役权关系。最终拜占庭法学家对古典文献进行改造,提出统一的役权结构:“役权或者是人役权,比如使用权和用益权;或者是地役权,比如乡村地役权和城市地役权。(D.8,1,1)。”(15)Longo, Carlo, “La Categoria delle Servitutes nel Diritto Romano Classico”,Bullettino Istituto di Diritto Romano, No.11,1898,p.281.由此用益权和使用权以及居住权也被称为人役权。
人役权的体系概念对现代的居住权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居住权被看作是人役权体系中附着于用益权的“子权利”。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优士丁尼将居住权看作是一种与用益权相互并列的独立权利,但是在逻辑上并没有区分两者,基于现实的需求,他认为居住权也可以具有收取孳息的权能,其基础并不是法学逻辑而是基于“仁慈”(adhumaniorem)(C.3,33,13.1.)。
罗马法居住权经验中的“人役权”、“类使用权”和“强人身性”这三要素为现代居住权定义模式确定了轨道。此后的中世纪法没有给居住权提供有用的经验,因为中世纪物权和罗马法不同,不区分最终归属和现实利用,而是将它们同等视为所有权,只是级别有所不同:直接所有权、用益所有权和准所有权等,这样的物权体系没有给居住权留下空间。(16)陈晓敏:《大陆法系所有权模式历史变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1—32页。
三、居住权概念在现代民法典中的发展
忠实地追随罗马法的轨迹,现代民法典都制订了完整的人役权体系。虽然受到这一时代意识形态的影响,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废除了在字面上含有“人”与“奴役”有关的人役权以显示对自由价值的重视,并影响到了其他的民法典,但实际上人役权的各个类型都得以保存。(17)Leicht Silverio, Storia del diritto italiano, Milano: A. Giuffrè, 1941, pp.145-146.与罗马法的思维不同,现代民法是以提取公因式和形式逻辑为基础重新建构了人役权体系,罗马法一直不能清晰地区分用益权、使用权和居住权三者的界限,但现代法则通过意思表示解释努力矫正这一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现代居住权概念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一)现代民法典中的居住权定义
即便遵循了共同的罗马法传统,各个国家的法典对居住权的界定模式也不尽相同,比如法国法直接以“居住”(pour l’habitation)界定居住权,《法国民法典》第632条规定“对房屋享有居住权的人,得协同其家庭在该房屋内居住,即使在给予居住权利时其本人尚未结婚,亦同”(18)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以下《法国民法典》条文皆引自此书。。德国法则通过“使用(Benutzung)”进行界定,《德国民法典》第1093条规定,“居住权是将建筑物或建筑物的一部分作为住宅使用的权利也可以作为限制的人役权而设定”(19)陈卫佐译注:《德国民法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以下《德国民法典》条文皆引自此书。。而意大利法则使用含义更宽泛的“用益”(godimento,也有“享用”的意思)进行界定,《意大利民法典》第1022条规定,“对房屋享有居住权的人可以在自己和家庭需求的限度内享用房屋”(20)费安玲译:《意大利民法典》,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以下《意大利民法典》条文皆引自此书。。虽然在立法中语词表述不尽相同,但是在教义学内容上是一致的。以意大利法为例,《意大利民法典》第1022条将居住权看作是对房屋的用益(享用),学理就明确提出限制:尽管用词是“用益”,但居住权没有给予权利人全面的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而仅仅是一种有限度的使用,绝无收取孳息的权能。权利的客体仅仅是居住的房屋,除了在此居住,居住权人没有其他的用益,无论是直接收取的自然孳息还是间接收取的民事孳息,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第1022条所谓的“用益”,仅仅是在房屋中居住的这样的权能。(21)Bigliazzi Geri, Usufrutto, uso e abitazione, Usufrutto, uso e abitazione,Milano:A. Giuffrè, 1979, p.333.
所以,在居住权的界定中,无论是“居住”还是“享用”都意味着“有限度的使用”。在物权体系中,将“居住权”的内容界定为“有限的使用权能”是最为合适的,不仅避免了以“居住”界定“居住权”的同语反复,而且有效地将日常语言中的居住建构于教义学的基础上。优士丁尼极力赋予居住权以独立性,但基于功利的角度放开了居住权出租的限制,在现代民法典的体系中,基于形式逻辑的要求,严格区分了各种用益权和居住权的边界,没有给予居住权人孳息收取的权能。
居住权的界定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立场是遵循罗马古典法学家的意见,直接将居住权看作是使用权的一种,即以住房为客体的居住权,比如《葡萄牙民法典》第1484条规定“使用权系指权利人及其亲属得在本身需要之限度内使用他人之特定物及收取有关孳息之权能。涉及住房之使用权,称为居住权”(22)唐晓晴等译:《葡萄牙民法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澳门民法典》第1441条也是如此界定,“涉及住房之使用权,称为居住权”,因此居住权仅仅是客体为住房的使用权,仅在名称上有其特殊性。另一种是德国法和意大利法的立场,认为居住权包含了使用权能,但仍有其独立性。德国法没有直接规定使用权,而是更开放地规定为“限制人役权”,其内容比用益权更为狭小,这一范围允许当事人自由约定,只有在有疑义时才能仅以个人需求为限(《德国民法典》第1091条和第1092条),(23)[德]鲍尔著,张双根译:《物权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55页。在这种意思表示推定规则之下,居住权即是内容最为狭窄的权利。意大利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学说对于《意大利民法典》第1021条的使用权和第1022条的居住权进行了区分:使用权意味着对物全面的使用,而居住权仅仅是以权利人的家庭生活状态进行有限的使用。(24)Caterina Raffaele,Usufrutto, Uso, Abitazione, Superficie, Torino:UTET, 2001, p.176.值得注意的是阿根廷法,1998年《阿根廷民法典》将居住权看作是一种特殊的使用权(第2984条第2款),但是2014年《阿根廷国家民商法典》(Código Civil y Comercial de la Nación)则将居住权与使用权分开,将之规定为一种独立的权利(第2015条)。
由此可见,居住权的特性不仅在于客体的类型,而且在于主体状态所决定的使用限度。明确区分使用权和居住权,不仅是基于维持权利独立的逻辑需求,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这种对典型权能的区分可以更好地满足权利人的不同需求。(25)传统的使用权是指以权利人直接使用不获取孳息为主要内容的权利,我国用益物权体系中存在的各种“使用权”内容都包含了全面的收益功能甚至处分权能,比如建设用地可以出租甚至抵押,海域使用权包含了对海域的使用和收益的权能,宅基地使用权改革也谋求放开出租和抵押的限制,由此可见,我国的“使用权”在教义学上实际上包含了用益的权能,而不是一种单纯的使用权。因此《民法典》第366条的定义模式与德国法和意大利法更为接近。
(二)居住权的有限使用权能
基于前文的研究可知,在现代民法典体系中,居住权的本质是有限的使用权,与独立使用权相比,它受到了两方面的限制:第一是建筑物用途的限制,第二是权利人家庭生活状态的限制。
第一,建筑物的居住用途限制。根据用益权的原理,权利人只能在特定的经济用途下进行使用收益,这样的意义在于权利结束后,用益物可以保持在一个良好的状态中,不损害所有权人的利益。对于物的使用方式,可能有主观用途和客观用途两种,前者是当事人的偏好,后者是物的物理效用。在物有多重用途时,通常可以由所有权人自由决定物的使用方式,理性人选择的主观用途优先于物的客观用途。居住权的客体对于权利内容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主流学说认为,只有一开始就以满足生活居住为目的的住宅才能被设定居住权。(26)Giovani Pugliese, Usufrutto Uso Abitazione, Torino:UTET, 1972, p.834.权利人可以在房屋内进行职业行为,但是职业活动的开展不能以住房为手段实现。(27)Paolo Basso, Il Diritto di Abitazione, Milano:A. Giuffrè, 2007, p.81.
居住权人不能改变其住房的用途,那反过来,非居住性质的建筑物,如仓库和酒店等是否可以基于所有权人的意愿设定居住权呢?对此,意大利学界的新观点认为,经过一定改造之后的建筑物,只要符合同时期公共卫生和市政关于居住的行政规章的要求,也可以设立居住权;反之,若不能满足市政居住和卫生要求,则构成标的物违法。同样需要讨论的是,对于未全面完工的房屋设立居住权的问题。如果居住权设立时房屋尚未完工,那么需要进行装修之后才能满足居住使用。但是装修属于事实上的“处分”,这超出了“使用”的范围,考虑到当事人的意愿是设立居住权,只要房屋本身是以居住为用途,就应该允许居住权人超出使用权能对之进行修缮,除非所有权人明确表示阻拦。(28)De Martino, Dell’Usufrutto, dell’Uso e dell’Abitazione in Comm. Scialoja-Branca,Bologna-Roma,1978, p.185.
第二,权利人家庭生活状态。如果一座房屋被设定使用权,那么权利人可以对整个房屋进行使用,但如果一座房屋被设定居住权,权利人只能按照自身所需要的空间进行使用,这正是罗马法中居住权的人身性的体现。《法国民法典》第632条、《德国民法典》第1093条第2款以及《意大利民法典》第1022条,都规定居住权以权利人的家庭生活需求为限。这实际上意味“家庭生活”所需是一种弹性的标准,居住权的范围会随着权利人的家庭生活状态的改变而改变。首先,在权利人尚未结婚的情况下,只能以个人需求为限进行使用,此时所谓家庭的生活需求只是潜在的范围;其次,在他结婚生儿育女之后,居住权的范围应该延伸到足以满足全部家庭的使用;最后,家庭的范围,除了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之外,还包含为家庭提供服务而一起生活的人,包括权利人的护工和保姆等等。(29)Caterina Raffaele, Usufrutto, Uso, Abitazione, Superficie, Torino:UTET, 2001, pp.182-183.
(三)居住权界定模式的根源:人役权中的意思表示推定
“居住”是人类的一切生存活动的基础,对此会有很多不同的界定方式,而在物权法中,居住权的理论基础不在于居住本身,而在于人役权体系和用益规则。首先,用益权处于核心地位,用益权人在经济用途的限定范围内对物进行全面的使用和收取孳息;随后是扣除了收益权能的使用权,使用权人可以在经济用途的限制内对物进行直接的全面使用;随着客体进一步固化到房屋,权能进一步地缩减直至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之时,就出现了居住权。
将居住权界定为仅满足家庭生活基本需求的住房使用权,并不是物权法定的任性和武断,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法国民法典》第628条规定,在用益权的框架内,当事人通过权利文书规定权利范围不同的居住权和使用权。对此,法国教科书认为,各方当事人可以通过约定排除这种权利与用益权的某些差别,并据以设立范围各不相同的与真正的用益权更加接近的使用权和居住权。(30)参见[法]弗朗索瓦·泰雷、菲利普·森勒尔著,罗结珍译:《法国财产法》(下册),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0—1001页。《德国民法典》第1092条规定,限制的人役权不可转让,但获得许可时则允许将权利的行使进行转让。意大利法虽然对此没有明文规定,但学理和实践同样重视意思自治对人役权内容的影响:“通过对双方的意思表示解释,可以发现,当事人说的是居住权但可能是使用权,或者说的居住权和使用权,但实际上却是用益权,反之亦然。”(31)Orlando Cascio, Abitazione(diritto di), in Enc. dir., I, Milano:A. Giuffrè, 1958, pp.94-95.意大利最高院也在判决中承认权利人可以通过合意调整使用权的范围(Cass.,26-2-2008,n.5034)。
既然如此,在没有任何特殊意愿的情况下,仅仅提出“居住权”,此时可以默认为,只是给予满足个人对房屋最低程度的需求的权利,这种默认的权利范围应该比用益权和使用权的范围都更为狭窄,这种限制可以通过主体需求和客体范围的交错限制体现出来。
四、《民法典》第366条诸要素的结构与解释
越过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狭隘视野,我们民法典中的居住权重新衔接上大陆法系传统。与此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中国法与罗马法的差别:罗马法是顺着用益权的轨迹,权能不断分解形成居住权,居住权的功能不过是锦上添花、简化交易;而中国法反过来,基于最迫切的实践需求制定了居住权,没有用益权基础,所以它的作用是填空补白、雪中送炭。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理论基础,不得不借鉴既有的用益物权规则(特别是地役权),可能效果并不妥帖。
因此,下文结合传统教义学理论和中国法自身特点对第366条的诸要素展开研究。
(一)人役权、地役权与第366条“合同约定”的边界
在我国的用益物权体系中,多数的用益物权都不是通过合同设定的,《民法典》第331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定义、第344条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定义以及第362条宅基地使用权的定义,都不涉及合同约定。只有地役权的内容才有“合同约定”的要素,第372条规定“地役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利用他人的不动产,以提高自己的不动产的效益”。
将规定居住权的第366条、第377条与规定地役权的第372条和第373条相对照,非常明显看到居住权的定义在这一点上受到地役权的影响。但问题在于两者的原理并不兼容。从历史发展上看,居住权、使用权和用益权共同被称为人役权,而人役权又与地役权统称为“役权”,不过这种形式上的共性并不能掩盖两者实质的差异。首先,从用益范围上看,地役权的用益是对于土地或者建筑局部的用益,地役权用益的内容不会妨碍到所有权人的基本经济生活,所以同一个不动产上可以存在不同类型的地役权;而居住权实际上剥夺了所有权人对于自己房屋的使用和收益,使之沦为空虚所有权,具有绝对的排他性。其次,从用益方式来看,地役权的种类多样而灵活,包含了通行权、汲水权、导水权、排水权、眺望权等难以穷尽的类型,内容上的广泛不确定性成为地役权的基本特征,使得地役权与物权法定原则出现了一种复杂的关系,它的不同类型需要当事人通过合同的方式予以约定,形成物权合意并记录于登记簿中。(32)参见耿卓:《地役权的现代发展及其影响》,《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6期,第6页。与此不同,居住权的基础内容不需要当事人合意确定,法律对此已有明确规定:居住权不得转让和继承(第369条);随着权利人的死亡而消灭(第370条),这些规范不能由居住权合意而改变,否则会彻底架空所有权。
因此,居住权的合同约定在多大范围和程度上能构成物权合意,不能借鉴地役权,只能依靠结合人役权的原理进行判断,因为居住权是用益权在主体、客体和用途上不断缩限的结果,一个完整的用益权可以使得住房建筑得到更为充分的利用,如果要通过意思自治来发挥物的效用,那么扩大到住房用益权也能够与其自身的制度逻辑相符合。《民法典》第369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可以通过约定排除设定居住权的房屋不能出租的限制。考虑到我国没有完整的用益权体系,可能引发用益物权类型供给不足的问题,通过合意允许居住权出租,可以更为灵活地满足居住权人的需求。(33)参见薛军:《地役权与居住权问题评〈物权法草案〉第十四、十五章》,《中外法学》2006年第1期,第97页。
(二)第366条“住宅的占有和使用”与主客体的限制
第一,对于“使用”的界定。第366条以“占有”和“使用”来界定居住权的内容,两者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是使用,占有只是使用的前提。在用益物权理论中,使用权能包含两方面的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在获得孳息之外对于物的直接利用,虽然没有新物产生,但用益权人可以此种方式来享受物的利益,比如居住房屋或者用牛耕地;第二种含义是指为了获得孳息而进行的准备活动或者生产过程,比如在田地里播种或者将房屋出租所进行的修整,这就与收益有着直接的联系。(34)Arangio Ruiz, Istituzioni di Dirtto Romano, Napoli: Dott.Eugenio Jovene,1956, p.243.显然,居住权的使用权能属于第一种,而建设用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中的使用权能则属于第二种。从第392条的规定上看,如果允许登记当事人出租的约定,这就是第二种意义上的“使用”,此时物权法中实际存在着两种居住权,“典型居住权”和非典型的“住房用益权”。
第二,对于“住宅”的界定。根据2006年建设部的《住宅建筑规范》(GB 50368—2005)的界定,住宅建筑是“供家庭居住使用的建筑”(第2条),但实际上,建筑的性质还受到土地性质和房产管制政策的影响。与欧洲法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建筑物用途变更相比,我国对建筑物的用途的管制更为严格,在建筑物完成之前,土地分类上已经开始界定住宅用途(参见2011年《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因此对于本条中“住宅”的含义,必须结合相关的行政法规以及第366条自身的立法目的进行判断,下文尝试对城市和农村的主要居住建筑类型进行检索。
1.城市的住宅建筑
(1)完全产权的住宅建筑。在交易实践中,“住宅”在房产交易中常常特指在住宅用地上建造的具有完全产权的建筑,包括“商品房”、“房改房”和“集资房”这三种类型,此外还有1998年商品房政策前的“老公房”。虽然这几种类型的房屋出资方(开发商、国家、集体和企业)不同,但是买受人支付了全部的价款,也没有受到保障房管制规范的限制,可以自由交易和继承,完全满足设立居住权的要求。
(2)商业公寓。商业公寓是指在土地性质为商业用地上建设的住宅用房。它是商业地产中最为广泛的一种形式,但同样具有居住用途,包含了满足家庭居住需求的基本结构,只不过在建筑方面住宅建筑有更严格的要求和标准,比如不得设置阳台,规划间距更狭小,没有小区环境等。从政策上看,商业公寓用途本身就有商用和居住两种可能,所以可以直接在上面设立居住权,而且即便原本是经营用途,也可以经由所有权人的意愿改变为居住用途。
(3)经济适用住房。经济适用住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优惠面向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供应,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2007年《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2条,下文简称《经适房办法》)。从目的上也属于居住用途的建筑,但是从政策目的上看是对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保障,申请购买经济适用住房需要满足严格的条件(《经适房办法》第25条)。在转化为完全的所有权之前,个人购买的经济适用住房不得用于出租经营(《经适房办法》第33条),只有在继承人符合申请条件时才能成为继承财产。显然,依照这一标准,经济适用住房不能自由设立居住权,除非新的权利人同样符合经适房的申请条件。
(4)共有产权房。共有产权房是住房保障体制改革中的新制度,既有的规范文件将之定位为“按份共有”,(35)参见2016 年《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上海管理办法》)第2条;2017 年 8 月的《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北京暂行办法》)第2条规定。但是共有产权房人不能出租、抵押共有产权房,也不享有继承以及优先购买的权利,所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按份共有,(36)关于限制出租的规定参见《上海管理办法》第32条第2款和《北京暂行办法》第23条;关于限制转让,参见《上海管理办法》第32条第1款,《北京暂行办法》第27条;关于继承限制的规定参见《上海管理办法》第39条规定,《北京暂行办法》第26条;关于抵押限制参见《上海管理办法》第32条第3款,《北京暂行办法》第28条;关于优先购买权限制参见《上海管理办法》第35条,《北京暂行办法》第26条。更近似于居住权和所有权人的关系。共有产权房同样具有住房保障目的,在既有的各地区的共有产权房规则中,在受让人满足共有产权房的申请条件的情况下,允许转租和继承房屋。(37)参见《北京暂行办法》第23条,《上海管理办法》第39条规定。因此共有产权房也不能自由设立居住权,除非新的权利人同样符合经适房的申请条件。
2.农村的住宅建筑
在宅基地上建造的房屋,当然也属于可以居住使用的范围,但小产权房则不同。小产权房指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未办理相关证件且不在政府机构对商品房统一管理范围内的房屋。从管制目的上看,小产权房不是非法建筑,建筑目的也属于生活居住用途,但是根据2011年《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第10条规定小产权房不能登记发证,而根据《民法典》第368条第2款规定居住权登记生效,因此自然不能在其上设立居住权。
综上所述,对于第366条的“住宅”的解释必须依据土地用途、建筑物用途、住房保障管制目的多方面的标准进行综合的判断。仅以土地性质属于住宅还是商用为标准显然过于狭窄,“住宅”的范围应该包括城市和农村所有的以居住为用途的建筑,但也应该注意到保障性住房的政策目的,此类建筑只有在权利人同样具有符合保障条件的情况下才能设立居住权。而非居住用途的建筑,如酒店、旅馆、仓库,即便能够满足短期居住需求,但由于建筑用途先天的差异,即便所有权人愿意改变建筑物的经济用途,也不能设定居住权。
(三)第366条的“满足生活居住需要”的界定和家庭状态
与2005年《物权法草案》第180条相比,《民法典》第366条对居住权增加了一个全新的内容,“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从比较法上看,虽然没有完全一致的立法例,但其内涵近似于罗马法传统定义模式中的“满足家庭需求”。
如果说“住房”是针对客体的限制,那么这一要素就属于主体状况的限制。从教义学上看,这一限制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居住权的行使以满足权利人需求为限,因此不能转让不能抵押,在权利人死亡的时候权利结束,这具体体现在第369条和第370条之上;第二,生活居住需求可以满足实在或者潜在的家庭生活需求。“生活居住需求”应该是一个具有弹性的标准,它随着当事人身份的变化而改变,如果权利人处于单身状态,则生活需求范围仅仅是个人需求,如果权利人已经建立了家庭,则居住权的范围必须满足配偶和子女的需求,如果权利人由于年迈或者疾病需要护理,则居住权的范围应该满足保姆或者医护人员的需求,所以对于居住权可能会割裂权利人和近亲属在感情和生活上的联系的担忧是不需要的。需要注意的是,当居住权人先于其家庭成员死亡时,根据第370条的规定居住权消灭,此时不适用第732条的规定,承租人在房屋租赁期限内死亡的,与其生前共同居住的人可以继续租赁该房屋。
(四)居住权与近似权利的区分
在我国居住权立法过程中,一直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居住权和扶养义务中的“居住性权利”以及房屋租赁权的差别。2005年物权法的起草过程中,人大法工委认为既有的扶养制度和租赁合同完全能够替代居住权,最终在第五审的物权法草案中删除了有关居住权的规定。而基于前文对居住权的定义和性质的研究,我们就能够将之与近似权利顺利地区分开来。
第一,与家庭法中的居住性权利区分。在家庭法中存在着两类居住性的权利:一类是离婚配偶居住权,另一类是老年人居住权。离婚配偶居住权源于《婚姻法解释一》第27条的规定:离婚时,一方无房可居属于生活困难,双方可以协商或者法院可以判决有房一方以居住权或者所有权的形式予以帮助。老年人居住权源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3条的规定,“赡养人应当妥善安排老年人的住房,不得强迫老年人迁居条件低劣的房屋”。
虽然现实生活中,《民法典》第十四章规定的居住权多数是发生在亲属关系中,但它不是来源于法定的身份义务,而是由所有权人基于自由意志通过法律行为创设而出。从性质上看,第366条的居住权体现的是人对于住房的直接支配关系;而《婚姻法解释一》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3条的“居住性权利”源于人与人之间的扶养义务,前者是离婚夫妻在婚姻关系结束后的互助义务,是原有的夫妻扶养义务的转化,而后者则是子女对父母赡养义务的体现,其性质属于法定之债,不经过法律行为设立,也不具有物权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第二,房屋租赁权的区别。居住权和房屋租赁一样,都是经过法律行为设立,虽然两者在性质以及众多具体规则中存在差别,(38)比如在期限上居住权是终身,租赁权不能超过20年;在继承方面居住权不能继承,但租赁权可以继承等等。详细论证参见王利明:《论民法典物权编中居住权的若干问题》,《学术月刊》2019年第7期,第97—99页。但根据买卖不破租赁的原则,租赁权人不因为所有权人的变化而影响自己的居住状态,因此在效力上有相似之处。但两者在财产分割功能上存在重大的差别。
居住权是一种分割财产的方式,它使得财产分配更为多元,所有权人可以把居住权移交给一人而所有权移交给另一人;也可以空虚所有权交给他人自己保留居住权;或者自己保留空虚所有权,而居住权留给别人;还可以在所有权人之外,将空虚所有权和居住权交给不同的主体。这种灵活多变的财产分割手段,对于满足身份和财产混合关系有着独特的功能,这是租赁权难以企及的。(39)[法]弗朗索瓦·泰雷、菲利普·森勒尔著,罗结珍译:《法国财产法》(下册),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923页。这也正是学者在论证居住权没有价值的时候,民众和法官们前仆后继绕开物权法定的限制自发创设居住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