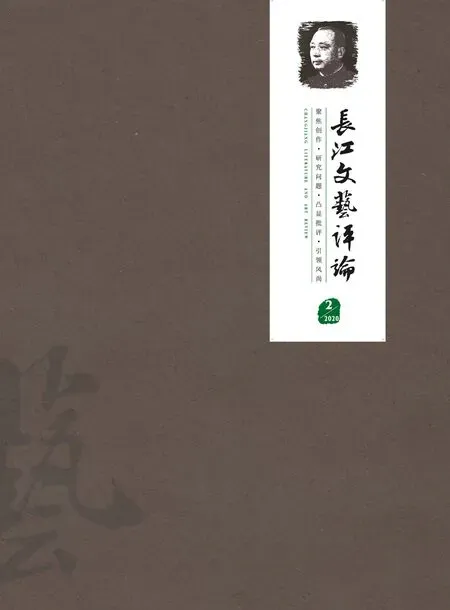当“80后”遭遇自己
——关于《择校记》与《80后,怎么办?》的历史现场
2020-11-17王朝军
◆王朝军
2009年9月,出生于1980年的杨庆祥博士毕业并留校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与身份转换并行的是个人生活处境的改变:他不得不离开学生公寓和它所带来的便利条件的诸多荫庇,开始居无定所的租房生活。这种“被抛弃”的实感和“失败的实感”纠结在一起,引发了他对自己、对与他经历相似的“80后”一代人经验和想象的求证式书写。随笔集《80后,怎么办?》的出版所造成的巨大效应,便是对该书写的价值确认。时隔四年之后,当“80后”的集体创伤尚未完全愈合之际,同是教师身份的王刊,又一次将我们带进了已经并正在发生的历史现场。是的,他是中学教师,他写的是小说,可正因为此,他在基础教育一线的实感虚构、他对“80后”教师基本情感的直面、他对工具理性之于卑微灵魂的碾压,便有了更迫切更坚硬的精神依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长篇小说《择校记》尽管有“回头看”的嫌疑,但它在使社会获得自我意识层面,可能会成为“80后”乃至“90后”“00后”定位自我与世界关系的心灵坐标。那么,就让我们来测量一下它灵魂的色度吧。
我知道,王刊的《择校记》有一个“前文本”,那是关于他的人物的另一种结局。他沿着情节铺设的轨道一路走下去,在即将到站时,他突然发现原先的站台消失了。他左顾右盼,希望找回记忆中的终点。但这是徒劳的,现实已将它拆除,不留丝毫痕迹。他只能变轨,而且是强行变轨,否则他的叙述将无法完成——尽管他的“完成”可能仅仅是新一轮“地震”的开始。
当然,这并不是说王刊为此付出的努力是无效的,至少他在文本之外邂逅了《择校记》这部小说的现实“知音”。这就像一场体外循环,周文从小说中走出来,附体于王刊,他要向叙述者发出指令,并带领他经历和见证“他们”共处的世界,然后悄然折回,留下一句不咸不淡的话:“看,就是这个样子。你和我还不一样!”
哪里一样了?这个“一样”的边界有多大?如果有谁认领了这个“一样”,是不是意味着他也是“他们”的成员?或者说,他已经自愿归顺了?这是《择校记》向它的围观者发出的挑衅,也是决定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收获“精神同盟”的逻辑起点。
是的,“逻辑”这个词一旦闯入人的生活,就变得和生活一样复杂。“那不合逻辑,又全在逻辑里。”前者许是逻辑的本义,我们也可叫它“客观规律”,它是被社会所整理和承认的经验性共识。后者则更像被“逻辑共识”覆盖的角落,在那里起作用的依然是“逻辑”,但却是由“逻辑”一手促成的“反逻辑”。简单点说,就是“逻辑”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失控了。它满以为真理在握,所向披靡,却不曾想正是自己的极端自负,造就了一个个义无反顾的叛逃者。刘赢是,周笑是,阿加也是,他们都是资本逻辑在教育领域疯狂扩张的副产品或异数,是位于教育终端的“废品”。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和他们的同类简直是《择校记》的天然同盟。但王刊的志向显然不止于此,他不想把小说写窄了,他不想让自己的文字变成一声轻易的叹息。他在寻找更可靠更坚实的同盟,在这个巨大的同盟构成的场域里,他、周文、李琦、张章……还有我,还有我们这些“80后”,都遭遇了自己。
在此之前,我曾问王刊是否读过杨庆祥多年以前写的一本叫《80后,怎么办?》的书,王刊很是郑重地否认了。我确信,他和杨庆祥在文本关系上的完全“隔离”,恰恰是“80后”一代人在经验、情感、意识、想象等方面具有内在共性的绝佳证据。请注意,我这里所说的“80后”袭用的是杨庆祥的解释,即含混年龄概念的特指。“含混”指的是出生于1980年左右,“特指”则将这一群体限定在普通工人、农民、小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范围内,他们在人数和体量上都具有普遍代表性,更关键的是,他们具有相似的生活“实感”。而那些出身于优渥家庭的“80后”则属于另一个群体。他们和他们的价值观建基于雄厚的经济基础,几乎无法参与到普通“80后”的经验历程中,也就是说,这里只有“布衣”,没有“富户”。
《80后,怎么办?》和《择校记》能够迅速达成默契的基本前提或先决条件,是二者共同的精神背景。在这个原生的背景下,惊人的一幕出现了:杨庆祥在自身困惑的驱使下,历经艰难思索、反复求证后的所得——“80后”的根本境遇或曰精神黑洞,竟然在《择校记》中得到了高度生活化的还原。
一个是非虚构类的思想随笔,一个是虚构类的长篇小说,它们经由两位“不相干”的写作者,穿过不同的话语系统,居然轻易“会师”。这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在“80后”的旗帜下,同道同类者甚众;说明“我”不是“我”,或者已然是抽象的“我”,是复数的“我们”,是一个容纳了“80后”整体生命意识的历史主体。《择校记》将《80后,怎么办?》带回了“历史现场”。现在,王刊全神贯注地凝视它、翻检它、讲述它,他知道这段历史的隧道幽深、晦暗,前路并不明朗,但他执拗于发出声音,意图让这声音划出一道微弱的自由。
那么,先让我们看看王刊讲述了什么。大地震、奥运火炬传递、次贷危机、GDP高歌猛进、社会办学白热化——它们汇集成历史的时段。形同“孤岛”的K城外国语学校——它规定了空间场所。一群刚刚大学毕业,步入社会的“80后”——他们被指认为教育产业化的先行者和实践者,是小说中的人物主体。
人物有需求:爱情、事业、理想。人物要行动:为爱情、事业、理想而行动。但他们都在“孤岛”。这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人物自认为他们是行动的主体,但他们却注定与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宏阔历史绝缘。如果说他们与世界还有什么无法割舍的东西的话,那只能也必然是钱。在小说中,“钱”被赋予了多种形态:工资、提成、培训费、房子、车、租金等等。当然,还有爱情、友谊、婚姻……几乎所有的价值都可以提炼出商品的本性——交换。掐尖、挖人、择校、补课、办班、劝退,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无一幸免,因交换而生存。交换成为意义的中心,人的选择和行动只不过是围绕中心的机械操作,已经脱去人的成分,滑向了物的怀抱。
对此,文中人物周文曾以“情书”的名义表达过“一己之见”。他向女友如实复述了自己和好友张章的一次争论。
科技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但它首先瓦解了人类的自信,尤其是天体物理学告诉我们宇宙是怎样的,上帝存不存在。所以才有人喊出上帝死了。上帝死了,我们就埋葬了自己的信仰,由一个精神的人堕落到物质的人。我们今天还信仰什么?物质才是我们的宗教。你敢说你一起床想到的不是钱?人一旦把自己只看成一具物质,那就否定了所有的崇高。……你不能否认人还有精神和情感,不能因为它们看不见就当它们不存在。比如文学、史学、哲学,它们作用于我们的精神世界,很少有能看得见的作用,但取掉之后人类还剩下什么?现在,我们正走在这样的路上,你看到在重奖科学家,看到在奖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吗?你让那些人没有尊严地活着,他怎么去筑魂,怎么去当灵魂工程师?这些现象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那就是:资本。但也不全是资本。
从现在的眼光看过去,这段话其实并不全对。但我们应该原谅周文的“过火”。因为这封“情书”写于2007年。2007年已经过去,成为历史经验的一部分。在瞬息万变的中国社会中,个人的部分经验也会“过时”,但这不是问题的核心。核心是周文从个体的角度对资本的狂飙突进表达了他的警觉:资本无处不在,其巨大的惯性最终可能会毁掉一切,包括人类公认的某些根本价值——善良、正直、勇敢、公正……而教育作为这些根本价值的传递中枢,它对资本的态度,直接决定着民族生存延续的方式。周文身在其中,他屡受影响,并深感焦虑。这“影响的焦虑”证明,他还保留着一份清醒,还在奋力挣扎,但是当他抬眼四顾时,看到的却是一片废墟。甚至这封情书的对象——李琦,也离他而去。至于好友张章,则变得比资本还要贪婪。终于,他成为“孤岛”上彻底而唯一的孤独者。
谁都可以察觉,周文的孤独源自资本的覆盖性力量。资本步步为营,攻城略地,很快抢占了社会伦理的高地。在它的傲慢逼视下,人类开始怀疑自我意识的正当性,并为此懊恼、自责,进而主动投诚。它的“雪球”越滚越大,几乎无法遏止。这种造成“后现代危机”的资本强权,在全球化语境下迅速蔓延,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标准和体系。人类待改造、待分工、待检验、待消费和被消费。效用成为衡量人类内在和外在生活的根本尺度。
但这依然不是问题的全部,我注意到,在周文的这段“牢骚”中还留了一个尾巴:“但也不全是资本。”除了资本,还有什么呢?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得更阔远一些,就会发现:这是中国遭遇急剧变化的现代转型期间,尚没有形成理性应对的“权宜”状况。也就是说,当大多数人还生活在古老中国的精神自足中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已率先就范,他们要吃饱穿暖,在经济上富足,就必须遵守“纪律”——服从资本的秩序权威。可是,这个世界变化得实在太快了,商品更新换代一日千里,物质主义的版图不断扩张,并试图僭占人的“灵魂”。而人却在资本制造的幻影中安然沉睡,他们满足于肉体的舒适,他们来不及思考“我是谁”,或者根本就拒绝思考。
而教育这个牵动亿万中国家庭的基础议题,则面临着更为艰难的处境。一方面是物质幻觉在中国人的精神地表上撕开的巨大裂缝;一方面是脱胎于传统中国的成功学见缝插针,重新激发了活力。成功也不再仅仅是“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更是现代社会标榜社会身份的唯一标志。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资本开启了新一轮的“奇迹”创造。
作为这个“奇迹”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周文们站在“80后”群体经验的中心位置,展开了以教育为轴心的对自我精神世界的审视和表达。小说由此获得了它的合法性。与此同时,小说也敞开了它得以延伸的可能性。那块延伸出来的区域无限广大,在那里,教育者正在向受教育者滔滔不绝,并心有戚戚。说到底,他们都是人,他们都要在历史喘息的瞬间恢复人的面目。只是,我怀疑,这人的面目还能否被拼贴得光滑而整全?
很遗憾,迄今为止,我的怀疑都如磐石般坚定,最新的证据是:在何冰慷慨激越的“后浪”声音背后,资本的眼正肆无忌惮地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