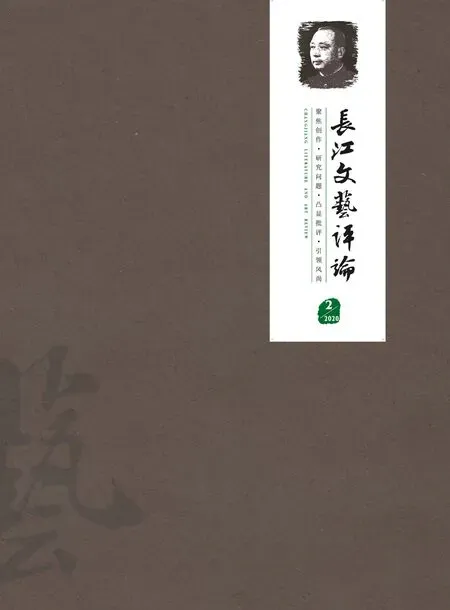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
——理解石一枫小说的一种方式
2020-11-17◆宋嵩
◆宋 嵩
一
2018年,石一枫凭借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以下简称《陈金芳》)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不到半年后,凭借“鲁奖效应”,他早期的几部长篇小说便很快获得了再版的机会,这其中自然包括迄今为止他篇幅最长的作品《红旗下的果儿》(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以下简称《果儿》),而此时距离该书初版(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不知在“版本批评”已成文学研究领域“显学”的当下,“青年作家”(石一枫出生于1979年,刚过四十岁的他仍然符合文坛对“青年作家”概念的界定)作品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是否也会被纳入研究的视域?然而,尽管新版《果儿》并无任何作者“前言”或“后记”证明这是一个“修订版”,笔者仍然在阅读这个2.0版本的《果儿》时发现了它在文字上的若干不同之处。如果说,杨沫对《青春之歌》的历次修改可以被视为建国后作家心态随时代和社会政治变化而作出调整的绝佳标本,那么,从石一枫在十年后对“少作”的修改中,我们或许也可以探得某种解读他思想发展历程的密码。
新旧两版《果儿》在文字上的不同,集中体现在对男主人公陈星父母及家庭关系的叙述上。陈星的父母都在一所区属图书馆工作,“可以说,他们是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坚守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风格的知识分子。当然,这种坚守也是被迫的。他们没机会和上面的人勾结,也没资格受到下面的人同情。他们的清高是真清高,悲愤也是真悲愤。”[1]作为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因为腰肌劳损,陈父在家里只能坐在沙发里“一遍又一遍地复习各个电视台的新闻”。但就是在对待电视新闻的态度上,两个版本的描述大相径庭。新版中的陈父仅仅是这样的:“陈星从未听他对新闻,以及对那些新闻评论员的水平发表过意见,这其实就很不像一个知识分子了。对于新闻与新闻评论,父亲唯一的兴趣就是单方面接收。”[2]但在旧版中,陈父的表现却复杂得多:
看新闻时,父亲大多数时间都是沉默不语,双眼目视前方,那表情既像在看,又像什么都不看。他也几乎从不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那些新闻做出评论。这其实就很不像一个知识分子了。
只是别让他喝酒。一旦父亲的手里握着一瓶“牛栏山”牌二锅头,他的眼睛就睁大了,额头也放出了光芒,有时甚至会不顾劳损的腰肌,一下子从沙发上弹起来。对于正在发生的新闻,他也要做出评论了——只不过,那些话仍然不符合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常常是“什么玩意儿”“这些狗娘养的”“你们丫的骗谁呢”之类的只言片语。那些短句饱含着冷嘲热讽,轻轻地从他的嘴唇里爆出来。[3]
在作者的进一步叙述中,这种行为上的分裂被赋予了复杂的历史原因:陈星的父母当初都是知青,恢复高考之际,分别考入了大学哲学系(具体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文系。“他们当时还是相当风光的,据说那时候,只有成绩最好的学生才能进这两个专业。”而这种“风光”在幼年陈星的印象中,就是父亲“迷恋于在家里高谈阔论”“挥斥方遒”:
在那个年代,父亲一度被视为一个“思想启蒙者”……是几条胡同里知识青年的偶像。他们在一起讨论“人性解放”“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以及弗洛伊德。据说这个习惯还被当地的治安联防部门“注意过”,但这又是多么值得骄傲的待遇啊!那年头,几乎所有诗人都被定性成潜在流氓犯呢![4]
日后发生的事情,所有经历过二十世纪末重大社会变革的人都心知肚明,但唯独只有陈父“想不通”:“当年他认为,庸俗的人一定愚蠢,但现在看来,人家的庸俗反而是因为聪明。那么多他当初看不上的人,或者变成了‘民营企业家’,或者在官场上平步青云,甚至还有成为知名学者的。”而这种“想不通”,亦是前面引文所述“(被迫的)坚守”的根本原因。
但在新版《果儿》中,这些内容都被刻意删去或改写了。而陈星对父母的看法也随之在两个版本中产生了偏差。在旧版中,“刚开始,他认为父亲的内心充满了厌恶——厌恶一切。但厌恶久了,连厌恶的力气也没了,就只剩下了漠然——生活在别处,对什么事情都毫不关心了。他的心态当然也会影响到母亲。”[5]而在新版中,这一段叙述却被改成了:“刚开始,他认为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厌恶——从互相厌恶到厌恶一切。但后来他发现自己错了,父母并不厌恶生活。当父亲因为腰椎间盘突出住院的时候,母亲照顾父亲时的责任心,以及手术后父亲在恢复身体方面表现出的毅力,这一切都不是厌恶生活的人所能具备的。”[6]
对比这两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在旧版中,“厌恶一切”的仅仅是父亲,而由“厌恶”发展而来的“漠然”(具体表现为“生活在别处,对什么事情都毫不关心”)又影响了母亲,因此夫妻二人才会表现得如陈星好友小北所评价的那样:“早就把颓废贯彻到骨子里了”;而在新版中,一开始被陈星认为“从互相厌恶到厌恶一切”的却是父母二人,但他很快便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因为他从母亲对待父亲病情的态度上明确地意识到“父母并不厌恶生活”(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于是,旧版《果儿》中冷酷而生硬的家庭关系(包括夫妻、父子两方面),在新版中却令人惊讶地闪耀出了温情的光芒,尽管这光芒微弱,却有了融化当代都市人心底坚冰的可能。
二
这种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闪现出的温情关系,在石一枫的小说序列中显得格外另类。他笔下的主人公往往幼年丧父,如《地球之眼》中的安小男、《借命而生》中的许文革、《陈金芳》中的陈金芳、《我在路上的时候最爱你》中的莫小萤;此外,《特别能战斗》中雅乔的父亲因为妻子苗秀华的过于强势而毫无存在感,《我在路上的时候最爱你》中的林渺干脆连自己的生父是谁都无法确定。或父母因感情破裂而离异,如《我妹》和《心灵外史》里的杨麦、《节节最爱声光电》里的节节、《借命而生》中“有爹也相当于没爹”[7]的姚斌彬;而在《果儿》中,尽管男女主人公的家庭都是完整的,两代人之间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隔阂:陈星惊叹于张家父女之间居然可以坦率交流,但张红旗却对这种“民主的氛围”感到“越来越不舒服”,而更期待“野马”式的生活。种种“缺失”给小说主人公们的成长过程造成了巨大的心灵伤害,更重要的是,主人公们的家庭破损几乎都能寻找到深刻的时代、社会乃至历史根源:许文革的父亲作为一名“政治积极分子”,因为曾在特殊年代带头批斗老工程师、组织造反战斗队而在运动结束后被清算,最终把自己吊在了车间的钢梁上;姚斌彬的母亲作为“有政治污点的人”的女儿,拒绝组织上安排的婚姻而一气之下嫁给农民,后来因为观念的鸿沟和家庭暴力而离婚;作为土木工程师,安小男的父亲因为不肯与公司领导同流合污而被诬陷,最终“为一个浩浩荡荡的宏大谜团殉葬”[8];杨麦父母之间的关系在作者笔下更是化身为“不同意识形态、‘大我’和‘小我’之间的激烈斗争”而互相敌视:“我父亲自认为是某种光明的、宏大的思想理念的化身,致力于改造我母亲身上那些被他视为自私和无聊的剥削阶级习气。后来政治气氛宽松了,母亲却又摇身一变成为‘自由’和‘人性解放’的代表,对我父亲反戈一击。”[9]孟繁华和张清华在为《身份共同体——70后作家大系》撰写的序言中曾指出:“整体看‘70后’作家的创作,历史全面隐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虽然切合了这代人的身份,但也从另一个方面暴露了他们难以与历史建构关系的真实困境。”[10]而在石一枫的作品中,克服这一困境的一种方式,便是通过复杂家庭关系的溯源,使历史的梦魇融化在主人公们看似令人眼花缭乱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贯穿于一首首时代交响诗始终的“执拗的低音”。
另一方面,这种“缺失”以及随之而来的弥补这一“缺失”的努力,成为石一枫许多作品情节发展的动力。在几部早期作品中,主人公们即使表面上玩世不恭,孤独得“酷”劲十足,但无论是陈星、李红旗还是节节、许洋、赵何,亦或是杨麦、小米、莫小萤,却又无一不在寻找家庭的温情。尽管张红旗早已拿定了主意“要做一个心理独立的人”,认为“心理独立的人应该尽量摆脱对人际关系的依赖”,却只有在身怀了陈星的孩子、并最终在汶川大地震的废墟上与陈星重逢,她才真正“觉得自己是一个女人了”。[11]而在白手起家的孤儿赵何眼中,节节“是他亲手抓到的唯一一个与爱有关的东西”[12],为此他宁可放手卖掉公司,下定决心离婚,打算带着节节出国定居;尽管这段感情因节节的放弃而没有了下文,但这份感情注定将成为赵何灰暗的一生中难得的亮色,而节节最终与母亲和解,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她从这段经历中领悟出了爱与亲情的伟大。即使是在被视为克服了“青春后遗症”(尽管并不彻底)并在石一枫创作道路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陈金芳》中,我们仍然能看出“我”和陈金芳试图“相濡以沫”、互相温暖的痕迹:当“我”未能如愿考进音乐学院而颓丧时,在街上偶遇为买钢琴而与豁子争斗的陈金芳,一场“见义勇为”后,“毫无预料地,陈金芳转过身来,像鸟一样张开双臂。我便如同受到了什么神秘的召唤,一头扎过去和她拥抱。……此时此刻,我却毫无邪念,就连少男下意识的血脉偾张也没有发生。我心里很清楚,这是一个失意人和另一个失意人的拥抱。”[13]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几年后俨然已是“新贵”和“交际花”的陈金芳对失意人“我”的第二次主动拥抱,但此时二人在财富和心理上的巨大落差(集中表现在陈金芳精心策划的那场弦乐四重奏上),却只能促使“我”决绝地推开陈金芳。而那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相濡以沫,在《心灵外史》中“大姨妈”和杨麦的关系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甚至贯穿小说始终,成为支撑叙事的一条龙骨。
有论者指出,“石一枫近期的一系列中长篇小说,很多都同时带有‘成长小说’及‘社会问题小说’的双重特征”,作品中“‘渴望—出发—寻求解答’的基本模式,与‘成长小说’十分相似”,只是“缺少了最后的关键一环,那就是‘获得解答’”[14]。严格意义上说来,所谓“成长小说”,源自德语中Bildungsroman一词,该词由“修养”(Bildung)和“小说”(Roman)两词复合而成;而作为产生于德国18世纪下半叶的一个综合人文概念,“修养”(Bildung)含有人格塑造、成长发展和教育的意思,因此“修养小说”这个德语文学中的特殊体裁又被翻译成“成长小说”或“成长发展小说”。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在《体验与诗》中将“成长发展小说”的特征概括为: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在幸福的朦胧中踏上生活旅途,寻找意气相投的心灵,遇到友谊和爱情,陷入与世间残酷现实的交锋,在获得丰富人生经验后逐渐成熟,找到自我,并坚定自己在这个世上的使命。”[15]而在艾布拉姆斯看来,“这类小说的主题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叙述主人公从童年开始所经历的各种遭遇——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的危机——然后长大成熟,认识到自己在世间的位置和作用。”[16]从“漫游”“寻找”等角度来考察石一枫的这些作品,的确可以看出某些“成长小说”的意味。但问题在于,作为一种伴随着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而出现的文学倾向,“个体”和“自我”在“成长小说”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西方的小说扎根于浪漫主义文化传统中,这就是它的观念性,以自我为中心,表现情感,表现病态的情感,表现人的精神困境,表现人的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以至于是病态的和绝望的”;“如此的文学经验,都是从个人的内心向外发散的文学。一切来自内心的冲突,自我成为写作的中心,始终是一个起源性的中心,本质上还是浪漫主义文化”。[17]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通常被认为是最典型的Bildungsroman,译者杨武能先生将全书主题归纳为“逃避庸俗”:“逃避庸俗,摆脱自己商人家庭的无聊市民生活,既是威廉登上舞台、长期在外浪荡漂泊的初衷,也是他进入贵族圈子、参加秘密会社的动机。逃避庸俗,是刚脱离了蒙昧状态的新人进一步自我完善的要求。逃避庸俗的结果,使威廉认识了社会、人生,经受了磨炼,完成了‘学业’。”[18]此处的“初衷”和“刚脱离了蒙昧状态”,都说明成长小说主人公在开始“漫游”的时候心中并不是一片空白,他似有所知,但并不成形,因此需要通过“漫游”“学习”的过程来加以确证和考验。《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有一段话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同演员梅利纳交谈之后,威廉发出了如下感慨:
你缺少一个融会贯通的整体感觉,这种感觉,只能靠心智去发现、理解和求得。你感觉不到,在人的内心,活跃着一颗向善的星火;它即使得不着养料,未受到激发,深深地埋藏在了日常琐屑需要和漫不经心的灰烬下面,却久久不会、甚至永远不会被窒息。你感觉不到内心存在任何能吹燃这星火的力量;你心胸狭隘,没有滋养这复燃星火的丰富蕴藏。[19]
也就是说,“成长小说”的主人公在漫游中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将原本已经存在于内心的“向善的星火”吹燃,这与“寻求解答—获得解答”的模式显然有所区别,反倒有了禅宗“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意味。我们还可以参考《奥德赛》中特勒马科斯(Telemachus)寻父的情节来理解“求证”:特勒马科斯是大英雄奥德修斯(Odysseus)与珀涅罗珀(Penelope)所生的儿子。父亲在外征战多年未归,儿子长大后在雅典娜的陪伴和指点下踏上了寻父之路,并最终找到了父亲,一起回乡;儿子亦在此过程中成长为像父亲一样的英雄。父子二人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确凿无疑的,但各地的王子都来向珀涅罗珀求婚并挥霍奥德修斯的财富、珀涅罗珀面临若不改嫁母子二人的生存便难以为继的危机时,原先的父子关系就有可能动摇。特勒马科斯的寻父之举,即是从个体出发、主动复燃父子关系“星火”的努力。
在解读石一枫小说的时候,以上关于“成长小说”概念的分析,或许能给予我们启发:“渴望—出发—寻求解答—(不一定)获得解答”的模式,对于他的小说来说并不完全适用,倒不如说他笔下的许多人物是在“寻求确证”。这样一来,便很容易理解石一枫在小说中屡屡用来形容人物性格的那个词:“轴”。而对于新版《果儿》中那些修改之处,我们便也有了理解的可能——生活的本来面目应该是在平淡中充满温情的,那种激昂的“风光”并非常态;既然温情日复一日地衰变、耗散了,那么就要用时间、甚至用青春去把它寻找回来。
三
在讨论“轴”这个词之前,我们还要对比两处异文,它们来自《陈金芳》中“我”家邻居老太太对拒绝回湖南老家、坚决要求留在北京的陈金芳的评价。小说最早在《十月》刊发时,这句话写作“没见过那么狠的孩子”,此后的多个选本(如山东文艺出版社的《合奏》、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2014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等)均是如此;唯独2014年第7期的《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在转载时将这句话改成了“没见过那么犟的孩子”。“狠”“犟”二字,字形字音均差别很大,应该不是鲁鱼帝虎、手民误植的错误,不知选刊编辑此处改动用意何在?
石一枫小说中至少还有一处用“狠”来评价人的地方,那就是在《地球之眼》中,庄博益说李牧光“从来就不是一个心理强悍的狠角色”。而“犟”这个词在《借命而生》中用来形容姚斌彬和他的母亲,其他作品中,凡是类似的意思基本上都用“轴”来代替。“轴”是典型的北方方言,形容一个人爱钻牛角尖,说话或做事情爱较真儿、不变通,而且不听人劝。从庄博益的角度看,一个角色似乎只有“心理强悍”才配得上“狠”这个评价,而这显然不是“轴”或“犟”必须要具备的。换句话说,死缠烂打强词夺理可以被视为“轴”或“犟”,但肯定不是“狠”。结合《陈金芳》中老太太的语境,把“狠”改成“犟”可谓败笔,因为这样一来不但抹煞了陈金芳“心理强悍”的特征,还使老太太话中那种感叹、甚至不无赞叹的意味流失殆尽。
在石一枫小说中被直接赋予“轴”这一特征的,有颜小莉(《营救麦克黄》中黄蔚妮斥责她“你这人也太轴了”)、苗秀华(《特别能战斗》中女儿雅乔评价说“她性子轴”)、安小男(《地球之眼》中“我”评价他的性格“一根筋、特别轴”)等等,而他在近年来的每一部作品中都会设置一个或几个特别“轴”的人物。这些人物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秉持着某种信念,并在生活中不惜代价地为这些信念求证。
颜小莉的“轴”最简单,基于最朴素的“人命大于天”的观念,同时她早就清醒地认识到黄蔚妮与自己之间所谓的“友谊”是虚假的,本质上是“互相利用”,因此在试图劝说黄蔚妮而遭到失败以后,她能够义无反顾地和于刚联手“执行那个计划”。安小男的“轴”,源于他坚信人和社会应该有“道德”,因此他要通过各种方式来寻求解决中国人道德缺失的问题、恢复社会道德体系的办法,包括学历史、对雇用自己替考的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直至用高科技监控和“黑客”手段来向不道德的人实施惩罚与报复,像“蝼蚁”那样“钻过现实厚重的铠甲缝隙,在最嫩的肉上狠狠地咬上一口”。苗秀华的“轴”则与“特别能战斗”互为因果,有其深刻复杂的历史原因:用女儿雅乔的话来说,她“年轻的时候脾气也好着呢,没说话先脸红,根本就不是能跟人家吵架的人”,但是为了在特殊年代里不被人欺负,只能以“战斗”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而这种方式的有效又反过来加剧了她的“轴”,“内化成了苗秀华的本质”。在《借命而生》中,无论是警察杜湘东、老徐,还是犯人姚斌彬、许文革,都属于理想主义者,希望能在有限的生命中实现自我价值,“在新的世道里,人应该有种新的活法,活得和以前不一样”,只不过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当怀揣刑警梦却一辈子只能当狱警的杜湘东认识到“许文革、老徐,他们都是扑在尘土里也身上带光的人”,为“他依稀也想过那样去活,而许文革却替死去的姚斌彬活了出来”而感到痛心和惭愧时,心底那种“星火”也便复燃了,促使他做出了一生中最光辉灿烂的举动——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焰火中,救出了试图自杀的许文革。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目前能够见到的关于石一枫作品的评论中,对于苗秀华这个人物似乎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肯定者认为,“石一枫的思想力量表现在不服输、不认输。他要挑战时代的主流意识,那就是安小男对李牧光的胜利,苗秀华对单位、对物业的胜利,尽管这些胜利道德上可疑,有精神瑕疵,但迈出了积极抗争的一步。抗争而不是认同,是我们时代最稀缺也最宝贵的品质。这个小说的能动性、创造性溢于字里行间,在弥漫当下小说的悲观气息之外,平添了一种昂扬气息。”[20]“苗秀华精力充沛、疾恶如仇,……《特别能战斗》让我们看到,这世界上还有一种逻辑——面对不公,积极发声;面对问题,迎难而上。”[21]而否定者则大多将批评的矛头指向她的“文革”思维。其实,将这两方面的观点推而广之,石一枫笔下的很多人物都会把读者推向两难的境地,比如说上述第一段引文提到的安小男。再比如说陈金芳这个人物,通常我们会认为她的悲剧是由“虚荣”导致的,是咎由自取;但是,她所有的行为都是建基于“只是想活得有点儿人样”这一信念之上的,我们能否轻易断定杜湘东、许文革等人“实现个人价值”的信念就一定比这个信念高?同样,对于因涉及宗教和信仰问题而格外复杂的《心灵外史》,在几乎所有评论者都认为小说反映的是中国人“信仰缺失”的普遍状况,并根据大姨妈“我的脑子是满的,但心是空的,我必须得相信什么东西才能把心填满”和“我觉得心一空就会疼,就会孤单和害怕,……信什么都无所谓了,关键得是先找个东西信了,别让心一直空着”的自述而将其冠以“盲信者”之名加以否定时,是否忽略了乡村牧师刘有光所说的“主都有安排”和“可我们也不能不信主”本身就是一种信念,而“启蒙思想”与“怀疑主义”在同信仰问题直接交锋的时候有可能并不在同一频道上而陷入“鸡同鸭讲”的尴尬境地?因为在西班牙作家、哲学家乌纳穆诺看来,信仰意味着“我愿意相信”而非“我相信”(《生命的悲剧意识》),而大姨妈的信念恰恰就是这种“我愿意相信”[22]。
“男人战斗,然后失败,但他们所为之战斗的东西,却会在时间的某个角落里恍然再现。”
“这座城里,我看到无数豪杰归于落寞,也看到无数作女变成怨妇。我看到美梦惊醒,也看到青春老去。人们焕发出来的能量无穷无尽,在半空中盘旋,合奏成周而复始的乐章。”
无论是《借命而生》还是《陈金芳》,石一枫都选择以抒情的方式来结尾。“周而复始的乐章”“恍然再现”,仿佛在向读者昭示一种五味杂陈的循环论,就好像他在《恋恋北京》中曾经提到的一首小提琴曲《无穷动》[23]那样,可以永无休止地演奏下去;而Perpetuum Mobile这个曲名,原本就是“永动机”的意思。任何一个具有初中物理知识的人都清楚,“永动机”并不存在,因为它违反了热力学第一、第二定律。几个世纪以来,尽管无数人遭到了失败,但始终有人秉持着永动机的信念,试图去挑战看上去坚不可摧的热力学定律。王小波曾借热力学第二定律打比方,说爬山、写作这些“趋害避利”的行为都是“反熵”的;而石一枫笔下的安小男、颜小莉、杜湘东们,同样也在做着“反熵”的事情,仅仅是为了不让自己心中的“星火”熄灭。
那周而复始的乐章为他们而鸣。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
注释:
[1]石一枫:《红旗下的果儿》,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页;亦见于石一枫:《红旗下的果儿》,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97页。
[2]石一枫:《红旗下的果儿》,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98页。
[3][4][5]石一枫:《红旗下的果儿》,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页,63页,64页。
[6]石一枫:《红旗下的果儿》,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99页。
[7]石一枫:《借命而生》,《十月》,2017年第6期。
[8]石一枫:《地球之眼》,《十月》,2015年第3期。
[9]石一枫:《心灵外史》,《收获》,2017年第3期。
[10]孟繁华、张清华:《“70后”的身份之谜与文学处境》,《文艺报》,2014年6月20日第2版。
[11]石一枫:《红旗下的果儿》,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558页。
[12]石一枫:《节节最爱声光电》,《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11年第2期。
[13]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十月》,2014年第3期。
[14]李壮:《如此完好的撕裂——谈石一枫近年来的小说创作》,《新文学评论》,2018年第3期。
[15]谷裕:《德语修养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29页。
[16]【美】M.H.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词典》(第 7版),吴松江等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7页。
[17]陈晓明:《世界性、浪漫主义与中国小说的道路》,《文艺争鸣》,2010年第12期。
[18]杨武能:《逃避庸俗——代译序》,【德】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杨武能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19]【德】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杨武能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20]师力斌:《思想力和小说的可能性——从石一枫、蒋峰看70后、80后小说》,《创作与评论》,2016年第22期。
[21]李婧婧:《超越“人与城”——石一枫论》,《名作欣赏》,2018年第3期。
[22]相关论述参见宋嵩:《仿佛若有光——读石一枫的长篇小说〈心灵外史〉》,《芒种》,2018年第3期。
[23]“无穷动”是18、19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一种器乐体裁,特点是乐曲自始至终保持一种重复的音型,速度极快,给人的感觉是音乐、时间永远在流动,人和万物也都随着时间前进而成长、变化着。在德语中,“无穷动”(Perpetuum Mobil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永动机”,因此也有人译成“常动曲”。许多作曲家都写过“无穷动”,其中以意大利作曲家帕格尼尼和奥地利作曲家约翰·施特劳斯所作最为著名。《恋恋北京》中提到的《无穷动》应该就是帕格尼尼的作品(Niccolò Paganini:Moto Perpetuo,Op.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