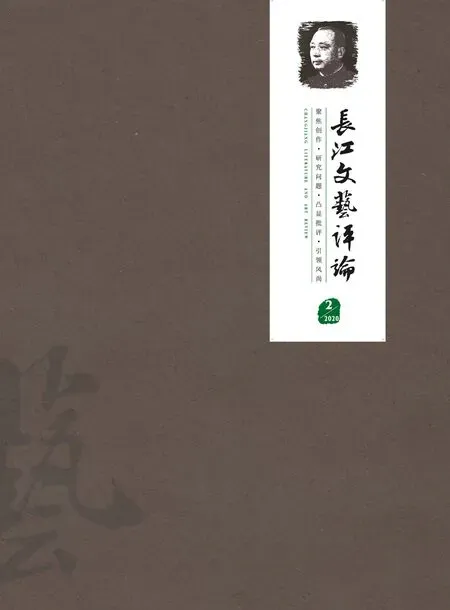中国古代的江南与江南文学
2020-11-17熊海英
◆熊海英
唐朝开国之初,魏徵编撰史书,对汉魏六朝文学概括评论道:“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此论把文学艺术风貌特征与南北作家所处的地理环境很确定地联系在一起。所谓关西大汉、燕赵悲歌、骏马秋风、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自然是北方;提到江南,就想到杏花春雨、小桥流水、吴娃越女、低吟浅唱。景也好,人也好,文也好,或阳刚重拙,或温柔清丽,气质似乎是一致的。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大自然的气候温润或苦寒,山水壮观或优美是天地注定,而人群形体之长短、情性之刚柔、才思之巧拙,似乎也随自然环境有所区分。基于这种观察,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法国的孟德斯鸠、德国的黑格尔和拉采尔都认为人类的身心特征、民族特性、社会组织、文化发展等精神文明和人文现象受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直接或间接支配。法国的丹纳在其艺术史及人类文化学的巨著《艺术哲学》中,进一步强调种族、环境、时代为制约精神文化的三要素,其中种族是“内部动力”,环境是“外部压力”,时代为“后天动力”,他的理论在文学艺术领域影响很大。或许接受了这类学说的影响,晚清刘师培撰著《南北文学不同论》,云“声律之始,本乎声音。古代音分南北。北音谓之雅言,南音谓之楚声。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他将南北之分作为先在框架,依此展开对中国文学史的叙述,尽管不无方凿圆枘之弊,又将文质对立而重质轻文,但刘师培的论述仍然折射了中国古典文学因南北地域而不同的风貌特色。
一
自古中国以长江为天堑,界分南北。若说何处是江南,从地理范围来看,具体所指却随时代有所移易,并不固定。最早提到“江南”的是战国时楚国的屈原。楚顷襄王三年(公元前296年),怀王作为人质客死于秦,屈原作歌招其魂魄,末句云“魂兮归来哀江南!”其时楚国幅员辽阔,包涵今天的两湖地区以及安徽、江西的部分,郢都则在荆州一带。南朝梁时,庾信出使西魏被羁留,后在北周“虽位望显通,常作乡关之思,暮年乃作《哀江南赋》以致其意”。此赋感怀身世与国史,痛述个人遭遇与民族灾难,精神与楚辞《招魂》相通;而庾信取其末句“哀江南”为题,当亦为梁武帝定都建业,元帝定都江陵,二者都属于战国荆楚之地。事实上,西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八王之乱”后,司马睿率中原士族世家南渡,团结江东豪强,定都建康(今南京),凭着长江天险建立偏安政权;此后南朝各代基本上继承东晋领土,在江南先后兴起了建康、江陵、扬州等城市,宋、齐、梁、陈繁华竞逐,又悲恨相续。
隋唐统一天下,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太宗分天下为十道,其中江南道所辖包括今天两湖地区、江浙和江西的部分,东到福建,南至广东和贵州,以越州(今绍兴)为道治。北宋的江南东路和西路则辖治江苏、安徽和江西大部;今天的浙江主要归于两浙路;先秦的荆楚之地主要属于荆湖南路和北路,在唐宋两代都不甚发达,然而春秋战国时期尚且断发文身的吴越之地,历经东吴、东晋和南朝,到北宋时,杭州已有“参差十万人家”。两宋之际,中原士大夫再一次“衣冠南渡”,高宗赵构以杭州为都城,南宋立国153年,艺文绍兴,经济繁荣,江浙一带尤为全国中心。蒙元亡宋以后,在南宋国土设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狭义的江南则单指江浙行省所辖区域,与明清时期太湖平原的“苏、松、杭、常、嘉、湖、太”六府一州地域大致相当。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从先秦到明清,“江南”指称的自然地理范围和行政区域都呈现从西到东、从大到小、由泛指到特指的变化。
与地理范围和行政区域的变化相应,江南人的构成也在变化。“不服周”“三户亡秦”的是南蛮楚人,睚眦必报的伍子胥、卧薪尝胆的勾践则是吴越东夷,江南原住民的情性朴蛮剽悍。此后历史上先后发生三次从北向南的人口大迁移,到宋代时南方人口已经占全国一半以上,并一直保持、延续到明清时代。每一次人口迁移同时也是经济、文化向南方转移、传播的过程,尤以西晋“八王之乱”和北宋“靖康之变”后的两次“衣冠南渡”为最。贵族和士大夫世家把中原文献及学术传至南国,以中原文明的醇厚来改造南方文化;移民作家带来中原文化创造的精神财富,如此一来,江南文人群体既浸馈于中原文化的营养,又与南方的地域文化、风土习俗、自然山川相交融,遂得以形成有南国风味的学术和文学风貌。纵观历史,南宋正是人口、经济、文化、文学全局的重心发生转移的关捩点。蒙元代宋后,由于对江南实行不流血征服和粗疏管理,江南社会的经济文化繁荣得以持续,并在明清时期再次发展。
无论江南地域范围大或者小了,人口少或者多了,江南自有一种STYLE不变,总令别离者眷恋难舍,在此境者沉醉而感伤,游子过客念念不忘。屈原在《招魂》中“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招怀王魂魄。楚国之美在何处?是宫室豪华、酒肴丰盛、歌舞曼妙,是“美人既醉,朱颜酡些。嬉光眇视,目曾波些”,充满诱惑;“川谷径复,流潺湲些。光风转蕙,氾崇兰些”,令人心醉。正是这“亵慢淫荒”之词铺陈形容的江南乐土,能令亡魂不忘归途。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上巳,贵族们在会稽山阴兰亭修禊事,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之间,清流激湍,“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在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时,感悟“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人生又“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深为可痛,更可悲者“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兰亭集诗书高雅、名士风流、景物清美、感慨深沉,这一场“醉”堪为千古典范。庾信羁留于北朝二十余年,然而记忆中江南故国的种种仍如此鲜明:“于时朝野欢娱,池台钟鼓。里为冠盖,门成邹鲁。连茂苑于海陵,跨横塘于江浦。东门则鞭石成桥,南极则铸铜为柱。橘则园植万株,竹则家封千户。西赆浮玉,南琛没羽。吴歈越吟,荆艳楚舞。”五十年间江表无事,人民安居乐业,“天子方删诗书,定礼乐;设重云之讲,开士林之学”,梁武帝乃延揽学士,讲求诗书礼乐,修明佛法。字里行间,分明读出庾信对江南富足与文明的不胜恋慕。唐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随后又任苏州刺史(公元825年)。十二年后,他在洛阳写下《忆江南》词三首,开头便道“江南好”。离开了江南的白居易记得苏杭的风物与美人:何日再来山寺寻桂、钱塘观潮,品美酒而重逢善舞的吴娃呢?漂泊在江南的韦庄则是另一种惆怅,“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甘愿老死于温柔乡,却不得不告别。也许游子别后,见水是眼波横,见山如眉峰聚,将一遍一遍地抒写思念,低吟肠断吧。
想到江南,你想到什么?是江南山水与女子的美丽,是纵情任性的快乐,是优裕清雅的生活,这大概就是江南不变的文化基因。而塑造它、描画它、传播它的是诗词歌赋,是江南的文人和文学。
二
中国最早的诗人是江南的屈原,以他和宋玉作为主体的《楚辞》奠定了古典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读着《天问》《离骚》《九歌》,就陷入玄远惝恍的传说、迷离奇丽的天地。那含睇而窈窕的弃妇与山鬼,芬芳凛冽的杜若与江离,绵渺曲折的愁怨,九死未悔的追求,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风”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和面貌截然不同。《招魂》末句云“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与《湘夫人》起头的“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写出缠绵依恋、千回百转的微情,写出长江与洞庭湖的水色波光、碧树清风相映相交融,片段文字堪为中国古典诗词伤春悲秋的滥觞。
晋人渡江南来,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南朝承续东晋,诗歌写得声色大开,情灵摇荡。齐朝小谢清发,“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诗句秀逸一如江南山水。梁、陈帝王与贵族生活奢华,以诗娱情,至“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其浮艳轻靡、轶荡绮丽已极。宫体诗一味追求感官之美,都说是亡国之音;其实南朝诗人精研辞藻、对偶与声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实为唐诗繁荣奠定了基础。
词为有宋“一代之文学”,唐圭璋《两宋词人占籍考》考得词人占籍也以浙赣闽江南三地为先。北宋柳永曾作《望海潮》,描写杭州风光美丽、富庶繁华,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钓叟莲娃“羌管弄晴,菱歌泛夜”,长官“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生活十分快乐闲适,竟然激起金主完颜亮“投鞭渡江”之志。柳永因为年轻时行为放浪,作词多涉情爱,格伤轻艳,往往受到士大夫讥评,禁不住“流俗人尤喜道之”,流传极广;词体终究也以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低吟浅唱“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柳词为正宗。说到底,还是因为其微词婉转、深情绵邈的特性,倚声而歌的形式,与南国氛围天然合拍,以故素有南方文体之称。而多情与美丽、婉约而缠绵庶几也是江南文学的共性吧。
江南的文人多为在野、退隐之士,或是漂泊江湖的布衣,远离庙堂是他们的共同处境。屈原放逐,行吟泽畔。他不愿“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宁赴湘流。渔父却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屈原与渔父的对答,正是后世江南文士人生选择的象征和寓言。
史上大一统的盛世,国都多在北方。从地理位置来讲,江南地区离政治权力中心很远,而且南朝以后到南宋之前,江南经济又不甚发达。沉滞江南之人进不得名利场,退亦不得安闲享乐,往往吟出失意的诗篇。就如李白酒隐安陆,蹉跎十年;孟浩然幽居鹿门,难获济助。刘禹锡弃置巴山楚水,白居易与琵琶女共伤沦落。他们退避在野,固然是被抛弃于权力场域的边缘,但从另一面看,精神得以脱弃名缰利锁的羁縻,不也获得了自由安顿人生的可能?尤其南宋后期到元代,因为科举竞争激烈和易代后入仕制度的变化,汉族士人失去了向社会上层攀升的路径,此前独享统治权力与社会荣耀的“知识精英”多遭摈斥于统治阶层以外,成为布衣平民,只有以文学艺术创作为精神支撑和个人价值的依凭。南宋后期出现了不第举子和低阶官吏为主的诗人群体,他们怀携诗集,游谒江湖。入元后江南更是诗社林立,彼此声气相通。元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在浦阳举行的月泉吟社征诗,吸引了东西两浙二千七百余人参加,声势耸动江南。至正初年,杨维桢在杭州与友人唱和《西湖竹枝歌》,“好事者流布南北”,属和者非仅名人韵士,也有闺阁女子以及僧道和异族诗人,掀起一股社会风潮。元末昆山富豪顾瑛在自家园林举行雅集182次,活动时间长达33年,参与者至少有222人,除了本地文人,也有流寓和游宦经过吴中者,几乎囊括了元代后期长于书法、绘画与戏曲的名士。杨镰称其“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主持玉山雅集,成为玉山雅集的东道主、首席诗人。”随着这一次次规模前无古人的诗歌唱和与雅集,那些脱离政治、献身文艺的诗人,他们致力于文学的态度和生活方式也逐渐在江南社会被接受、获得尊重。
另一方面,宋元以来仕宦受阻的江南士人逐渐转向重视家族在地方的经营。他们以学术和文艺等为媒介,通过参与地方政教文化事务,群体酬唱交游,编织社会人际网络,以获得和发挥社会影响力。在交游酬唱过程中,文艺趣味和主张一致者逐渐聚合、切磋研炼,文学创作和理论呈现地方性特征,甚至形成体派。如明代湖北的“公安三袁”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又推重民歌小说,是平民文学的先声。其后钟惺、谭元春二人以微官寒士倡导“幽深孤峭”诗风,“竟陵派”崛起于江汉平原,成为反对诗文拟古潮流的重要力量。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在词学“中兴”的清代,江南各地词派此伏彼起,如云间派陈子龙、阳羡派陈维崧、浙西派朱彝尊、常州派张惠言、临桂派王鹏运等等。这些文学流派都带着浓厚的地方色彩,但其创作主张往往能将影响扩展到全国,引领文学潮流,与中央文坛分庭抗礼。
《文心雕龙·体性篇》说作家的创作风貌受先天的禀性和后天的陶冶影响。“才”和“气”是先天因素,“学”与“习”是后天因素。就地域和群体文学风貌而言,影响因素大概亦有先天与后天之分。盖因南方人与北方人之才华各有庸俊,气质亦分刚柔;所谓“学”,应是江南偏于缘情绮靡的诗词文体传统。所谓“习”,就是社会文化与习俗风尚。从宏观角度来看,从南宋历元到明清,由于商品经济和市镇不断发展,教育普及,学术和文艺持续繁荣,江南地区开启了中国走向近代之滥觞。从某种角度来讲,前文所讨论的宋元以后江南文学的纯文学化和地方化特征、平民化与通俗化趋势正体现了江南文化先进的一面。
三
几千年来,“江南”从地理地域概念,已经逐渐演化为包含地理、经济、文化等多种内涵的专指性概念,与经济发达、文化昌盛以及相对统一的民众心态相联系。江南从“江南之江南”的地域性概念,而成为“全国之江南”的政治、经济、文化性概念的关捩点在南宋,是伴随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文化和文学重心南移的现象发生的。元、明、清三朝大一统国家均以北京为国都,长江以南地区虽然只是国土的一部分,但江南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地位却已无法改变。
观察历史容易得到一种印象,南方的国家往往显得不够长久和强大,终究以臣服的姿态结局。无论是楚国、吴国和越国、东晋、南朝和五代时偏安于江南的短命王朝,以及南宋,莫不如此。南方国家似乎总是处于偏位,而又极力支撑,令人慨叹惋惜。这似乎又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史的暗喻:京城作为政治、文化中心,中央文坛和馆阁学士群体举足轻重,理所当然最受关注。南方文学的风貌是美丽、任情而文雅的,南方文人多退隐在民间和地方社会,隐然有一种与中原正统、京城和庙堂相抗的意味,情势似乎又落在下风。然而历史学家刘子健断言:“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以江浙一带为重心的模式”,从宋元到明清的历史,唯有以江南社会发展的链条可以衔接;江南文化与文学的内涵与层次本来极为丰富,其间更蕴涵从近世到近代文学的变化,理应得到足够的重视,以与其地位相匹配。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形成,文学是南北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工具、文化融合的媒介和中原传统文化涵养化育的结果。盛唐的山水田园诗清新美丽、边塞诗慷慨磊落,风貌截然不同,追究作者的出身与行迹,却并没有南北的截然分别。词虽是所谓南方文体,风格却有婉约也有豪放。北宋苏轼的豪放词风南渡以后才得以张大发扬,辛弃疾是出身北方的英雄,其词鞺鞳铿鍧,有横绝六合的气魄,却亦能作“试把花卜归期,才簪又重数”的秾纤绵密之语。正是因为南北交融、刚柔相济,词体才能开拓境界、深化内蕴,成为有宋“一代之文学”。如此谈到盛世文学或者文学之盛,若问如何能盛?即如魏徵所言:南北各有长短,若能“各去所短,合其所长”,刚健风骨与精妙技巧,充实内容与情辞之美结合,方能文质彬彬,尽善尽美。就江南文学而言,它自有独立姿态与风貌,但江南亦是全国之江南,文学亦须积极吸纳与融汇,方能有向上和持续发展的空间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