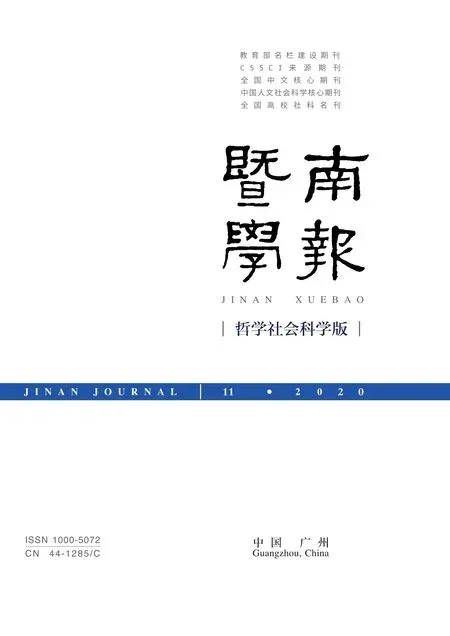国籍观念在晚清中国的生发与实践
2020-11-17邱志红
邱志红
国籍观念与制度系源自西方社会,其相关概念于19世纪随着西力东渐而出现于晚清社会的生活中,并通过1909年清政府制定颁行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近代意义的国籍法——《大清国籍条例》及其施行细则,奠定了父系血统国籍观念的法理基础,其影响所及,自民国初年以来的两部国籍法(1)北京政府1912年11月18日公布、1914年11月30日修订颁布的《修正国籍法》,南京国民政府1929年2月5日颁布的《国籍法》。,及至当代的国籍政策都有程度不同的继承和表现。关于晚清“国籍”问题,学界从华侨史、外交史、法制史等角度已有相当的研究,主要基于晚清国籍问题的复杂背景,考察清政府对海外华侨政策的历史演变、处理华侨国籍问题的法制化进程,以及国籍身份问题引发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等。(2)代表性研究如[澳大利亚]颜清湟著,粟明鲜、贺跃夫译:《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晚清时期中国对海外华人的保护(1851—1911)》,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年版;袁丁:《晚清侨务与中外交涉》,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许小青:《晚清国人的民族国家认同及其困境——以国籍问题为中心》,《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许小青:《清季国籍问题与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齐凯君、权赫秀:《近代中国政府处理华侨国籍问题的法制化进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缪昌武、陆勇:《〈大清国籍条例〉与近代“中国”观念的重塑》,《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阎立:《〈大清国籍条例〉制定过程之考证》,《史林》2013年第1期。近年来李章鹏、江世昕等学者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材料、新观点,尤其值得关注。(3)李章鹏:《〈大清国籍条例〉及其施行细则制定过程新探》,《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8年第4期;《中荷设领谈判与华侨国籍问题交涉(1907—1911)》,《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4期;《双重国籍还是单一国籍政策?——清末国籍政策析论及其现实启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江世昕:《近代中国国籍观念的演变》,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但已有研究对国籍观念在晚清中国的产生、发展过程还缺乏具体、深入的阐释,特别是“国籍”相关概念在中国传统法律中的思想因子与呈现方式,国人对这一概念及制度早期理解与运用的时代特点,及其对晚清中国政治社会的影响,均还有进一步探究的空间。本文尝试从概念史的角度考察国籍观念在晚清的形成与实践,以期丰富对中国近代国家转型过程中国籍问题引发的复杂历史细节的认识与思考。
一、外与内:国籍观念的思想因子
国籍是伴随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从国际政治体系中演变而来的新的法律概念。现代英语世界中Nationality和 Citizenship均表示有“国籍”的意涵,用以指涉一个人在法律上的国家成员身份,二者经常交替使用。研究显示,Nationality 来源于法语nationalité,最早出现在1835年的《法兰西学院法语辞典(法语释义辞典)》(Dictionnairedel’AcadémieFrançaise)中。一般情况下Citizenship经常是在国内法层面上强调“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更多地被译作“公民权”或“公民身份”,而Nationality则是在国际法的层面被使用,强调国家与其管辖下包括本国人、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在内的“国民”之间的法律联系。(4)参见Maximilian Koessler, “Subject, Citizen, National, and Permanent Allegiance”, Yale Law Journal, Vol.56, No.1,1946; [奥]凯尔森著,沈宗灵译:《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40—349页。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国籍,既是具有领土、主权、政府的现代民族国家国民身份的主要标志,也是国民与国家之间权利与义务的主要依据,是连接国民与国家身份关系的重要的法律纽带。换言之,国籍的本质是区别不同国家国民的身份问题,即其是“哪国人”的问题。
国籍观念脱胎于现代民族主权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在数千年以帝制为核心的王朝国家统治之下,无法衍生出指涉个人与王朝政府关系的“国籍”及其相关概念,完善的“户籍”制度则是连接二者关系的重要纽带,是历代统治者保障兵源、征收赋税、稳定社会秩序的工具,即所谓“稽其众寡,辨其老幼,以令贡赋,以起职役”。(5)《宪政编查馆奏遵旨议覆国籍条例颁行折并清单》,《清末民初宪政史料辑刊》(第2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377页。
但在中国法律传统中,从唐律开始,便存在着“化外人”“化内人”的概念,前者且为后世所沿用,并且生发出“外夷”“外国人”等词汇。兹将《唐律》《大明律》《大清律例》中相关内容迻录如下:
1.《唐律疏议》卷6《名例》“化外人相犯”条:
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
[疏]议曰:“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其有同类自相犯者,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类相犯者,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6)长孙无忌等著,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页。
2.《大明律》卷1《名例律》“化外人有犯”条:
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
《大明律集解附例》注曰:
化外人,即外夷来降之人,及收捕夷寇散处各地方者皆是。言此等人,原虽非我族类,归附即是王民;如犯轻重罪名,释问明白,并依常例拟断,示王者无外也。(7)怀效锋点校:《大明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明律集解附例》,修订法律馆光绪式申重刊万历三十八年本,第2册,第85页。
3.《大清律例》卷1《名例律》“化外人有犯”条:
凡化外(来降)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隶理藩院者,仍照原定蒙古例。
4.《大清律例》卷15《户律·市尘》“把持行市”条“例”:
凡外国人朝贡到京,会同馆开市五日,各铺行人等将不系应禁之物入馆,两平交易。
5.《大清律例》卷19《兵律·军政》“漏泄军情大事”条“例”:
在京在外军民人等,与朝贡外国人私通往来,投托拨置害人,因而透漏事情者,俱发近边充军。通事并伴送人,系官,革职。(8)张荣铮、刘勇强、金懋初点校:《大清律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276、305页。
就法史学研究而言,究竟上述律例中的“化外人”“外国人”概念是否与近代国际法意义上的“国籍”概念相一致,值得考察。有论者从近代法学和国家理论出发,认为唐律中已经孕育有中国传统的国籍观念,唐律中的化外人便是外国人,“同类自相犯者”之“同类”即为同一国籍之外国人,“异类相犯者”之“异类”则为不同国籍之外国人;(9)钱大群、夏锦文:《唐律与中国现行刑法比较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页;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79页。有论者虽对此观点持怀疑态度,但仍将二者“定性”为所指涉对象相类似的概念。(10)陈惠馨:《从规范概念史的角度谈中国传统法律中“国籍”、“化外人”、“外国人”观念的变迁》,甘怀真、贵志俊彦、川岛真编:《东亚视域中的国籍、移民与认同》,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8年版,第1—15页。
根据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国籍”观念的发展脉络,一个国家在制定“国籍法”以区分本国人和外国人的法律身份时,是以承认有其他平等主权“国家”的存在为前提的。这个前提条件在传统中国显然并不存在。19世纪,尤其是40年代前作为“天朝上国”的中国封建王朝,与周边邻国(包括边疆民族)关系的展开是在朝贡体系之下进行的。朝贡体系的核心理论来自传统中国的“天下”观念与华夷之辨。在古代中国人的知识体系里,“中国”与“天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是指封建王朝直接控制下的区域,亦即“中原”,由“受命于天”的天子皇帝所统治,其上之人为有户籍之“民”,因受天子之教化,因而成为文明之“化内人”;天下则除中原王朝所辖之地外,还包括周边没有受天子直接控制的区域,因政令难通,故称为“化外”之地。化外之地上亦有相当数量的政治体,由其君长以藩属、朝贡的名义建立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天下之外,还有人的理性所无法认知的异域空间,居住在上面的人,文献中称为“非人”,皇帝不需要对该地域进行支配或教化。(11)张文:《论古代中国的国家观与天下观——边境与边界形成的历史坐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此外,朝贡体系下化外、化内的边界并不是完全明确和固定的,而是随着各朝代朝贡形态的变化,呈现出相当的模糊性和巨大的变动性。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中国法律传统的外化人概念,可以发现,无论是唐律中属于“蕃夷之国”的化外人,还是大明、大清律中来降、朝贡的外化人、外国人,表述的内涵虽有变化,但他们所从属的国,即所谓的“蕃夷之国”、夷国和朝贡国,都不是基于纯粹的政治地理空间,而是文明、文化观念上建构的国之概念。作为中原王朝的中国,面对这些所谓的“他国”,不是按照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原理,如平等、主权等与之交往,而是通过“书同文”的文化推进,不断将其纳入“四夷怀服”的朝贡体系。
传统中国的天下观念中难以完全生发出明确的现代国家意义上的“国界”或“边界”意识,但中国法律传统中,针对不同的法律适用对象,仍有不同的法律规范,如唐时的化外人依自国所谓“俗法”或“本俗法”的法律管辖;化外人与化内之“民”间的交流,如旅行、贸易、婚姻等,则皆为法律所不允许,且严格限制民人外出的范围。(12)参见《唐律疏议·卫禁》“越度缘边关塞”条,长孙无忌等著,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194页。早在秦汉时期开始的沿海等地民人私自出洋和化外贸易的活动,自唐以降多有变化,到明代发展成海禁政策。明朝政府将那些违反海禁国法而前往化外之地的海外移民视为“逃民”与“罪民”。清朝开国之初,为了防止沿海民人与郑氏集团或“三藩”等反清势力相结合,清政府大力推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将出洋者一律视为“政治犯”“谋反者”和“逆贼”予以重处。台湾郑氏政权被消灭后,清政府虽然解除了海外贸易的禁令,并准许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前出洋者回籍(即返回家乡而编入户籍)为民,(13)《世宗实录(一)》卷58,雍正五年六月,《清实录》(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版,第892页。但人民出洋仍在禁止之列,那些“甘心异域”“存留不归者”即被归为“不安本分”之列,被政府视为海外潜在的威胁。一直到嘉道时期,面对内忧外患的纷至沓来,清政府对待海外华人仍大抵视其为“天朝弃民”,抑或是“自弃王化者”,采取“概不闻问”的消极态度。(14)[澳]颜清湟:《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晚清时期中国对海外华人的保护(1851—1911)》,第12—18页。至于乾隆皇帝对1740年爪哇华人在“红溪惨案”中的回应,即“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这则史料最常被华侨史研究者所征引,以此作为讨论乾隆时期海外华人政治地位的重要论据。但笔者遍查《清实录》《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等史籍,并未找到这句话的官方原始出处。查此条系最早出自李长傅1937年的《中国殖民史》,李氏引自1909年阿诺德·赖特(Arnold Wright)编纂的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Netherland India: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20世纪荷属印度印象:其历史、人民、商业、工业与资源》,参见李长傅:《中国殖民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71页),所引原文为“He was little solicitous for the fate of unworthy subjects, who, in the pursuit of lucre, had quitted their country and abandoned the tombs of their ancestors”(Arnold Wright &Oliver T. Breakspear,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Ltd., 1909, p.76),实际上这句话原文早在斯当东(Sir George Staunton)1797年出版的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已经出现(Sir George Staunton, Vol.I, London: W. Bulmer and Co. for G. Nicol, 1797, p. 265)。中文表述相似的还有“莠民不惜背弃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殊非本政府所愿闻问”以及“莠民不惜背弃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等语,更早分别出现在岑德彰1928年译自宓亨利(H. F. MacNair)的《华侨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4页)、李长傅1929年的《南洋华侨史》(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第31页),均未明确表示出自清官方文献。故乾隆帝所谓“天朝弃民”、“朝廷概不闻问”等态度的表述,笔者判断,是李长傅等人根据英文著作的直译。至于乾隆帝本人对红溪惨案的真正态度,有学者表示乾隆并未覆书(见李长傅:《南洋华侨史》,第34页)。由此观察,海外华人身份问题之所以长期为清政府所忽视,其来有自。
二、晚清地方官民与西方国籍制度的初次接触
世界上第一次国籍立法实践发生在法国大革命时期,1791 年的法国宪法确定了宪法规定国籍的方式,并以法律形式确认了对海外国民的保护权利,此种精神后为大多数国家所仿效和继承。(15)[美]宓亨利著,曾德彰译:《华侨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3页。直至1842年普鲁士颁布世界上第一部单行的国籍法,单行法取代附属法的国籍立法模式逐渐发展为世界趋势。血统主义(Jus Sanguinis),即以父母的国籍为准赋予子女原始国籍,与出生地主义(Jus Soli),即以子女的出生地为准赋予原始国籍,亦被确认为国籍取得的两大基本标准。(16)李浩培:《国籍问题的比较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5、45—48页。据清政府修订法律馆在20世纪初的调查,其时西方各国确定的取得国籍的立法标准,在血统主义、出生地主义之外,实际上还存在着以血统主义为主、出生地为辅或以出生地主义为主、血统主义为辅的两种折中主义标准,而后两者则更为多数国家所采纳,例如以血统主义为主、出生地为辅为标准的国家有俄罗斯、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意大利、日本等,而诸如英国、美国、葡萄牙等国则采用以偏重出生地主义的折中主义标准。(17)“修订法律馆会奏国籍条例草案奏”(宣统元年二月十八日),《修订法律馆会奏国籍条例草案原奏(附清单一件)》,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感谢湛晓白赠送此书复制件。按照西方国籍法理论,除了以出生赋予原始国籍外,西方国家还接受继受国籍以及以婚姻、收养等方式取得国籍。海外华人移民在侨居生活中逐渐接触到西方社会发展出来的典章制度,包括国籍等法律制度,一些华人通过出生、婚姻、归化等方式,建立起其与这些西方国家法律上的联系。而随着西方列强殖民势力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侨居殖民地国家的华人便有取得相应宗主国臣民身份的可能。调查研究数据显示,在海外移民最多的东南亚地区,1826年英国建立英属海峡殖民地时,新加坡有华人6000余人,根据英国普通法标准,但凡出生于此地的华人均被殖民地政府视为英国臣民。(18)[美]宓亨利著,曾德彰译:《华侨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26页。1841年英国占领香港岛时,英国政府即宣布该地的香港居民7450人(19)The Chinese Repository,1841,Vol. 10, No. 5, p. 289.为英国臣民,这也成为近代以来第一次中国人民因领土割让而发生国籍身份变更的事例。但对清政府而言,虽然被迫交出了香港主权,却未由此切断与香港居民的联系,依然视其为大清子民。(20)张勇、陈玉田:《香港居民的国籍问题》,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就清政府的实际统治与管辖区域而言,近代国籍问题最先集中出现于五口通商开放时期的英籍华人群体,其中以厦门最为突出。这些来自英属海峡殖民地、享有条约特权的英籍华人,大部分是明清之际或是新加坡开埠以后移民东南亚的华侨后裔,无论是外貌、衣冠服饰,还是语言、生活习惯,都与原乡民人没有太大差异。当他们在通商口岸开放初期回到中国时,其中一些人善于利用自身“双重”身份的优势,游走于清政府和殖民地政府管辖的中间地带,甚至有不少加入秘密会社、从事非法活动者。每每与当地官民发生摩擦、纠纷时,他们便以外国人身份为护身符,利用领事裁判权加以干涉,此种情况,积弊日久,严重破坏清政府的司法制度和地方秩序的安定。而英国领事与当地政府官员围绕有关英籍华人的身份问题的争议,也极易引起外交纠纷与冲突。1851年发生在厦门的陈庆真案,便是清朝地方官员初次处理国籍问题的重要案例。
1851年1月3日,厦门地方官员福建兴泉永道张熙宇将参与小刀会活动的新加坡华人陈庆真等4人逮捕审讯,并将陈氏拷打致死。此时陈氏的公开身份是英国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厦门分行的书记官,且是业经英国驻厦领事馆登记注册的英国属民。英国驻厦领事苏理文(G. G. Sullivan)将陈庆真之死,视为厦门开埠后首次发生的外籍人被捕受刑致死的惨案,因此发布照会,谴责厦门地方当局侵犯了陈氏作为英国属民的条约权利。张道台则坚称陈氏衣冠服饰与厦门乡民无异,是大清子民,故应按照中国法律审理。双方立场分明,互不相让,英方甚至表示派遣舰队至厦门,以图向清政府施压。关于此案的谈判最终虽以张道台的调任而不了了之,却因交涉层级提升至驻辕广州的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徐广缙与在香港的驻华全权公使文翰(S. G. Bonham)层面,引起咸丰皇帝及英国外相巴麦尊(Lord Viscount Palmerston)的关注。(21)黄嘉谟:《英人与厦门小刀会事件》,《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8年第7期;彭思齐:《五口通商时期厦门英籍华民管辖权交涉(1843—1860)》,《政大史萃》2009年第16期,第49页;秦宝琦:《中国洪门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9—225页;《筹办义务始末·咸丰朝》卷4,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7页。
分析陈庆真之死引发的这场中英外交风波,可以看出双方辩论的焦点集中在中英两国官员对待国籍这一概念的不同认识和理解上。张熙宇在回复苏理文的一篇照会中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兹转录如下:
查贵领事此次照会,系恐中国人生长贵国属岛之人,回至内地或滋事端,原是好意。惟查前定各条约中,并无中国人民生长英国所属地方、回至中国仍作为英国人民之例。现在五口通商,英国客商携眷居住者不少,其在五口生长之人,并无作为中国民人之说,将来回到英国,更无作为中国编氓之理,彼此易观,事理不难分晓。本升道查两国人民,总以衣冠制度为分别,其留发而服英国之衣冠者,应作为英国百姓,归英国管事官管理。其薙发而服中国之衣冠者,应作为中国之百姓,归中国地方官管理。如此界划分明,可免将来争执。现在贵领事开列人名,皆系中国衣冠,并未留发,且住居中国村社,断难作为英国人民。(22)《甘肃按察使司福建兴泉永道张熙宇致英领事苏理文照会》(咸丰元年正月二十三日),F.O. 663/52 &56. Chang Hi-yu to G. G. Sullivan, February 23, 1851.转引自黄嘉谟:《英人与厦门小刀会事件》,《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8年第7期,第324页。
很显然,张熙宇据理力争的立足点是《南京条约》等各条约中并没有中国人民生长在英属地方、回到中国仍作为英国人民的规定,并坚持以衣冠制度作为分辨是“谁的属民”的标准。张熙宇的观点得到新任闽浙总督裕泰以及两广总督徐广缙的支持。裕泰称“中国民人衣冠制度,均与英国迥别,自不能因其生长英国属岛,即作为英国民人”(23)《闽浙总督裕泰奏就所谓生长英国之中国民人回至中国应归英领事管理事同英使交涉片》(咸丰元年三月二十二日),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福建·上海小刀会档案史料汇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徐广缙在1848年处理槟榔屿土生华商李顺发涉讼案时就曾指出:“李顺发本系内地民人,亲族朋友时有往来,服色言语毫无分别。该村百姓只知其在外生理,未必知其为外国之人。如谓生于英国所属即为英国之人,则英国通商自有定地,更不应于五口之外居住行走,致违和约而起事端。”(24)《大清钦差大臣署理两广总督徐致大英钦差全权公使德照会》(1848年3月23日),Chinese Records for 1848, FO 677/26,转引自彭思齐:《五口通商时期厦门英籍华民管辖权交涉(1843—1860)》,《政大史萃》2009年第16期,第49页。此次更明确表示“中外之分,以发辫衣冠为断”(25)《徐广缙致文翰照会》(咸丰元年四月初三日),转引自黄嘉谟:《英人与厦门小刀会事件》,《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8年第7期,第328页。。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国籍问题属于国际私法调整的范畴,为一国之内政事务。陈庆真案中,在苏理文、文翰等英人关于国籍法律的普通法认知里,按照英国以出生地主义为主、血统主义为辅的标准,凡是在英国本土及其属地出生者,自然即为英国属民。但是在张熙宇、徐广缙等清政府地方官员的知识系统中,国籍还是完全陌生的概念与法律制度,自然难以理解英领事解释的属人管辖权等相关国籍原则与观念。双方在国籍概念认识上的分歧,造成了陈庆真案处理及交涉过程中不同法律制度间的矛盾与冲突。关于此类英籍华人的国籍归属问题,中英双方虽最终未能达成共识,清政府地方官员却在与英领事的辩论中,激发了对国人身份归属即国籍问题的认知与思考。他们将衣冠服制作为分辨标准和立场的坚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血统主义国籍观念的初步萌芽。而此一时期清政府官员在面对此类华洋交涉引发的国籍问题的处理方式和态度,也为日后国籍问题交涉中的“出生地主义”与“血统主义”之争埋下伏笔。
三、国籍知识的早期引介与实践
鸦片战争后,伴随西方各国坚船利炮而来的不仅仅是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以及条约体系下围绕中英双方对外籍华人身份的各种争端,国际法知识也开始传入中国,其中美国在华传教丁韪良(W. A. P. Martin,1827—1916)翻译出版的一系列国际法著作,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有关国籍的概念和制度知识。
作为近代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客卿”,丁韪良自1850年来华后,曾于1858年以翻译的身份参与美国与清政府在天津大沽口进行的修约谈判,并长期担任同文馆总教习、清政府国际法顾问。丁韪良以美国著名国际法学家、律师、外交家惠顿(Henry Wheaton,1785—1848)的ElementsofInternationalLaw为蓝本,历时两年译成《万国公法》一书,1864年由总理衙门印行在中国出版,是19世纪晚清中国首次系统接触国际法的重要译著。在该书中,丁韪良对国际法的三个基本原则,即尊重各国主权、国与国之间平等往来以及遵守国际公约和双边条约的相关理论进行了介绍。他还首次解释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法律关系,如权利、国家管辖等国籍问题的相关内容,强调主权国家“莫不有内治之权”,可以制定法律,“以限定人民之权利、分位等事”,管辖疆域之内包括“本国之民及外国之民”的所有人,“并审判其所犯之罪案”。(26)《丁译〈万国公法〉中英文对照研究》,杨焯:《丁译〈万国公法〉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31页。
《万国公法》还专门以英、美两国为例,译介了入籍制度,书中将其译为“准外人入籍”,以对应原书中的Naturalization,并解释道:
凡一国自主自立者,皆有权准外人入籍为本国之民,并可以土著之权利授之。或云人既生在某国,则终身不能弃绝本国管辖,如若获罪于本国,无论在何处仍当永听其法制。(27)《丁译〈万国公法〉中英文对照研究》,杨焯:《丁译〈万国公法〉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32—333页。
丁韪良和他的同文馆学生相继又翻译了《星轺指掌》(1876)、《公法便览》(1878)、《公法会通》(1880)等国际法著作。就国籍相关概念与制度而言,《星轺指掌》详细介绍了外国人加入美国籍后所具有的外交保护等权利以及相关义务。(28)[瑞士]马尔顿著,联芳等译:《星轺指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173页。《公法便览》向国人输入了人民有自由迁徙,寓居他国之人有入籍、复籍的权利与规范等国籍方面的知识与观念。(29)[美]吴尔玺著,汪凤藻等译:《公法便览》卷四,北京:同文馆聚珍版1878年版,第30页。《公法会通》第四卷第364章至374章专论“定籍之例”,对英、法等国的国籍法知识予以系统介绍,包括赋予原始国籍的标准,获取国籍的方式与权利,国籍冲突的解决等内容;而第375章至380章,则详论保护侨民的意义和一般原则。(30)[瑞士]布伦著,丁韪良等译:《公法会通》卷四,长沙:长沙南学会1898年版,第2—9页。
通过《万国公法》等国际法著作在晚清中国的译介和流传,国籍相关的国家主权、平等、权利、侨民保护、自由迁徙等法律知识和观念逐渐为国人所了解和接受,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国籍观念在晚清中国的萌生、发展和传播。研究显示,1879年闽浙总督何璟在处理厦门当地的英籍华人国籍身份争议时,已经能够援用《万国公法》中有关国籍的法律知识与英国领事进行针锋相对的谈判。(31)转引自[日]村上卫:《清末厦门的英籍华人问题》,[日]森时彦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7—168页。在19世纪80年代中荷关于华侨国籍归属问题的交涉中,驻德荷公使许景澄利用国际法知识与荷兰外交部据理力争,不仅取得了外交上的初步胜利,还基本确定了清政府对华侨国籍的基本原则,即原始国籍的血统主义原则,继有国籍的妻从夫籍原则和有限出籍原则,这三大原则奠定了20世纪初《大清国籍条例》的主要内容。(32)转引自袁丁:《光绪初年中荷关于华侨国籍的交涉》,《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此外,条约体系的建立过程中,伴随着国际法知识的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政府遵从国际惯例,废除海禁政策,进而确认了华人移民的合法性。早在广东率先打破这一禁令之初,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Frederick W. A. Bruce)就强调,“(广东巡抚柏贵)终于承认移民出洋如加妥善管理是可以准许的。这在中国的行政制度中是件新奇而重要的发展”,“这等于事实上承认他们的法律必须顺应社会变革和文明进步”。(33)《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致马姆兹伯里文》(1859年5月3日),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第2辑《英国议会文件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2页。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两国签订《北京条约》,华工出洋始得以允许,但为“保全”华工,限以“华民情甘出口”为条件,且在外华人仍不准回国。(34)参阅中英《续增条约》第五款,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5页。随后其他条约也有类似规定。特别是1868年《蒲安臣条约》明确规定“民人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听其自便,不得禁阻为是”,从而以法律形式确立了近代国际法意义上国籍申请、保护侨民的基本原则,显示出清政府初步的国籍法意识。同时“中国人至美国,或经历各处,或常行居住,美国亦必按照相待最优之国所得经历与常住之利益,俾中国人一体均沾。”但“中国人在美国者”,不能因此而“即时作为美国人民”。(35)参阅中美《续增条约》第五、第六条,《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262页。诚如有论者所言,此规定首次明确了中国血统主义国籍法原则,为光绪初年清政府驻荷德公使许景澄在处理荷属华人国籍问题的交涉中提供了有力的依据。(36)袁丁:《光绪初年中荷关于华侨国籍的交涉》,《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除了华工出洋合法化之外,在郭嵩焘、张之洞、薛福成等大臣的吁请下,清政府对海外华人的重要性,尤其是对其经济力量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自1876年起,清政府在海外陆续设立公使馆和领事馆,为保护华商和华工提供了制度保障。1893年,驻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根据对南洋华侨的实地调查,上书驻英公使薛福成,指出南洋华侨不能归国是受“不准出番华民回籍各条”之“中国旧例”所限,当今“邻交已订,海禁久弛,与往昔情形,截然不同”,因此主张解除禁令,“庶华民耳目一新,往来自便”。(37)黄遵宪:《上薛公使书》,吴振清等编校整理:《黄遵宪集》(下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63页。在黄遵宪上书的基础上,薛福成正式奏请清政府废除出洋华人不准回国之禁例,请求朝廷“严议保护出洋华民良法”。(38)《使英薛福成奏请申明新章豁除旧禁以护商民折》,王彦威辑、王亮编,李育民等点校整理:《清季外交史料》(第4册),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87—1788页。总理衙门奉旨议奏时称:应请如所奏,“将私出外境之例酌拟删改”。嗣后,海外“良善商民,无论在洋久暂、婚娶、生息,一概准由出使大臣或领事官给予护照,任其回国谋生置业,与内地人民一律看待,并听其随时经商出洋”(39)《总署奏遵议薛福成请申明新章豁除海禁旧例折》,《清季外交史料》(第4册),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91页。。至此,清政府正式废除海禁,确立了允许海外移民的法律制度。(40)《德宗景皇帝实录(五)》卷327,光绪十九年八月癸丑,《清实录》(第56册),第201页。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用以指称移民海外的中国侨民,或华人侨寓者的“华侨”一词,逐渐在官方和民间流行,并在20世纪初的政治风云中得到广泛使用,进一步凸显和固化了其所附丽的政治意涵。(41)华侨史学界关于“华侨”一词的定义和起源问题,一直都存有争议,此处笔者依据王赓武先生的论断。参见王赓武:《“华侨”一词起源诠释》,《中国历史著作中的东南亚华侨》,《天下华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3、第35页;《越洋寻求空间:中国的移民》,《华人与中国——王赓武自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7页。
四、清政府的国籍立法实践
清政府自1893年正式立法护侨之后,有两个方面的发展愈来愈引起统治者的关注。一方面,随着海外移民人数的增加,加入所在国国籍的趋势也逐渐凸显。例如,英属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殖民地,1870年至1881年间有华人29 785名,其中91人领取有入籍凭证,受排华法案的影响,到1887年取得英国国籍者增至2 689人,而新南威尔士殖民地在1849年至1887年共有908名华人入籍。(42)澳大利亚于1901年改为英联邦自治领、1902年颁发联邦国籍法之前,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昆士兰等六大行省殖民地入籍问题各自为政,并从1855年起相继颁行排华法令。[美]宓亨利著,曾德彰译:《华侨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62页;Charles A. Price, The Great White Walls Are Built,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277,转引自黄昆章:《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孙承译:《日本对南洋华侨调查资料选编(1925—1945)》(第2辑),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53页。横跨塔斯曼海峡的东邻新西兰,亦是英属殖民地。1877年至1886年间,新西兰共有华人3325人,其中124人归化入籍。(43)Ng Bickleen Fong,“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 A Study in Assimilation”,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21, 36.与侨居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但未入籍的华侨相比,此类华人移民享有入境免交人头税的权利,以及在地方、国会选举的投票权。当这些外籍华人以领事裁判权回到祖籍地与当地民人发生各种纠纷,处理华洋交涉的国籍问题时,足令各地方官员和各国领事牵扯大量精力,已如前文所述。这种情况在清末的福建、广东等沿海城市的英籍华人、葡籍华人中更为普遍。(44)参见[日]村上卫:《清末厦门的英籍华人问题》,第159—210页;蒋志华《晚清中葡交涉中的国籍问题》,《岭南文史》2015年第2期,第14页。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当那些并未远赴海外寓居、始终居住在清政府统治管辖范围内的民人,发现具有外国籍便可以左右逢源,并获得逃债、逃捕等种种切实好处后,亦纷纷寻找各种途径取得外国国籍,此即所谓“改籍”问题,主要集中在各地租界、沿海城市,甚至京津地区。甲午战争以后国内华人改籍现象开始明显,至20世纪初已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且与边疆危机连在一起。清末延边朝鲜移民问题引发的间岛问题,沙俄在新疆恣意发展华民为俄籍侨民,俟机对新疆实施侵略(45)白京兰:《清末民初新疆中俄“民籍问题”》,《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等,均可视为一种变相、畸形的“国籍”意识。此外,遍布东南亚、南北美洲以及其他地方的契约华工等海外移民,他们因长期遭受侨居国的不公平对待,迫切希望和欢迎得到祖籍国政府的承认和保护。凡此种种,都使得清政府需要重视国际法、各国移民条例、国籍法律等相关知识,并反省自身法律规范方面的缺失。
据笔者看到的档案材料,最早向清政府提出国籍问题咨询的是日本外务部门。日本自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到1899年,陆续通过修改与欧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外国人居留地和领事裁判权,并在这一年完成国籍立法,以该年法律第66号公布《国籍法》。同年,即有旅日华人郭拱宸、张维平等人向日本方面提出入籍申请。根据日本新颁布的《国籍法》规定,外国人需符合五年以上持续居住在日本,满二十岁以上,依日本本国法,有能力,品行端正,有独立谋生能力或资产,无国籍或因取得日本国籍后丧失本国国籍,以及因国际婚姻以及由此而出生之人,可以归化为日本国籍。(46)参见《(日本)国籍法》第七条、第九条,见南洋公学译书院初译,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补译校订,何佳馨点校:《新译日本法规大全》(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71页。为了确认郭、张等人是否符合归化条件,日本向清政府驻长崎领事张桐华发出照会,张桐华回复照会时称:清政府既“无曾准其国民归化于外国之例”,“无许与入籍于外国之法律”,“又无禁止之明文法律”。最后郭、张等人归化入籍事以“任其本人之自便”而解决。(47)《华商愿入日籍办法一案抄送往来文可否咨商修订法律大臣著为定律由》(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务部档案,档案号:02-21-015-01-002。档案中所附长崎县知事荒川义太郎函中提及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二十六日清政府驻长崎领事回复照会内容。至于长崎领事姓名,系根据《清季中外使领年表》考证,参见故宫博物馆明清档案部、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编:《清季中外使领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8页。1906年,又有长崎华商陈世望等8人提出归化申请,长崎县知事荒川义太郎向清政府驻长崎领事卞綍昌(48)《清季中外使领年表(光绪元年至宣统三年1875—1911)》,第78页。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询问,即欲归化之人,是否丧失其本国国籍,清政府是否有允许国民脱离出籍的规定?在得到驻日公使杨枢请示清政府外务部的意见后,卞綍昌给予的官方答复是:
查敝国人愿入外国籍者,如未在本国禀报,并不认为外国人,故入籍出籍并无专条。……敝国既无此项专条,则出籍入籍,或入外国籍后仍愿不失本国籍,均需问明本人。……如入贵国籍后,愿出本国籍,既愿出本国籍,必在敝国内地实无房地财产。……如该商等入日籍后,仍愿不失本国籍,则将来凡在敝国地方有诉讼事件,即按敝国法律办理,与敝国人民无异。
可以说,上述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当时清政府的主流观点,亦是无明确国籍规范下的临时应对之举。但是,杨枢并未止步于暂时的交涉成功,他认识到:“惟中国本无此项专条,遇有华商愿入外国籍者,既无一定办法,一经外人问难,往往以无例可援,致有各埠不同,前后互异之弊。”为彻底解决此类海外华人入籍问题,他向外务部建议:“兹值我国修订法律之际,可否请由钧部拟定华人改入外国籍办法,咨商修订法律大臣,着为定律。”(49)《华商愿入日籍办法一案抄送往来文可否咨商修订法律大臣著为定律由》(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务部档案,档案号:02-21-015-01-002。
事实上,在杨枢向外务部提出制定华人改入外国籍办法之前的一个多星期,外务部已经就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有关国籍规定等问题的询问,致函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50)另一修订法律大臣伍廷芳已于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十九日因请假回乡修墓离去,时两大修订法律大臣仅剩沈家本。参见陈煜《清末新政中的修订法律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一段往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进行相关咨询。柔克义向清政府外务部提出6个非常具体的有关国籍法的问题:
一、贵国律例中有何条载明出入国籍事;二、中国人应因何事故方能有逐其出本国籍贯之律;三、中国律例准听人自行弃本国之籍与否,若照准听便出籍,厥后欲复入本国籍者,当有何例;四、按照中国律例,如有华人仅住外国,是否与其籍贯之权利有碍。若有此情,系如何阻碍其权利;五、中政府照何等条规保护常寓外国之华人;六、有洋人来华,是否有律准其入籍?(51)《咨法律大臣美使询出入国籍律例六事查照核复由》(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九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务部档案,档案号:02-21-015-01-001。
可以看出,柔克义所提出的6个问题,除了涉及国籍的取得、丧失和恢复方面的内容外,还特别提出对华侨权利的保护、来华外国人入籍等需要清政府解决的新问题。
外务部致函沈家本的时间是1906年8月28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九日),四天后,清政府下发预备立宪之上谕,旋即改革官制,京师法律学堂开学,刑部改法部,大理寺改大理院,(52)李贵连:《沈家本年谱长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3—156页。身处政局旋流中心的沈家本,在外务部的多次催促下,(53)《咨法律大臣华人改入外国籍办法准杨使来函酌复由》(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务部档案,档案号:02-21-015-01-003;《咨法大臣美使催询入籍律例事即查核声复由》(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务部档案,档案号:02-21-015-01-005。直到1906年11月13日(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才复函,内称:
中国数千年来闭关自守,从未与外国交通,故向无国籍之说。即海通以后,凡民户之移徙外洋者,其如何管理,亦并未辑有专条。现在民法尚未成立,一切咸无依据。……本大臣以国籍出入中国律例既无明文,当即饬令馆员调查东西各国成法,妥为议订。惟事关重要,非旦夕所能定议。(54)《国籍出入俟考查明晰详慎订定再行咨呈以凭转复美使由》(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务部档案,档案号:02-21-015-01-006。
由上观之,刚刚履新大理院正卿的沈家本对制定国籍条例基本持肯定态度,且采取他一贯的修律风格,即从组织人员调查外国法律开始,徐徐图之,不能操之过急,仓促而行。但在随后的一年中,由于官制改革引发的部院之争、人事纠葛、立宪分议,沈家本深陷其中,心力交瘁,直到1907年10月11日重新被任为修订法律大臣,12月2日修订法律馆作为清政府独立的法律修订机构再次开馆,(55)陈煜:《清末新政中的修订法律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一段往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2—66页。有关各国国籍法规的调查、翻译等事项似乎还未正式启动,这一点从沈氏于当年6月28日上奏所陈修律馆自开办以来取得的成果中略可概见。(56)《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奏修订法律情形并请归并法部大理院会同办理折》(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八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38页。
然而这时清政府对待国籍立法的态度却有了实质性的变化。1907年11月22日闽浙总督松寿在奏折中报告了福建地区严重的华人改籍问题,已从福州、厦门蔓延至漳州、泉州各属地方,且其他各省“籍民案情,亦复层见叠出”。为了严格限制国内民人擅自改籍,他从维护清朝主权的立场出发,建议“请旨饬下外务部民政部参考中西法律,明定国籍条例,迅速通行遵守”。这样,国外、国内两股有关国籍问题的建议形成合流,汇聚到一起,促使清政府认识到积极制定国籍条例新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光绪皇帝接到松寿上奏后的当日,即下旨“该部议奏,钦此。”(57)《松寿奏严定人民移籍限制一片奉朱批该部议奏钦此》(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十七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务部档案,档案号:02-21-015-02-010。至此,外务部、民政部奉旨开始参与国籍法的制定。由于此时修订法律馆还未正式开馆办事,因此民政部建议由位居各部之首的外务部领衔主稿。(58)《议复闽浙总督松奏请明定国籍条例折应由外务部主稿由》(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务部档案,档案号:02-21-015-02-011。
1908年3月22日,驻法公使刘式训上奏光绪皇帝,再次重申国籍立法的重要性。笔者认为,刘式训的这份奏折是代表晚清国籍观念成熟、推动国籍立法进程的关键性文件,特迻录如下:
为臣民国籍关系重要,亟宜妥订条例,以培邦本,而保主权。……
窃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道同风,罔有歧视。向所谓籍贯者,仅系生长地方及出身之区别,无对于外国之关系也。今当万国交通之世,情事繁赜,决非旧有之简单法律所能因应。即以国籍而论,我既无治外法权,而租界中外杂居,南洋华侨甚众,若不早定入籍出籍条例,则日后流弊有不堪胜言者。……各口租界林立,居民良莠不齐,奸黠之徒,每投领事馆注册,受其保护,一经犯案提究,则领事强为干预,使享免辖权利,此等事端,业已屡见。若凡有领事之处,相率效尤,则侵损主权,伊于胡底。此国籍之关于主权者一也。西国收纳客民入籍,限制甚严。凡在领事馆殖民地注册之客民,仅视为顺服之民予以保护,不准享国民权利。故注册之后,仍华装华俗,与平民无异。若往内地置产设肆,地方官何从觉察禁阻,而我禁外人在内地置产设肆之条约,已为此辈暗中破坏,若不早为防范,其贻患且甚于教民。此国籍之关系现行条约者二也。即使中国将来收回治外法权,普准内地杂居,二者之害,可以无虞矣。而臣以为国籍之关系,更有甚于此者。查西国定例,有生于其地即入其籍者,有夫或妻虽系客籍,在其地所生子女及岁时不自陈明,即作为入籍者。今华侨散布于香港、星加坡、西贡及南洋各地,数逾百万,多置田园,长子孙,旅居数世。倘彼族觇我本无国籍定制,而设例以尽没入籍,我将何所据以与争。闻荷兰属地尝持即生其地即入其籍之说,来相尝试以隐拒我设领之谋,其用心已可概见。此国籍之所宜急定条例者三也。方今预备立宪,他日国民程度稍高,或推行选举,或仿行军役,凡属国民,虽远客他国,皆应享此权利,尽此义务。尤非明定国籍条例,无以示限制而杜趋避。此中消息,关系非轻,此国籍之尤宜早定条例者四也。臣愚以为,核定国籍专制,为民律之始基。凡在本国入他国籍者,应由领事随时知照地方官立案,其未立案而遇事始行自陈者,概不作准。若旅居他国而改籍者,须由本人呈请该国地方官,报明中国领事署立案。其在他国生死婚嫁,亦须在领事署注册,按季呈报民政部,以资稽核。至已入他国籍者,自不得与本国人民共同利益,亟宜明示区别。拟请饬下修律大臣会同外务部、民政部、法部妥定入籍出籍条例,请旨颁行。(59)《刘式训奏请饬修律大臣会同外务部民政部法部妥定出入国籍条例折奉朱批该衙门议奏钦此》(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务部档案,档案号:02-21-015-03-001。
刘式训在奏折中言简意赅却又鞭辟入里地阐述了国籍与籍贯的区别,国籍重要性的四个方面,即关乎主权、关乎现行条约、关乎海外华侨的政治地位、关乎国民的权利与义务,并提出本国人入外国籍的程序及规范。尤其重要的是,他特别提醒清政府注意荷兰拟根据属地主义原则改变殖民地华侨身份,并以此为清政府在荷属东印度设领设置障碍,这也为不久后荷兰新订殖民地入籍新律引起当地华侨强烈反弹埋下了伏笔。和杨枢、松寿相关的国籍问题建议相比,刘式训对国内、国际国籍问题的把握无疑更全面。后来驻荷公使陆征祥形容刘式训:“广方言馆、同文馆同窗,法文专家,学贯中西,外交老手。”(60)《布鲁日资料 561》,比利时布鲁日圣安德鲁修道院藏陆征祥档案,档案号:LZXDA-05-0725-0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复印件。此言非虚。
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在接到清政府批准刘式训奏请的旨意时,修订法律馆起草新刑律的过程基本暂告一段落,正在开始进行更大规模的起草新律的活动,国籍立法就成为其中重要的一项。“参酌各国法律,首重翻译”(61)《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奏修订法律情形并请归并法部大理院会同办理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37页。是沈家本一贯的修律准则,制定国籍法时,亦然。1908年6月30日,沈家本向昔日同僚、时任驻美公使的伍廷芳发电代购各国国籍法资料,正式启动编定国籍法的程序。(62)《请代发驻美伍大臣电由》(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务部档案,档案号:02-21-015-03-006。10月,荷兰当局准备颁布新律,企图以出生地为原则,将久居荷属殖民地的华侨收为荷兰子民,消息通过驻荷公使陆征祥传到国内后,荷属东印度各埠华侨商会速定国籍法的呼吁亦纷至沓来,迅速引起外务部、民政部、修订法律馆等多部门的连锁反应,加速了国籍法的编定速度。(63)《收出使荷国大臣陆征祥致外务部电为荷兰拟定新律吞并华侨事》(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35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此时,修订法律馆翻译各国国籍法的工作已经完成大半,但因为缺乏熟悉荷兰文人员,且荷兰国籍法与此次国籍立法关系密切,因此敦请外务部致电驻荷公使陆征祥派人代为翻译。陆征祥回电应允聘请荷兰本地人先译成法文,继而译成汉文。(64)《发出使荷国大臣陆征祥电为会商妥订国籍条例事》(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九日),《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26册),第435页;《驻和大臣陆征祥致外务部电》(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三十日),骆宝善、刘路生编:《袁世凯全集》(第18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7页。与此同时,沈家本从修订法律馆先后选派章宗祥、章宗元、熊垓、陈簶、朱献文、马德润以及曹汝霖等7人,与外务部所派人员会同草拟国籍条例草案。(65)《派章宗祥等六员会同妥拟国籍草案由》(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务部档案,档案号:02-21-015-03-012;《添派本馆纂修曹汝霖会同妥拟国籍条例由》(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务部档案,档案号:02-21-015-03-013。这7名国籍法起草人员,皆为“一时通博之士”。(66)[美]宓亨利著,曾德彰译:《华侨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50页。比如,章宗祥、朱献文、曹汝霖、熊垓4人为日本法政留学生,章宗元留学美国,陈簶毕业于法国巴黎法律大学,(67)转引自阎立:《〈大清国籍条例〉制定过程之考证》,《史林》2013年第1期。马德润为德国柏林大学法学博士。(68)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地方法院档案,档案号:J65-3-544。此外,沈家本又请驻日公使胡惟德留意搜集日本司法省方面讨论国籍法相关之资料。(69)《请代发致驻日本胡大臣电由》(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六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务部档案,档案号:02-21-015-03-015。
在荷属各界华侨、各地封疆大吏、海内外社会舆论的共同请愿和期待中,至迟到1909年2月,各国国籍法的翻译工作亦全部完成,统计有单行法8部,分别是《英国国籍法》、《美国国籍法》、《德国国籍法》、《奥国国籍法》、《法国国籍法》、《葡萄牙国籍法》、《西班牙国籍法》和《罗马尼亚国籍法》;国籍法规2部,意大利民法关于国籍各条、日本条约改正后关于外国人之办法;国籍法研究专著4部,分别是《各国入籍法异同考》,日本立作太郎的《比较归化法》,志田钾太郎的《国籍法纲要》和《制定国籍法意见书》。(70)《修订法律大臣奏筹办事宜折并单》(宣统元年正月二十六日),《政治官报》宣统元年二月初二日,第471号。与此同时,在参考各国国籍律例、尤其是日本国籍法的基础上,同时吸收日本商法和国际私法专家志田钾太郎所提出的“应注意辅助中国之宗法社会”、“采取血统主义”及“应采取单行法”之意见,(71)袁德辅:《我国国籍法之检讨》,《中央警官学校校刊》1942年第5卷第3期。修订法律馆终于在3月5日完成《国籍条例草案》的草拟工作,提交外务部会签。外务部在该草案基础上于3月9日正式形成《国籍条例草案》5章25条,(72)《会奏国籍条例草案希核定会画并开列堂衔由》(宣统元年二月十四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务部档案,档案号:02-21-015-04-013;《修订法律馆会奏国籍条例草案原奏(附清单一件)》。需要说明的是,在修订法律馆会同外务部起草国籍条例草案期间,《华商联合报》(1909年3月6日第1期)、《东方杂志》(1906年3月25日第2期)、《广益丛报》(1909年3月31日第197期)等报刊中接续刊登《中国国籍法草案》(不分章28条及“施行法”4条)的文章,《东方杂志》且声称此即为“法律馆所未经奏定者”,很多研究者均将此视为《大清国籍条例》的草案。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1919年3月19日清政府官方报刊《政治官报》第497号曾专登“纠正”一栏,明确表示“近日本京各报所载国籍法草案与外务部会同修订法律大臣所奏国籍条例草案不符”。明确提出国籍立法采折中主义的偏血统主义原则,即以血统主义为主、出生地为辅,并参照各省历年交涉情形,拟定《施行细则》11条。(73)《修订法律馆会奏国籍条例草案原奏(附清单一件)》。李章鹏指出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一部油印本《国籍条例草案》,内容由“国籍条例草案说帖”“国籍条例草案”5章25条以及“国籍条例施行细则”12条组成。这一新的发现无疑对研究《大清国籍条例》的制定过程有积极的推动意义。但由于该材料无具体的作者与时间,属于孤证。虽然通过文本比勘,《修订法律馆会奏国籍条例草案原奏(附清单一件)》所附《国籍条例草案》与《施行细则》内容与之大同小异,但其“实施细则”12条却与沈家本、奕劻等人在《原奏》中“先经臣家本等督率各员参酌各国异同,拟就国籍条例二十五条施行细则十一条。复经臣部详加考核,尚属妥协,正拟缮稿具奏”一语存在着矛盾。因此他认为国图藏本为修订法律馆3月5日提交外务部“会签本”的这一论断,恐怕值得商榷。具体的研究详见李章鹏:《〈大清国籍条例〉及其施行细则制定过程新探》,《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8年第4期。
《国籍条例草案》起草工作完成之后,即进入“宪政中枢”宪政编查馆的审定复核程序,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生、时任宪政编查馆考核专科帮办的汪荣宝参与其事,对草案内容悉心校阅,多有签改。(74)韩策、崔学森整理:《汪荣宝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1、13、14页。最后经宪政编查馆核议的《大清国籍条例》共分固有籍、入籍、出籍、复籍和附条5章24条,并附《施行细则》10条,于3月28日,经宪政编查馆大臣奕劻奏请颁行。(75)《宪政编查馆奏遵旨议覆国籍条例颁行折并清单》,《清末民初宪政史料辑刊》(第2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377—393页。与《国籍条例草案》相比,《大清国籍条例》文字上更加精练、严谨,内容上对外国入籍者、本国复籍者担任政府官职的条件、职务、范围以及入籍者、出籍者的资格条件做了更为完整、明确、严格的限制,进一步强化了清政府的国籍立法意图和原则。(76)具体异同参见李章鹏:《〈大清国籍条例〉及其施行细则制定过程新探》,《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8年第4期。据孟森研究称,《大清国籍条例》“乃兼有日本新旧两种限制国籍之法律者”,所定条文,较日本法文更为细密,符合中国宪法大纲所载臣民权利义务、外国人居住租界等政治现实。(77)即1873年(明治六年)《内外通婚律》和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日本国籍法》,孟森:《论说:论中外国籍法性质之不同》,《外交报》1909年第250期;《国籍条例与各国国籍法之比较》,《外交报》1909年第251期。
纵观《大清国籍条例》从酝酿、动议、制定到出台的历史过程,由于国籍问题本身的复杂性,驻外使节(如驻日公使杨枢、驻法公使刘式训、驻荷公使陆征祥、驻荷参赞王广圻等)、封疆大吏(如闽浙总督松寿、两广总督张人骏等)、清政府各中央机构(如外务部、民政部、法部、农工商部、修订法律馆、宪政编查馆等)、荷属各埠华侨组织及国内商会(如南洋泗水中华商务总会、谏义里中华学堂、上海商务总会、闽省商业研究所等)多种力量参与其中,形成合力,最终促成清政府统治者在国籍立法思路上逐渐从明确海外华人自愿改籍,严格限制国内民人擅自改籍,以及确定海外华侨的合法身份三个层面达成共识,推动了政府层面国籍观念的成熟。此外,来自社会舆论的力量也值得重视,除有人从国家主权、民族平等、维护国家司法主权完整等层面强调国籍法的重要意义外,(78)汪精卫:《研究民族与政治关系之资料》,《民报》1906年第13期;杨煜辉:《论改籍协约为国际最要之问题》,《东方杂志》1908年第7期。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一批知识分子,积极著文立说,普及国际法和国籍法律知识,从学理上探讨国籍问题的解决方案,(79)参见许小青:《晚清国人的民族国家认同及其困境——以国籍问题为中心》,《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在译介日本国际法学者方面尤其不遗余力,如中村进午的《日本国籍法讲义》经由江苏吴县留日学生吴兴让翻译,在国内广为传播,(80)[日]中村进午讲述,吴兴让译:《日本国籍法讲义》,《北洋法政学报》1908年第53—58、60—61、63—66期。而在广东中山留日法学士唐宝锷对中村进午的国际法访问录中,专门问及国籍归化之去从,(81)《国际法访问录》,《北洋法政学报》1908年第67期。其他诸如广东番禺留日学生朱执信也从“心理的国家主义”层面对国籍关涉的“忠诚”问题进行反思,为其民族主义思想张本。(82)县解(朱执信):《心理的国家主义》,《民报》1908年第21号。凡此种种,均可视为晚清中国社会精英国籍意识高涨的一个表现。
五、余 论
黄兴涛教授曾深刻指出:“对于近代亚洲弱国来说,其政治话语,往往受到西方列强制定的现代国际法则及其相关知识和概念的复杂影响。通过国际法知识、概念和精神带有时代印记的理解与运用来表达自身的内政外交诉求,以促进国内的改革运动,并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通常成为近代中国‘弱者话语’的突出特点之一。”(83)黄兴涛:《强者的特权与弱者的话语:“治外法权”概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运用》,《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6期。国籍作为近代中国出现的确定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的新概念,亦可作如是观。
1907—1911年中荷设领谈判期间,荷方强硬地将设领和华侨国籍问题捆绑在一起,这一突发事件成为推动清政府国籍立法的催化剂。(84)李章鹏:《中荷设领谈判与华侨国籍问题交涉(1907—1911)》,《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4期。荷属殖民地华侨国籍冲突是突然发生的个案,却真实地反映了鸦片战争以降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国籍问题的长期酝酿与积累,一方面沿海商埠、租界、边境等地的国籍身份争议日益复杂,另一方面海外侨民政治地位不断提升,二者相互交织,相互建构,共同推动清政府国籍观念从被动应对到主动立法的转变。
还应该提到的是,早期英汉字典类工具书的编纂与流通对新概念标准化、规范化进程的展开,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如前文所指出的,作为一个法律、政治概念,Nationality一词在外文世界的正式出现是较晚近的事,这一现象在鸦片战争前后来华传教士编纂的早期英汉辞典中有所反映。无论是马礼逊(R. Morrison)1822年的ADictionaryofChineseLanguage,还是麦都思(W. H. Medhurst)1847的EnglishandChineseDictionary中均未收录Nationality,甚至也没有Citizenship一词。直到1868年罗存德(W. Lobscheid)的《英华字典》(EnglishandChineseDictionary)第三卷出版时,才出现Nationality词条,罗氏用“国之性情,好本国者”定义之,且将“What is his nationality?”解释为“系边国嘅,属何国乎?”(85)W. Lobscheid,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part III, Hong 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868, p.1212.这已经涉及个人与国家隶属关系的含义,但还未真正地将这种政治内涵加以概念化和科学化提炼。就笔者掌握的材料,早期英汉字典中明确用“国籍”直接对译Nationality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出现在1908年颜惠庆的《英华大词典》中。(86)在颜氏的《英华大辞典》中,Nationality意为“国风、国体、民情、民性、国之特性”,“国籍、籍”,“国民、人民、百姓”以及“爱国心”;Citizenship意为“国民权、籍贯、城民或公民之身份”。颜惠庆:《英华大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年版,第1506、378页。这也与当时清政府制定国籍法的进程相一致。此后,用“国籍”这一词汇表示国民与现代主权国家之间的法律联系,逐渐成为定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