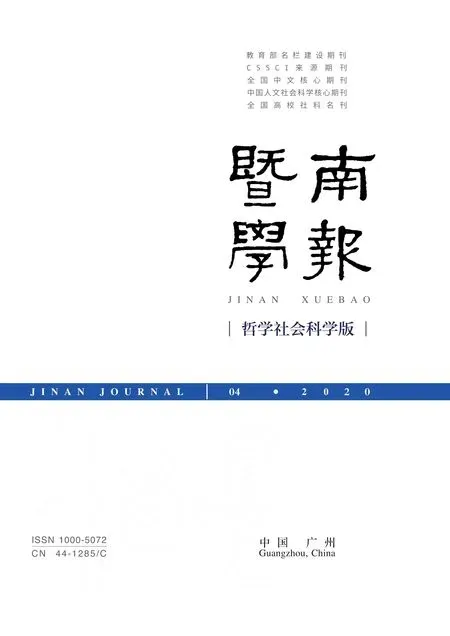早期“天心”观念初探
——基于政治语境和哲学语境
2020-11-17贺敢硕
贺敢硕
一、引 论
“天心”或“天地之心”是中国哲学的常辞。前贤多认为其大致发端于战国时期对“天”与“天道”的讨论,(1)徐兴无:《释“诗者天地之心”》,《岭南学报》2015年第3期。而在两汉期间它很快成为一个相当常用的语词,大量出现在《潜夫论》《论衡》《太平经》《老子指归》等哲学文本中;并屡现于《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著记载中,成为诏书简策内的套话。遍观“天心”辞例在汉魏南北朝的运用,其理论含义虽大体有规律可循,但总体仍呈现芜杂无端的样貌。直至两宋道学,对“天心”一语的运用才似乎获得了一些规整与哲学语境内的固定,我将其大略概括为二端:
(1)以“人心”推至“天心”。如朱熹《中庸章句》曰“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张载论“尽心知性”曰“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正蒙·大心》);二程亦曰“同即是天心”(《遗书》卷二五)、“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卷二)。
(2)借由《复》卦彖辞“复其见天地之心”语,予以“生生”的发挥,(2)例如,胡瑗的《周易口义》卷五曰“天地以生成为心,未尝有忧之之心,但任其自然而已”;欧阳修的《易童子问》:“天地之心见乎动。《复》也,一阳初动于下矣,天地所以生育万物者本于此。故曰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为心也”。(《宋元学案》卷四)《朱子语类·易五》曰:“天地之心,别无可做,‘大德曰生’,只是生物而已”;《语类·朱子二》“天地之心,只是个生。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如草木之萌芽,枝叶条干,皆是生方有之。人物所以生生不穷者,以其生也。才不生,便干枯杀了”。另外,约撰于东汉的《周易参同契》已经发其端倪。即将“天地之心”以某种意志的隐喻,理解为宇宙生化万物的内在趋向。例如,陈来将其诠释为“天地运动的内在动力因”,且强调其“并不是有人格的天意或主观的情意,而是宇宙之中的浑然生机和闇然生气”(3)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43页。,又言:
在中国哲学中,天地之心的概念并不意味着这个天地之心有意识、能知觉、能思维,或是一种精神。“天地之心”可以只是指天地、宇宙、世界运行的一种内在的主导方向,一种深微的主宰趋势,类似人心对身体的主导那样成为宇宙运行的内在主导。(4)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27页。
陈来的结论是围绕宋明理学论述“天心”的两条线索展开的。可见,以“人心”推“天心”这一思路背后的实质,是以“心”的概念为中心表达的天人结构性相似,“心”所呈现的“主导”之态势正是这一联结的枢纽;对这种主宰力量的表述来源可以追溯到诸子时期,而“天心”语例作为秦汉思想的一个新表达,也首先需要借由对“心”的概念的分析而得到阐发。我的基本观点是,“天心”观念是早期思想对主宰之“天”的性质或作用之思考的精细化,古人使用这一辞例深化了“天”作用于人事的理论机制与观念逻辑。
理学的两条解释路径对于分析梳理早期“天心”观念来说,既是起点也是某种阻滞:一方面,宋儒以“人心”推“天心”,强调二者在结构上的比拟,是我们理解这一概念的重要思路,但“心”的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使得这种比拟往往模糊不清;另一方面为避免一种神学乞灵,陈来用“动力因”的说法排除了意志化倾向,宋儒也言“别无所做”“只是个生”,试图祛除“天心”本身所附带的主宰的神学特性,但是,“天意”观念本就是两汉解释“天心”的重要途径,早期思想家们亦时常需要以“天意”化的“天心”来辅助完成其政治哲学的表达。简言之,“心”这一概念的理论内涵落实在“天心”上时,既是结构性的,也是内容性的;前者构成“天心”这一观念形成的关键,后者则关涉先民对“天心”的进一步规定与思索。
从秦汉乃至魏晋南北朝的“天心”语例来看,我的意见是与其把“天心”看作一个严肃的哲学概念,不如将它视为一种单元性的“观念”(idea),理解为整体思想语境的构成元素,或一种杂糅的“看法”。这要求我们既要在哲学语境中思考“天心”观念自“天”的思考中产生及运用的内在逻辑,也要探寻“天心”作为一个政治辞命中的套话的理论意义;这两条路径具有同一性。也即我们在分析过程中所选取的文本材料不应局限于哲学内容,而是要求有多元化的线索,非如此不足以勾勒出“天心”话语的完整性;这项研究需要对辞例进行大范围、长时段的蒐讨与更精细的分析,限于篇幅本文的工作只能算是预制性与框架性的。
本文首先在诸子刻画为“心术”的思维模式中考察“心”的概念所具备的理论结构,从而论证它指向某种政治表达的合理性,并分析它与“天心”观念在语境中所具有的同构性。其次,以“心”所具有的意志、思考、筹划的能力,分析“天心”的运用及其解释史中所蕴含的“天意”语义层面。最后,从心性学的角度对“天心”观念进行二元性的分析,将“天意”的分析结果归于其中一端,从而为一种更为复杂的“天心”观念分析划出论域、奠定基础。
二、“心”与“天心”
“心”在早期思想中是一个重要的语汇,且在心性理论的发展脉络中逐渐衍化出深邃复杂的哲学概念。“心”的理论意义可笼统地概括为能动的“能治能思之官”(5)有关中国哲学中“心”的著述可谓不胜枚举,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说法,可参考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问题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10年版,第263页;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55—156页。。“心”作为日常语词多见于故书,强调某种在人一身之“内”的事情,例如情感、意志、欲求、思考、算计、筹划,乃至某种道德性。在这一系列语词意义构成中最为突出的是所谓“身之主宰”,即能对在“外”的行为或感知活动产生影响: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
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大学》)
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荀子·正名》)
“心之官”的作用在于思虑,而作为感觉的“耳目之官”的作用只是“物交物则引之”。故而这种思虑在语境中指向某种不同于具有被动色彩的耳目感知的“主动性”,乃至对感知予以把控、影响的能力。在此思考基础上,诸子对“心”的论述往往是对立耳目天官所代表的感知活动,并且在这种对立叙述中组构成“心”的思想语义:
耳目者,视听之官也,心而无与于视听之事,则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过而不见,声至而耳不闻也。(《管子·心术上》)
心忧恐,则口衔刍豢而不知其味,耳听钟鼓而不知其声,目视黼黻而不知其状,轻暖平簟而体不知其安。(《荀子·正名》)
夫悲哀在中,故形变于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礼记·问丧》)
这种描述把控或影响的观念结构,很容易被推类演绎为一种政治语境中的统领;反过来也可说,传统思想对“心”在人之一身中的地位叙述,自一开始就蕴涵某种政治性的隐喻。《管子》将“耳目”描述为“视听之官”即体现了这种“君主—百官”二分的思维方式,“心”的概念恰是在与其他官能的对比中才被诠释为“君”的位置:
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嗜欲充盈,目不见色,耳不闻声。(《管子·心术上》)
夫心有欲者,物过而目不见,声至而耳不闻也,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术者,无为而制窍者也。(同上)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荀子·解蔽》)
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荀子·天论》)
“心”之“制窍”或“治五官”的功能体现了其相较具体感官而言的特殊性,故其在人之一身中被摆放到了最为重要的位置。“九窍”“五官”云云与其说是对感官的实指,倒不如说是外在的“形”的代名;具体来说,即导向身体、行为、形容、威仪等内容的思考。新出清华简《心是谓中》首章即充分地体现了“心—天官”与“心—形”乃至“心—行”之间的同构性:(6)宽式释文据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版,第149页。
心,中,处身之中以君之,目、耳、口、肢四者为相,心是谓中。心所为美恶,复何若影(7)原释文作“倞”,读作“谅”,此据陈伟说读作“景(影)”,参见陈伟:《〈心是谓中〉“心君”章初步研读》,简帛网,2018年11月17日。;心所出小大,因名若响。心欲见之,目故视之;心欲闻之,耳故听之;心欲道之,口故言之;心欲用之,肢故举之。
与外在的动作周旋相反,“心”是内向化的、“无形”的,能够宰制有形之动作的东西,如王博指出“心无形但却真实存在者,而且应该是形的真君和主宰”(8)王博:《庄子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页。。换言之,在人之一体的整体中,“耳目”等其他器官被叙述为处乎外在的“形”,而“心”则被诠释为内在的无形主宰。这一思路形成的观念,即相对人之外在行为而言,把捉其“心”显得更加重要。
《管子》所称“心术”为黄老文献的常辞,(9)就使用状况来看它并不是黄老文献的专利。如《荀子》就多处提到“心术”,例如《非相》“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顺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解蔽》“圣人知心术之患,见蔽塞之祸”,《修身》“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夫是之谓治气养心之术也”。《礼记·乐记》亦曰“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韩诗外传》卷二曰“原天命,治心术,理好恶,适情性,而治道毕矣。原天命则不惑祸福,不惑祸福则动静修”,等等。可笼统地将其概括为一种“用心的方法”。一方面从黄老的使用看来,“心术”更多指一种养心的工夫,即一种心性论意义上的方法;另一方面,它也被使用于某种统治策略的保障,无论是实现一种礼乐教化,或者是对“无为制窍”之政治的施行。治心与治国二者实呈现互为表里、内外的关系,其前提与逻辑是内在的“心”与外在的“形”(或“行”)之间存在的交互作用。后者如张舜徽所强调,更接近一种“主术”(10)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台北:木铎出版社1988年版,第203页。。在“心术”这一共同理论语境中呈现出来的,就是“心”的概念作为“制窍”指关键在整体中所具的中心地位,即政治话语中的统领与主宰。因此,“心”在“心术”的语境中并非指向单独孤立的、物理化的五藏之一,而是具有特殊的意义畿域;它处于“心—官”“心—形”“心—行”的整体关系中,从而是结构性地被给定出来;在“心术”的哲学语境中言“心”,意味着对这种整体结构的承认,即“心”在整体内的优先性向来就已被结构性地揭示出来了。
“天心”这一术语作为一个复合语,其意义需要借由“心”在文本语境中的含义得到理解;进一步来说,其体现的就是“心—形”的结构化思考向着“天”这一超越性至高存在的投射。《管子·枢言》谓“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心”“日”对举,其意甚明。“心”的结构性呈现在人之一身即为“神明之主”,在“天”则成为“天地之心”: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复·彖》)
就文意看,“天地之心”显然是就“天行”的讨论而发,后者是更为具象而外呈的描述。(11)我们放弃对于“复”的概念的讨论(尽管诸儒对此有大量的思考与分析),而将其仅仅悬置为一种“见天地之心”的方法或途径。无论“复”具体为何,它都是在一种与“天地之心”的互动、感通,甚至是“观看”中呈现出来的;如王弼注《老子·三八章》曰“天地虽广,以无为心。圣王虽大,以虚为主。故曰以复而视,则天地之心见”。因此,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中,“见天地之心”这一目的背后的思维结构才是优先重要的,即对于“心”予以“看见”与掌控之方法论的重要性。王弼将这种“天地之心”诠释为“天地之本”,确乎对这种“内在”的性质有所洞察,即将“天地之心”理解为“天行”的根据,这种思考范式虽引入了“本末”的术语体系,其观念内涵却未尝脱离“心—形”的君臣关系及“心”所展现的统领作用。“天”的概念作为整体,在“天地之心”的讨论语境中,也被“心—形”的思考模式二分化了,也即先民对“天”的理论思考在“天心”的表达方式内被“心术”化。换言之,象征为君主的“天心”隐含着对外呈为现象的“天行”(包括“阴阳”“四时”之类)予以统领或宰制的意味;在“心—形”的语境中,对“天心”的把捉就等同于掌控了“天行”。如《周易参同契》曰:
圣人不空生,上观显天符。天符有进退,屈伸以应时。故易统天心,《复》卦建始萌。
又《太平经》曰:
道者天之心,天之首。心首已行,其肢体宁得不来从之哉?(《太平经·王者无忧法》)(12)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45页。
“天符”作为一种可形象的征兆,就是在“心—行”二元对立中有形的“天行”。仰观俯察的圣人在这一思维中要把捉(“统”)的并非变化屈伸的现象,而是背后左右前者的“天心”,“天行”犹如“宁得不来从之”的“肢体”。汉代帝王常诏云“承顺天心”的政治意义即体现于此,它表明在人效法天的汉代话语环境内,统治者能够在上接“天心”的宣言下对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皆制诸于掌;某种意义上,这种辞命是对早期思想中常见的“顺应天命”的说法之更细化、更具理论目的的表达。“天心”在政治话语中得到广泛运用的内在逻辑即出乎此。
三、“天心”与“天意”
在将“心”刻画成“心—形”结构中呈现的观念,并以此完成对于“天心”的投射之后,我们已结构性地阐释了“心术”的思维模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凸显的政治话语逻辑。进一步阐释“天心”意义所遭遇的困难是早期思想中“心”的概念过于复杂,很容易简化地理解“天心”的含义。纵览秦汉书内“天心”“天地之心”语词比比皆是,在史籍中所见的两汉诏书简策中,它几乎成为一个修辞性的套话;其意义大多未逃离“天命”“天意”“天志”这种人格化的理解;即便如此,“心—形”的政治结构仍然在发挥作用。澄清这种理解,才能够深入“天心”的观念形态,更进一步对“天心”予以分析。
先举例考察以“天心”辞例对先秦文本的注解,因为经传的形式经常有助于我们更直接地发现观念的挪移。如《论语·尧曰》谓“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汉魏古注有:
简阅在天心,言天简阅其善恶也。(孔颖达《尚书正义》引郑玄注)
言桀居帝臣之位,罪过不可隐蔽。以其简在天心故。(何晏《论语集解》)
原文的“帝心”在注释中被替换为“天心”,表现对“心”的主体的认识所发生的变化。汉代旧注多以“帝”为“天帝”,能够简阅善恶的“天心”无疑体现出人格神灵的气质。从“帝”到“天”的转换,或许可说是自殷商至西周以来道德化转变的余绪。“心”在此处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自内向外主导其“行”的意志,并且是一种道德性的意志。(13)若对比朱熹《论语集注》对于《尧曰》此处的解释,会发现朱熹在解释中仍然保留了“帝心”的原貌。这多少说明《尧曰》本身蕴涵的人格神气质为朱熹所觉察,也体现他试图区分“帝心”“天心”两个概念,而将前者落实于“上帝”,后者落实于“人心”与更为道德化的“天命”“天地之心”的意图。根据我们的分析,这种思路显然不同于汉代这一语汇的呈现。再如王符对乾卦《彖》辞的重写曰:
苟非其人,则规不圆而矩不方,绳不直而准不平,钻燧不得火,鼓石不下金,金马不可以追速,土舟不可以涉水也。凡此八者,天之张道,有形见物,苟非其人,犹尚无功。则又况乎怀道术以抚民氓,乘六龙以御天心者哉?(《潜夫论·思贤》)
“乘六龙以御天心”语本自彖辞“时乘六龙以御天”;其与“怀道术以抚民氓”语对举,则所谓“御天心”看来是一种治国之法的描述;更重要的是,王符所提“有形见物”的“八者”(14)即《潜夫论·思贤》曰“规不圆而矩不方,绳不直而准不平,钻燧不得火,鼓石不下金,金马不可以追速,土舟不可以涉水也”,简单来说都可以概括为一种“自然现象”,也就是一种有形有象的“天行”。是一种可见可形的“天行”,“则又况乎”的转折则指向价值层面更高的内容,也就是“天行”背后内在的、左右前者的“天心”。从“御天”到“御天心”的变化意味着一种政治语境内控御的具体化与精细化,即尝试抓住外在呈现为“天行”的“天”其背后的主宰者。这一思路也渗入“御天”语的经学解释中,如王弼释为“乘变化而御大器”,“器”正是古代哲学描述有形有象内容的代表概念,即王弼所谓的“形器”;《正义》以“大器”为“天”,“御天”为“控御天体之所以运动不息”,亦指一种对外在“天行”的控御。进一步看王符对“御天”语的理解:
天道日施,地道日化,人道日为。为者,盖所谓感通阴阳,而致珍异也。人行之动天地,譬犹车上御驷马,蓬中擢自照矣。虽为所覆载,然亦在我何所之可。孔子曰:“时乘六龙以御天”、“言行,君子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从此观之,天呈其兆,人序其勋。书故曰:“天功人其代之。”如盖理其政以和天气,以臻其功。(《潜夫论·本训》)
并列于“御天”语的“言行动天地”语出《系辞》,王符解释为“天呈其兆,人序其勋”,强调一种以人施加主动的“为”;“天兆”的现象语境,等同之前所析的“天行”或“天符”,“兆”意味着它试图表述某种可形可象的物事,它背后隐含着“天心”的逻辑。“人道日为”的目的恰是一种“合天心”“承(顺)天心”或“御天心”,“序其勋”则意味着自“天兆”进而把握“天心”的做法,并使其成为君主施政之权威性与合理性的保障。
因此在“心—形”的基础上,“人为”和“天心”存在必然的理论关联:被认为由“天心”主导的“天行”,即天地自然大化,需要被纳入政治人文世界中,成为前者为政合理性的论证与保障;并且在一种人格神的余绪下,“天心”作用于人事的方式经常被诠释为意志性的。在许多辞例中可见,作为“张道”“呈兆”之主体的“天心”,通常且首先被理解为“天意”(15)陈来:《汉代儒学对“仁”的理解及其贡献》,《船山学刊》2014年第3期。或“天志”(16)徐兴无:《经纬成文——汉代经学的思想与制度》,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50—52页。:
周公推心合天志也。上天之心,在圣人之胸,及其谴告,在圣人之口。不信圣人之言,反然灾异之气,求索上天之意,何其远哉?(《论衡·遣告》)
夫圣人为天口,贤者为圣译。是故圣人之言,天之心也。贤者之所说,圣人之意也。(《潜夫论·考绩》)
其为人君者,乐思太平,得天之心,其功倍也。……治不合天心,不得天意,为无功于天上。(《太平经·努力为善法》)(17)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8页。
令得其至意,乃上与天心合。(《太平经·解师策书诀》)(18)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9页。
吾文出之后,帝王德君思此天意,勿忘此言,此言所以致得天心之文也。如得天意,命乃长全也;不得天意,乱命门也。行而不称天心,亦大患也。(《太平经·三光蚀诀》)(19)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79页。
无论是“推心合天志”“原天心以人意”抑或“推得失,考天心”,都呈现出相似的尝试理解“天心”的理论策略;“心”所具有的意志、运思的含义在“天心”的意义构造中起了主要作用,即“天心”被理解为天的意志与运思。这种神秘意志以一种道德性的尺度,在政治语境中成为对人事治道正确与否的评判依据。“合天心”(《太平经》《后汉书》)因此被诠释为借由“天行”,对彰显为意志和运思的“天心”所生发的一种揣测,董仲舒又以“观天道”表述之:
夫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知天,诗人之所难也。天意难见也,其道难理。是故明阳阴、入出、实虚之处,所以观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顺逆、小大广狭,所以观天道也。(《春秋繁露·天地阴阳》)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汉书·董仲舒传》载对策)
“观天道”意味着人能以某种“理性”的方式,借由对阴阳虚实的自然规律与灾异祥瑞的观察,从“人心”出发怀着一种政治目的对“天心”所代表的意志进行推证;也可以说,它是一种比譬连类,即所谓“原天心以人意”(《论衡》)。
以“人心”猜度“天心”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古文献中时常出现的“天心”与“民心”的系联。如《潜夫论》多次应用与民意结合的“天心”词例:
凡人君之治,莫大于和阴阳。阴阳者以天为本。天心顺则阴阳和,天心逆则阴阳乖。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本政》)
当此之时,万民怨痛,泣血叫号,诚愁鬼神而感天心。(《实边》)
白起、蒙恬,秦以为功,天以为贼。息夫、董贤,主以为忠,天以为盗。此等之俦,虽见贵于时君,然上不顺天心,下不得民意,故卒泣血号啕,以辱终也。(《忠贵》)
这里“天心”近似《太誓》所谓“天听自我民听”之“天”,但显然包含了更明确的理论性;“上顺天心,下得民意”云云为两汉诏书祝文之常辞,如前、后《汉书》常曰“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上合天心,下顺民望”等。无论是属于民意表现的“万民怨痛,泣血叫号”,还是更抽象的“阴阳乖”与灾害怪异,我们要强调的这些都是“天行”,百姓的状态实际上在天人关系的背景中被演绎为“天行”的变体。对“民心”(其实就是“民意”)的观察梳理,并以此观“天心”的思路,直接呈现了古人借道外呈之现象(“仪”),尝试捕捉能够宰制外物的、作为意志的“心”这一行为的观念基础。又如《汉书·息夫躬传》曰“天之见异,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觉悟反正,推诚行善。民心说而天意得矣”,与之类同,“天心”“天意”在此实为同一表达。
在“天心”观念所寄托的理论基础上,“统天心”或“顺天心”被认为是善政的基础,甚至就是善政本身。而作为善政代名的“天心”则需借由对“天行”的观察来考定与猜测,这一思路与诸子时期那种“视其所以,观其所由”的观察没有太大区别,后者本出自一种礼仪性的“威仪”的语境。(20)我们可以从《左传》《国语》等文献中发现大量相关例证。例如《国语·周语下》中单子预言“晋将有乱”的判断基于“夫君子目以定体,足以从之,是以观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处义,足以步目,今晋侯视远而足高,目不在体,而足不步目,其心必异矣。目体不相从,何以能久?”这就是一种对仪态、“威仪”的观察所进行的判断,其言“观其容而知其心”,理论含义甚明。换言之,这种思路是将作为整体的“天”视作人之一身,以外在化、客体化的“行”来确认内在的“心”。所以,一种“知”的语境蔓延在这类思考中。先前在引述分析作为“天意”的“天心”时,我们留意到诸如“推”“原”“统”“考”这样的语词不断出现,它们构成了一种相似的思维气质,即认为我们能利用人心的思虑、筹划与推理,通过显象完成从“天行”到“天心”的摸索还原。“天心”从而在这种理论形态中显示为类似组织结构、运行规律、刻意筹划之类的东西,可以由外呈的现象进行推演。《春秋繁露》有《天容》篇,强调“圣人视天而行”,就是这种传统的体现;“天容”的说法直接体现了早期以威仪容止来察“心”的思路。与之相关的是,学者也会将“天心”看作作为自然规律的“天道”。(21)参见徐兴无:《释“诗者天地之心”》,《岭南学报》2015年第3期;刘雅萌:《复见“天地之心”——论王弼〈周易注〉对汉代天道观的突破》,《周易研究》2017年第5期。刘氏文就其引用原典与相关论证看来,其结论基本是在徐兴无先生的既有研究上得出的;另一方面,基于汤用彤先生所开创的魏晋玄学研究框架,为了论证王弼的易学诠释与汉易在思想与方法论上的截然两分,刘氏深化了在两汉文献与王弼《周易注》的“天心”观念之间的区隔,在这种特殊论证语境内将前者解释为一种自然宇宙论。故推知“天心”的方法大多是卜卦考灾、则象阴阳之类:
《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汉书·翼奉传》)
今以陛下明知,诚深思天地之心,迹察两观之诛,览《否》《泰》之卦,观雨雪之诗,历周、唐之所进以为法,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汉书·楚元王传》引刘向说)
某种意义上说这似乎是一种“科学精神”的体现,但其背后复杂的理论动机是不能被忽视的。语境中的“天心”不完全是一个作为宇宙之本的物质性内容,意志性的因素、筹划着的“天意”仍然左右着“天心”语义的构成。例如“考天心”的下一步就是颇具神学色彩的“承顺天心”。并且,圣人也被认为需要延顺天心以制法度:
昔文王一动而功显于千世,列为三代,此所谓因天心以动作者也,故海内不期而随。(《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汉书·伍被传》)
圣人既躬明悊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动缘民情,而则天象地。(《汉书·刑法志》)
圣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显天心。(《礼记正义》引《演孔图》)
圣人所具有制礼设教的能力是“天心”赋予的,因而其所施设的制度威仪也就必然因循“天心”而“则天象地”;“天心”因此成为其政治哲学论述语境中不可动摇的价值预设。(22)《周易正义》即认为“天本无心,岂造元亨利贞之德也;天本无名,岂造元亨利贞之名也。但圣人以人事托之,谓此自然之功为天之四德,垂教于下。使后代圣人法天之所为,故立天四德以设教也”。张载《经学理窟》亦曰“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一人私见固不足尽,至于众人之心同一则却是义理,总之则却是天。故曰天曰帝者,皆民之情然也,讴歌讼狱之不之也,人也而以为天命”。即认为“天心”立法皆是以人事托之。这些观点都是后世出现的一种“袪魅”。这显然与“天”这个概念所具有的至高地位脱不开干系,“心”则代表了这种至高观念作用于人事治理的枢纽。
总之,借由天人同构的理论预设,通过“天行”的外在彰显(祥瑞、灾异)以“人心”猜度“天心”,并因循“天心”作为最高的价值预设完成政治哲学系统的论证,或以“承顺天心”为名,标举君主施政的合理性与不可动摇性;这些形式皆成为以“天心”观念所呈现的两汉政治文化与政治话语的重要特征,且作为一个固定的辞命格式为后世诏书史籍所继承。
四、“常心”与“天心”
现在的问题在于,“天意”的解释模式能否套用到所有的“天心”辞例上?我们发现,这种解释大大削弱了“心”的概念所具有的复杂性,连带着对“天心”的认识也变得平面化。我认为应该借助当前的心性学研究弥补这个缺陷。在“天心”含义内最重要的元素是“心”这一判断的基础上,对“天心”给出某种心性学的思考,即将一种以庄、孟为代表的心性学投射到“天心”概念上去。
简单来说,“心”在心性学讨论中被分为两个层面或维度:一为思虑的、理性的层面,二为体悟的、直觉的层面;借用《庄子》的术语,称前者为“机心”,后者为“常心”。(23)参考蒙文通:《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蒙文通全集》(一),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版,第31—55页;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6页;郑开:《道家形而上学研究》(增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1—174页;郑开:《庄子哲学讲记》,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5、142—143、187—188页。我们所言的“心”的大部分日常语义,如思虑、筹划、意志、愿望,乃至诉诸形迹的“威仪”与“德行”,皆应归于前者。所以,“机心”简言之就是头脑聪明,能基于感知理性地进行规划、推理、判断,总之是一种将所有东西都以为是可“知”的、对象化的思考;与“常心”进行对比,它属于“心”的浅层、即较易见的层次。当古人以观察“天行”来对“天心”进行思考时,就是将“机心”投射在“天心”之上;或者说,“天心”以一种可被“机心”理性化认识的对象的状态,得到了后者的理性化认识,故它能以一种“推知”的方式被理解为一种思虑或意志;也可说,“天心”在某种“知”的语境中被设立为一个德行化的、可被推知的东西,即在心性论思路中被划归到“机心”理论语境的畿域。
与之相对,“常心”不可对象化,从“心”的结构上来说它是“心中之心”,是“心”的深层内容;从状态来说它被表述为“诚”“真”“和”;从工夫实践维度来说它是“一心”。作为不可对象化、不可以“知”来认识的“心”,文献往往以“神明”“鬼神来舍”等多种角度来提示它。“常心”不需要诉诸形迹的“行”来作为依据,它自身就是自身的依据,故可认为是“无心”或“无为”。我们能从一部分“天心”辞例中发掘出这种“常心”的理论痕迹。但是,应如何对这种在理论上要求脱离“天行”的“天心”进行认识?它能否继续保证“心—形”的结构,并在政治语境中继续借由“天行”来论证自身的合理性?
此类“天心”话语的复杂性在一些道家思想文献中初见端倪,例如严遵《老子指归》曰:
不建法式,不事有为。上欲不欲,天下自化,敦厚朴素,民如婴儿,蒙蒙不知,所求茫茫,不知所之,其用不穷,流而不衰。……故不郊祀而天心和,不降席而正四海,故曰大巧若拙。天道自卑,无律历而阴阳和,无正朔而四时节,无法度而天下宾,无赏罚而名实得。隐武藏威,无所不胜;弃捐战伐,无所不克。无号令而民自正,无文章而海内自明,无符玺而天下自信,无度数而万物自均。大辩若讷者也。是以赢而若绌,得之若丧,无钟鼓而民娱乐,无五味而民食甘,无服色而民美好,无畜积而民多盈。夫何故哉?因道任天不事知,故使民自然也。(《大成若缺章》)
圣人去知去虑,虚心专气,清静因应,则天之心,顺地之意,政举化流如日之光,祸乱消灭若云之除事。(同上)
上德之君,性受道之纤妙,命得一之精微,性命同于自然,情意体于神明,动作伦于太和,取舍合乎天心。神无所思,志无所虑,聪明玄远,寂泊空虚。(《上德不德章》)
引文所述乃对“有为”的反对,即对“知”或“机心”的反对。“不郊祀而天心和”的“天心”有一些日常修辞的味道,看似无法作为一个严肃的可供分析的概念;然而“天心和”所表达的是一种整体的哲学语境,是一种状态,即“蒙蒙不知,所求茫茫,不知所之,其用不穷”。在“无……”句式的否定过程中,以“律历”“正朔”等“知”的语境内的知识形式通达这种整体状态的路途被截断了。这里的“天心”所指的政治内容,在“和”所营造的语境中得到了点化,故需要被理解为一种“因道任天”的政治状态。“去知去虑”也提示我们这是一种心性论语境中的状态。而“天心—天行”的结构并未消失,它在某种完全不同的理论环境中继续隐秘地发挥作用,即在心性、政治浑沌为一的整体性(“太和”)中转化为不同的理论形态;“形”或“行”因此被描述为“敦厚朴素”“蒙蒙不知”的理想政治形态。道教存思术也常见“天心”辞例:
当此之日,清斋烧香,弃诸异想,愿合天心,存思苦念,修行灵文。(《上清玉帝七圣玄纪回天九霄经》)(24)此经已见《真诰》著录为“七圣玄纪”,其引用未见从现存版本中找到;经文又为《无上秘要》等类书所引录。贺碧来(Isabelle Robinet)将其定为东晋所撰的古上清经,参见Kristofer Schipper & Franciscus Verellen ed.: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p.178-179.
精思微妙,幽感天心,是以灵降扶身,上升帝庭尔。(《裴君传》)(25)《云笈七签》(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278页。引文乃太素真人传授裴君日月结璘之法,本质上可理解为一种基于心性修炼的存思之术。
清斋炼养、结璘存思的修行,意味着进入特殊的精神状态,从而与耳目之知迥然区隔。经文借由存思的心神集中,以求得一种冥通与感应,正是上清经派独有的修炼法门。(26)李丰楙:《仙境与游历——神仙世界的想象》,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5—146页。“精思”“幽感”之类的描述提示了一种特殊的洞见与观照。可见,“天心”在此并不诉诸感知与推论,而是在某种神秘中直接“幽感”到的,这正是心性哲学语境中常见的论述方式。
以上,我并无意用一种新的“天心”观念来取代对“天意”观念的理解,“常心”“机心”的心性论投射也并未隐含任何价值上的判断;本文的很多分析也指出,在许多文本阅读中,对“天心”采纳“天意”的解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当我们采用文本细读、语境分析的研究方法时,就能在这些“天心”的辞例中梳理出不同寻常的部分。至少,用一种“天意”的观念无所不包地囊括这些辞例,并且认为只有“天意”的含义才能够成为“天心”的代表,或者以一种袪魅的思想框架分割将观念自语境中割离,这些思路本身是值得反思的。对“天心”辞例初步分析的结果能够与目前的心性学研究发生一些对应,足以证明这并非偶然。当然,这种关联如何发生、如何进一步细化,能否梳理出更细致的思想史脉络,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讨论。因此,从两汉至魏晋南北朝的“天心”辞例及其所代表的观念本身具有一种复杂性,从内容上说,它并非“天意”的解释模式所主宰的一言堂;而结构本身则以一种特殊语境发挥了表达作用,又被一种不可“知”性所消解。本文故可作为一项以结构形式与内容指向为基础,对早期“天心”观念给出进一步分析的先期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