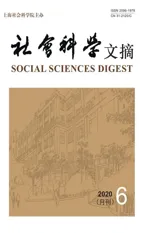中国何以须要一个国族?
2020-11-17周平
文/周平
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支撑着共和国的大厦,构成了共和国大厦的基石。然而,中华民族在认知和观念层面却明显存在问题。在中华民族与少数民族都称之为“民族”的特殊语境中,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往往以一般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去阐释,中华民族的国族性质被抽离并蒸发了。以中华民族的构建性质来抹杀它的实体性质,以及以其构建性来否定其存在的实然性的声音不时出现。因此,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性质、地位和意义并未得到全面的论述和科学的认识,中华民族并未得到准确的认知和论述。这种问题的出现,既非偶然也并非中国独有,这与“民族”概念的拓展性使用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的问题随之突出并成焦点,政策层面和学术研究层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学术环境和话语环境中,“民族”概念就逐渐地演变成为一个专指少数民族的概念了。于是,中华民族之民族与少数民族之民族的差异性被模糊了,它与现代国家结合并支撑整个国家制度体系的本质也就淡出了人们的认识和观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国家发展目标的另一种表达和论述方式后,尤其是党的十九大围绕中华民族来确定国家发展目标、论述党的历史使命,不仅凸显了中华民族的国族性质,而且使中华民族认知方面长期存在的问题凸显了出来。在此情况下,恢复中华民族的国族性质,把中华民族的构建与发展同中国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的构建以及未来的国家发展结合起来,全面认识中华民族与国家发展的相关性,就成为了学术研究和学者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
国族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
国族意义上的民族首先出现于西欧。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的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王权、教权、贵族、民众成为了持续而稳定的社会政治力量。在这四种力量数个世纪的互动中,王权逐渐地获得了主导地位或绝对地位。于是,即存的各种形态的国家演变成为了君主的国家,即王朝国家。在王朝国家巩固并逐渐演变成为绝对主义国家的背景下,君主的权力也逐渐增强并走向绝对。在此过程中,民众对教权、贵族等的依附关系日渐式微,与君主的关系则日渐巩固和明晰。他们效忠君主并得到君主的庇护,从而进一步地变成为与君主相对的臣民个体。此种变化过程中所实现的社会人口的“去地域性”和“去依附性”,突出了个体在国家中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这样的变化也将基督教民众对上帝的皈依转向了世俗的对国王的臣服。王朝国家在通过日渐强化的君权而对社会人口的依附关系进行解构的同时,也将逐渐个体化的臣民在王朝的框架内整合起来,分散的国民最终凝聚成一个国民整体,即民族。
王朝国家将国民个体整合为民族整体的同时,国家权力向君主集中的进程还在推进。君主权力的不断加强,一方面将国家“王有”的性质推向了极端,另一方面也促成了国民权利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增强,从而致使矛盾朝着不可调和的方向演变。最终,这样的矛盾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彻底爆发,并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国家的主权由“王有”转向了“民有”,“君主之国”转化成为了“民族之国”。于是,一种新形态的国家——民族国家——出现了。在国家主权体制已经形成以及君主主权得到确认的条件下,民族国家构建的实质,就是国家的主权由君主个人转向了民族,从而使民族成为了国家的主权者。民族拥有了主权,也就实现了民族与国家的结合。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来看,民族国家本质就是民族拥有主权的国家。
民族拥有主权,实现与国家的结合并具有国家的形式,也就成为了国族。这样的国族从形式来看,表现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组成的人群共同体,即国民共同体。但透过这样的表象,国族却蕴涵着一系列的机制。一方面,国族在形成的过程中,对曾经的人口形式进行了分解,使处于复杂关系中的人口成为了简单的国民个体。在民族国家构建起来以后,国族便将这样的人口国民化机制蕴涵于自身,成为一种内在的机制。另一方面,国族又将原子化的国民个体整合为一个整体,通过民族国家的制度框架将其固定,并维持这个国民共同体的稳定和巩固。因此,国族至少蕴涵着人口国民化和国民整体化两种基本的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族是在国家框架内形成并蕴涵着一系列社会政治机制的社会人口组织形式,也是国家框架内最基本的人口组织形式。
国族这种制度化的人口组织形式及其蕴涵的机制,对于现代国家制度和现代社会的形成和运行都发挥着基础性的影响。首先,它通过人口国民化机制彻底解构了传统的多样化的人口存在方式,将其从各种地域性、依附性关系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转变成为原子化、同质化的个体,进而赋予其权利,促使其变成为权利、地位平等并能自主支配自己行为的个体,成为有效的社会行动者。其次,它以国民个人权利和逐步实现的权利平等机制,为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提供支撑。现代国家本质上是一系列制度机制的整体。而这样的制度机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都是建立在一元性的国民权利基础之上的。最后,它通过国民整体化机制来整合国民认同,再经由民族与国家的结合而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有机地结合起来,构建起现代国家通过国民认同而为国家提供道义基础和道义说服力的国家伦理,同时也为国家力量的凝聚以及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竞争力的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上述因素结合起来,就促成并支撑了西方社会现代秩序的建立。国族的形成、完善及其功能的发挥,既为西方现代文明的形成提供了基础,也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强盛提供了保障。没有国族的形成和支撑,就不会有西方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当然也就不会有现代文明的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族尤其是国族内涵的社会政治机制,也是理解西方文明的一条线索,或者说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密码。
中华现代国家构建须以国族为基础
中国自秦统一并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开始,就具备了王朝国家的基本特征。在这样的国家体制下,社会人口主要通过家庭、家族和部落等方式来组织,社会又通过王朝而实现统治和治理。这样的体制和政治框架并不排斥甚至不理会地方政权、社会组织和人口形态是否具有异质性。但是,古老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在鸦片战争后中断了。中国人在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中,最终选择了通过对传统社会和制度的改造而实现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发展道路。中国要想建立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国族。
日本明治维新后成功地由传统文明转向现代文明,并实现了所谓的“脱亚入欧”,走的也是这样一条道路。在民族国家尤其是日本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下,中国在19世纪末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国族机制,并开启了国族机制构建的历史进程。一方面,中国从外部尤其是日本引入国民观念后,国民观念在社会上迅速传播,并促进了一个实际的人口国民化进程。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的概念提出和传播后,国人的民族意识被一步步唤醒。在此背景下,政党、政府和社会组织积极推动逐渐具有国民身份的人口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凝聚,从而便促成了作为国民整体的国族的构建。
中华民族的构建与现代国家即民族国家的构建又是结合在一起的。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表现为一个依照现代民族国家制度体系框架,建立具有现代国家特点和国家伦理本质的制度体系的过程。而这样的民族国家制度体系,须要一个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民族共同体来支撑。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古老的中国在辛亥革命开启民族国家构建以后,一步步地将通过国民化改造而形成的人口凝聚成为了以“中华民族”为族称的民族共同体,以此来配合民族国家的构建并提供必要的支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完成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之时,中华民族拥有了国家主权,具有了国家的形式,成为了国族。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不论是构建过程还是现实的存在,都具有突出的特殊性。这是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与现代国家体制相结合的产物。但是,在中华现代国家构建完成以后,在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建立起来以后,这样的特殊性又是在现代国家的大框架内存在和发挥影响的,因此,它们的存在并未弱化更没有抹杀中华民族的国族性质,也不与中华民族内涵的国族机制相冲突。中华民族所包含的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机制仍然明显而突出。
正是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及其蕴涵的社会政治机制,为中华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并促成了新型国家伦理和一系列社会政治秩序的形成。首先,新的人民共和国就是以“中华民族”来命名的,突出了中华民族的主权者身份;其次,国家的“人民民主”性质是建立在人口的国民身份和国民权利基础上的;再次,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企业等各种社会制度和组织皆以国民的权利和行为自主性为基础;最后,国家认同经由中华民族认同实现,国族机制巩固了国家的道义基础。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族之间的内在联系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确立以后,国家面临着如何将各个少数民族及其聚居的边疆地区的地方政权纳入到新的国家政权体制中的问题。为了应对这样一个对国家整合具有根本影响的重大问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一系列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成为了民族话语的主要内容。中华民族本身反而在逐渐淡化、虚化和空洞化的过程中被淡忘和解构。但是,当这样的问题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其对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国家伦理和国家秩序的影响也日渐突出,并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忧思。
在这样的背景下,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点,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和国家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在肯定国内各个民族的实体性的基础上,提出并强调了中华民族的实体性存在。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后续讨论中,尤其是从不同角度来对“多元一体”的诠释中,一些论者纠缠于“多元”与“一体”优先顺序以及虚实的争论,也有一些论者通过“多元”是实“一体”为虚的论证而得出了否定中华民族是民族实体的结论,从而将对中华民族的认知和讨论推向了窘境。
在此背景下,政治学的研究在此领域出现了。政治学视角的研究,把国族与民族国家结合起来,基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从国族的角度来论述中华民族,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中华现代国家基石的观点,将中华民族置于现代国家的框架中认知,为中华民族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拓宽了中华民族认知的视野,也促成了新的理论平台的形成。
国家崛起的实现须有国族的支持
在中国经济总量居于世界第二位而将强国的特点逐渐凸显的情况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一个浸透着文化和道义内涵的表述,把中华民族作为强国建设的主体和最终归宿,从而使强国目标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这样一来,中华民族便被纳入到国家治理和发展的总体格局中考虑,并被凸显于当代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国家发展目标的特定表述以后,中华民族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的性质一再被强调,突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内涵。但是,今天对中华民族的界定和各种论述归结起来看,突出的根本内容或核心要求,仍然是将全体中国人在国家的框架内凝聚成一个整体,强调的本质内容仍然是国民的整体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和部署,进一步凸显了这样的国民整体性要求。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天一再强调的中华民族,本质是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民族实体,即国族,从而将国族机制与国家发展目标的本质联系进一步凸显了出来。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尤其是人类再次走到新的十字路口的当下,我们深化中华民族的认知,还必须关注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即19世纪末中国在多次尝试后,最终选择了通过现代国家制度、社会制度的构建而实现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发展路径,这样的转型在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后在今天已经基本实现了。今天的中国在整体上已经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了。因此,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也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新的挑战。
20世纪初开启的中华民族的构建,不论是人口国民化机制还是国民整体化机制,都是在传统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可是,今天的中国已经实现了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并正在经历着新的一轮工业革命。因此,曾经在刻画或塑造国内民族群体及族际关系中发挥根本作用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今天的中华民族已经处于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或文明环境中,国族的维持和巩固面临着新的环境和问题,尤其是面临着利用新的技术环境塑造各种新的族群意识和诉求,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观念对国民整体化的挑战。如何协调中华民族内部的族际关系,进一步巩固人口国民化的成果,促进国民整体化水平的提升,塑造一个更具凝聚力和韧性以及内在机制更加强大的中华民族,是一个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并找到有效应对方式的重大的历史性课题。
国族与民族国家一样,最早形成于西方。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推进,西方国家在人口流动日常化、规模化和持续化的背景下出现了“多族化”问题。而“多族化”反过来又对西方国家的国族产生了侵蚀及解构性影响,从而导致了相关国家的国族机制被逐渐消解,进而对西方引以为傲的民族国家体制造成了实质性和严重的影响,逐步演化出一系列困扰西方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新矛盾,甚至使民族国家面临着解体的威胁,国家发展的进程更是受到了严重的困扰。
西方国家国族问题上出现的困扰,给快速发展并实现了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中国发出了一个警示:建设一个强大的国族,使国族内涵的各种社会政治机制有效发挥作用,对于国家的巩固、稳定和发展仍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中国要在站起来、富起来的基础上实现强起来的目标,国族及其蕴涵的国民化、国民整体化机制仍然具有根本的意义。同时,中华民族完成了强起来的目标后,要在那时的世界历史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尤其是在世界文明的发展中扮演领跑者的角色,中华民族及其内涵的一系列机制仍然是基础性的社会政治资源。西方国家在国族问题上遇到的麻烦也给了我们一个启发:国族的维持和建设的机制需要创新。
中国国族的维持和建设当然需要国民个体权利机制的支持,但更应该发挥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功能。在五千多年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中华文化,不仅对众多民族群体的形成及其朝着一个整体的方向融合提供了条件,也是今天促进中华民族的巩固和凝聚,以及涵养其内在社会政治机制的重要资源。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组成,国民分属于不同民族群体,中华民族组成单位的刚性化和自我意识的增强,就会导致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内部张力的增加。因此,发挥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的作用,既要立足增强各个民族群体之间的团结,又要努力塑造全体国民的共同体意识,并使这两者相辅相成。只有这样,才能对国族进行有效的维护并促进国族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从而为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有效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