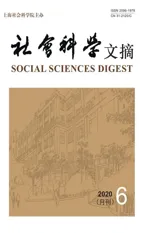中国和平发展学研究
——兼与王帆教授商榷
2020-11-17胡键
文/胡键
中国和平发展学的缘起
王帆教授的《论观念差异与国际合作——“合异论”的提出》(以下简称《合异论》)一文是一篇非常有创建性的文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该文认为差异是一种长期存在的、难以改变的客观实际情况,国家间的合作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开展的一种良性互动。一方面,国家间合作交往越多,彼此间存在的差异所带来的碰撞也就越多;另一方面,差异并不必然影响国家间的合作,关键是如何处理协调好差异。第二,该文指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强调观念一致是推进合作的有效途径,但这种主张在现实国际关系中难以充分实现,因为实现深度合作的关键不在于消除差异而在于实现“合异”。第三,该文认为良好的合作不是仅仅寻求共识,而是在寻求共识的同时协调好差异之间的互动。正是在上述“合异”思想的基础上,王帆教授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全球国际关系学研究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大一统世界”,而是要学会如何和平共处,因此,“中国学派”的重点是要解决不同制度之间如何协调共处的问题。
本文认为,《合异论》一文的上述观点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有关国家间不同制度关系问题上的一个重要超越。其超越之处在于,“观念”的差异是可以通过转化而成为一种走向合作的康德文化(Kantian culture)。不过,《合异论》一文也认为“国家间差异包括文化差异、观念差异、制度差异、发展水平差异,等等,但归根到底都是文化差异的表现”的表述似乎不太准确,因为文章“探讨的问题更多涉及的是主观差异问题,也就是集中表现了文化差异的观念差异问题”。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文章对“差异”的分类是欠科学的。其一,既然观念差异是文化差异的一种,那么就不应该将“文化差异”和“观念差异”并列在一起。其二,“观念差异”可以算是“主观差异”的一种,但“文化差异”似乎又不完全属于“主观差异”。在没有界定文化内涵之前,我们不能轻易把“文化差异”简单地视为“主观差异”的一种,因为物质性文化始于客观性的存在。甚至“观念差异”也不完全属于“主观差异”,因为观念既可以建构包括客观性的利益,也可以被嵌入制度之中而成为制度利益的要素,即它可以“通过制度的运行而产生影响”。从具体实践来看,当涉及政治价值观念差异时,国家之间的合作的确会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在政治价值观念上的“合异”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也正是“合异论”的局限性所在。其三,既然有“观念差异”,那么什么是“非观念差异”?“非观念差异”是否可以“合异”呢?这个问题应当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但在《合异论》一文的讨论之中似乎没有涉及,希望作者在以后的文章中有所补充。但无论如何,笔者认为《合异论》一文关于“合异”问题的探讨,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和“中国学派”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王帆教授提出的“合异论”旨在倡导差异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强调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应该从“求同存异”转向“求同合异”。在他看来,“合异”就是“差异之间的融合”。如果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能够做到融合差异,那么就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就能够成为“合异”的典范。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外交事务中,融合差异似乎是一种外交理想,而不是一种外交现实;另一方面,固然应当大力倡导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来丰富中国当代的外交思想,但是否一定要用传统的话语、概念甚至思维模式来概括当今中国的外交思想还需要认真斟酌,因为外交思想作为对外宣传的重要内容,其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外界容易理解我们的外交目标和做法,而不是让外界在此问题上产生费解甚至误解。此外,王帆教授将“合异”翻译成“integrating the concept differences into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s”似乎不太妥当,因为我们在对外宣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时始终都使用的是“reserving the differences”,如果我们现在把“reserving the differences”转变为了“integrating the concept differences into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s”,那么国际上就有可能认为中国是打着“合作”的旗号来推行一种同化甚至消除“他者”身份的“新殖民主义”。因此,外交上的“合异”有可能会让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动机产生误解。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任何探索和尝试都应该理性化,切勿走向极端。中国的和平发展理论上要求我们必须解决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如何避免陷入“大国成长的历史周期律”之中这一重大课题。一方面,我们要从实际出发来构建理论,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梳理中国理论的源头。中国国际政治学研究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就是如何尽快通过融合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西方理论来推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本土化,从根本上消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之间长期存在的不对称现象,并最终通过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来摆脱“权力政治学”的羁绊,从而形成全新的中国国际关系学,即和平发展学。
中国和平发展学的逻辑起点
“合异论”提出的主要目的是促使国家间在差异状态下的合作成为可能,因而与中国和平发展学的逻辑起点问题密切相关。由于“合异论”强调“合异”是“合作进程中最为重要的阶段”,是“差异”的“融合”,因而必然要涉及谁融合谁的问题,即“合异”的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同时也涉及“合异”的逻辑起点问题,即在什么样的客观条件下才能够实现“合异”,因为并非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具有“合异”的资格。然而,《合异论》一文并没有指明“合异”的逻辑起点和合异的主体与客体。不过,我们通读全文后完全可以推测出“合异”的主体是中国,而客体则是中国外交的对象国。换句话说,“合异”的逻辑起点就是中国国家实力成长壮大的客观实际。根据这一情况,我们可以推断:“合异”的前提是中国的大国成长即中国的和平发展,这一实际情况不仅使得中国可以拥有足够强大的实力作为外交资源,而且还使得中国可以拥有把外交资源转化为外交工具和外交手段的能力。但是,这里涉及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是中国是否完全具有这样的实力和能力?二是国强是否必然会促进外交对象国与我们开展合作?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研究中国的社会实践,因为一切理论的逻辑起点就是社会实践。因此,社会实践不仅是“合异论”的逻辑起点,也是中国和平发展学的逻辑起点。
从中国的历史实践特别是近代中国的历史实践来看,中国遭受殖民主义侵略的历史实践,是中国和平发展学的逻辑起点之一。新中国在成立以后的相当长时期里深受革命逻辑的影响,因而一直扮演着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的“革命者”角色。在此背景下,新中国的外交实践既不是“合异合作”,也不是“和平发展”,而是一场争取主权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但是,这从另外的角度也为后来的“和平发展”提供了客观实际的证据。
当然,中国和平发展学最直接的逻辑起点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这个实践是由内部与外部的互动构成的一个整体。首先,内部改革是推动中国和平发展的逻辑原点。由于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状态,中国改革的原始资本严重欠缺,必须从外部寻找改革的“第一桶金”。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逐步融入国际体系之后,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也不断提高,无论是国际议程的设置能力还是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力,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从此,中国不仅开启了自己与世界良性互动的新历程,逐渐以一个平等的角色与西方国家打交道,而且还通过以中国的智慧为全球化提供新的动力的方式开启了新型全球化的进程。
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外交已经拥有了“合异”的实力和能力呢?本文认为,即使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目前依然不拥有“合异”的实力和能力。虽然中国用自己的实践开创了一条成功的现代化道路,并且开始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但中国并不是在国际权力转移过程中替代美国的角色,中国自身也没有这种主观愿望。中国与美国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经济规模并不能独立地成为有效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指标,只有把经济规模与国家创新力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其才能在国家实力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至于国强是否必然会促进其与外交对象国之间的合作问题,从二战结束以来国家间合作的情况来看,我们还不能看到这种合作的必然性。本文认为,国家间是否开展合作,关键取决于相互之间是否存在有效需求,与观念的异同关系不大。只要相互之间存在有效需求,无论观念相同还是不同,都会开展合作。
综上所述,两方面的实践决定了中国必须走和平发展道路,而指导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只能是以“和平、合作、共赢、发展”为基石的和平发展学,不能是以“权力政治学”为基石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和平发展学的内容架构
在《合异论》一文中,作者一方面强调差异之间的合作,即“照顾好彼此不同和差异的合作”,一方面又强调消除差异性的“合异”,即“让合作催生共同的美好事物,也让合作使各自变得更好”。概括起来说,“合异”就是融合差异,创造新的事物。但是,如何消除观念差异呢?又如何使差异转化为合作呢?《合异论》一文似乎没有进行详细阐释。如果不讲清楚差异的消除与转化过程,那么“合异论”就很可能被认为是在步建构主义的后尘。另外,“合异论”在逻辑上还存在一个矛盾现象:一方面,它倡导差异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又强调通过消除差异性来创造“共同的美好事物”以加强相互间的合作。当然,长期的合作确实有可能催生共同的东西,但也不是一定就能够产生出共同的东西,因为从二战后的国家间合作来看,长期的合作既有可能产生新的东西,也有可能始终处于原地踏步的状态。需要指出的是,“合异”究竟是一个阶段性的互动过程,还是一个长期的互动过程?如果如《合异论》文章所说的那样:“‘合异’是合作进程中最为重要的阶段”,那么“合异”就是国家间合作的一个阶段性的描述,而不是国家间合作过程的全部描述。这样,“合异论”就很难涵盖国家间合作理论的全部内容,也难以涵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全部内涵。
一切理论研究都是为实践服务的。当前,中国正在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和平外交也正在积极主动地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服务。在此背景下,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所从事的国际关系研究,也都是围绕着“和平发展”的主题而展开的。因此,“中国学派”的核心内容必然是以“和平发展”为主题,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学派”就是以构建和平发展学为历史使命的学术创建。那么,和平发展学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呢?本文着重从定义、假设、假说和预测四个方面来对此进行阐述。
第一,关于和平发展学的定义。和平发展学的定义就是在和平发展的主题之下,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围绕“和平发展”的主题而进行的理论研究,它着眼于阐释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和中国与世界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清华路径”“道义现实主义”“关系理论”“国际共生论”“文化国际主义”以及“合异论”等都包括在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之中。
第二,关于和平发展学所适用的前提条件的假设。既然和平发展学是中国实践的产物,也是中国处理与国际体系及其行为体之间关系的理论,那么这种理论必须首先是为中国自己量身定做的理论,或者说是从中国的外交实践总结出来的理论,一定要适用于中国自身的实际情况。其次,这种理论还必须适用于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实践:一是坚定支持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二是积极鼓励所有与中国保持正常外交关系的国家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坚持和平发展原则,但同时也要反对他国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选择来绑架中国的做法。
第三,关于在两个或多个变量的前提下可以对和平发展学进行检验的理论假说。首先,我们引入中国和美国两个变量来验证和平发展学。中国提出构建以“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核心内容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完全符合和平发展学的内容和基本原则。其次,在多个变量的情形下,中国主要通过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来保持与其他行为体之间的和平发展。这一切都是对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性超越。
第四,关于和平发展学的理论预测功能。和平发展学的预测功能应该聚焦在全面系统地分析“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辩证关系上面,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外交取向做出科学、准确的判断。一方面,我们要确保“韬光养晦”不影响中国在国际问题上发挥正常的作用,不能让它成为“有所作为”的束缚;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确保“奋发有为”时不能完全放弃“韬光养晦”,更不能使其成为不断推动民族主义膨胀的“催化剂”,进而产生“排外、拒外、仇外”的进攻性民族主义思潮。
总的看,和平发展学的理论不是理想主义的乌托邦理论,而是从中国的外交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科学理论。它在确保中国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同时,并不回避战争问题,毕竟世界上的局部冲突依然存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更重要的是,中国还没有实现统一大业。因此,当核心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中国绝对不会因为走和平发展道路而听之任之。和平发展学将和平发展与正义战争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构建中国和平发展学面临的困境
中国只是国际社会中的一个成员,众多的国家和不同的国家利益自然导致国际矛盾与冲突的频发,在此背景下,中国与其他国家发生矛盾和冲突既不可避免,也非常自然。最重要的是,一旦发生矛盾和冲突,当事国应当尽力管控好这些矛盾和冲突,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王帆教授在《合异论》中指出:“当双方均不愿做出任何妥协时,往往成为‘合异’最为艰难的时刻。但是,由于对方寸步不让而导致己方不愿或不能做出让步的差异,在处理起来时可能更为复杂尖锐一些。”同时,他还认识到一个国家不可能全面同化另一个国家,因而主张“差异并存”,并提倡通过“共同性”“互动性”“包容性”“互补性”和“相互塑造”等手段来“促进合作”。但是,任何合作都是双方和多方之间的合作,一厢情愿的主观合作愿望难以促成真正的合作。因此,“合异论”有可能陷入一种“应然”的理想主义之中。实际上,这不仅是“合异论”的困境,也是我们构建中国和平发展学的困境。这些困境既有来自我们自身的问题,也有来自客观环境的因素。
从我们自身来看,由于对中国传统历史知识的梳理很不够,从中国传统文献中去挖掘理论的深度也很不够,以至于我们还没有构筑起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体系,发展中国家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依然还是主要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舶来品”。古希腊修昔底德(Thucydides)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不仅最早提出了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的一些基本概念,而且还发现了国家间权力变化的一些基本规律,的确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经典之作。但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明白,这本经典之作所研究的对象仅仅局限于希腊半岛这一地区的国际关系,并不能代表当时整个世界国际关系的全貌,更不能代表中国的历史实践和传统经典思想。由于修昔底德将一场规模并不大的战争的来龙去脉、各方之间的博弈过程等都记录得非常详尽,因此他所撰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对后人的有关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中国史书对历史事件的记录则力求简洁,加之汉字的表达力非常强,这让记录者省去了不少笔墨功夫。但是,这种记录方式对后人的有关研究所发挥的作用不如前者那么大。也就是说,中国这种简洁的历史记录方式与当今国际关系研究的宏观视角不符,因而对中国国际关系知识体系的构建形成了一定掣肘。
从历史上看,东亚地区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中国的主导之下,的确存在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相对独立的东方国际关系体系。该体系主要是以文化为纽带,而西方国际关系体系则是以利益为纽带。在以文化为纽带且“无外”的东方国际关系体系中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国际关系理论,因为中国不仅将自己视为东方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中心之国”,而且还把体系之外的一切国家都视为低人一等的“夷”。因此,在东方国际关系体系崩溃之后,中国才隐隐约约地出现了“外交”“国际关系”“国际法”等话语。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首先也是从苏联和欧美国家引进来的。显然,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在抛弃了“天下”观念之后一直严重缺乏本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滋养。
此外,我们自身目前还存在着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即国家统一问题。台湾问题虽然是中国的内政,但它的背后始终具有复杂的国际背景。因此,只要国家没有完全统一,中国虽然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但绝不会轻言放弃使用武力。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所面临的最大的现实问题,也是构建中国和平发展学所面临的最大困惑。
从客观环境来看,当前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的因素不少,其中最关键的是四大结构性矛盾对我国构成的战略挑战。
第一,中国和平发展的较快速度与西方对华认知停滞不前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人眼里的中国是一个落后、贫困的中国,即便中国的客观实际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他们依然习惯于用老眼光来看待新中国。这二者之间的非良性互动会引起西方国家与中国不必要的分歧,这种分歧的长期积累既不利于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也不利于我们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发展学。
第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使中国愿意主动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对中国的国际作为的担心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当今中国对国际体系拥有了一定的塑造能力,但西方国家的对华认知一直还停留在中国作为国际体系参与者的角色上,因而对中国塑造国际体系的理念和做法产生误解,甚至认为中国所做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颠覆既有的国际体系。
第三,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周边国家的非武力挑衅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周边的安全形势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能否成功和持久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周边国家“安全上依赖美国,经济上依赖中国”的现象非常突出。这种“分离”现象决定了这些国家总是想方设法地寻找某种战略平衡,而“借助美国的支持对中国进行非武力挑衅,借助中国的支持反对美国对本国内政的干涉以保持自身的政治独立地位”就是这些国家寻找战略平衡的结果。
第四,中国与美国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与美国的“和平遏制”之间的矛盾。所谓“和平遏制”,是指美国断然不敢使用武力对中国进行封锁,尽管它时不时地在中国周边“展示肌肉”,甚至还可能刻意到中国周边进行挑衅。这就必然涉及所谓的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的矛盾问题。本文认为,守成国出于维护自身霸权利益的考量必然对崛起国采取种种遏制手段,但是否必然会像雅典与斯巴达那样爆发战争则不能一概而论。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的国际关系史来看,国家的兴衰主要取决于其是否能够处理好内部问题,而不取决于外部力量的干预。从当前中美两国的实力和国际环境来看,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概率极低。因此,中国的和平发展尽管面临诸多外部挑战,但归根到底还是要把自己内部的问题解决好。同样,中国和平发展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也一定要聚焦中国内部发展问题以及与中国发展相关的国际问题。
结语
一个大国的成长进程必须具有持续性动力,必须要有相应的理论加以支撑。中国传统文化历经了五千年而不衰,而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越来越具有生命力,这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础。同时,我们只有不断汲取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成果,才能创新国际关系理论,才能够为我国真正成长为大国提供智力支撑。
第一,中国的客观实践需要中国的理论原创,这个理论体系就是中国和平发展学。第二,构建中国和平发展学一定要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一定要正确对待现代文明成果,一定要正确对待世界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第三,中国和平发展学的世界关怀在于这种理论不是要取代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而是在复杂的国际社会中向世界提供一种新的理论思考和理论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