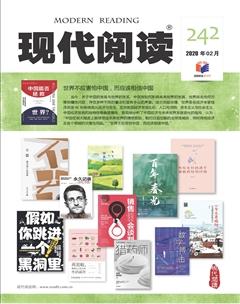苹果的故事
2020-11-16
不知您注意没有,尽管说是“三个苹果改变了世界”,但中国古典诗文里说遍了桃、李、杏、梨乃至远来的葡萄、岭南的荔枝,却唯独找不见苹果的影子。
倒不是古人觉得苹果不值得吟咏,而是因为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苹果——既没有“苹果”这个词,也没有我们今天吃的这种清香脆甜、又大又圆的果实。
古书上记载着一种类似于苹果的果子叫“林檎”,虽然能招来很多飞禽在林中栖落,可人们却并不怎么吃它,只是用来熏衣裳或放在床头闻香——想来口感并不太诱人吧?不过也有人讲林檎就是现在那种个头儿不大的沙果。
元朝的时候,一种的新奇水果从西域被引入大都,嫁接在林檎树上长出了色泽红润的果实。该叫它什么呢?有人想到了佛经里提到的色丹且润的“频婆果”,于是就这么叫了起来。由于是音译,又被写成了“平波”“平坡”“苹婆”等。当时的频婆果非常稀罕,与金桃、玉桃一起种植在郊区的皇家苑囿里。直到明朝万历年间,“上苑之苹婆、西凉之葡萄、吴下之杨梅”依然都是天下名果。那时候安定门和崇文门外,专门设有两丈多深的冰窖储藏苹婆果供宫廷享用。入冬之前存进去,开春之后启冰取出来,像刚从树上摘的一样鲜灵。
也就是在万历年间,农学家王象晋编纂的《群芳谱》里第一次把苹婆果简写成了“苹果”,说它出产在北方,尤其以燕赵之地的最好。它形似林檎但个头儿要大。没熟的时候是青绿的,熟了之后半红半白,或者完全红透,光亮可爱,几步之外就能闻到香气,嚼起来口感甘松。若是不熟,嚼着像棉絮,完全熟透了又沙烂得不好吃了,唯独八九分熟的口味最好。这分寸好难拿!
康熙年间,北京的苹果依然金贵。皇帝为了表现隆恩浩荡,在南巡途中赏赐了宿迁的河道总督一盆苹果。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头,树上掉下来的一个苹果正巧砸到了牛顿的脑袋。那是一颗来自地中海希腊史诗时代的苹果。不知不觉世界要改变了。
到了乾隆年间,京城里的苹果似乎略微放下了些身段儿。当时的价格比南方来的橙子和柑橘略低,但要高于梨、桃、李、杏这些本地水果。苹果雍容华贵,不仅皮薄绵甜,而且让人联想起平安吉祥、太平盛世等等好字眼儿,于是成了宴席上必备的四鲜果之首,淡淡的余香至今留存在相声《满汉全席》里。
不过,令很多人想不到的是,今天市场上常见的本地苹果,听着很本土,却并不是康乾盛世时的北京苹果,而是来源于遥远的太平洋彼岸旧金山的西洋果。
19世纪中叶,有位爱好园艺的美国牧师倪维思先生来到山东烟台。他开辟了示范农场,引进了果大瓤脆、皮红肉硬的旧金山苹果加以培植。这种苹果虽没有中国土生苹果气味清香,却产量高、易储藏,很快被当地农民接受并推广种植,命名为金山苹果。20世纪初,又与本地苹果嫁接出了日后享誉中外的品种,不仅让烟台成了著名的苹果之都,也促使苹果广泛种植于中國北方的大地上,成为这里老百姓最熟悉的水果。
以至于当一种叫蛇果的洋果子假模假样端坐在玻璃柜台上傲视群果的时候,人们一眼就认出来:这家伙不就是大红苹果吗?和蛇有啥关系?蛇果和蛇的确没半毛钱关系,只不过是因为香港地区把delicious apple音译成了 “地厘蛇果”,传到北方又按惯例精简成俩字——蛇果。
苹果的形象越来越亲民,甚至成了现代人的生活符号,印在电脑、手机上,缝在牛仔裤的屁股上,还激励着老大妈们跳起了广场舞。
(摘自商务印书馆《果儿小典》 作者:崔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