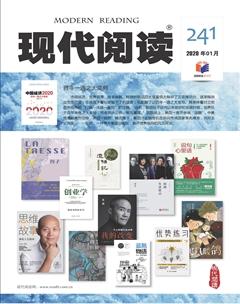撒尼秘境
2020-11-16
楠密是云南省一个有着明净山水的撒尼人小山村,也是民间传说中阿诗玛的逃离之地。这里远离城市的纷乱喧嚣,独享自然的和谐宁静。秀丽的风景、淳朴的民风和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治愈了所有来自城市的旅人疲惫的身心。这里是一个真实的世外桃源,一处能让厌倦城市文明的人们回归田园的理想之地。
寨民都在准备过年,年味儿渐浓。路上仍见有人从八道哨方向回来,有的担着挑子,有的开着小机动车,载回各种年货。家家户户小院子堆着松枝,不知是用作祭祀还是用作挂房檐的吉祥物。后一种可能性大。我曾看见打鱼或下田归来的农人将草帽或木桨等农具插一根松枝,支在墙边或悬挂,我断定是一种吉祥的祷祝。问农人,他们说是习俗。可我认为松枝是代表神灵护佑的符号,还有感恩的意思。农具对撒尼人来说是重要的生存工具。有了农具,便有了生活福音。对于撒尼人来说,农具是祖先传下来的宝物,更是神的赐予。
撒尼人对于农具的熟悉程度与生俱来。村子里,谁若是不能熟练掌握农具的使用,特别是男人,就会被认为是懒汉,很难得到姑娘的青睐。过去的撒尼人无论男女,皆是“椎髻”“跣足”“坦胸”。尽管现在再也无法见到这种古风的形迹,但他们曾经的生存,是与土地肌肤相连的,因此获得了繁育后代所需要的地氣。少数民族这种“过去式”的存在是美好的、不加掩饰的,它有着西南少数民族特有的风韵。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衍进,这种不加掩饰的风韵,被逐渐遮盖,变“敞开”为“遮蔽”。在外人看来,也愈加神秘。
我始终认为:文明的高度发达,不是以科学的进步来证明的,而是人的头脑仍保留着对“原始态”的追求。这种“原始态”,最是接近于人的本态和自然性。自然性、人性、原始态、人的本态,是大地所应该呈现的光芒。现代社会,愈是开放,愈应古朴;愈是理性进步,愈应尊重传统。
现代文明的浸入,让人最自然最自由的身体趋向衰弱。过去,这里的撒尼人都是擅长骑术和射术。他们身体轻捷、矫健,奔跑迅速,肌腱发达,过着捕猎打鱼、山田耕种的原始生活。这种技能的传承,就更要求人人都必须掌握劳动绝技。那时候,在山里或湖边,随便网到一尾大鱼、捕到一只野兔或山鸡,是轻而易举的事。生态环境,也比现在好多了。人们也是自觉维护生态,猎物够吃就行,决不赶尽杀绝。在对土地的开垦上,按着大家族的分配形式,以山峦为界,部落之间不互相争夺。粮食够吃就行,决不互相侵占,更没有偷盗行为。在撒尼人眼里,自然的一切皆为神、为灵、为祖先留给他们的,不能随便掠夺、占有。
我一点也不怀疑,他们的生活本态和习俗是直接由天授予的。这个“天”,是自然,也是祖先。祖先把农具传给他们的同时,也是把生存的手段给了他们,更是把信仰和教诲给了他们,让他们牢记。撒尼人许多规矩都是慈悯的,比如:不能做坏事,做坏事会得到老天的惩罚。撒尼人笃信好人会得到“葫芦神”的救助。我常看见撒尼人家的房檐上铸立一只瓷葫芦,在窗子上悬挂起瓦罐,在村路口塑起虎和蛇的雕像,等等,就连最易生长的松树也成了撒尼人的吉祥之树。
在一家院子前,我还看见有一位老汉织渔网,那网口很大,一问是网大鱼用的网子。专用在山岩下的深湖区。檐下老汉的儿子在给另一位老人理发,那老人像个孩子,披着氅布,佝偻着腰。过新年理发,辞旧迎新。一路所见,全是此种景象。贴山根住的人家也是,撒尼女人坐小院绣彩色花布、擦洗锅碗盘盆或整理厨房;男人修补船只、整理农具、往檐下吊灯笼、往家畜圈栏上拴红布条。要过春节了,下地干活的人少了。家家户户院子里草料充足,特别是节前,不能随便消耗,喻示来年仓丰畜旺。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撒尼秘境》 作者:黄恩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