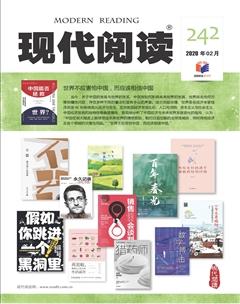对岸是苏联
2020-11-16
1969年开春的黑龙江上,冰封雪盖,我们从北安坐汽车颠簸了一整天后抵达黑河。作为到呼玛县下乡的首批上海知青,我们这帮毛头小伙子顾不得舟车劳顿,一下车便直冲黑龙江边,迫不及待地想要一睹对岸苏联的究竟。
在我18岁的头脑里,此刻的“苏联”这一符号,混杂着矛盾和多重意味:从昔日的“社会主义老大哥”、中国人最好的朋友和楷模,到卫国战争打败德国法西斯的英雄人民。小学时在一本杂志里读过一则故事,赞颂中苏边境地区人民的友谊,说苏联医生如何救助生病的中国居民,由此,也就第一次知道了呼玛这个地名,不承想若干年后竟会与我命运攸关。
然而,到我念小学四、五年级,即1960年代初,苏联的形象慢慢变得狰狞起来。下乡东北边疆,首先是冲着卫国戍边去的,不全是一般意义上的“接受再教育”。在我的内心深处,尽管还隐伏着一个曾经美好而亲近的正面形象,但如同那时大部分人一样,态度鲜明,毫不动摇地把“苏修”当作最危险的敌人看待。
早先东北人喊俄国人为“老毛子”,中苏关系恶化后,这一俗称就更流行。当地各级组织一再告诫知青们提高警惕,以防“苏修”对我村屯发起突然袭击。我在家信里,將一些上面传来的讯息告诉父母:说苏方已将他们自己村落的居民撤空,为避免暴露备战真相,晚间将房子点上灯玩“空城计”,只是烟囱不冒烟。还说苏方一反常态,春耕时节不忙种地,听不见拖拉机的轰鸣声……
我插队的新街基,恰巧坐落在中苏界河黑龙江畔,朝夕可见对岸的邻国山水。我头一次乘船在黑龙江上航行,是下乡一个多月后的事,我请假去县医院拍片检查。当时新街基不通公路,开冻后主要的对外交通靠乘船。那年虽有边境冲突,国境河流的航运却还照常。那是一种蒸汽动力的老式木壳大船。
船行当中,时有苏联边防军的巡逻艇擦肩而过。苏联军人举止随性,全然没有我们的紧张感,时而用望远镜朝我船瞭望,时而又嘻嘻哈哈,无拘无束。此刻两船相遇,他们仍十分礼貌地向我船主动挥手致意。出于一般礼节,我本能地想举手回礼。略环视周围,只见船上的中国旅客全都木然注视,无一人回应。忽然,我瞥见站在左侧的新街基边防站指导员伸手招了招,我也赶紧挥起了手,心说不能叫老毛子看低了中国人,以为我们不懂礼貌。
从新街基到呼玛县城的百多里航程,中间要途经两个较大的苏联村落,其中一个叫乌沙克沃。船过乌沙克沃时,江岸上有不少苏联老百姓,向我船热情招手,且频频呼喊。喊什么,听不懂,神态则显然没有敌意。
到黑河,少不了去江边转悠,碰巧赶上一场双方边防军的会晤。按边境事务规则,会晤往往由有事一方主动提议,挂旗告知对方。待双方商定后,再举行正式会晤,或在此岸,或在彼岸。那日我在江边,和几个路人一起目击了会晤结束时的一个场景。
从会晤室走出的苏联军官,个个身穿笔挺的灰呢长大衣,足登高筒皮靴,派头十足。几位中国军官陪同他们步下江岸台阶,目送他们登上回程的苏联巡逻艇。中方不忘给客人捎上一纸板箱的礼品,大约不外乎饼干糖果、鱼肉罐头之类。
后来我又见过一次双方会晤,也在近距离。会晤的级别显然比黑河那次低,我方只是连级的边防站。道别前,中苏军官轻松地互相敬烟,我清楚地听到,一位苏联军人用俄语感谢中国东道主敬他的香烟:“斯巴西巴(谢谢)!”他们中也有人向中方人员回敬俄式的大白杆香烟。
中苏两国分分合合的悲喜剧,终成历史了。后来,“老毛子”从敌人重又变回朋友了。
(摘自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民间记忆》 编著:《老照片》编辑部 本文作者:沈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