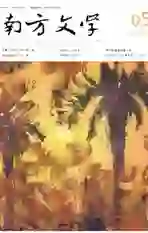两个跳蚤去跳海
2020-11-16谢丁
谢丁
一
2019年夏天,我和赋格前往爱琴海北边的这个小镇。镇子叫乌力诺波利斯,是通往圣山的门户。长途大巴在镇子中央的小广场停下。下车时,赋格把老花镜掉在了车上。他瘦了很多,走路步伐轻快,看不出实际年龄。我的样子估计很疲倦。这是八月底,海滩季快结束了,我们都晒得很黑。
这里很少有亚洲人。我们住在两百米之外的马其顿旅馆。当天下午,赋格去海滩游泳,我找了一块礁石,躺着晒太阳。海滩上有女人在游泳。赋格说,也许这些女人的丈夫都进了圣山,而她们只能在海滩消磨时间。傍晚,我们大吃了一顿,为未来三天存储脂肪。回旅馆的路上,我们在超市买了六块芝麻饼干,每人每天两块。我们对圣山半岛的物质状况一无所知。
第二天清早,镇上的圣山办事处排起了长队。每人缴30欧元,可拿到一张打印的圣山许可证。半岛上,吃住都免费,但为了这次行程,赋格写了十几封邮件,打了几十通电话,终于预订到三家修道院,分布在半岛的三个方向。这次不走回头路,除非我们信仰东正教,否则似乎没必要再来。因此这张证书值得纪念,得稳妥保存,我们小心地折叠起这张纸,放进背包。
九点半左右,我们朝码头走去。赋格穿了一件花衬衫,戴白色棒球帽。我穿黑色T恤和短裤。为了减少重量,背包里只带了一件T恤,一条长裤,一条内裤和一双袜子。有人说岛上不允许吸烟,我在背包里藏了三包烟。如果被发现,我就扔进海里。码头上,所有男人正从广场那边涌来,朝渡轮走去。岸上站着一个工作人员,也许是警察,没穿制服。他拦住了我们。
他指了指我们的下半身,露出的小腿,摇摇头,又摆摆手。我们背着包逆着人潮,回到码头的移动厕所。赋格说,他早上穿短裤时就有点担心。我说,露小腿是对神不尊重,还是对教士?站在厕所外,我们脱了短裤,换上长裤。穿裤子的时候,我担心下船时是否还要脱裤子检查。
这艘渡轮一共三层。第一层停放汽车,第二层是室内客舱,第三层是个带顶棚的露台。我们爬上了顶层的露台。
赋格找了个空座坐下。我卸下背包,搁在甲板上,然后倚着栏杆,看海底下的鱼。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鱼聚在水底,像一艘黑色潜艇埋伏在这艘渡轮底下。旁边一个男孩正在投喂面包屑。我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中一条鱼身上,看它抢到了多少面包块。它什么也没抢到。几分钟后,这里吸引了一群海鸥过来。那条鱼也许会被海鸥吃掉。
我扭过头,打量着这个露台上的男人们。甲板上弥漫着一种懒散的气氛,可能是因为强烈的阳光,也可能是没有女人在场,无人在意自己的形象。几个修道士站在角落,一身黑衣,留着标志性的长胡须。
一个老头出现了。人们还没搞清楚他是怎么出现的,他就从甲板隔层掏出两个巨大的黑色塑料袋,袋子里装满了各种小饰品,他全部倒在了甲板上。手链、十字架、项链和圣母像。他身上的教士服很破旧,导致人们对他售卖的东西也产生了怀疑。我走过去,挑选了片刻,买了一条手链。这条手链是皮制的,嵌着一个金色十字架。我戴在右手。
海水太蓝了,蓝得耀眼,水面上像铺了一层玻璃。一群海鸥跟在船尾,船尾翻滚着浪花。赋格说,你看到飞鱼了吗?我说,那是飞鱼?我以为那只是被螺旋桨卷起来的小鱼。听说海鸥跟着船走,就是因为可以吃到它们。船上有几个男人掰着面包屑,摊在掌心,海鸥漂亮地滑翔过来,像一尊雕塑停在空中,轻轻叼走了那片面包。我看着不远处的陆地,寻找圣山和乌力诺波利斯之间的分界线,没有河流,也没有栏杆或电网。我说,难道不会有女人就那么坦然走進去吗?
轮船开始在一些小码头停靠,每个码头几乎都有一个修道院,颜色鲜艳,像童话里的城堡。接着我们看到了一座庞大的崭新建筑,像一栋海边的五星级酒店。这家修道院看起来很有钱。赋格说,也许是俄罗斯的。
中午十二点,我们准时抵达了圣山的达芙妮港口。排队下船时,前面的修道士背着一个黑色大背包,两侧口袋里分别插了两瓶葡萄酒。背包很鼓,也许里面也是酒。
一下船大家就开始跑,跑向不远处的大巴车。我们行李不多,跑起来比别人快,上了车找到两个空位,赶紧坐下。很快车就满员了,但男人们还在往里面挤。他们全都又高又壮,走道上站满了人,几个修道士也站着,但没人让位。大巴车不情愿地上路了,开始爬山,沿途都是土路,玻璃窗外全都是飞扬的尘土。我们立即睡着了。
醒来时发现已到了一个小镇,名叫卡里埃斯,是圣山的商业交通中心。所有男人都下了车,沿街站成一排,行李全都搁在地上。画面有点诡异,可能是颜色太单一,也可能是太安静,或者只因为全都是男人。几个小男孩也无精打采,跟着父亲坐在街沿上。
赋格说,我们得先去办理通行证,再坐中巴车,去预订的第一家修道院。他说完就去寻找办公室。我跟那些沉默的男人站在一起。因为个子太矮,我觉得自己也像个被父亲带出来的小男孩。几分钟后,赋格回来了,说没找到办公室。他盯着墙上的各种通告看,但只有希腊字母,没有英文。然后他走进商店。商店老板说,往前走有个蓝色窗口,去那里问问。我们一起走过去。蓝色窗口的人说,办公室已经关了,明天才开,但你们想去的那家修道院太远了,现在没有中巴车了,只能坐船去,或者出租车,需要150欧元。听完后,我们都沉默了。我说,实在没地方住,镇上也是可以露宿的。赋格固执地绕了两圈之后,回到了蓝色窗口。那个人说,你们也可以去试试旁边的那家僧侣团,说不定那里有客房,走路几分钟就到。
到目前为止,卡里埃斯的情况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镇子虽然不大,但有一家咖啡馆,一个小型超市,超市里卖很多红酒,还有乌糟酒。我发现了我们昨天买的芝麻饼,这里贵四毛钱。镇上还有几家小商店,什么都卖,卖很多建材五金。有一家餐馆,屋子里坐了几桌男人。我们也走了进去。
赋格要了一份蔬菜沙拉。我点了一碗汤,汤里有很多豆子。面包很硬。吃饭时,我建议去那家僧侣团看看。
远远看去,那个僧侣团更像一座大修道院,而且是俄罗斯风格的。金色圆顶,富丽堂皇。我们走过大铁门,铁门上有一把大锁。穿过一个露天院子,过一座人行天桥,走进一栋像学生宿舍似的大楼。一楼右手第一间屋里,一个修道士正在整理桌上的玻璃杯。另外两个男人坐在沙发上,沉默地看着我们。
我们被安排在二楼的46号房间。走廊很宽敞,两边都是房间。和宿舍一样,楼层中间是盥洗室。房间里有五张单人木床,干净的床单和毯子,两个幽深的窗户,窗台上立着一个画框,画上是圣母玛利亚。修士临走时说,晚饭是四点,祷告五点半,八点锁大门,第二天凌晨四点又是祷告,接着是早饭,抽烟到大门外。我去厕所,撒尿时我看到了大海。
那天下午,我们决定只在附近转转。一走出大门,我就点燃了一支烟。我们几分钟就走回了卡里埃斯,又花几分钟逛完了小镇,再往前走,我们发现了一座外表破旧的修道院。赋格看了看地图说,这是圣山最古老的三个修道院之一。走进庭院,赋格进了小教堂看壁画,我坐在外面的走廊上。离我不远,坐着一个中年男人。我们互相看了很久,没有说话。
出了这家修道院,我们继续往前走,走到一个俯瞰大海的斜坡上。天空很蓝,海水也很蓝,山上全是绿色。我们坐在亭子里休息。亭子里有个修道士,摆了个小摊,也在售卖纪念品,比船上的便宜。赋格挑了很久,最后选了一串蓝白相间的编织手链。他立即套在了手腕上,越看越喜欢。他又担心时间久了会不会掉颜色。他说白色会逐渐暗淡。
下午四点,我们慢慢走回宿舍。食堂在对面的地下室,门还没开,院子里四处站着一些男人。因为人群比较分散,互相又隔得很远,这里看起来像一个熟悉的电影场景。所有人都沉默着,好像等这顿晚饭等了好几年。我低声说,四点已经过了。然后不知道哪里冒出来一队黑衣修士,急速地走下台阶,进了食堂。我们排在了队伍的最后。
这个地下室透着凉意,穹顶上挂满了吊灯。餐桌由十几个长条桌组成,摆成了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形。修士们坐在十字架的上方,客人坐在两边。赋格坐到了十字架的末尾,我坐在倒数第三桌。
每张桌子的食物都一样。盘子是铁制的,我好像听到了牙齿划过铁器的滋滋声。一盘鱼,分成了十几块。鱼盘里有几颗大土豆。一小碗蔬菜沙拉。两个铁杯,一个装了半杯酒,一个倒扣着,杯底放着四颗葡萄。此外还有一大盘葡萄和面包。
所有人全都站着。一个修士开始祷告,所有人立即坐下了。
我刚坐下,对面的那个男人迅速抢了一颗土豆。另一个男人瞬间拿走了鱼盘里的夹子。那个夹子再也没轮到我手上。我只好用叉子叉了一个鱼块,吃了一口,放下了。面包又酸又硬。我倒了一点酒,坚持喝完了。最后,我也没抢到土豆,只吃了几颗葡萄。
我身邊坐着一个年轻人,留着稀疏的胡子。他吃得卖力而且欢快。他一坐下就先吃了几颗葡萄,夹了两个鱼块,并且把鱼盘里的汤也倒进了自己的盘子里,用面包蘸着汤吃。他一共吃了十片面包,喝了半杯酒。当汤和酒都快没了,他把凉水掺进了剩下的酒里,吃光了最后的面包。这时,一直站在窗户前祷告的修士突然结束了祷告,所有人立即停下了手上的动作,站起来,排队走出了地下室。
走到外面,赋格说,这个葡萄是他这辈子吃过的最好的葡萄。
回到房间,其他三张床来了客人。一个年轻男人只穿了一条内裤,仰躺着睡着了。另一个很瘦的中年男人蜷缩着身体。第三个是老人,他睁着眼睛望着我们。没人说话。我们躺在各自的床上,再次立即睡着了。
醒来时,天还是亮的。只睡了十几分钟,却像睡了一夜。我们下楼,走到院子里。迎面走来一个人,端着一个大碗,碗里叠着一堆面包、西红柿和苹果。他拦住了我们。我发现他就是晚饭时坐在我身边的那个年轻人,看来他又去厨房拿了很多吃的。他费力地从裤兜里掏出手机,说要给我们一个网址,那里有东正教的很多信息。他用不熟练的英文说,那些信息都是中文。他说自己从俄罗斯来。他犹豫着,迟疑着,问我还要不要面包。
我们再次走出大门,又点燃了一支烟。又去镇子里逛了逛,最后坐在另一个眺望大海的凉亭里,再次睡着了。醒来后,我在亭子的栏杆上发现了一张海报,手绘的黑白宗教画。我们又坐了半天,没人前来。赋格最后带走了那幅画。
傍晚,天空沉下去了。赋格独自回到房间。我还在院子里走动,想找个僻静无人的地方抽烟,大门已锁上。但无论去哪里,我都会看见一两个男人待在那些角落。他们什么也没做,只是站着,沉默着,注视着一棵树或者天空。我最后放弃了抽烟,独自站在那里,看这些男人。
回到房间,赋格递给我一个冰箱贴,上面是一幅圣母玛利亚的画像。他说是那个瘦男人送的。他来自罗马尼亚,住在雅西。我想我坐火车去摩尔多瓦时,曾路过那个城市。
夜里十点,罗马尼亚人开始打电话。打到半途,他突然走到赋格的床边,把电话递给赋格,说他儿子在电话里。他打开了免提。儿子说,他父亲有些问题想问你们,他负责翻译。我躺在床上,打开电脑,记录了整个通话过程:
——我们每周日都要去教堂,你们去吗?
——我大多数时候待在家里。
——你们明天早上四点去祷告吗?
——可能会。
——你们明天早上会祷告多久?
——我们不知道祷告有多长。如果有英文,也许我们可以待长一点。
——语言其实不是问题。我去过好多教堂,我也听不懂,但只要用你的心,就能感受到。
——好的。
——在你们的宗教里,神是什么?
——如果你是佛教徒,也许没有具体的神,更像是一种哲学。
——那个冰箱贴上的图片,圣母玛利亚,很重要。
——我知道了。
——你手上戴的那个手链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今天才买的。
——你戴这个回去,朋友们不会让你摘下吗?
——不会。
——记得明天早上去祷告啊。
——太早了,但我们会尽量的。
这时走廊上传来一阵脚步声,有人敲门,大声吼道:小声点!赋格松了一口气。他拿起洗漱用具,打算去盥洗室。我突然看到,赋格一直戴着一副墨镜。自从丢了老花镜之后,他晚上只能用老花墨镜看手机了。
第二天,赋格摘掉了他新买的手链。
二
半夜三点多,黑夜中传来一阵敲钟的声音。第一道和第二道是敲的木板,第三道敲的是小铜钟,最后一次洪亮极了。我听见罗马尼亚人和老头在穿衣,那个只穿一条内裤的年轻大汉纹丝不动。赋格不作声响。等再次醒来,七点半,天已经亮了。我们收拾好背包,整理床单,叠好毯子,准备离开。
这时那个罗马尼亚人进了屋,看见我们要走,立即转身又冲了出去。我站在窗口,看见他冲出这栋楼,跑到了大门处的礼品店,然后又迅速冲了回来。他手里提着一个纸袋,好像是买了东西。我隐隐觉得不对,跟赋格打了招呼,先出了门。在楼梯间,那个罗马尼亚人拦住了我,从纸袋里掏出一条项链。我不知所措,任凭对方把项链挂在了我的脖子上。那是个木头的十字架。随后那罗马尼亚人进了屋,我听见一阵争论。赋格出来后说,他没收下那条项链。
在楼下,我们又碰到了那个年轻的俄罗斯人。他刚吃完早饭,手里没拿任何东西。他再次掏出手机,试图打开那个链接。他亲切地称呼我们为兄弟。他的华为手机屏幕裂了一道缝,让我在手机里输入电子邮箱地址。然后他从挎包里掏出一个无线网络发送器,关掉手机,重启,看见邮件发送成功,他才放我们离开了。
赋格说,这个年轻人长得不像斯拉夫人,也许身上有蒙古人的血统,而且眼神里有一种谦卑。我说,他应该没有恶意,那个罗马尼亚人也没有。
我们走到镇上。小广场再次站满了男人,大家都在等中巴车。咖啡馆人不多,我们走进去,要了一杯咖啡,一杯茶,两张菠菜饼。坐了一会儿,这里就挤满了人,外面也是黑压压一片,路上全都是行李,还有人带了户外装备。赋格说,可能是去露营的。我们看了地图,发现第二天预订的修道院在海边,离镇子只有几公里,并不远。我们决定走过去。
走下一道斜坡,又走上了一条水泥公路,往东海岸方向走,可是海到底在哪里呢,我们也不知道。我关了手机,赋格偶尔看看地图,路上其实有指示牌,而且也没什么车,更没有行人。上午的太阳一点儿都不烈,公路两边全都是树。我们像行走在一座大山森林的腹地。有时回头望,我能看见背后的整个山脉起伏,大片大片的绿色中间,会突然出现一些五颜六色的建筑,一些金色的圆形尖顶。可能是隐士自己修的房子,我听说很多人在这里悄悄地度过了一生。天空就像海水那么蓝,有时出现一些云朵。我们心情很好,讨论着那个罗马尼亚人,那个俄罗斯年轻人。我有點后悔,是不是态度不够友好。如果我也有信仰,该多好。
突然看到了海,海边就是那个修道院。赋格说这是圣山规模最小的一家,建在海边一个巨大岩石上。走到近处,我们在一个很像罗马式水渠的地方停下来,水渠也许还在使用。我抽了一支烟,再和赋格走向大门。
接待处是个非常小的房间,一个修士坐在屋里。他很瘦,留着长胡子,因为太高了,他站起来的时候仿佛要顶到天花板。他倒了两杯水,抓了三颗土耳其软糖放在盘子里,然后坐下来,坐在房间的角落。他慢吞吞地轻声说,这个修道院有五百年历史了。晚上六点和凌晨三点祷告。他说,你们从中国那么远的地方来吗?赋格说,很早就想来了,但现在才拿到了许可证。他又问你们是东正教徒吗?不是。那么祷告时只能坐在最后面,不能进里面的小教堂。
然后大家都沉默了,我们只好分别吃了一颗糖。
修士拿上钥匙,我们跟着他,没进修道院,却走到了外面水渠边上的一栋两层小楼,看样子是新建的。一共十个房间,共用两个卫生间。我们住在八号房,屋里有三张木床,铺着淡蓝色的床单,一条毛巾。还有一张桌子,桌上一盏玻璃煤油灯,盘子里有一盒火柴。修士说,走廊上有充电的插座,但晚上六点后就没电了。我朝窗外望去,可以看到一片菜地,再远一点点,还能看见大海。
十分钟后,我们听到了打铃声。午饭在大门内侧的二楼,我们迟到了,楼上传来集体坐下的声音。这个食堂很小,墙上都是壁画,好像坐在文物里吃饭。窗外就是海,能听到海浪拍打着礁石。就餐的人也很少,除了几个修士,客人不超过十个。我对面坐着一个亚洲男孩。除了我们,他是我在圣山看到的第一个亚洲人。食物很简单,每人一盘绿豆汤,汤里有洋葱。大家分享一篮面包,一盘橄榄,一个切成四份的大西瓜。最后,每人可享受两个西红柿。我全部吃掉了。
吃完饭下了楼,赋格说,这可能是圣山最舒服的住宿地了,但这里这么好,我们凌晨三点要去祷告吗?
接下来,我们有一整个下午可以闲逛。修士说,可以沿着海边的悬崖步行,朝两个方向走,都有修道院,都需要一个小时。我们随便选了个方向,往北走,走进了一条林间小路,地上全是落叶,枯黄的落叶。我们闻到了一股臭味,往下看,是一个垃圾场。这条路似乎很少有人走,爬坡,再下坡,弯弯曲曲,有时前面好像根本没有路了,我们不得不顺着岩石滑下去。有时一条水沟挡住了去路,如果下雨,肯定是过不去的。我捡了一根树枝,害怕有蛇。每次踩在树叶堆积的路面,我都听见旁边的草丛似乎有动静。我看见一条很小的四脚蛇爬过前方。赋格说,他听说山上有狼。我说狼群会在白天出现吗?我们途经一个废弃的房屋,建在临海的一处峭壁上,也许是某个隐士突然想回到尘世,因此把房子丢在这里了。然后前方突然跑来了一只狗,套着项圈,它的主人在后面追过来。我们还碰见了三个少年,嬉闹着从身边经过。最后,当我们终于抵达了那家修道院,站在已衰败的海滩上,我看见一个巨大的十字架,立在一个巨大的礁石上,好像在朝我发出怒吼。
一个小时后我们开始往回走。在那家修道院,赋格什么也没看见。他等待着小教堂开门,想看看里面的壁画,他等了很久很久,但没人理会他。我们原路返回,再次踏上了那条曲折的山路,又碰见了那三个少年,那条套着项圈的狗,狗的主人,闻到了垃圾的味道。但回程的时间似乎快了很多。我想怎么总是这样,去程很慢,返程很快。就像活着是很慢的,死却很快。
回到房间,我突然感到了一种自由。因为这个宿舍楼建在修道院外面,所以没有大门,我们甚至可以深夜走去海边,随时去户外抽烟。我刚到时就发现了走廊外放着两个烟灰缸。赋格打算洗澡。我带了一本书,走向海边。
在修道院大门的不远处,有一个悬崖露台,搭着葡萄架。我找了个木桩坐下,凉风吹来,身后的十几米下面,惊涛拍浪。有一阵我没看书,望着远处的圣山,那山名叫阿索斯,是这个半岛上最高的山峰,峰顶似乎还有积雪,是白色的。我犹豫着,要不要跟坐在旁边的人打招呼,就是那个午饭时坐在我对面的亚洲男孩。
他又瘦又小,穿一件皱皱的花衬衫,戴着眼镜,手腕上有一块黑色电子表,还戴了几串黑色手链。他低着头,正在看一本像字典一样的书。我打了个招呼。他没反应。我又大声叫了一句。那男孩回过神来,好像突然发现这里还有一个人。他脸上的表情似乎很高兴,但英语不太顺畅。他说他来自印度尼西亚,21岁,要在这里待一年。我听到一年,僵住了。男孩窘迫地笑了起来。他说已经待了两个月,还剩下十个月。我问他看的是什么书,他说是词典,他正在学习希腊语。他问我来自哪里,我说中国。他说他有一半的中国血统,父亲是中国人。他有个18岁的弟弟,两个姐姐。但是全家除了他,其余都是穆斯林。读高中的时候,他被书上的东正教堂吸引了,他想知道这个宗教到底是怎样的。他说印尼差不多有二十万东正教徒,却没有一家修道院。如果他能在这里成为一个修士,他最终会回到印尼,建一个修道院。我说,钱呢?男孩说,先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他目前面对的问题是,除了学习希腊语,他还想学俄罗斯语。我没说话。男孩说,听听你内心的召唤。
这时来了一个没戴帽子的修士,他的黑色长袍卷到了腰间,叼着一支烟坐在男孩身边,看起来像个嬉皮士。男孩说,这是我的希腊语老师。
我回到房间,马上把这个男孩的故事告诉了赋格。他洗完澡躺在床上,盯着手机看资料。他好像不太关心,心不在焉地问了几个问题。我想他是出于礼貌才问的,而昨天晚上被那个罗马尼亚人缠了那么久。他此刻还戴着那副老花墨镜,说他查到了一些这家修道院的资料,这里有一个非常珍贵的文物,是一幅圣尼古拉的画像。据说人们无意中从海底捞出了这幅圣像,一只牡蛎粘在圣尼古拉的额头。扒开牡蛎后,这位圣徒的额头流出了鲜血。
六点过了,我们离开房间,走进了修道院。在小教堂,我们只能坐在最靠外的一排椅子上。屋里很黑,我们花了好长时间才适应光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怪的香味。难熬地坐了十几分钟后,我们悄悄走了出去。晚饭前,我在露台抽烟,赋格在翻读一本《圣经》。晚饭和中午几乎一模一样,但西红柿少了一个,西瓜变成了红色大李子。
天快黑了。我提议去海边散步。我们沿着一条小路走下去,到了一个废弃的码头。这里还有几处房屋,停了两艘小船。赋格说,明天三点怕是起不来了。我说算了,我不会再来了。赋格说,我也是,不会再来了。我们又慢慢走回去,经过了白天看到的那一大片菜地,种着茄子、西红柿、南瓜、豇豆,以及绿油油的青菜。
回到宿舍,走廊上点起了煤油灯。卫生间和淋浴间也都点上了。赋格躺在床上,我觉得屋里很闷热,走到外面抽烟。凉爽的海风吹过来,我听到远处传来一阵窃窃私语声,找了很久,也不知在哪里。
晚上十点,我还没睡着。我起床出了门,走到户外抽烟。石阶上坐着两个年轻人,一边卷烟一边聊天。我坐在旁边,一抬头,突然发现满天都是星星。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明亮的天空,像一张密密麻麻织成的网,每一个交汇处都有一颗星星。我跑回房间,把赋格叫了出来。最后,我们四个人坐在台阶上,全都仰着头。赋格指着空中的一条带子,说那就是银河。他上次看到银河还是小时候。他说,有一年在阿富汗旅行,中途在沙漠里过夜,他也看到了类似的天空,但那次仍然没有今晚的好看。我说,月亮呢,月亮不见了。赋格喃喃自语,真好啊。我又说,我们是不是太渺小了。赋格说,真好啊,一颗流星划过去了。
三
第三天中午,我们回到了卡里埃斯,坐在同一个餐馆里,柜台里的蔬菜沙拉也没变。我们点了两盘茄子,一份豆子。这是我们在圣山吃过的最满意的一顿。赋格说,他想明白了,因为这些菜有油水,难怪昨天在修道院的食堂,他看见有人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小瓶橄榄油。
刚吃完,门口走进来一个人,朝我们挥手。又是那个年轻的俄罗斯人。
他换了一件白色T恤,黑色长裤,肩挎着一个黑色小包,手里还拎着黑色提包。他睁大眼睛望着我们的样子,好像是神的旨意把他带到了这里。他问我们什么时候走。明天。明天去哪里?回塞萨洛尼基。太好了,他惊喜地叫道,你们一定要去塞萨洛尼基的一个修道院,那里有一座圣徒的墓。我们说,好,一定去。但我想肯定不会去的。他又掏出了手机,问我收到邮件了吗,我说上不了网。他打開手机,在邮箱里寻找已发送邮件。我探头看了看,他一共发了五封邮件给我,发送人叫亚历山大·切尔托夫。
亚历山大就这样站在桌边,没坐下,但也没走,他又陷入了迟疑、犹豫的状态,好像舍不得离开我们。有一会儿他打算走了,到了门口又转身回来,掏出一支笔和本子,开始在上面写字。他写了整整一页半,还画了一张地图,告诉我们如何寻找那家修道院。最后他终于决定要走,倒退着一步一步离开,他挥手告别的时候,我想再也见不到他了。
赋格说,他的皮肤很好,甚至是透明的。
我说昨天晚上蚊子特别多,几乎没怎么睡。半夜我问赋格,明天下午有没有船离开这里。我问了三次,赋格都没回答。赋格说,我以为你在说梦话。我问他,只剩下一天了,还要裸泳吗?他说,就今天。
我们坐上了开往第三个修道院的中巴车。沿着海边的公路风景很美,但我们立即睡着了。醒来是下午两点。下车时,我看见这家修道院有一个巨大的停机坪,但我从没听到过直升机的声音。
接待处的年轻修士严格遵守了四道待客程序。首先端上来一盘软糖,接着是一杯凉水,然后是一杯酒,最后是咖啡。我说这里太奢侈了。赋格说,这是圣山的第一家修道院。年轻人介绍说,下午五点祷告,接着晚饭,凌晨四点再祷告,早上六点半有中巴车,但需要登记。厕所在楼下,他警告,去厕所不能穿短裤,必须要穿拖鞋。所有这些规则都用英文贴在了墙上。
这几乎是一栋全木结构的房子,我们的房间在三楼。屋里共有十一张木床,北边靠窗的两个床位已经被占了,我们赶紧占领了南边靠窗的两张床。推开窗户,眼前就是大海。我们好像住到了梦中的地方。
我把背包里的东西腾出来,搁在床上,然后出门下了楼。大门外有一条土路,看不到尽头,也许是去海边的。我们沿着那条路默默往前走,但越走越没底,这条公路始终与海岸线平行延伸,没有拐弯的意思。我突然看见旁边一条小路,杂草丛生,好像荒废已久。我率先走了进去,赋格在后面跟着。两边的树枝遮住了视线,看不到这条路通往哪里,有时踩在倒掉的枝蔓上,有时不得不拨开树丛。最后,我们跳下了一个小坡,到了海边。
眼前也是一个废弃的码头,跟昨天晚上见到的那个码头很像,一个停靠船的仓库,还有个小港湾,但明显已很久没人来过这里。岸边的石头屋,只剩下了石墙,屋顶不见了。我们在废墟里走来走去,直到看见一个破旧的小木门。推开那扇门,迎面一阵海浪袭来。这里有巨大的礁石堆,海水清晰见底。朝四周望去,看不到公路,只能远远看见半山腰的修道院。
赋格放下背包,取出一条围巾。他说如果有紧急情况,或许能遮挡一下。然后他顺着礁石溜下去,走到水边。他叹了口气,忘了带拖鞋。
我没敢下去,也不会游泳。我坐在上面的礁石上,点燃一支烟。然后我脱掉T恤,半裸着躺在石头上。阳光射在皮肤表面,我感到自己正在变黑。礁石下面,赋格慢慢脱掉了衬衫,长裤,内裤,光溜溜地走向水里。水温也许很凉,他花了好几分钟才把自己全部沉入水下,然后挥动手臂,朝更远处游去。
有时我好像听到了一阵耳语声,朝树林望去,什么也没看到。也许这个下午,在圣山的最后一天,就应该这么刺激地度过。赋格一丝不挂,我也半裸着,而这里连上厕所都不能穿短裤。然后我打了个盹。
半个小时后,也许十几分钟,赋格游了回来,爬上礁石。他把围巾围在腰间,坐了片刻,晒干了身体,慢慢穿上衣服。他说,够了。我们把东西塞进背包,回到那扇木门,走回废墟,再沿着刚才的土路往山上爬去。太阳越来越烈,我们都没带水,渴得厉害。不知怎么,走到了一条小路,路中间铺了一些白色的大理石,蜿蜒着伸向修道院。这是一片漂亮的橄榄林,橄榄已经熟了。如果不是很渴,我们可以在这里坐一阵子的,但两个人都没说话,沉默地继续往上爬,直到站在了修道院的吊脚楼下。
回到房间,赋格直接去洗澡了。我躺在床上,盯着窗外的蓝天。对面的两个人回来了,一个老人,一个中年人。老人说他来自摩尔多瓦,中年人是他儿子,如今居住在西雅图,这次专程陪他到圣山。他们说,这里出现过很多神迹,世界各地的人都想到这里来,尤其是那些有伤痛的,你们来这里干吗?我说,我们有其他的伤痛。钟声又响了,两个摩尔多瓦人迅速离开,祷告的时间到了。
赋格推门进来,我说对面是一对父子,两个摩尔多瓦人,老人可能生病了。随后我也换上长裤,穿了拖鞋,去二楼洗澡。淋浴间有隔断,地上的中央嵌着一块白瓷,我站在那里,想了片刻,这几天遇到的人都是来治疗伤痛的?很快地上积满了水,地漏出了问题,水已经漫到脚踝了。
晚饭前,我们坐在院子里的石阶上。几个修士和客人在附近游荡,等待吃饭的钟声敲响。一个拄着拐棍的老修士突然走了过来。听说我们从中国来,他说他年轻时是个海员,他的货船原打算运送一批货物,从里约热内卢前往中国,但刚出海就出事了,他再也没去过中国,眼睛也受了伤。然后他拄着拐棍缓慢地朝食堂走去。
这家修道院有一个硕大无比的食堂,以前可能是个大教堂,墙上有很多壁画,但整个屋顶却没了,如今是一块临时搭建的蓝色棚顶。桌子也很有特点。桌面是一块白色圆形大理石,围成一圈的凳子也是石头做底,铺着木板。食物也很奢侈。每人一盘主食,由黄瓜、青椒和大米煮成的稀粥,桌上有几盘西红柿,一盘苹果,一盘橄榄,一盘黄瓜,以及一大篮面包,随意取用。
我们已经有了经验,必须在修士祷告结束之前吃完晚饭。祷告有多久,你就可以吃多久。我迅速吃完了米饭,但祷告的时间太长了,我只好开始吃橄榄。吃到第二十颗橄榄时,祷告结束了。
大家排着队离开食堂,又各自散去。我们走向大门,门外的山坡上有一座凉亭。我坐下来抽烟,看着碧蓝的海水。摩尔多瓦父子也来了,他们打了招呼,再也没说话。还有两个希腊人正在交流一款单反相机。天色正在暗下去。赋格说,这里八点关门。我说如果允许,我可以在这里坐到明天,甚至永远坐下去。我问赋格,如果一个人到了圣山,没有离开,但是也找不到了,警察怎么办?赋格说,只能等待你的尸体被人发现了。我说如果是在海里,就彻底消失了。
夜里十一点,我还是没睡着。我没听见蚊子的呼唤,但全身瘙痒难当。起初是脚,然后是腿,手背,手臂,最后痒到了脖子。我用床单裹住全身,忍了一会儿,等赋格从厕所回来,我说这里不能睡了,床上有跳蚤。赋格呆立了片刻,没敢坐下,说,去外面吧,外面有凳子。
我们悄悄掩上房门,走了出去。三楼这里有个非常宽阔的走廊,有一个长桌,两条长椅,正对着修道院内的院子。院子中央的小教堂此时漆黑一片,远处有一排平房,屋檐下挂着一盏路灯。赋格开始看村上春树的游记,我坐在长椅上,感觉身上有虫子在游动。我摸了摸脖子,那里出现了一长条鼓起的肉包。借着走廊的灯光,我开始看一篇侦探小说。
半夜两点,我再也坐不住了。我想下楼去看看大门是否真的锁上了。如果锁了,我打算冒险在院子里抽一支烟。我一步一步小心走下楼梯,木板咯吱咯吱。踏上院子的石板地时,我松了一口气。院子里有凉风吹来,我抬头看天空,星星没有昨天那么明亮,也许是楼上走廊灯光的缘故。我走向大门,紧锁着,通道黑漆漆的。然后我张开耳朵听了半天,除了海浪的声音,没有任何脚步声。我站在通道里,点燃了一支烟,刚吸了一口,赶紧灭了,好像哪里不太对。往回走,走到楼梯口,我突然听见石头墙里传来的呼噜声。爬到三樓,赋格问,你去哪里抽烟了?我说,在一片阴影里。几分钟后,我们听见院子传来脚步声,一个修士似乎正在巡逻。而走廊上又多了一个人,赋格说,那个人是从另一个宿舍走出来的,可能也被跳蚤咬了。
赋格躺在长椅上睡着了,他没戴墨镜,但戴了一副眼罩。
凌晨四点,祷告的钟声敲响了。我下了楼,大门仍然紧锁,整栋宿舍楼都没有人出来,看来不会有客人起床了。我独自朝小教堂走去。教堂外的小走廊仍然一片黑暗,没有开灯。在黑暗中的阴影里,我看见几个黑色的影子坐在那里。小教堂的门敞开着,我走了进去,发现只是外屋,头顶有一盏吊灯,点着两根蜡烛。我在墙根找了个座位,静悄悄地坐下。几分钟后,我的眼睛适应了这里的光线。我看见两个修士站在内屋门口两侧,对着墙壁祷告,墙上是壁画,画的是圣母玛利亚。他们面前各点了一支蜡烛。偶尔,从内屋出来一个修士,甩着铃铛,飘着奇怪的香味。有时他们手里拿着蜡烛,绕着墙壁行走,嘴里念念有词,再亲吻一下墙壁上的画像。我一动不动,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些人。不知道是天快亮了,还是蜡烛点多了,我觉得这房间越来越明亮。但我没有感觉到神明,也没有听到谁的召唤,我甚至有点困了。不过,我认为在这里待下去,就像这样,像一个黑暗中的影子,贴在墙壁上,也未尝不可。但是几个小时后,我们就得坐船离开这里了,回到乌力诺波利斯,然后再回到塞萨洛尼基。可是接下来,我又要去哪里呢。一想到这个,我快要在黑暗中哭出来了。
四
达芙妮的码头上到处都是人。我看见了几条流浪狗,还有很多很多猫。我买了一张快船的票。赋格买了慢船。中午十一点五十,快船先来了。我排队上船,直接爬到了顶楼的露台,找了个座位,放下背包。
船开了,我站起来倚在栏杆上,朝码头望去。赋格站在露天的等候区,挤在人群里。我试着挥挥手,但他没看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