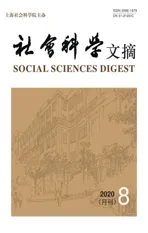现代政治与道德:涂尔干与韦伯的分殊与交叠
2020-11-16王小章
文/王小章
作为经典社会学的两大家,涂尔干与韦伯既分处法德两国不同的思想传统和历史命运之下,又分享着共同的现代性时代背景,在许多问题上,他们既呈现出显著的思想上的分殊,又常常表达出共同的关切。这种分殊与重叠,同样体现在他们对于现代政治与道德关系的思考上。
政治何为:现代政治的正当性
涂尔干和韦伯对于政治与道德之关系的思考,无疑首先必须从他们对于“政治”的理解开始。
涂尔干对于政治的理解源于对“公民道德”的关切,从对“政治社会”和“国家”的探讨开始,落脚于现代民主制下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涂尔干认为,政治社会的基本要素,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拥有权威的人和服从权威的人之间的关系,政治社会的权威就是最高权威。国家,就是被委托代表这种权威的公职群体,是统治权威的代理机构。而“公民道德”所规定的义务,就是公民对国家应该履行的义务,其内容取决于国家的性质与功能。那么国家的功能或者说目标是什么呢?涂尔干指出,对此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解决方案。一种是个人主义的方案:社会只是个人的集合,国家的作用,只是防止个人对其他人进行非法侵越,使每个人维持在其权利领域之内。另一种则是“带有神秘色彩的方案”,每个社会都有与个人目标无关的、高于个人的目标,国家的目的,就是要执行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目标,而个人,只能是施行这一计划的工具。在指出了这两种“截然对立”的方案之后,涂尔干通过对历史的简要追溯指出了与上述这两种方案显然矛盾的事实:“一方面,我们确认国家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个人积极对抗国家权利的权利也同样获得了发展。”如何应对这一难题?涂尔干采取的方式类似于马克思将人的自由不是看做单个的孤立个体所固有的东西,而是在历史中不断发展和实现的进程:个人权利不是先天固有的,人之所以为人,只是因为他生活在社会之中,如果把所有带有社会根源的事物全部从人那里排除掉,那么人就是动物;正是社会提升、滋养和丰富着个人的本性。而“国家的产生并不是为了防止个人滥用自身的自然权利:不,国家绝非只有这样的作用,相反,国家是在创造、组织和实现这些权利。”“解放个人”“创造、组织和实现”个人的权利,这就是涂尔干所认为的作为政治社会之最高权威的国家的目标,也就是伦理的世界中“政治的家园”之所在,或者说,政治之道德正当性之所系。
跟涂尔干一样,韦伯对于政治的理解也从对“国家”的理解开始,不过,韦伯对国家的理解与涂尔干不同:国家“是这样一个人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这或是发生在国家之间,或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团体之间。”献身于政治,就是投身于这种在国家层面上展开的权力斗争,特别是对“暴力的合法使用权”的争夺。而献身于政治的根本价值是什么,也就是在最终的意义上,争夺这种对暴力的合法使用权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目标而去争夺和使用这种“暴力的合法使用权”才具有道德正当性?
如同在“国家思考的取向”上,涂尔干面临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解决方案,在韦伯之前,德国也存在着两种主要的有关政治之道德正当性的理念。一种以康德、洪堡为代表,主张个人的自由权利是根本的政治价值,国家若不是个体自由的条件,政治若不是为了捍卫自由权利,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其存在的正当理由。一种以黑格尔为代表,基于国家不是为了保卫个人自由权利而人为建构出来的人造物、而是有自己的自然生命的有机体这种认识,认为,政治的根本价值和目的,就是国家的实体性权力。韦伯在“政治”上从根本上讲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就韦伯关于“政治之使命”的立场而言,根本上还是民族主义的。德国是单一民族国家,因此民族主义事实上就是“国家主义”。在政治行动中,凡事都要以德意志民族的生命和力量为取向,是韦伯最基本的政治观念。但需要说明的是,民族主义乃是就韦伯关于“政治之使命”的立场而言,而不代表韦伯在个人自由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紧张面前的终极抉择。比瑟姆曾清理概括了韦伯在使用“自由”这一概念时的三种涵义:第一,经济个人主义的自由;第二,公民与政治的自由;第三,偏于精神的人的自主性或人格形成的能力的自由。在这三种自由中,只有第二种涵义的自由,在性质上才是属于“政治”的。不过,除了这种“政治的”自由,还有两种涵义的自由。第一种涵义的自由在韦伯看来随着大工业时代的来临在现代社会中正在消失,况且这是一种非政治的价值,其层次“低于”政治,因而必须服从于政治的价值。第三种涵义的自由,这种自由事实上是指在现代社会价值领域中“诸神复活”的前提下,每个人自己选择操持自己生命之弦的“守护神”而成就一种“人格”的问题,涉及的是个人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这固然同样是非政治的价值,但是,在韦伯的这里,是一种高于政治的价值。
大众、政治家与政治:现代政治参与者的德性
涂尔干与韦伯在理解“政治何为”、在认定“政治”的道德正当性上存在明显的分殊,那么,在这分殊背后,他们又面临着共同的、现实的政治运作所必须面对的时代特征:这是一个大众社会的时代,这是一个民主化的时代。
涂尔干区分了两类社会意识。第一类来源于社会的集体大众,分布于大众之中,由各种情感、理想和信仰组成,渗透于每个人的意识之中;第二类来源于国家或政府这种专门的机构。而所谓民主,就是一种具有反思性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下,一方面,公民和国家之间存在一种持续不断的沟通,对个人来说,国家不是纯粹作为外在强制力为他们注入一种完全机械的动力,另一方面,国家依旧保持着其“优先的位置”,并非一味顺从公民,仅仅是公民意志的单纯回应。但是,这乃是涂尔干期待的“民主的政治体系”运行的理想状态。而问题的严峻性恰恰在于,在现实中,在“个人是社会的主导原则,而社会仅仅是个人的总和”的现代个体化、原子化的大众社会状态下,上述这两个方面事实上都面临着威胁:要么国家完全听命于“个体组成的大众”;要么国家以“强有力”的形式脱离公民的有效影响而牢牢地控制住公民。如何避免这种状态?涂尔干的回答明确而简单:我们的社会疾病和政治疾病同出一源,那就是在个人和国家之间缺乏次级组织,因此,解决社会疾病和政治疾病的不二法门,就是重塑这些次级组织,经由各种中介群体的集体生活而型塑社会化、道德化个体,而这种中介群体中最根本的就是职业法团。
在关于“政治”的根本价值上,韦伯的基本取向与涂尔干不同,是民族主义的,但置身于今天这个时代,民族主义的目标只能通过赋予公民以“平等选举权”的民主制来实现。尽管在对于“民主”本身的理解上,韦伯与涂尔干不同,但他与涂尔干一样,把民主看成是促成现代社会(民族)整合的不二途径。
不过,肯定大众参与的民主对于现代社会整合、对于民族走向“政治成熟”的意义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依旧与涂尔干一样,韦伯注意到“大众民主”本身对于现代政治在他所理解和期待的正确方向与轨道上的良性运行来说也包含着巨大的威胁。对于“大众”的“群氓化”或“暴民化”倾向,韦伯有着与涂尔干一样的、甚至更深的担忧与警惕。在韦伯看来,对于负责任的重大政治决策来说,大众是绝对不适合的。作为“近代大众民主制之必然的伴随物”的官僚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平衡、克制大众非理性的冲动与激情。但是,就官僚制本身而论,它只是一架“机器”,它真正适合的是“行政”,而不是“政治”。于是,韦伯的基本思想是,糅合了大众普选、官僚制和强议会制的领袖民主制:大众普选在通过普遍的政治参与促进民族的政治整合、政治成熟的同时可以使当选政治家获得“克里斯玛”的权威;获得“克里斯玛”的权威的凯撒式领袖能够摆脱官僚制的掣肘,并能驱使它服务于他的目的,从而实现领袖“挟官僚机构”而治;而强议会,则是现代社会中政治领袖的训练基地。接下来最后的一个问题是:当恺撒式的政治领袖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之后,当一个民族由一个天才政治家来统治之后,会不会又重复俾斯麦统治德国的情形呢:“对一个政治家的人格毫无节制的赞美,竟导致一个骄傲的民族那么彻底地牺牲了自己的客观信念。”由此,韦伯提出了它著名的责任伦理理念:“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龄大小),他意识到了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在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令人感动的表现。……就此而言,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便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惟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
“政治成熟性”的道德维度
“政治成熟”是韦伯一直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政治成熟”或“政治成熟性”可以分为三个彼此联系的层面。第一,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政治有自己的、不同于其他领域的价值目标和追求。政治成熟的第一个层面,就是清楚地领悟到这一点,进而能够认识把握这种特定“政治的”的价值目标。第二,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政治有自己的、不同于其他领域的运行法则。政治成熟与否的第二个层面,就是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对此有清醒的意识,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能把这种法则作为无法回避的现实加以接受,并围绕着上面所说的“政治的价值”而冷峻务实地在这种法则下使政治有效地运行起来。第三,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衡量评价政治过程之参与者的行为有着与衡量评价其他领域中的行为所不同的特定原则或标准。第三个层面的政治是否成熟就是,无论是作为行为者,还是作为观察者,是否能够清楚地认识、使用、贯彻这种“政治的”评价标准或原则。
如果我们将上述三个层面看做观察衡量现代政治成熟与否的三个一般性的层面,那么,从道德的角度来分析这三个层面,则实际上凸显了衡量“政治成熟性”的两个道德维度,那就是上面所说的政治本身的道德正当性与政治运行过程之参与者的伦理德性。第一个层面即“政治的”价值目标关联着政治本身的正当性:这一维度上的政治成熟意味着能够理性认知、准确把握这种价值目标;而全部三个层面又共同对政治参与者提出了必需的伦理德性上的要求:这一维度上的政治成熟意味着能够自觉地使自己合乎这种要求。
回到涂尔干和韦伯的比较。关于“政治的”价值目标,置身于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之后共和主义和保皇主义长期对峙的法兰西,涂尔干旗帜鲜明地反对极端民族主义,而将“解放个人”“创造、组织和实现”个人的公民权利,以完成法国大革命所启动的事业,促成在“道德个人主义”基础上从传统社会秩序向现代工业社会秩序的转型,视作作为政治社会之最高权威的国家的目标,现实的“政治”,唯有在这一价值目标之下运行,才算把握住了“政治的”正确方向,才显示出其在这一维度上的成熟。与此不同,置身于德国当时的时代背景,韦伯在“政治的”价值目标取向上明确坚持“国家理由”,把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实体性权力作为政治的“终极决定性价值”,明确并不动摇地把握和坚持这一点,是政治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不过,这种对立并不否定两者之间存在的相通性。这并不仅仅在于涂尔干和韦伯都关注重视“政治的”价值目标取向这一对于现实政治的运行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更在于,他们都是联系其所置身的具体历史语境,从民族国家的“时代命运”推导出现实政治的使命。“政治的”的使命是一种“历史的”使命,或者说,“时代的”使命。实际上,不仅对当时的德国、法国来说是如此,对于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包括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的当今中国,也同样如此。
“政治的”价值目标关系着政治本身的正当性,关系着“政治”的“正确性”,政治参与者的伦理德性则关系着政治能否在“正确的”价值目标取向上有效地运行,关系着现实政治运行的有效性。涂尔干和韦伯的思想都认识到并肯定大众参与对于现代政治有效运行的动力意义,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都敏锐地注意到大众参与的民主所潜在地包含的对于政治之有效运行的威胁。这种威胁的关键在于,仅仅作为“个人的总和”的大众,一方面往往是情绪化的、冲动的,另一方面其释放出来的则又通常是“只与自身相关”的利己主义。如何克服这种共同的威胁?涂尔干与韦伯所关注的侧重面是不一样的。涂尔干关心的是如何使构成大众的利己主义个体得以“道德化”,即通过重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各种中介组织,特别是职业法团,通过将原子化的个体吸收进这些中介组织,以此培植型塑个体的“集体心灵”,也就是公民德性、公共精神。而韦伯,基于其在“政治上”对大众民主和大众本身所持的“工具主义”态度,将关注的重心投放在属于少数掌握权力的支配者一方,即官僚和政治领袖一方,特别是政治领袖。也许,分开来单独看,涂尔干和韦伯各自都只涉及了一个侧面,不免各有所偏,而且这种“所偏”,显然与涂尔干和韦伯分别所处的近代以来法德不同的政治和政治思想传统密切相关。不过,如果我们脱离开涂尔干和韦伯的具体而特定的语境,并且在经历了现代不同形态的极权主义灾难和痛苦之后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他们各自的所偏,那么,也许不能不说,相比涂尔干,韦伯的所偏显然更引人注目。确实,韦伯对于领袖责任的强调一定程度上可以使他免于“为希特勒铺下了康庄大道”的指责,而且,像卢卡奇、雅思贝尔斯等与韦伯有过深切直接交往的人也都为他做了辩护,但是,一方面,韦伯对大众民主的工具主义态度确实隐伏着走向“选举专制”的可能;另一方面,韦伯对于普通公民作为国家主人之政治责任意识的淡化处理则也弱化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从而使其“公民身份”停留于消极的形态中。而在这些方面,涂尔干对于中介团体之功能,对于具有公共精神的积极公民的重视和强调在某种意义上正可以纠偏补缺。因此,如果我们脱离开涂尔干和韦伯的具体而特定的语境,而从一般的角度着眼于现代政治成熟性的道德维度,那么,我们或许不妨将他们综合起来而笼统地说,成熟的现代政治,是由具有公民道德、公共精神的公民和兼具激情、远见和高度责任担当的政治家共同打造的。当然,公民和政治家的这种政治德性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在特定现代政治制度架构下通过实际的政治参与、政治实践而培育、历练、锻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