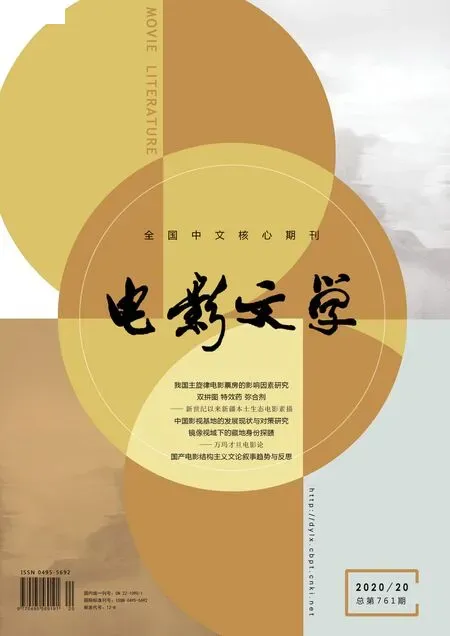阳光下的阴影:《阳光普照》空间叙事研究
2020-11-14樊姝彤
樊姝彤
(爱丁堡大学,英国 爱丁堡 EH8 9YL)
电影叙事作为一种以电影语言为表达工具的叙事活动,影像产生过程本身就天然包含了一定的容纳行动的空间环境。在电影的叙事构成中,空间叙事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影片中大量的表意功能都需要借助空间手段来实现。因此,也有很多人将电影画面称为“完美的空间能指”。电影《阳光普照》娴熟地驾驭空间叙事元素,通过鲜明的空间对比、外部空间的塑造、心理空间的建构等手段,赋予了影片更加深刻的情感震撼力,且更加立体地展现了台湾底层真实的社会生态。
一、阳光和阴影——被规训的私域空间
《阳光普照》中的哥哥阿豪,有一段关于“阳光和阴影”的表述,他说:“这个世界,最公平的是太阳。不论纬度高低,每个地方一整年中,白天与黑暗的时间都各占一半。前几天我们去了动物园,那天太阳很大,晒得所有动物都受不了,它们都设法找一个阴影躲起来。我有一种说不清楚模糊的感觉,我也好希望跟这些动物一样,有一些阴影可以躲起来。但是我环顾四周,不只是这些动物有阴影可以躲,包括你,我弟,甚至是司马光,都可以找到一个有阴影的角落。可是我没有,我没有水缸,没有暗处,只有阳光,24小时从不间断,明亮温暖,阳光普照。”
这段文字不仅是片中阿豪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遗言,也是点出全片主题的一段台词。本片的片名为《阳光普照》,看似只提到阳光的一面,但纵观全片观众可以发现,片名中实则暗含了阳光普照下的那些同样占有巨大空间的阴影。有阳光的地方就有阴影,只是这些阴影往往由于阳光的耀眼而失去了应有的存在感。全片围绕着阳光和阴影这一组概念进行展开,阿豪和阿和这一组人物设置是最直观的一组对比,配合这一组概念的不仅仅有台词的设计,还有一一对应的空间设计以及镜头语言。片中阿豪和阿和在电影前半段分别处于补习班和监狱两个物理空间中,这一对空间设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正好暗合米歇尔·福柯的空间权利说。福柯在对空间隐喻作用的研究中,融入了他对社会关系和哲学的思考,经过分析后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空间即权力容器,规训了人的时间与身体。
(一)补习班
校园本应该是充满温暖,给人带来希望的空间,但在影片中的补习班空间,却处处充满着秩序和强权,还有弥漫在空气中的压抑和窒息感。片中一共出现了两个学校里的片段,第一个片段是阿豪在教室里午睡的场景,在这场戏的镜头设计中,导演先给到一个人物背面的中景镜头:阿豪和周围的学生都趴在桌子上休息。但就在他缓缓抬头醒来时,镜头陡然切到阿豪正面远景,周围的同学竟全部消失,只剩阿豪一人在教室中怅然若失。而就在阿豪环顾四周几秒后,周围的人群竟然神奇般地又全部闪现回来。这一组简单的三个镜头,通过精妙的景别设计,配合精确的剪辑,极其有效率地表达出一种异常感,暗示阿豪的精神已经出现了某些问题。
第二次的校园场景则是发生在挤满学生的大教室里,阿豪与台上老师起了冲突。老师在课堂上讲到司马光的《训俭示康》时,阿豪将目光投向教室的另一边,目光呆滞,而在老师点名提醒他时,他却冷静地反问老师是否相信司马光的这篇古训。老师听到这句话后,便不由分说,粗暴地利用自己的职权将阿豪逐出课堂。这场冲突暗示了导致阿豪最后走向自杀的多重原因,不仅仅有他对家庭的不满,还有对教师、学校的绝望。补习班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处处充满着口号和宣言的地方,无论老师还是家长都心知肚明,这不是一个传播知识、教育学生的地方。它充满着赤裸裸的功利性和目的性,也包含着严苛的控制。正如法国思想大师列斐伏尔所言:“权力已然扩展了其起作用的范畴和领域,蔓延在每一个人的骨髓之中,深入到了意识的根源。” 这种心理控制十分隐晦,将外在的纪律内化为人自身的思维方式和行事风格,最终达到控制身体的目的。福柯将这种加之于其他场所的、类似于监禁教养的惩罚方式的控制力量称之为“纪律”。
(二)少年辅育院
与影片营造完全的阴暗、压抑的校园环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少年辅育院空间的设计,少年辅育院不同于一般的监狱,它是对少年犯进行教育和改造的特殊监狱。在《阳光普照》中,少年辅育院里的几乎每一个镜头都有阳光照进来,画面色彩也是随着时间变化而慢慢变得越来越温暖、明亮。与阿豪所处的补习班正好相反,阿和所处的辅育院里的教室,却意外地更加贴近校园的气氛,走道里布置着彩带和学生五彩斑斓的画作,学生与教辅人员之间的交流也并没有补习班里的冷漠感。更加具有视觉冲击力的例证是阿和与辅育院里同学之间关系的变化,虽然彼此多有冲突,但这种矛盾更像学校里普通同学间的打闹和暗暗较劲,阿和出狱前那场全班同学一起默契地合唱《花心》的片段,更是将这种实际上的同窗情推向了一个情绪高点。
从剪辑上也可以看出导演的用心,例如阿豪和补习班老师发生冲突的那场戏,刚好紧接在阿和进监狱的戏份后面。而在剪辑时,导演则通过相似构图将两个学校和辅育院空间巧妙地联系在一起,给予观众心理暗示:即学校和辅育院对兄弟俩产生了相似的压抑感。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提到了法国思想家马布里的一句话:“惩罚应该打击灵魂而非肉体。” 阿豪和阿和这一组空间对比,结合马布里的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为导演想要批评台湾社会中某些学校教育,它们对青少年灵魂上的伤害甚至远远大于少年辅育院中对少年犯肉体上的规训。
二、建筑与街道——迷茫困顿的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城邦中一些中心地带的空地被围篱圈出,成为集市(Agora)。这里不仅是希腊城邦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核心区域,更是西方民主思想诞生的地方,是政治参与和审议的舞台,是民主治理的基础。而现代的城市公共空间则形成于近代工业社会,它与私人空间相对,指的是城市或城市群中,城市居民进行公共交往,举行各种活动的开放性场所,它是最能体现国家、市民社会和个体三者关系的领域。
城市公共空间不仅仅是体现一个城市经济、政治发展水平的场所,更是连接着整个城市居民情感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曾说过这样一句话:“通过自己的五官来体验空间,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 人体验生活感知传统的要素是在不知不觉中使其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在这样运用各种感官体验空间的过程里,人在不知不觉中与空间相连接,并对空间注入了独特的情感体验。下文将通过对建筑,街道两个递进维度的分析,解析《阳光普照》这部电影关于城市公共空间的呈现以及内涵。
(一)建筑
建筑现象学认为,建筑是人造环境延伸到自然的领域,它的出现增加了人类切身体验世界、理解世界的机会和可能性。在建筑空间中的知觉体验是一个融合多种感官运用的整体过程,当人们初次靠近或者进入一个建筑空间时,很难将一个个知觉元素单独割裂来看,这与电影银幕空间带来的知觉体验有相似之处。与电影相似的还有,建筑自身也带有强烈而潜移默化的叙事性,建筑设计师可以通过材料、色彩、空间路径等方面来进行信息传递和隐喻构建,从而达到表情达意的目的。因此当影片中出现明显的建筑画面,对这些建筑元素进行解析能有效帮助理解电影内涵。
在《阳光普照》这部电影中,导演钟孟宏凭借对画面中建筑元素的精准调度,构建了充满隐喻的城市公共空间。在影片中,建筑的出现不仅仅是为了交代故事的发生背景,而是起到了推动叙事作用的关键性存在。通过调度摄影机、人物、建筑三者的相互位置,故事的氛围感以及人物的宿命感被极好地烘托出来。电影中阿豪去世后,在母亲看着阿豪最后留下的短信时,伴随着阿豪独白的是一连串台北建筑的蒙太奇剪辑。画面中的现代化建筑和老城区的街景交替出现,或拥挤或空旷,但相通的是绵延的压抑感和寂寥感。在这些镜头中,阳光和阴影将画面一分为二,而建筑成为画面中的主体。在其中一个主要场景中,阿豪背对着镜头,被高耸林立的建筑挤压在画面的中心。他虽然面对着太阳,却和画面中较大面积的阴影融为一体,几近被完全吞噬。此时这些光滑的建筑表面和锋利的几何边缘都成为阿豪内心世界的叙述者,诉说着主人公内心的荒芜和绝望。
(二)街道
街道与城市的诞生和发展密不可分,作为城市公共空间中最为普遍和便利的信息交流场所之一,对城市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街道同时也是都市电影中难以避免的故事发生地,各个阶级、年龄、不同精神状态的人们在街道上相互观察又彼此交会着。在《阳光普照》这部电影中有大量人物走在街道上的镜头,这些镜头有很多共同点,它们往往都发生在狭长幽闭的空间,且多数为手持跟拍长镜头。片中母亲、阿豪、郭晓贞、父亲都有这样类似的镜头,他们都在镜头中沿着街道长时间地行走,他们大都各自怀揣着心事,穿过那些漫长的或熙熙攘攘、或幽静无人的街道。
“街道漫游”这一概念脱胎于勒·柯布西耶的“建筑漫步”,他认为“建筑通过漫游其间而被体验”。在“街道漫游”的意义下重新观察影片中的这些人物时就会发现,街道并非场景和场景间的连接、过渡场所,而成为具有独特叙事意义的表演性空间。当人物的心理变化投射在漫长的街道空间时,这些街景变成了一个连接影片中人物与观众知觉的重要场所,且具有极强的表意功能。以郭晓贞补习班放学后的那一段街头行走为例,一段跟拍长镜头首先对焦在主角头顶的反光玻璃上,人物倒立着仿佛在云端行走,接着镜头下摇,观众意识到这是商场的外廊;下一个镜头接主角走进地铁旁的临时通道,通道狭窄而逼促,阿豪突然从后面叫住晓贞,继而两人一同走向公交站。在这几个连续的镜头中,街道两侧的建筑,都占据了画面较大的位置,几乎将主角紧紧地包裹在其中,同时用中远景拍摄,使得画面给观众一种极大的视觉冲击和压抑感。这种在偌大的灯光璀璨的都市空间的衬托下,主角的渺小感和孤寂感被完整地传递出来。
三、梦和寓言——反映内心的异度空间
(一)阿文的梦
梦一直是受到电影创作者钟爱的一种表意手法,在钟孟宏导演的作品中频繁出现的充满欲望和遗憾的梦境,每每充满隐喻而又引人深思。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愿望的达成,它绝不是无意义的”,《阳光普照》中出现的梦境片段也蕴含了丰富而复杂的人物情感,同时向观者传递了大量的重要信息。《阳光普照》中阿文的梦是片中最让人痛心、潸然泪下的片段。父亲阿文在梦中一个人走在漆黑狭窄的巷弄中,镜头在背后静悄悄地跟着,忽然阿豪的声音出现了,阿文一回头看见了已经逝去的大儿子阿豪就站在路灯下朝他走来。接着,阿豪平静地陪着父亲走了一段路,平常地聊天,从有路灯下的光亮处开始行走,经过一段长长的黑暗,然后停在下一个路灯的光亮下,微笑告别。
阿豪在父亲梦中的形象一如既往地充满阳光、面带微笑,即使梦中的阿文已经意识到儿子不在了。令人唏嘘的是,这是父子俩全片的第二次同框对手戏,与补习班那场戏中两人站位较远、显得充满隔阂不同,阿文梦中的这段相遇,导演终于给到父子二人同时正面出现在画面中的镜头,意味着父子俩终于有了一次真正的沟通与心灵上的共鸣。这个梦使得阿文在办公室的沙发上陡然惊醒,从梦中醒来的阿文好像冥冥之中受到梦的暗示一般,重新走了一遍梦中和阿豪一起走过的那条小巷。当阿文走出巷弄,好像巧合般地出现在他一向不愿承认的二儿子阿和工作的便利店时,他终于主动和二儿子交谈,并且谈论刚才的梦。阿文和阿和这对父子也凭借着谈论阿豪相关的话题,终于打破了沉默,重获了久违的默契与和解。
钟孟宏导演的电影中,常常出现父子关系的疏离和重建过程,这也是台湾电影中一直以来的一个创作母题。本片明显围绕着家庭关系展开,电影《阳光普照》的英文名叫作A
SUN
,和“A SON”读音相似,这种设计也暗含本片的隐含信息,即:一个儿子。在本应该是象征着团聚的家庭空间,观众可以注意到,两个儿子从片头到全片结束都没有同时出现在家庭这个空间中。在父亲和他人的聊天对话中,也常常提到自己只有一个儿子。父亲对两个儿子的区别对待和缺乏深层次的彼此沟通,也是造成这个家庭悲剧的主要原因。因此《阳光普照》中的这个梦,是全片的重要转折点,影片中由父亲阿文的梦构成的虚拟空间,不仅在情绪上使得观众有一个大的宣泄和释放,在叙事上也起到了开启下一篇章的推动作用。在梦中阿文终于与大儿子阿豪相见、告别,并且在潜意识中与自己的内心达成一种和解。一直积攒在阿文潜意识里种种压抑,在梦中得到释放,也是从这个梦为契机,阿文开始重新接纳二儿子阿和,并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对儿子予以关注。(二)司马光的故事
大儿子阿豪在公交车站台和晓贞讲述的那段关于“司马光”的故事,则构成本片里的另一个异度空间。导演选择用动画的方式进行呈现,动画短片以黑白灰为主色调,而主角司马光则一袭红衣,整个画面的人物塑造和环境氛围都给人一种恐怖、诡异的气氛。这个片段初看让人觉得疑惑,在这个片段前的阿豪看起来如此阳光而充满希望,即使出现了某些精神恍惚的表现,也最多被理解为普通的考前焦虑。但看到后面阿豪的选择后,可以发现这个“司马光”的故事实则是阿豪内心世界的外化,它暗暗铺垫了阿豪精神失常的趋向以及最后自杀的结局。
“日内瓦学派”的主将乔治·普莱认为:“没有地点,人物仅仅是抽象概念。” 这里的“地点” 指的就是人物的活动空间,也就是人物性格形成的场所。阿豪视角中的家庭空间正是充满阴暗和压抑的牢笼,昏暗冷调的灯光,古板陈旧的装潢,疲惫不堪的父母……阿豪在家中的几个片段里,房屋里没有一丝阳光,似乎是无休止、日复一日的黑夜。阿豪的房间也永远给人一种昏暗、幽闭的感觉,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阿豪的床边贴了一圈海洋生物的图片。那些自由自在的有阴影可躲的动物,是阿豪一直以来的渴望,但这些渴望,随着弟弟入狱被父母更加热切期盼的目光灼伤而逐渐暗淡。最后,阿豪在悄无声息地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后,一如既往不给人添麻烦地默默走向了阴暗。阿豪最后留在画面中的身影正是他投射在墙上的阴影,那阴影越来越大,最后占据了整个屏幕。
影片中司马光的故事来自台湾作家袁哲生的短篇小说《寂寞的游戏》里的《脆弱的故事》一节,与影片中虚拟的角色阿豪相似的是,本文作家袁哲生同样选择了自杀。近些年来台湾经历了剧烈的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在这种环境下,社会的浮躁、焦虑和人的异化则成为台湾的作者导演难以回避的叙事主题。《阳光普照》中几乎每一个角色都面临生活的困顿,且带有或多或少的病态:断手的黑轮、被抛弃的菜头、愚昧专制的父亲阿文、隐忍困窘的母亲琴姐。阿豪所讲述的“司马光”的故事作为片中最阴暗、诡谲的片段,是全片所营造的另一个虚拟的异度空间,也是片中全部人物所处的充满困境、束缚氛围的具象化和集中体现。
作为一部反映当下台湾社会现状,呼吁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影片《阳光普照》毫无疑问是2019年最优秀的华语电影之一,它完美地兼具了商业性和艺术性。影片不仅在文本上逻辑清晰,线索分明,兼具丰富而深刻的主题意蕴,还能准确地用赏心悦目的视听语言将文本思想传递给观众。而作为传递影片信息的重要叙事形式,空间叙事在这部影片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导演钟孟宏在构建影片世界时,用他摄影师独有的视角和构图经验为影片空间构建增添了信服力和感染力。而他构建的这个空间不是封闭的,它比现实更激烈,却又处处勾连着真实的世界。影片结尾处,母亲坐在阿和的自行车后座上,久久地凝视着头上的阳光和熟悉又陌生的街景,仿佛在审视着周围的一切,它们是真实的吗?而这一切结束了吗? 这不仅是片中角色的疑问,也是观者那一刻的内心活动。这就是电影的魅力,它将虚拟的空间与现实空间相连接,在那一刻,观众都成为剧中人,被带入了电影中。而故事没有结束,故事也不会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