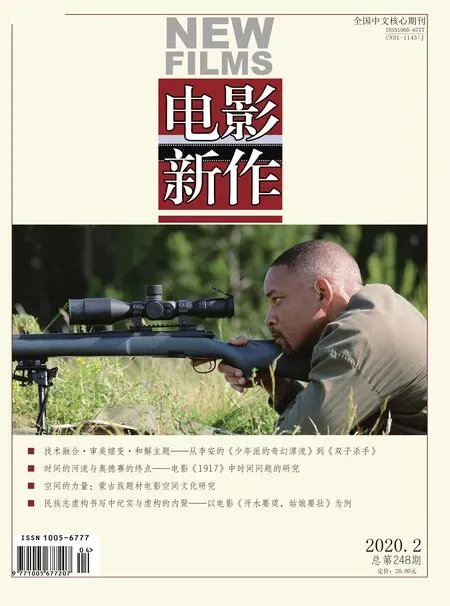王家卫电影的“空间诗学”—基于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理论的考察
2020-11-14战玉冰
战玉冰
一般而论,在我们分析王家卫电影的特点时,香港特殊的历史背景与文化身份、对都市人群精神气质的敏锐捕捉、极端风格化的视觉影像表现手法、哲理型画外音的大量使用,以及富有现代性气息甚至后现代意味的表述方式等,似乎都成了王家卫电影风格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王家卫电影的上述诸多特点最终可以回归到其对于空间的隐喻性思考(卡尔·荣格式)与想象性呈现(加斯东·巴什拉式)之中。概括来说,即王家卫电影的“独树一帜”与其强烈的作者风格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影片所选取和表现的特殊都市空间,及其所承载和象征的都市人的内心空间,并由此进一步引申出无根、漂泊、拒绝、遗忘等王家卫电影的经典母题。而这一系列特殊的“空间感”,既可以视为是对时间现代性宰制的某种反抗,也是基于香港自身历史境遇和文化身份的双重反思所致。
一、都市空间的细节想象
王家卫电影中对空间的选取往往别出心裁:从《东邪西毒》中广袤大漠里孤零零的茅草屋与囚闭却不停旋转的鸟笼,到《2046》中既现实又科幻的旅店与列车,都可以称得上是极具标志性意义的王家卫电影空间。除了选择电影所要表现的空间之外,王家卫也极擅长通过光影的技巧、镜头的变化、视听氛围的营造来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空间感觉”(spatial sense),或者说“空间气质”(space temperament),进而形成一种所谓“王家卫式”的电影风格。
按照精神分析学派的一般观点,外在空间和人的内在心理空间往往有着彼此对应的隐喻性关联,借此来分析王家卫电影中的空间意象,我们大概可以得出“幽闭”象征着“自我保护”“狭窄”表达着“拒绝”“流动交通”喻指“无根无安全感”“阴晦缺光”下遮蔽着的是“自我隐藏”的内心情结等初步结论。但正如法国学者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在批评精神分析学派时所说的那样,隐喻最多只具有一种临时性的解释力,而从具体形象经由想象力而延伸所得到的现象学解释才更有可能抵达空间意义的深处或本质。巴什拉认为“被想象力所把握的空间不再是那个在测量工作和几何学思维支配下的冷漠无情的空间。它是被人所体验的空间。它不是从实证的角度被体验,而是在想象力的全部特殊性中被体验”,并专门为此写就了一本研究专著《空间的诗学》。如果我们借用巴什拉“空间的诗
从这一角度反观现代都市中的单元公寓,显然不具备巴什拉所谓“家宅”的基本条件,而他也毫不客气地批评道:“巴黎没有家宅。大城市的居民们住在层层叠叠的盒子里。克洛岱尔(Paul Claudel)说:‘我们在巴黎的卧室,在它的四墙之间,是一种几何学的地点,一个我们用来摆放形象、装饰品和多门柜子的惯常洞穴。’马路的门牌号和楼层的数字确定了我们的‘惯常洞穴’的方位,但我们的居所既没有周边空间也没有自身的垂直性。‘在地面上,家宅用沥青固定住,防止陷入地下。’家宅没有根。对于一个家宅的梦想者来说这是无法想象的事:摩天大楼没有地窖。从地面到屋顶,一间间房堆积起来,无边无际的天空是一顶罩住整个城市的帐篷。城市里的建筑物只有外在的高度。电梯破除了楼梯上的壮举。住得离天空近不再有任何好处。在家的状态只不过是单纯的水平性。嵌在一层楼当中的一套住宅的各个房间缺乏一条最基本的原则来区别和划分他们的内心价值。”从巴什拉对于“家宅”的赞美与对城市住宅的批判来看王家卫,我们甚至能体会到其中的一丝反讽性意味,“重庆森林”指的是香港一座名为重庆大厦的建筑物,这里并没有“重庆”,也没有“森林”,所谓的“森林”不过是有钢筋水泥堆砌而成的现代都市“森林”而已,即这分明是一座巴什拉所批判的现代城市建筑,但名字却让人隐隐联想到自然与他所热爱的“家宅”。
与此同时,借助巴什拉的这段分析来看梁朝伟所饰演的警察663,其家宅的“马路的门牌号和楼层的数字”进一步被抽象成为人物身份的数字代号,而其“失根”的都市“家宅”其实是其“失根”的内心世界的某种外显性投射。即如巴什拉所反问的那样,“外在空间难道不是一个消失在记忆的阴影中的古老的内心空间?”同样有趣的细节在于王菲所饰演的女店员,在其刚出场时,是以缩在店铺一角的形象和姿态呈现在观众面前的。而在巴什拉看来,角落正是支撑内心“稳定性”的某种必要空间类型:“角落首先是一个避难所,它为我们确保了存在一个基本性质:稳定性。它是我的稳定性的确定所在,邻近所在。角落可以说是半个箱子,半面墙,半扇门。”
随后发生在两人之间的故事情节颇具有一点现代都市魔幻色彩,王菲趁梁朝伟不在家而潜入其家中,打开家门和柜子,帮助梁朝伟打扫卫生,同时还一件件观赏、把玩并最终替换掉梁朝伟的生活用品,如毛绒玩具、拖鞋、毛巾、牙刷、CD以及金鱼等等。在当代电影中,“闯空门”早已不止一次地被文艺片导演们所利用和描述,巴什拉认为,“每一把锁都是对撬锁者的召唤”,而这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人们对于打开别人紧闭的内心世界一窥究竟的某种天然渴望。如果我们沿着将梁朝伟“家宅”视为其“内心世界”“记忆的阴影”这一思路继续看下去,王菲进入家门后又打开了梁朝伟的柜子,而“柜子的内部空间是一个内心空间,一个不随便向来访者敞开的空间”,即象征着梁朝伟内心世界的更为私密处。梁朝伟的“家宅”被各种物品充斥且显得凌乱不堪,似乎是暗示着其前一段感情的创伤与回忆的混乱。王菲一件件观赏、把玩并最终替换掉梁朝伟的私人物品,也就意味着她一点点了解并改变/取代了梁朝伟曾经的情感寄托与爱情记忆。更有趣的是梁朝伟对这一过程竟然一直没有察觉,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单身男人对家中物品的粗心大意(实际上绝非这么简单,因为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对私人生活物品毫不在乎的人,同时又有着不断地和自己私人物品说话/自说自话的宛如“恋物癖”的习惯和孤独病症),实则象征着王菲在“润物细无声”中进入并改变了梁朝伟的内心世界。而从王菲的角度来看,这次“闯空门”也为她自己找到了内心的真正归依,看似一种“梦游症”似的行为背后其实是巴什拉所说的“家宅中的每一个角落,卧室中的每一个墙角,每一个我们喜欢蜷缩其中、抱成一团的空间对想象力来说都是一种孤独,也就是卧室的萌芽、家宅的萌芽”,即从影片开始时王菲缩在墙角的姿态到后来闯入梁朝伟“家宅”的行为之间存在某种心理学或想象力层面发展的必然性。
影片中王菲一整段“闯空门”的情节,完全可以视为是一场两个人之间情感戏的别样表达,而王菲每一次爱意的展示,即体现为其“闯空门”后所做家务的具体动作——换床单、拖地板、擦拭家具。我们或许可以说,这几场关于王菲做家务的戏份,是世界电影史上最为浪漫的“家务戏”,或者也可以说是最为特别的“情学”或者“空间现象学的想象力”来重新审视王家卫电影中的空间,会有很多新的发现和解读可能。
在巴什拉的空间理论中,关于“家宅”的一系列精辟论述无疑最为让人印象深刻。在他看来,“家宅是形象的载体,它给人以安稳的理由或者说幻觉”,而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中第一点就是“家宅被想象成一个垂直的存在。它自我提升。它在垂直的方向上改变自己。它是对我们的垂直意识的一种呼唤”。当然,巴什拉所热爱的“家宅”指的是有阁楼、有地窖、独立存在于自然之中传统家宅建筑,他甚至认为这样的家宅是和自然天地连结为一体的美妙存在,“家宅,地窖,底下的土地在纵深上融为一体。家宅成了自然中的一个存在。它依赖于形成大地的山和水。作为石头做的巨大植物的家宅如果在地基处没有地道里的水就不能很好地生长。梦想就是这样在广度上无尽延伸的。”爱戏”。而关于这种家务劳动中的诗意或诗学,巴什拉显然也是心有戚戚焉。在他看来,“主动地保存着家宅的,在家宅中联系起最近的过去和最近的将来的,将家宅维护在存在的安全性中的,是家务活。”他甚至使用了一种相当文学化/诗化的表示方式来进一步解释“家务劳动”中的“诗意”:“一旦我们给机械化的手势带来一线意识的微光,一旦我们在擦拭陈旧的家具时进行现象学思考,我们就会感到,在这一轻柔的居家习惯动作之下产生出新的印象。意识使一切重新变得年轻。它赋予最熟悉的动作以开端的价值。它支配着记忆。重新成为机械化动作的真正发明者,这是多么奇妙的事。于是,当一位诗人擦拭一件家具时(即使是通过他笔下的人物之手),当他在一块能使他所碰到的每样东西重获温暖的羊毛抹布上掺和了一点点香味醋,放到桌面上时,他创造了一个新的对象,他增加了对象的人性尊严,他把这个对象登记在人性家宅的户籍簿上。”“受到这般爱抚的对象确实诞生于内心空间的光芒;它们上升到一个现实性的层面上,高于那些冷漠无情的对象、由几何学的现实规定的对象。它们传播着一种新的存在的现实性。它们不再仅仅属于一个范围,而是范围的联合体。在卧室中,家务料理在一个对象与另一个对象之间编织起统一古老的过去和崭新的日子的连线。家务使沉睡的家具苏醒。”
除了梁朝伟的“家宅”与私人物品的象征性之外,以物品来隐喻情感,或者可以说是对于情感进行“物化表达”的例子还有很多,其中最经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一处当属那段有关“爱情”与“过期”的画外音旁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我每天都会买一罐五月一号到期的凤梨罐头。我告诉自己,当我买满三十罐的时候,她如果还不回来,这段感情就会过期”。类似的画外音表达“我就像是一家店铺,而她就是我,我不知道自己走进这家店铺会停留多久”。在这几段影片画外音中,爱情被物化为现代都市中的商品,因而像商品一样具有“保质期”,而作为爱情主体的个人则被物化为店铺。与此同时,影片中并不是简单地在爱情和商品之中做类比,而是进一步将“物”(商品)在时间上的有限性这一特点转移嫁接到了原本被认为似乎应该是“天长地久”的爱情身上,为都市中的男女爱情“赋形”(shaped),从而更增强了其表达的冲击力,并由此显得意味深长。有时候,王家卫还会通过某种“时空错置”的情节设计来为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表达来制造一些障碍或新的可能,比如《堕落天使》中的黎明与李嘉欣,他们出没于同一间屋子中,却互不相见,没有身体上的接触,但又“真的谈起恋爱来”“我不知她们是怎样相爱起来的,也许是一种共同患难、相濡以沫的不安全感吧!”影片中李嘉欣通过黎明留下的垃圾来想象黎明的生活,进而将对黎明的恋爱转变为一种“恋物”,或者说是对空间的依恋之情。即如巴什拉所说的,空间是某种“存在的集聚形象”“它唤起我们的中心意识”。
二、空间缺失的“无根”主体
生活在“无根”的都市“家宅”中的人们,内心也因此具有一种“无根性”的特点。这最典型地体现在影片《阿飞正传》中那个著名的关于“无脚鸟”的譬喻上:“我听别人说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的飞呀飞呀,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的时候。”“以前我以为有一种鸟从一开始飞就可以飞到死的一天才落地,其实他什么地方都没有去过,这只鸟从一开始就已经死了。”这个“无脚鸟”的形象可以说是贯穿了王家卫的每一部电影:从《阿飞正传》中张国荣饰演的旭仔常以“无脚鸟”自喻,一生到处找寻、流浪而无法停驻,到《蓝莓之夜》的时候,干脆直接讲述了一个“在路上”的故事。按照赵春的说法,“流浪几乎成了王家卫电影中的一个标签,离乡也成为王家卫电影中人物逃避情感的一个重要手段”。的确,“流浪”是王家卫电影中“无根”主体的行为表现,但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深入,来挖掘出“流浪”行为背后的本质性原因,即王家卫电影中的主体往往需要面对一种无法找到处身空间/无法自处的生存困境。被困于大漠茅屋中的西毒欧阳锋渴望回家乡,他也随时可以回去,但却迟迟不肯回去,他和影片中那只笼中鸟彼此指涉,化身为自我内心的囚徒。类似的,叶问与宫保田比武,“无脚鸟”这一意象也再度化身为身处笼中、无处着力、挣扎到死的鸟的形象而出现。
关于“无脚鸟”的隐喻,我们当然可以回到香港的历史背景之中来进行“索隐式”解读。比如《阿飞正传》中旭仔一生都在寻找母亲,却又拒绝母亲的关爱,同时对养母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是香港人对自己身份焦虑的表征。再如《花样年华》中周慕云最后选择离开香港,远赴南洋,或者是影片《2046》的片名,以及《一代宗师》中的那句意味深长的台词:“所谓大时代,不过就是一个选择,或去或留”……在这一视角的关照下似乎都有着耐人寻味的意义和指涉。
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主体存在空间缺失的角度来进一步理解王家卫所说的“无脚鸟”。让我们重新来审视下巴什拉所说的“家宅是形象的载体,它给人以安稳的理由或者说幻觉”中的第二个层面的含义,即“家宅被想象成一个集中的存在。它唤起我们的中心意识”。在巴什拉看来,“家宅”给予居住其中的主体以“回忆的安顿”和“精神的安全感”,是主体梦想中的归宿。“毫无疑问,由于有了家宅,我们的很多回忆都安顿下来,而且如果家宅稍微精致一些,如果它有地窖和阁楼、角落和走廊,我们的回忆所具有的藏身处就会被更好地刻画出来,我们终生都在梦想中回到那些地方。”而王家卫影片所着力表现的,正是那些失去“家宅”(或者可以进一步引申为“故乡”)的主体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即通常所说的“无脚鸟”。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归纳出,在王家卫电影中,无论是其对于都市空间的呈现,还是对于丧失空间的个人主体的表达,其实都是在反向证明了巴什拉空间理论的有效性。而如果我们说巴什拉所说的家宅空间是一种幸福,可以给生活其中的主体带来温馨、安全和勇气,那么王家卫电影则是借助与之对立的空间结构来描述了一群边缘人、漂泊者与不幸福群体的生存状态。
三、对空间的艺术化视觉呈现
无论是面对现代都市人的生存空间,还是那些失却空间归宿的“无根”主体,王家卫都能相应的采用恰如其分的镜头语言和呈现手段,而这正是导演王家卫与其“御用”摄影师杜可风的艺术功力之所在。
一方面,在镜头使用和影片构图方面,王家卫往往更注重镜头与构图的艺术性与情感性表达,而非叙述性功能。比如在表现建立在流动光斑基础上的现代都市生活时,王家卫在影片中总是把画面处理得特别恍惚,或是街头流动的车辆、或是夜里晃动的灯光,或是窗前转瞬即逝的人影,王家卫擅长抓住这些不稳定的形象来呈现出本雅明所说的大都市中人们面对街头汹涌人潮时所感受到的“惊颤体验”(Chock-Erfahrung),即在一个由几百万陌生人组成的现代都市社会中,人们在街道上每天都要面对大量快速涌动、奔走的陌生人群,并会由此产生一种“惊颤体验”(类似的,齐美尔将这种体验形容为“表面和内心印象的接连不断地迅速变化而引起的精神生活的紧张”)。在本雅明看来,“置身街上的人群,会不断面对一些不期而遇的情景。但是,簇拥的人流,不断变换的情景又让你无暇细嚼它们,于是出现惊颤,在一个惊颤还没有平息之时,下一个又接踵出现。久而久之,人身上就发出一种快速反应机制,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景象,尽可能快速地作出反应,以致人离开这样的人群,离开这样的都市反而会出现不适。于是,出现了闲逛者,特意置身人流,只为身上的快速反应机制能得到满足,只为身历现代都市中特有的惊颤体验,这是现代都市给人带来的深刻变化:不求甚解,快速反应。也就是说,对象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应对。”由此,这种都市生活中所带来或形成的“惊颤体验”就从一种“感觉”累积、固化成为一种“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在具体表现这些现代都市人的“惊颤体验”与“感觉结构”时,王家卫往往采用手提摄影机跟拍的拍摄方法、快速跳切的剪辑技巧、晃动模糊的画面处理方式,以及去中心化的构图策略来对其进行呈现和强化。而王家卫在采用“视角不稳”的拍摄方法的同时,电影中却往往又存在着一个全知的画外音,在冥冥之中絮絮叨叨,看似与整部电影相互脱节,却又弥补了王家卫镜头语言叙事功能的缺失,把整个故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由此形成了王家卫电影独特的影像与视听风格。
类似的镜头技巧还体现在《堕落天使》中,影片通过超广角镜头所呈现出的变形的空间、浮光掠影般的变格以及音乐对位类似于MTV中的视觉特征,完全在影像上营造出了一个主观化诠释的时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幕是金城武与李嘉欣两人在一间酒吧同时出现,影片的两条故事线索也因此产生交集。在这个双人画面中,王家卫使用了超广角镜头拉开了两人之间的距离,使得人物实际上相隔不远,但在镜头中却仿佛相隔很远,从而强化了现代都市中人与人彼此之间的疏离感受这一电影母题。
另一方面,王家卫喜欢在画外音文本中通过十分精确的空间度量单位来反衬人们空间感受的模糊性,比如:“我们最接近的时候,我跟她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公分,57个小时之后,我爱上了这个女人。”人类空间感知中重要的方面之一就是对于空间距离的估计,而“0.01公分”这种超脱于人们一般感知范畴的精确性空间距离描述,既是以精确的时空量度来计算原本无法被量化的感情,体现出工业化时代的“物化”与“科学化”思维方式对人类情感本能的戕害,又隐约透露出了画外音主体精神病患的某种症状(此外,影片画外音主体还患有倾诉欲和自说自话等心理“暗疾”)。
四、时间的空间化
在对王家卫电影中和空间有关的“都市空间的细节想象”“空间缺失的‘无根’主体”和“对空间的艺术化视觉呈现”三个方面进行了分别论述之后,我们不妨回过头来重新思考王家卫电影中的时间表现。一方面,王家卫电影中固然有对时间观念的深刻理解和出色表现,即如秦昕、袁智忠所说:“王家卫在电影中给予时间以生命的内涵,并借由时间概念,呈现出生命经验的相互渗透,使我们认识到,所谓时间的概念不过是过去经验、现在经验以及不可预测的未来经验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王家卫电影中也普遍存在着对于现代线性时间观念的反抗,而他的这种反抗正是通过空间来得以完成。
正如学者波林·罗斯诺在《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一书中所说:“现代的时间观念被说成是压迫性的,用来测量和控制人的活动的东西。”“线性时间被看做是令人生厌的技术的、理性的、科学的和层系的。由于现代性十分重视时间,这就从某种角度上剥夺了人类生存的快乐。”而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主义扬弃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对现代时间观念的反抗与破除。又如巴什拉所言:“在此空间是一切,因为时间不再激活记忆。记忆——多么奇特的事物。它不记录具体的绵延,伯格森意义上的绵延。我们无法重新体验那些已经消失的绵延。我们只能思考它们,在抽象的、被剥夺了一切厚度的单线条时间中思考它们。是凭借空间,是在空间之中,我们才找到了经过很长的时间而凝结下来的绵延所形成的美丽化石。无意识停留着。回忆是静止不动的,并且因为被空间化而变得更加坚固。在时间中找出回忆的位置,这只是传记所关心的问题,只和一种外在的历史有关,这种历史是用于外在用途的,用来告知他人的。比传记深刻的解释学应该把历史从对我们的命运无作用的相连时间结构中解放出来,从而确定命运的中心。对于认识内心空间来说,比确定日期更紧要的是为我们的内心空间确定位置。”通过空间来反抗线性时间在王家卫电影中最集中体现于《阿飞正传》的那个“一分钟”的镜头上:“十六号,四月十六号,一九六零年四月十六号下午三点之前的一分钟她和你在一起,她说她会因为你而记住这一分钟,从那一刻开始,你们是一分钟的朋友,这是事实,你改变不了,因为那一分钟已经过去,而她明天还会再来。”“你不知道她有没有因为你而记住这一分钟,但你却因此记住了这个人。”“一分钟”对于人的心理感受来说本来是一个抽象而模糊的时间概念,而王家卫在这里却把一分钟精确化了,影片中的钟表实实在在地转足了一分钟,本来最擅长电影写意的王家卫在这里却使用了看似最为写实的拍摄手法,反而产生了更加写意的表达效果。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个经典的“一分钟”表达中,“一分钟”的时间概念是通过钟表指针空间位置的变化来具体表现的,进而赋予了“不可见的”(invisible)时间以“可见的”空间感。另一方面,在这个“一分钟”的表达中,导演采取了一种“抽空情节”的表现方式,在这里,抽空本身即是一种感觉,剧中两个人物其实什么也没做,但是却因此有了一种“时间共感”,而观众在那一分钟里其实也并没有看到什么,但是同样与两位剧中人物共同拥有了一种“时间共感”,这种“时间共感”是抽干了一切故事而唯剩下时间的独特感受,也是影片将客观时间主观感受化之后所起到的表达效果。当然,王家卫电影中也并非缺乏对于时间和历史的直面和表现,比如《花样年华》的结尾字幕就直接诉说出了一种往事不可追的怅然心绪:“那个时代已过去。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而到了《一代宗师》中,这种不可追忆的怅然则又发展出了一种对过往难以割舍的眷恋,即所谓“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结语
法国导演让·雷诺阿曾说过:“有些导演一生只拍一部作品。之后的作品不过是这部作品的延续和补充。”而王家卫无疑是这句话的代表性人物和有力践行者。借助秦昕、袁智忠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王家卫各部电影中大到题材选取与故事情节,小到人物姓名与数字代号之间的彼此关联:“《2046》似是《花样年华》等故事的延续,又像它之后故事的开始。《堕落天使》是《重庆森林》凄美悲凉的版本,既可说是《重庆森林》的延续,也可说是《旺角卡门》的后记。”“同一个名字‘苏丽珍’,是《阿飞正传》中的前世,是《花样年华》中的今生,也是《2046》中的来世。《2046》中新加坡的苏丽珍(巩俐饰)是《花样年华》中的苏丽珍的替代,《花样年华》中的苏丽珍亦是《阿飞正传》中苏丽珍的重像。”当然,这种谱系学的追溯还可以一直进行下去。
只是除了这些情节与人物层面的关联之外,各部“王家卫电影”彼此间更深层次的关联可能还是体现在影片的精神内核方面王家卫自己也曾经承认:“我最后终于发觉原来我以前的电影之间都有关系,其实,全部都是讲被人拒绝和怕被人拒绝。”由此,我们再来看《2046》之于科幻爱情片等,其实是一种“反类型电影”(Anti genre film),即王家卫在用自己独特的作者叙事风格来颠覆不同类型电影的叙事语法与基本成规。
最后,再次回到本文所反复征引的法国学者加斯东·巴什拉的那本《空间的诗学》中,所谓的“王家卫风格”与其“反类型电影”的本质正是在于王家卫使用了不同的外在空间(包括电影类型空间)来表现同一种主人公的内心空间与导演的内心空间,即巴什拉的著名反问句:“外在空间难道不是一个消失在记忆的阴影中的古老的内心空间吗?”
【注释】
1 [法]加斯东·巴什拉,张逸婧译.空间的诗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27.
2 同1:19-20.
3 同1:27-28.
4 同1:31-32.
5 同1:298.
6 同1:174-175.
7 同1:103.
8 同1:99.
9 同1:173-174.
10 同1:84-85.
11 出自电影《重庆森林》(1995),导演:王家卫,主演:林青霞、金城武、梁朝伟、王菲。
12 出自电影《堕落天使》(1996),导演:王家卫,主演:黎明、李嘉欣、金城武、杨采妮、莫文蔚。
13 除了众所周知的“凤梨罐头”比喻之外,王家卫电影中另一处值得关注的爱情“物化”表达在于《重庆森林》中将梁朝伟与其空姐前女友之间的感情比喻为“速食口味”,感情的更换就如同吃速食食品换换口味那样简单。类似的例子也出现在王家卫的另一部电影《蓝莓之夜》中,只是在这部电影里,导演采用了截然相反的修辞策略,难以割舍的真爱象征性地表现为那块被人们所遗弃的蓝莓蛋糕。
14 同12.
15 同1:56、20.
16 出自电影《阿飞正传》(1990),导演:王家卫,主演:张国荣、张曼玉、刘嘉玲、刘德华、张学友。
17 赵春.安哲罗普洛斯与王家卫[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0(02):92-96.
18 出自影片《一代宗师》(2013),导演:王家卫,主演:梁朝伟、章子怡、张震、赵本山。此处可进一步参考学者张慧瑜关于这部电影的相关论述:“退居香港的叶问与北方(大陆)之间的关系也处在父子情深与情人相惜的双重想象之中。”参见:张慧瑜.王家卫的大时代与《一代宗师》的中国想象[J],电影新作,2013(02):50-54.
19 同1:19-20.
20 同1:7.
21 [德]齐美尔,涯鸿、宇声等译.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M],上海:三联书店,1991:259.
22 [德]瓦尔特·本雅明,王涌译. 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4-5.
23 这里的“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一词是借鉴雷蒙·威廉斯的相关概念。在雷蒙·威廉斯看来,“感觉结构”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感觉,一种无需表达的特殊的共同经验”。参见:[英]雷蒙·威廉斯,王尔勃、周莉译.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141.此外,雷蒙·威廉斯的“感觉结构”相比于弗洛姆所说的“社会性格”,更为内在于人的感觉之中。它和我们一般所说的“感觉”之间的区别则在于,“感觉”是对象直接在主体身上所产生的结果,而“感觉结构”则是感觉的累积与固化,甚至于最终形成某种主体的第二本能。而在本雅明看来,“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的感性认识方式是随着人类群体的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的。”参见:[德]瓦尔特·本雅明,王才勇译.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12.
24 同11.
25 秦昕、袁智忠.“永恒回归”——王家卫电影中的“差异与重复” [J],当代电影,2018(10):115.
26 [美]波林·罗斯诺,张国清译.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99.
27 同1:8-9.
28 同16.
29 出自电影《花样年华》(2000),导演:王家卫,主演:梁朝伟、张曼玉。
30 同18.
31 [美]大卫·波德维尔、[美]克里斯汀·汤普森,范倍译.世界电影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93.
32 同25:116-117.
33 黄爱玲、潘国灵、李照兴.王家卫的映画世界[M],香港:三联书店,2015:315.
34 同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