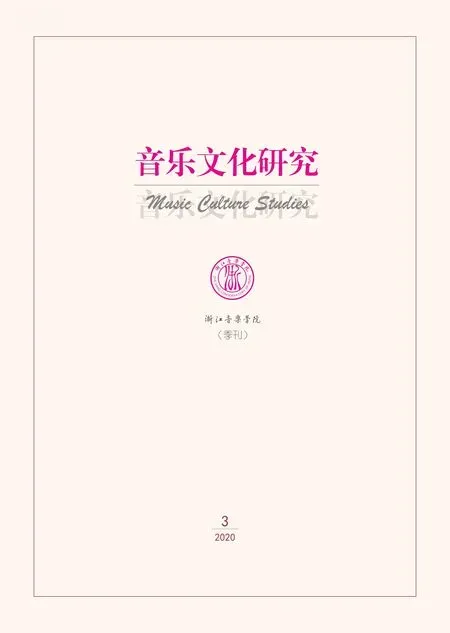愿做“语言音乐学”旗帜下的一名战士
——写在杨荫浏先生120年诞辰纪念之际
2020-11-13钱茸
钱 茸
内容提要:本文是作者在杨荫浏先生120年诞辰纪念活动上的发言。文章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简略汇报了21世纪以来作者引入现代语言学及其他非音符类标示与描述手段,以唱词音声本体解析为切入点,为跨界学科“语言音乐学”根植音乐院校所做的系统化一揽子建设进程;推介了新近面世的语言音乐学理论专著《探寻音符之外的乡韵——唱词音声解析》、相关教材《语言音乐学基础》以及在研的国家冷门“绝学”课题《中国“乐说”研究》。第二部分从“‘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地域性音乐的文化‘深描’”“中国元素音乐创作”这三个方面,进一步强调了语言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需求。
我本科读的是历史专业,曾经在几个报刊干了11年编辑工作,38 岁才通过考研,进入中国传统音乐学领域,虽无缘聆听杨荫浏先生讲课,却是杨先生中国音乐相关书籍的受益者与追随者。杨先生曾在《语言音乐学初探》一文中郑重强调:“音乐与语言的关系,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①
本人读研及40岁留校后面对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传统声乐品种(民歌、说唱、戏曲),越是深入其中越是发现根本就躲不开与语言的关系问题,所以对杨先生的提议深以为然。积年累月的中国传统音乐教学和研究工作,促使我日益增加对语言音乐学这一领域的垦拓欲望,并意识到这将是一个值得投入后半生的巨大工程。我清楚地看到,若要让语言与音乐的跨界学科“语言音乐学”在音乐院校扎根,急切需要的是:认识理念—基础理论—教学与研究实践的一揽子系统化建设,于是自21世纪初开始将事业的重心投向这个领域,我一边系统学习相关语言学理论,一边着手语言音乐学的基础理论与个案研究(陆续发表若干文章),并于2008年开始在中央音乐学院开设《语言音乐学基础》的选修课。最终步入三个语言音乐学的课题。
我愿借杨先生120年诞辰纪念活动,从“垦拓内容”与“对学科需求的进一步体察”这两个方面,向杨先生在天之灵作一个简略的汇报。
一、垦拓内容
我这些年完成和正在进行的三个语言音乐学课题包括:
1.中央音乐学院211 三期工程项目《语言音乐学基础》②(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
2.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重点项目《探寻音符之外的乡韵——唱词音声解析》③(中国青年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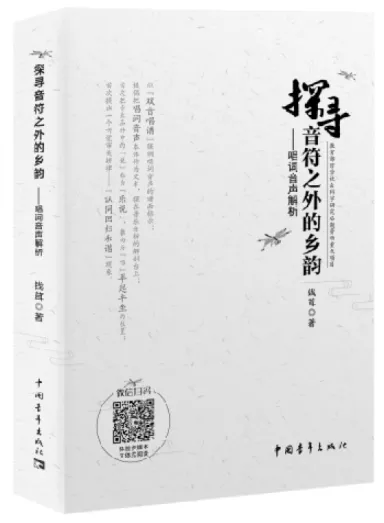
图2
3.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中国“乐说”研究》④(在研)。
这些项目的具体研究内容,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学科称谓及学科的定位
由于这个学科在全球还处于萌芽期,相关文章的称谓并不统一,也没有成熟明确的学科定位,因此给我留下了一定的探究余地。
1.学科称谓之斟酌
杨荫浏先生与章鸣先生都曾用“语言音乐学”,笔者曾在论文中使用“民族语言音乐学”,当时基于如下考虑:
其一,语言音乐学前面冠以“民族”二字,意在强调“多民族母语声乐品种”中之“多民族”。
其二,“民族语言音乐学”的英文名Ethnolinguistic Musicology是经音乐文献专业专家蒲实核定的,从内容到表达方式都与“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相一致,都使用Ethno(人类学)字头,以强调多民族母语音乐文化,并强调前者(人类学)对后者(音乐学)的从属学科关系。
后曾改用“音乐语言学”,原因是:
其一,中文“民族”二字的内涵,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前面冠有“民族”二字,有可能被人理解为研究对象只限于中华民族本土的音乐品种。而事实上,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并不限于中华民族本土。
其二,按照某些学者的观点,对于跨界学科,应把主要研究方法作为词根,这个学科的主要研究方法是语言学,研究对象是音乐作品。因此我曾从中文到英文都套用“音乐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Music,而使用“音乐语言学”Linguistics of Music。
但是,遇到的问题是,“音乐语言学”这个中文称谓,容易产生歧义,不少人把“音乐语言”理解为“音乐语汇”。
最终,在征求若干专家的意见后,我决定根据翻译界的允许常规,将此学科的中英文名称分立,即:此学科称谓的中文,仍沿用前辈们的习惯用法,即“语言音乐学”,而英文称谓则使用Linguistics of Music。意在对外使用时,与音乐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Music)配套。
2.学科定位
我为“语言音乐学”拟定的学科定位是:
“语言音乐学”(Linguistics of Music)是民族音乐学的分支学科,也是语言学的分支学科。
它是借鉴现代语言学方法(包括记音方法、分析方法、思辨方法、数字科技手段等各种非音符类手段),结合音乐学(音符类)方法,以地域性音乐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跨界系统学科。
其研究侧重点为:(1)人类各群体声乐品种的原生唱词音声本体及其与腔的关系;(2)各群体母语与相关地域音乐的关系。
“语言音乐学”不仅对理论界来说,是一门剖析多元地域音乐必不可少的基础理论,它同时对作曲、器乐(民乐)、指挥、声乐等艺术实践还是一种应用理论。
(二)对唱词音声的音乐性解析
针对一个问题:为什么长久以来,语言音乐学学科被音乐界边缘化?
我发现,一个重要根源在于音乐界(包括我自己)多年来,一直认为唱词在作为综合艺术的声乐品种中,只是单纯的文学符号。而事实上深究起来,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判。
我从符号学角度探究的结果是,唱词兼有文学与音乐两类艺术符号,兼具双重身份。
由于唱词的称谓中有“词”这个文学性很强的字,极易引导人们认为“词”只具有文学价值,只具备传达文字语义的功能。
其实,唱词所使用的文字符号在音乐作品之外就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只要不是聋哑人,人类所有文字的习得,都包括语义与诵读两个要求。当文字进入声乐品种成为“唱词”,它们不是仅仅带进了语义,同时由诵读功能带入了一定的音响。更重要的是,当文字成为声乐品种中的一部分时,这些由诵读功能带入的音响(我称其为“唱词音声”)就具备了音乐性。从艺术符号的角度说,“唱词”不可能是单一符号的载体,唱词的字符所传达的语义,是文学性的;而唱词的音声部分,即其音色、声调、形式美构词等许多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在声乐作品中参与了听觉美的构成,属于音乐成分,应属音乐符号。
由此我得出结论,语言音乐学的重点关注对象是作为音乐符号的“唱词音声”(而不是笼而统之的“唱词”)。由此可见,语言音乐学理所当然有资格落座音乐院校,进入音乐人的视野。
(三)唱词音声本体的音乐价值与“双六选点”
针对另一个问题:以往,即便是提及唱词在音乐中的作用时,往往只谈“影响”,唱词在声乐品种中,难道只具备“影响”吗?
当我从“唱词”整体剥离出装载音乐符号的“唱词音声”,就自然地发现了另一个被音乐界长久忽略的事实,即唱词音声本体所具有的音乐性,它们自身的存在就具有音乐价值,它们中的某些部分,又产生了对腔的“影响”。因此我梳理出,唱词音声包含两类音乐符号,只标示本体音乐价值的,是显性音乐符号;标示对腔有影响的那部分,是隐性的音乐符号。也就是说,那些具有隐性音乐符号价值的唱词音声必然首先具有显性价值,也就是具有两类音乐价值(见下图)。

图3
沿着以上思路,我从对地域性声乐品种的探究需求,归纳出唱词的显性音乐符号六选点和唱词的隐性音乐符号六选点。因为二者各自正好都是六点,故称作“双六选点”,用以启发学生对地域性声乐品种的唱词音声进行语言音乐学角度的剖析(不是固定模式,仅仅是启发点)。
(四)非音符类核心认知五范畴谈
其实,语言音乐学学科被音乐界边缘化的现象还存在一个深层原因,即音乐人受现有学院教育的影响,把音符类解析手段当作音乐分析主流,忽略了声乐品种与语言的关系,更忽略了中国声乐品种的地域性多元特征与语言的缠着关系。仍然是站在地域性声乐研究的角度,我提出,至少有五个研究范畴,非音符类手段(语言音乐学方法)的功用绝不亚于音符类手段,而应成为“核心认知手段”。这五个范畴包括如下:
1.“乡韵”溯源;
2.唱词音声本体解析;
3.字音连接解析;
4.双重“桥梁”解析(唱词音声既是音乐作品与大文化之间的“桥梁”,又是语言与音乐之间的“桥梁”);
5.“乐说”音声解析。
我强调非音符类解析手段在上述五个范畴里的“核心认知”作用,仅仅是为非音符类手段追寻本应存在的位置,绝对无意否定音符类解析手段。
(五)提倡“双音唱谱”
在传统的声乐乐谱里,音符是标示音腔之音高的符号,唱词在非拼音语言中,却只有标示语义的文字。基于“唱词音声解析”的理念,我提倡地域性声乐品种使用“双音唱谱”。
所谓“双音唱谱”,即兼有为唱腔标示音高、节奏的乐谱与为唱词注音的国际音标。上有音符,下有音标,只用于声乐作品,故称“双音唱谱”。
“国际音标”是一种通用语音符号,1888年由国际语音协会(1886年在伦敦成立)委托法国人保罗·巴西完成第一稿,以后经国际语音协会一百多年中不断地修订与完善,如今,已被公认为迄今最科学的语音记录符号而成为现代语音学的基础性、标志性记音符号。
因此使用“双音唱谱”不仅能使非拼音文字的唱词展示唱词的音声,还能让唱腔与唱词都具备通用的音响符号。
这里存在一个面对舶来品与维护文化特性的关系态度问题。我认为,一个现代人,既不应顶礼膜拜于外来强势文化,也不必绝对拒外来文化于国门外。“本土化”的提出,原本是针对盲目使用外来文化,强调维护本土文化特性的一个口号。那么,当维护文化特性的目的明确时,不利于这个目的的外来文化,自然要注意把它们放在适当的位置,以避免其对本土特性文化的冲击与替代;而当一种外来文化,恰恰有利于维护我们的本土多元文化时,我们岂不应该“西学为用”?
(六)“乐说”的垦拓
2015年5月,我受ICTM 中国理事萧梅的推荐,作为唯一的中国发言人赴法国参加ICTM 的“说与唱的阈限”巴黎论坛,我的发言稿 是“Speaking in Traditional Chinese Vocal Music and Its Relation to Singing”;2017年,以拓展修改后的中文稿《试析“乐说”及其与唱的关系》发表在《人民音乐》8月号;2019年我的后续课题《中国“乐说”研究》入选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项目。
所谓“乐说”,实指中国传统声乐品种中的“说”,为区别于言语中的“说”,也为强调其音乐属性,故冠以“乐”(yue),称“乐说”。这个概念,在此涵盖所有声乐品种中区别于“唱”的,与言语之“说”发声形态接近的音声,如各种“说”“白”“诵”“吟”以及唱段中夹杂的与言语(语言行为在语言界术语中谓之“言语”)中的“说”类似的音声(音符无法准确捕捉的声乐音声)。
“乐说”,在声乐品种中,是与“唱”平起平坐的另一种音乐表达方式。
以中国语言与音乐的缠络关系,中国各民族各地域方言在听觉形式上的丰富性,各地域各艺术品种之“乐说”形态所呈现的多种变异层次,以及“乐说”与“唱”之间纷繁的协同、映衬、转换……“乐说”的语言音乐学探索前景要比“唱词音声”更加广阔。
二、对学科需求的进一步体察
语言音乐学领域的垦拓进程,让我日益明悉中国语言与音乐的诸多具体关联;因此更让我日益确认音乐领域对语言音乐学这个学科的多方面需求。至少包括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需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1 世纪初开启的“非遗”事业,宗旨在于保护人类各群体的特性“非遗”文化,以维系人类的多元文化景观。“非遗”项目在音乐领域的关注点,当然是不同族群、不同地域音乐文化的特性维护。而这些族群和地域的原生态歌唱品种,恰恰必然是使用原生唱词的。由于这些原生态歌唱品种中的原生唱词是地域性音声基因的重要部分,能不能完满地记录下它们的真实音声样态,必然关系到保存与传承的工作效果。
录音录像不失为整体保存的好方法,但从传承角度,符号记录则无疑是拆解传递的更便利手段。腔的音高,固然可用音符,原生唱词在这些品种中的音声样态,音符却是捕捉不到的。甚至汉语拼音也捕捉不全,因为汉语拼音是为推广普通话而诞生的,普通话的音素较少,故汉语拼音的符号量实在有限,涵盖不了各地域的方言音素。一些族群的本族语音符号诚然可以在本族群中承担原生唱词的传承符号,但缺少通用性的弱点,势必影响在非母语人群的传承,尤其是在音乐院校的批量传承(院校的学生是来自五湖四海的)。
因此,显而易见,“非遗”事业在呼唤语言音乐学的非音符类手段。
(二)“深描”地域性音乐的需求
20世纪末、21世纪初,从海外传来的民族音乐学,在音乐学界掀起一场把音乐作为文化进行“深描”的写作潮流。这原本是提升音乐学研究的好事,但是,有些音乐学文章的音乐分析与“深描”部分出现缺少内在联系的现象,被一些学者诟病为“两张皮”。
我发现,语言音乐学的介入,其实有着解决“两张皮”现象的优势。因为语言音乐学是要把唱词音声也放在解剖台上进行音乐分析的。唱词所独有的特质,即音乐符号与文学符号的共同载体这点,使得其音乐分析(唱词音声分析)与文化“深描”,常常呈现水到渠成的自然态势。
因此,我认为,引入语言音乐学,不失为音乐学界对地域性音乐进行文化“深描”,摒弃“两张皮”现象的重要举措。
(三)中国元素音乐创作的需求
先说一度创作:
在追寻文化特性的当代,音乐创作人常常苦思冥想于“中国元素”。创作界的开拓精神确实令我钦佩,他们不仅收集传统音乐品种的腔调,而且跳出听觉范畴,向高山峻岭、江河湖海等地理景观开拓,推出一个个立体的“中国元素”作品。但这种创作规模往往更适合大型音乐作品。我站在语言音乐学的视角,更注意到另一些挖掘“中国元素”的创作群。他们在方言基础上,制作地域元素的音乐作品。这类作品的最大优势在于,腔与词的和谐度极高。素有这种创作传统的应首推广东,那里的粤语歌、潮语歌(闽南语系)早已自成规模,近年来上海方面也开始推出沪语歌曲。
我认为,让更多的音乐创作者像广东与上海的音乐人那样,能够认可方言(或民族语言)唱词是地域性音乐音响的必要参与素材,是真正的“中国音乐元素”,这将是语言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宗旨之一。
再谈二度创作:
为推广各种使用原生唱词的合唱作品,指挥界的吴灵芬老师主动邀请我,为她主办的网上合唱指挥学院开讲“双音唱谱视唱”,并把我的两本书推介给了合唱指挥界。需求是显然的,二度创作群体已经在叩响语言音乐学的大门。
结束语
请杨荫浏先生放心,尽管语言音乐学这个专业的硕博点还没有建立起来,“语言音乐学”旗帜下的队伍正在逐年壮大。您重视语言与音乐关系的观念正在日益深入人心。
注释:
①杨荫浏:《语言音乐学初探》,载《语言与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②钱茸:《语言音乐学基础》,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8。
③钱茸:《探寻音符之外的乡韵——唱词音声解析》,中国青年出版社,2020。
④钱茸:《中国“乐说”研究》,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项目批准号:19VJX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