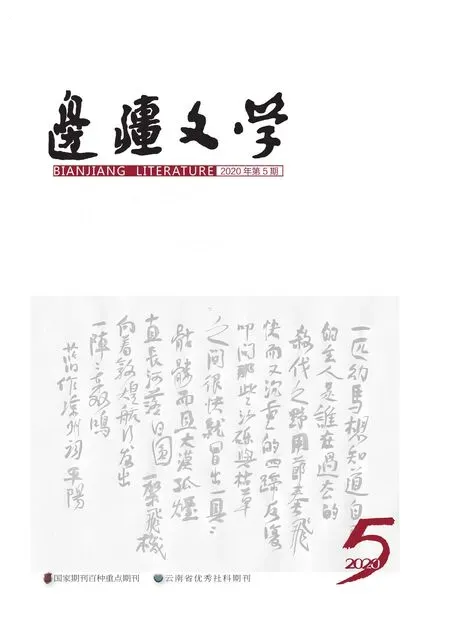所有的历险如今都已全身而退
2020-11-12
云南的青年写作者中,以诗歌作为主要创作方向的人数量众多。事实上,从事小说、散文等文体创作的年轻人,在正式确定自己的主业之前,一部分也经历过一段写诗的时光,甚至是从写诗开始介入文学创作。云南的文学杂志长期以来都在关注这个群体,除经常编辑发表大家的作品外,还不时推出专辑或专号,以呈现这个群体的某些共性。2015年底,在一次闲聊中,《边疆文学》的编辑雷杰龙提议编辑一期青年诗人专号,委托王单单、麦田和我组稿编辑,作者的年龄上限以1970 年为准。2016 年2 月,专号编竣出刊。时隔四年,《边疆文学》再次提议编辑一期专号,作者年龄上限调整为1980 年,因麦田工作繁忙脱不开身,仍由王单单和我代为组稿。
编辑是一个专业性特别强的职业,优秀的编辑,犹如一位拥有火眼金睛的地质勘测员,能够在一片旷野中准确地发现矿脉和矿藏。许多文学编辑同时也是具备一定文学素养的作家,但一位写作者,不一定能完全胜任组稿的角色。这个专号的编辑带有一定的探索性——让写作者承担编辑工作,专号会呈现出何种状态呢?感谢《边疆文学》杂志主编潘灵先生和本期值期编辑雷杰龙对我们的信任!在他们的信任和指导下,我们怀着忐忑的心情组织了这期稿子。
王单单和我是以写作者的身份参与组稿的,四年前,我们的时间较如今宽裕得多,而现在,我们都是驻村扶贫工作队员,自己可以掌控的时间少得可怜,这在一定程度上拖延了专号的进度。对我而言,更糟糕的是常年繁琐杂乱、劳心劳力的工作,几乎已经将我的写作磨损殆尽。幸而王单单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写作状态,始终没有离开过写作现场,在编辑过程中,他的意见、建议往往一针见血,直切核心。
发布征稿启事后,一共收到523 份稿件,剔除超龄作者及古体诗词、散文诗之后,符合要求的稿件一共495 篇,年龄跨度从1980 年至2013 年,王单单和我对每一篇稿件均进行了细致阅读。
专号正文按年龄段分为三个栏目,分别是80 后、90 后、00 后,按年龄段对写作者进行划分是否有效?不论在文学界还是评论界,这都是一个存在争议的标准,但在刊物具体的编排中,除此之外,似乎也难以找到一种更佳的处理方式。
来稿众多而篇幅有限,为了最大限度地展示云南青年诗人的整体面貌,专号“短歌行”的篇幅在以往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充。在我看来,这不是妥协或是折中,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呈现。优秀的写作者,笔阵独扫千人军,一个人就是千军万马;优秀的诗歌作品,一首有一首的分量,一首就可以体现作者胸怀和意志。
四年前的《边疆文学》青年诗人专号,收录了1970 年以后出生的诗人的作品,现在这期专号,年龄上限调整至1980 年,这已经在征稿启示中作过说明。在来稿中,仍旧有部分“超龄”写作者的作品,这些作品成熟优秀,但限于编辑原则,不得不割爱。《边疆文学》对青年写作者的关注是有力而持续的,下次再编辑青年诗人专号时,身为80 后的王单单和我估计也会被排除在外,作为作者,我乐于见到这种排除。
编辑一期专号的工作量,远比预想中的要大许多,也十分耗时,在编排中,我不时有力不从心之感,但还是坚持完成了这件事情。《边疆文学》策划这个专号,是对年轻写作者的鼓励和关爱,作为这些写作者中的一员,我深感自己有义务参与承担一些必要的事务。写作至今,受惠于许多编辑和师友的提携,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把曾感受到的温暖传递下去。
2002 年夏天,我16 岁,刚上高中,对文学抱有一种执著、稚嫩的激情,在之前的初中时光,我已经写满了一本绿色硬皮笔记本。我为投稿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改定一首诗歌,到街上找到一家打字复印店,请老板帮忙录入电脑后打印出来,然后去到邮局,把稿子装进信封,填写好地址,贴上邮票,小心翼翼地投进绿色的邮筒,然后开始漫长而焦虑的等待。我怀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紧张情绪在做这件事,以至于直到今天我都还记得当时的细节,比如把一首诗打印在纸上花费3 元钱,信封1角钱,邮票8 角钱。幸运的是,这首诗最终发表在了昆明的一份报纸《学生新报》上,还收到了一张10 元钱的稿费单。领取稿费同样费了很多工夫,根据邮局的要求,我到街上花3 元钱刻了一枚姓名章,又去学校办公室开了一个说明我是本校学生的证明,回家取了户口册,带着这些材料返回邮局,才把汇款单兑换成了现金。
以后投稿时,为了省钱,就请字写得好的同学帮忙誊抄,省去了打印的环节,但邮资却是无论如何省不了的。姚安办有一份文学杂志《荷城文艺》,编辑部离学校不到两公里,出于乡村少年和文学初学者的羞涩、敏感,每次投稿,我都是绕道到三公里外的邮局邮寄,连去编辑部,乘编辑不注意,丢下稿子就跑的勇气都没有。同校的一位学生去编辑部领稿费,得知也有我的,就约我一起去,那是我第一次踏进一家文学杂志的编辑部,也是第一次见编辑——饶云华和段海珍,现在仍旧在《荷城文艺》当编辑。去过一次,和编辑打了照面,以后就可以直接送稿子过去了。十多年后,饶、段和我都仍在坚持写作,但每次见他们,我依旧还是会紧张,虽然他们一直都是和蔼可亲的。
2005年夏天,我到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我从校图书馆现刊阅览室抄了《边疆文学》的投稿邮箱,每隔两个月,就往邮箱里发一组稿子。持续不断的投稿终于有了反馈,2008 年,三年级时,《边疆文学》发表了我的两首诗,那是我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处女作。如今,从作者的身份中抽离出来,暂时承担编辑的责任,认真阅读学习同行者的作品,辛劳中也感受到一种温暖和坚韧。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这个时代,每一位写作者都能发出自己独一无二的光芒,并且,没有那一道光芒能替代或者覆盖其他人的光芒。对立志将写作作为终身追求的作者而言,只要心无旁骛地专注于自身的创作,我们所专注的事物,一定会给予我们所期望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