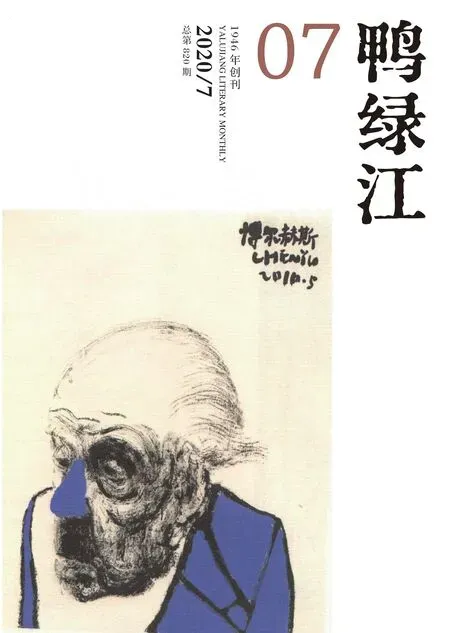唐诗中通感隐喻的认知研究
2020-11-12王丽静
王丽静
一、通感隐喻
语言不仅是人类交流的一种工具,也是一种基于体验的认知行为。人类的语言能力在随着自身与外界的相互体验与感知过程而逐渐发展。我国学者王寅认为: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人类语言不是一个自治的系统,离不开人类的体验感知,语言能力也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而是人类认知能力的一部分。人类对于世界的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认知系统是语言形成的根本理据之所在,人类的体验感知和一般认知能力对于语言的形成起着决定的作用。”由此我们意识到通感在人们感知世界与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用形象化的比喻描述了抽象无形的事物,是不同感官之间交错融合的体现。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来看,通感隐喻是人们进行感知世界的基本模式,它的本质同隐喻一样,是两个或多个感官域之间的映射和迁移,在人类认知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感又称“移觉”,它用形象的语言使感觉转移,将人的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等不同感觉混合,使意象更加生动活泼。Lackoff和Johnson 提出的“隐喻的认知观”与传统“隐喻的修辞观”相似而不同。Lackoff 认为隐喻是指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映射,而其本质是用一种事物去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是用具体的事物来理解抽象的事物,或利用已知的事物来理解未知的事物。根据 Lackoff和 Johnson 的隐喻观,通感也属于一种隐喻,因为通感是用一种感官经验的特征去表达另一种感官经验的特征,如此说来感官之间同样存在着如同隐喻一样的映射过程,即通过从某一感官范畴的认知域过渡到另一感官范畴的认知域,将属于源域中的某一感官的特征映射到目标域感官中。通感隐喻的特殊之处表现在它的源域是六种感觉,而它的目标域也是六种感觉。在诗歌中其具体表现为用具体的词汇表达较为抽象的内容,从而更好地抒发诗人的情感,在情感体验上引起读者的共鸣。
1.唐诗中的通感隐喻个案研究
诗歌往往被人们视为最精练的话语表现形式之一,古代文人通过较短的文字来向读者传递信息,通感隐喻这一创作手法在诗人以诗句传情达意的过程中屡见不鲜。在中国历史上,唐朝经济繁荣,国家空前统一,强大的物质基础促成了我国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这期间文人墨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他们尽显其才,留下许多流传千古、家喻户晓的诗词。本文以唐诗为例,从认知角度对通感隐喻进行研究,以期对通感隐喻在诗歌中的作用进行剖析和解读。唐诗中有丰富的感官意象,诗人运用非凡的想象力和高超的写作技巧,将复杂的主题通过诗歌意象生动形象地呈现出来。从认知的角度对唐诗中的通感隐喻进行分析,不仅可以使读者更为深刻地体验与感知诗歌的意境,同时还能加深读者对诗人所表达的主题思想的理解。以下将对唐诗中出现的五种典型的通感隐喻现象与类型从认知角度进行分析。
(1)视觉与听觉的通感
通感现象中最为常见的即为视听感官相结合,“以形喻声”赋予了事物动态感。唐代学者孔颖达曾说: “声音感动于人,令人心想其形状如此。”视觉与听觉相结合,将抽象的形象具体化,使其更加鲜活,虚实结合,升华了人们对美的体验,从而使诗句更加优美。
例1:“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李贺《李凭箜篌引》)
李贺这两句名诗中,前句以“玉碎”“凤叫”描写了箜篌的乐声:玉碎意为其声音清脆有力,而凤叫喻其声之悠扬舒缓,两者皆属于听觉形象。后句中乐声变得凄惨悲凉,犹如残败的芙蓉在幽咽哭泣,突然其声又变得欢快起来,仿佛芳香的春兰的微笑。此时听觉形象无形中转变为视觉形象,即从听觉域映射到视觉域,视听结合,给读者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之感。
(2)触觉与视觉的通感
触觉指身体某一部分与物质接触来感知物质的感觉。虽然触觉在人类感官系统中属于最低级的感官,但是与其他感觉相比,触觉通过皮肤接触,能最直观地告诉我们物体的感知体验,因此它的感受性也更为具体和形象。而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等其他感官经常借助触觉系统来帮助描述其感受,因此触觉域频繁出现在通感隐喻的源域与目标域中。
例2:“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李商隐《无题》)
此诗句中“月光”为人的视觉所感知,因此属于视觉域,而“寒冷”则为触觉域或温觉域所感知。诗中“应觉月光寒”,是触觉域向视觉域的映射。诗人以触觉域的“寒”来描写视觉域的“月光”,实际上也是诗人通过诗句表达其内心情感的一种映射,从生理可以感知的“寒冷”反映心理上无以言表的“凄凉”,更能凸显诗人内心的悲凉,引起读者的共鸣。除此之外,再如“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牛郎织女星”(杜牧《秋夕》), “杨花扑帐春云热,归家屏风醉眼缬”(李贺《蝴蝶飞》)等,都是诗人把视觉和触觉相互融通,借通感隐喻来达到生动形象效果的典例。
(3)触觉与嗅觉的通感
例3: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杜甫《月夜》)
“蒙蒙雾气,或许沾湿了妻子的鬓发;冷冷月光,该是映寒了妻子的玉臂”。诗人以“香”来修饰“雾”,给人以嗅觉上的视觉感受,从嗅觉域过渡到视觉域,将妻子独自赏月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
(4)触觉与听觉的通感
例4:晨钟云外湿(杜甫《夔州雨湿不得上岸作》)
在此诗中,诗人以属于触觉域的“湿”字形容属于听觉域的钟声。诗人闻之钟声如穿云过雨一般,故为“湿”之感,是触觉与听觉的相互融合。再如“夕阳依旧垒,寒磬满空林”(刘长卿《秋日登吴公台上寺远眺》)。诗人用触觉上的“寒”形容磬声的深远,“寒磬衬空林”,昔日辉煌的场所如今已是人去楼空,衰草寒烟,给人一种凄凉之感。
(5)视觉与嗅觉的通感
视觉和嗅觉是密切相关的,对于嗅觉的感受常常影响着人们视觉的感受,芳香会让人联想到与之相关的美好画面,而恶臭则会让人有无法直视之感。
例5:瑶台雪花数千点,片片吹落春风香。 (李白《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
在此句诗中,雪本身没有味道,但诗人却以“香”写雪,从视觉域映射到嗅觉域,诗人用雪花使人联想到花,春天是百花争艳的季节,春风吹动,总带着屡屡花香,因此雪花便有了香味。再如在诗句“雨洗娟娟净,风吹细细香”(杜甫《严郑公宅同永竹》)中,竹经雨洗显得秀丽而洁净,微风吹来,可以闻到淡淡的清香。竹本无香,诗人却通过嗅觉向读者呈现了竹的视觉形象。
二、结语
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表明,人类在感知与体验世界的过程中生理感官机制和感知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类思维定势和认知方式。通感隐喻是隐喻的一种特殊类型,它的本质也是通过一种事物的特征映射另一种事物的特征,而不同之处在于通感隐喻的源域与目标域都仅涉及六种感觉域。唐诗中运用了大量的通感隐喻,它的使用使诗歌的主题思想更加清晰,诗歌意境跃然而出,让人如聆其声,如睹其物,给予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生动鲜明的感官意象将蕴含在诗人内心世界的真实情感活灵活现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因此,对通感的认知性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感受文学作品传达的意境和情感,充分体会诗歌语言的魅力,探究诗歌中所折射的人生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