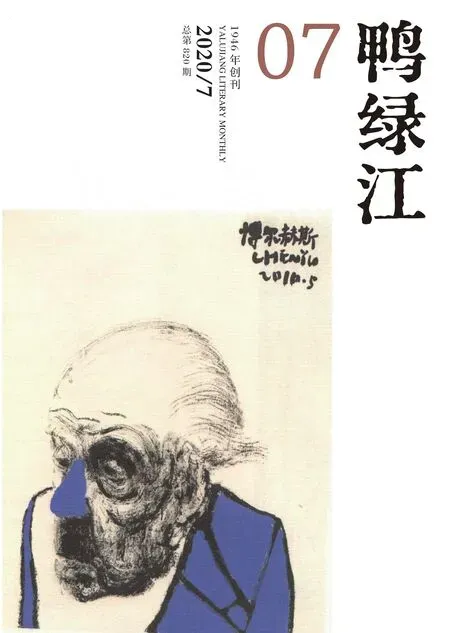论柔石《为奴隶的母亲》中的女性形象
2020-11-12闾庆超
闾庆超
柔石不仅在政治上是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而且就文学上来说,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大多以底层劳动人民为题材,展示封建社会压迫下农民的悲惨命运。值得注意的是,柔石小说有一个显著特点:特别注意和同情妇女的悲惨遭遇。他接受了屠格涅夫等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用自己的笔为改变妇女命运而抗争。《为奴隶的母亲》第一次将被“出典”的妇女作为小说主要人物,从而正面地、集中地暴露“典妻”所造成的悲剧。作品塑造了春宝娘和秀才妻子这两个典型女性的悲剧形象,从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妇女命运的另一种悲剧形态。本文主要探析春宝娘和秀才妻子身上所体现的中国劳动妇女悲剧命运的两种不同形态。
一、春宝娘——撕裂的情感
1.婚姻关系中的“商品”
春宝娘的丈夫本是一个皮贩,但由于生活境况日渐窘迫,所以他擅自做主将妻子以一百元的价格“出典”给年过五十却膝下无子的秀才一家。如此一来,春宝娘就在两个家庭中生活,实际上是两个人的妻子。作为皮贩的妻子,她没有享受过一丝一毫的疼爱,也从未感受过夫妻关系中的温情与呵护。她是一个在家庭中没有话语权的人,只能默默忍受着一切,这显然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在丈夫眼中她不是一个妻子,而是可以换取钱财的“商品”,是一个挣钱的工具,在春宝娘被出典的那一刻,就被夺去了作为一个妻子应有的权利和地位。
春宝娘是作为一件商品被卖到秀才家的。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春宝娘作为一个女人所拥有的生育能力。在这个家庭中,她过着妻子不像妻子,仆役不像仆役的生活。作为“被买来的肚子”和“生育的奴隶”,她成为秀才泄欲和传宗接代的工具;与此同时,还要承受来自秀才大妻的冷嘲热讽,被支使做一些下人该做的事情。以这样一种尴尬的身份在秀才家生活,她更加没有任何权利可言。她在两个家庭中不仅没有享受到妻子应有的权利,而且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作为妻子的感情产生了撕裂,这无疑是她悲剧命运的深刻体现。
2.骨肉分离的痛苦
作品从未提及春宝娘的真实姓名,她是以一个母亲的身份走进读者视野。母亲和子女间的感情是人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中最为亲密的一种关系,可以说“母性”是一种本能。但在作品中,春宝娘却多次经历了与亲生骨肉的生离死别,她作为一个母亲的情感被撕裂,灵魂深处的痛苦使她只能绝望而无奈地隐忍。
春宝娘一共有三个孩子:春宝、秋宝和刚出生就被烫死的女儿。女儿是她第二个孩子,也是唯一一个已经与她“死别”的孩子。刚刚出生的女儿还没等得及洗去身上的脏污,就被丈夫扼杀了生命。刚生产完的春宝娘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活活烫死,即使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叫喊,也没能阻止惨剧的发生,当即就如同“剜去了心一般地昏去了”。春宝娘是一个全心全意为孩子付出的母亲,春宝是她第一个孩子。在得知自己被丈夫“出典”之后,她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自己将要承受的屈辱,而是即将与母亲分离的孩子。为了春宝,她敢于鼓起勇气向丈夫控诉,即使到了秀才家也时刻挂念着她的孩子。但令人真正绝望的是,当她历经艰难终于回家时,春宝已然完全不记得她了,他害怕陌生的母亲,宁可躲到爱打他的父亲那里,也不愿接受母亲的触碰。她失去了春宝的信任。秋宝是她第三个孩子,但名义上她却是秋宝的“婶婶”。虽然和秀才之间没有感情,但孩子却是她的亲生骨肉,她像爱春宝一样爱这个孩子。可她只是这个家的买来生孩子的工具,三年期刚满,秀才大妻就迫不及待的将她扫地出门。她带着难舍难分的感情离开了秋宝,并且她明白,这一辈子她再也无法见到秋宝了,她与秋宝的母子缘分到此结束了。
春宝娘身为母亲,愿意为孩子付出一切。但她却多次被迫与孩子“生离”或“死别”,到最后她失去了所有孩子。悲惨的生活将她和儿子隔开了,她不仅经受着无爱的冷漠,还经受着不得所爱的痛苦,这对一个善良的母亲的心是多么严重的摧残。她炽热的母爱被命运无情地摧残,伴随着她余生的将是对春宝的无限负疚和对秋宝的无尽思念。
3.被侮辱的人格
春宝一家的困境可以说是广大贫苦人民的缩影。社会黑暗和阶级压迫使一个小小的三口之家濒于灭亡的边缘。而这时剥削者王狼步步紧逼要债,皮贩经沈家婆一番“点拨”后,决定以一百元的价格将妻子“出典”。我们固然愿意相信皮贩是由于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但他所作所为也确实剥夺了春宝娘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人格。而且秀才也是剥夺她人权的帮凶,如果以他为代表的剥削阶级不执着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思想观念,那么“典妻”习俗也就不复存在。在那暗无天日的年代里,遭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双重剥削,是整个社会底层劳动人民共同的悲剧命运。除此之外,春宝娘又两次被迫和儿子分离,充当“生育机器”。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黑暗社会和封建礼教的戕害下,不仅在经济上走投无路,在人格上被侮辱,连作为一个母亲的权利也被无情剥夺。
总之,春宝娘是统治阶级压迫的奴隶,她以被侮辱为代价换来的依然是没有尽头的奴隶生活,疾病和贫困仍然包围着她。阶级压迫和封建礼教无情地摧残折磨着这个善良的母亲的心灵,使她陷于无法摆脱的不幸和痛苦之中,她的悲剧命运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压迫造成的。
二、秀才妻子——共享的婚姻
在这部作品中,除春宝娘之外还有一个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女性形象——秀才的妻子。她是一个具有双重性的人物:既是剥削者,又是受害者。秀才妻子作为地主家庭的女主人,不可避免地站到了剥削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压迫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而且她自身也逃脱不出正统妇道观念的桎梏,所以将春宝娘找来给丈夫传宗接代,成天冷嘲热讽,把她当佣人一样使唤。这是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压迫,也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压迫。那么秀才妻子的生活真的就像表面上那样幸福美满吗?其实不然,在更多时候这也是一个具有悲剧命运的女人。
首先,她是一个有“痛失爱子”经历并且失去生育能力的悲惨女人。在春宝娘刚进秀才家时,秀才妻子曾透露自己有过一个男孩,可是不到十个月,便患了天花死去了,虽然文中秀才妻提及此事的神态可以用“轻描淡写”来形容,但身为母亲眼睁睁看着孩子病死,内心如何能不痛苦。更何况,那是个男孩,按照“母凭子贵”的观念来看,作为家中的长子,不但可以继承家族财产,而且也能让母亲在家中的地位日益稳固。无论是从母爱出发还是从利益考虑,“痛失爱子”对她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其次,她是一个不得不与他人共享婚姻的可悲女人。自古以来人们常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观念也深深烙印在秀才妻子的灵魂中。或许真的像她对春宝娘说的那样曾经拥有“美满而漂亮的结婚生活”,夫妻之间即便没有感情但也相敬如宾。可由于她之前孩子的死亡以及随后失去生育能力,不但丈夫对她越发冷淡,而且她自身也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所以即使万般不愿,但为了整个家庭,最终还是同意给丈夫“典来一个妻子”。同时为了保住自己正宫的地位,她向介绍人要求“人要沉默老实,又肯做事,还要对他底大妻肯低眉下手”,这是作为一个女人的悲哀与无奈。春宝娘进家之后,她像变态一样成天监视秀才和春宝娘的互动,稍有异动就提心吊胆,尤其是后来当得知春宝娘怀孕后,她的心理变化非常复杂:“她起初闻到她底受孕也欢喜,以后看见秀才的这样奉承她,她却怨恨她自己肚子底不会还债了”。作为这个家的女主人,从理性上她是高兴的,但作为一个女人,从感性上她无法抑制自己疯狂蔓延的嫉妒心,所以整天恶意讥嘲、奴役春宝娘。以至于后来秀才提出“愿意再拿出一百元钱,将她永远买下来”,她回答道:“你要买她,那先给我药死吧。”她恨丈夫三心二意,她更恨自己不能给家里增添一儿半女,让她不得已亲手将婚姻拿出来与她人共享,这对她来说是一种侮辱,更是一种永不泯灭的痛苦。
最后,她是一个深受封建观念的桎梏的可怜女人。在封建礼教的影响下,婚姻的缔结通常是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秀才和他妻子因父母包办而结合的可能性很大,这种无爱婚姻深深压抑了人情感需求的自由结合。虽然秀才妻子自称她的婚姻“美满而漂亮”,但从秀才的口中我们可以得知,这只不过是说给别人听的漂亮话,夫妻间的矛盾早已根深蒂固。秀才妻子是一个具有正统而强烈封建观念的女人,她坚定的奉行妇道所要求的“从一而终”,这就使她的情感需求处于深刻的矛盾冲突之中。据秀才说,她曾经也有一个很爱的人“她以前很爱那个长工,因为长工要和烧饭的黄妈多说话,她却常要骂黄妈的”,但是由于她的自我约束,只能将这种得不到满足的情感发泄在她的情敌“黄妈”身上。从此,“妇德”制约下的秀才妻成为一个极力压抑人性、得不到人情温暖和满含着嫉妒、怨恨、自责的女性。
结语
人类社会进入封建统治时期以后,妇女就被压制在社会底层,长期形成的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观念严重束缚着妇女。因此,柔石特别同情妇女的悲惨遭遇。虽然春宝娘和秀才妻子由于阶级不同,导致悲剧呈现的方式不同,但都可以从她们身上看到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从而达到作者对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进行揭露和批判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