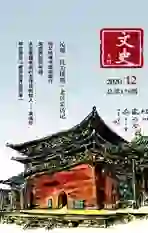坂地印象
2020-11-09冀成武
冀成武

坂地与俺村西靳屯接壤,小时候去没去过,想不起来了。我搜寻记忆,只记得从俺村到坂地的那条道是土路,下雨天几乎不能行走,两边有俺村的地块儿。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一清早,老有村干部在学校门口圪蹴着抽烟,等着老师领着学生娃儿到地里去干活。低年级的学生干不了啥高级活计,无怪乎捡个麦穗儿,除个草,摘个棉花。摘棉花这活可不轻省,得一朵一朵摘,摘得人手疼。摘好的棉花放在大大的棉包里,年轻的代教是城里人,她坐在棉包上,风呼呼地刮着长长的发辫,不时撩一下刘海,捣蛋的男孩子看着发呆。老师也不看我们,望着远方,眼神怪怪的。我们都觉得老师真好看。长大了才知道,这种眼神忧郁中带着渴望,渴望着离开乡村,那是青春的迷茫。
我的曾祖母薛三姑娘坐着大花轿从坂地启程,一路沟沟坎坎,轿夫们着实费了一把子力气,用不着恶作剧,自然晃晃悠悠颠得厉害。嫁了一户好人家,丈夫是天津酱合园的伙计,西靳屯又是一马平川,眼睛里没有一丝迷茫,全是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隔三差五曾祖母就要回坂地村一趟,或步行或骑驴,最风光的是坐着家里自备的轿。回娘家是一件大事,这排场,这威风,搅动了平静的山村,三姑娘回来了。好日子过了没几年,丈夫病故了,只好改嫁给我曾祖父,曾祖父是个贫苦农民,日子艰难,三姑娘回娘家的次数就少了。曾祖父年年给大户人家安瓜护园。西瓜开园的时候,每年东家都要奖励一些,作为额外的酬劳。曾祖父挑最好的几颗放在口袋里背着,兴冲冲地到丈人家走一趟。
每年收完秋,枣儿红了,太老舅薛守金从坂地背着一小口袋脆枣来了,一进门,放下口袋,解开扎口,伸手抓出满满一把往炕上一抛,对着眼巴巴瞅着口袋的几个外甥子说,俺孩们吃吧。爷爷和他的几个弟弟就一哄而上,抢着吃。几十年后,爷爷说,那是我们的节日,年年都盼着坂地的脆枣,盼着舅舅上门。
20世纪20年代某一年秋天,太老舅空背着手,脸色铁青着上门来了。爷爷唐突地问了一句,舅,咱坂地的脆枣今年没下来?一句话,点着了太老舅的满肚子火儿,说啥?还想吃枣儿?说着就上了手。爷爷转着花栏栏跑,太老舅追着打。太老舅气性也大,打个不停。曾祖父不停地拱手说,兄弟,对不住你,舅舅打外甥打几下没事,别把你气着。曾祖母见他还在打,就和他撕打在一起。边打边说,你这是要造反?看你是他舅,让你打几下,你还没完了。在众人的拉扯下太老舅住了手,蹲在地上,哈赤哈赤喘着粗气。“不就是俺们日子穷,今年西瓜下来没给你送,你就登门造事,从今往后,活不见面,死不送丧。”曾祖母气哼哼地说。太老舅啪地站起来,狠狠地瞪了姐姐一眼,出了门。从此两家十几年断了往来。
爺爷挨的这顿打到底因何而起始终不知。有的说,是因为俺村东头的表亲时不时给太老舅送这送那,亲姐姐家反而寡淡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有的说,太老舅不好活,没好气;有的说,矛盾不是一天积下的,谁知道呢。我说,具体缘由不重要,重要的是,因为亲,因为在乎,因为贫穷,贫穷才是万恶之首。
多年以后爷爷学了木匠,没忘记那顿好打,一气之下就在院子栽了四棵枣树,门口一棵,房前一棵,堡墙跟前两棵,品种是椴枣,口感胜过坂地枣,只是不易存放。但爷爷碰上太老舅还是毕恭毕敬,递烟打火,舅长舅短,两家的关系缓和了,又走动起来了。有一年,太老舅的儿子廷贵在岳家湾被国民党军队杀害,爷爷带着家伙什去坂地给做了棺材,打发廷贵入土为安。人说廷贵是民兵队长,也可能是游击队员,没人知道详情了。父亲回忆,他七八岁时,太老舅去世,爷爷和弟兄们领着他前去坂地吊唁,担着食盒,坂地道上俨然来了一哨人马。太老妗走不了路,用椅子扎了个“爬山虎”,让人抬着去坟地,送老汉最后一程。曾祖母,脾气也犟,说到做到,不去吊丧,但也悲切切没有了往日的威严。太老舅会做醋,会做茶叶,还会做酱,不知这些手艺是否是曾祖母传给他的,这些本事曾祖母门儿清。
太老舅就廷贵一个儿子,从外孙中选了一个给廷贵续了香火,这就是二虎,大名薛安祥,二虎1966年就入党了。1972年坂地村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书记是武启富,二虎是支委。二虎的亲哥玉虎,大名叫孙永昌,也是1966年入的党,在1973年到1977年间当过村支书。二虎担任过23年村会计,账目清清楚楚,两袖清风,是个干净人。二虎之后的村会计是梁秀芝,秀芝1989年接的会计,一干又是31年,秀芝的工作让人放心,但历届村干部少有私心也是一个原因吧。秀芝的父亲叫梁仲,小名叫拉害。拉害和我爷爷是结拜兄弟,当年五人结拜,号称五虎弟兄,都分别给五家父母磕了头,视对方父母为父母,亲如一家,不分彼此。困难时期互通有无,互帮互助,今天我给你家拿来一小袋粮食,不几天你给我家送来半口袋萝卜。弟兄们喝酒就大葱,大葱也不能管够,你一口我一口,其乐融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坂地这个地方能容人,对外来户不排斥。父亲有个学生叫李呼闻,其父祖籍山东,原是傅作义部队的军人,1953年落户坂地。村里人没有欺负他们,呼闻高中毕业后,在村卫生所干了三十多年,打针输液开处方,还会针灸,村里把他当宝贝一样对待,给他盖了房子,2007年还帮他娶了媳妇,呼闻无子女,2018年离世,最后是温锦滨出资操办丧葬所有事宜。
坂地人尊师重教也是远近闻名的,村民们有的,村里老师也有。钮定山、钮定芳兄妹俩先后在坂地长期执教,定山是个大高个,近视眼,说起坂地来,镜片后面亮晶晶的。“再穷不能穷教育”,这个口号坂地人没有贴在墙上,而是记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中。村里的小学校几易其地,但凡有点办法,总要设法改善,以期尽善尽美。1976年,父亲和靳元年老师用了四五天时间家访,两人各骑一辆自行车,走遍了西靳屯公社的每一个村庄,走到了每一位学生的家里。到了坂地,在温锦春同学家受到热情接待,可以说是倾其所有,盘盘碟碟好几样,主食是杂面面条。锦春妈妈还遗憾不已,没让老师们吃上一顿好面,白面实在是拿不出来,如今50年过去了,父亲依然记忆犹新。
锦春是个人才,会木匠,是他大哥锦奎教的,高中时新建教室主要是学生们干,学校只请了几个大工。锦春还帮助学校修理课桌凳,干啥像啥,不讲二话。1974年4月,锦春从西靳屯社办中学高中毕业后回村务农,当时的高中生是很稀罕的,18岁的锦春心情是低落的。一天锦春正在村里平整土地,村支书孙永昌派人通知他到本村小学。他匆忙赶去时,西靳屯公社指导员李尧卿等两位领导正在等他。李指导员对满头大汗的锦春说,“经过研究决定:让你担任坂地村民办小学教员,充实坂地小学教师队伍”。这个意外的消息让锦春欣喜万分,锦春在坂地当了两年多民办教师,下力气改善教学环境,改进教育质量,好评如潮。
1976年锦春光荣参军,走在坂地道上,心潮澎湃,欢呼雀跃之余,回望家乡,也有一丝难舍。部队是著名的38军,锦春从战士、班长、排长,一直干到连长,后来回到介休武装部当军事科长,又在介休人民法院干了17年。走出大山,走出一片新天地。
锦奎就更了不得了,平凡的世界,苦难的人生。当锦奎带着二十多个木匠进城,到工矿企业承揽活计,走在坂地道上,自有一股豪情。 他打小就不怕吃苦,不怕吃亏,从木匠起步,走出山村广交朋友。锦奎靠着说话算话,做事靠谱,低调虚怀,积极有为的品行,从事运输、洗煤、房地产等行业,不论给公家干还是给自己干,干啥谋啥,干啥成啥,成为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他总结了五句温氏家训,“言之必行是信义;表扬别人批评自己是美德;有所作为彰显祖德是孝行;兄弟和睦家族繁荣是悌行;面对利益一定要谦让。这五条是立身的根本。”有修为有作为,有标准有方法,是对过往的总结,也是对后来人的殷切期盼。
锦奎是温氏家族的主心骨,锦奎觉得光自己辦好企业还不够,还要注重解决企业持续发展问题,于是把接力棒交了出去,企业在年轻一代的手里拓展得更好。城里的豪华别墅,锦奎住不惯,搬回了村,和夫人一起伺候九十多岁的老母。天不亮就下地干活,锦奎闲不住,还有新的梦想。他说,“人生一世,总要给坂地做点实事,也算对得起坂地的老祖宗了。”这个梦想不仅有规划,有蓝图,还在一步一步地变为现实。这就是反哺,是真金白银的投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
坂地走出了一条新路,原先的穷山恶水换了人间,在新农村建设中异军突起,坂地的田园综合体模式无疑是一场良好的变革。面对困境,坂地人没有退缩,而是在积极寻找出路;坂地人吃苦耐劳,倔强勇敢;坂地人不甘人后,敢于做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坂地人战天斗地,敢叫日月换新天。坂地人感天动地,坂地变了,在持续的变化中旧貌换了新颜。
绵绵秋雨中徜徉在坂地丰收的氛围中,眼前一座小型工程正在兴建,一问方知是新建的污水处理站。黛顶白墙,近旁的庄稼地黄绿相间,和谐着呢。村里“尚节俭”“广积德”“勤读书”的牌匾落落大方,激励村人。宜居坂地、美丽坂地近在眼前,让你目不暇接。耳边响起呱呱呱的叫声,一群肥硕的大鹅呼呼啦啦从此岸游向彼岸,平添了些诗情画意。老有个疑问在脑子里挥之不去,坂地模式能否复制?坂地能否实现由投入驱动到内涵式发展的华丽转变?也许下一步应该着力打造文化坂地和幸福坂地了吧。
回家后向因病致残的父亲说起坂地举办了介休的丰收节,坂地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父亲来了精神,非要我说说坂地到底变成啥样了,我说,“变美啦,变得你想象不到了,改天陪你去转转,就怕您回来睡不着觉。”不过我觉得坂地最美的还不是风景,坂地美在人心,最美不过坂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