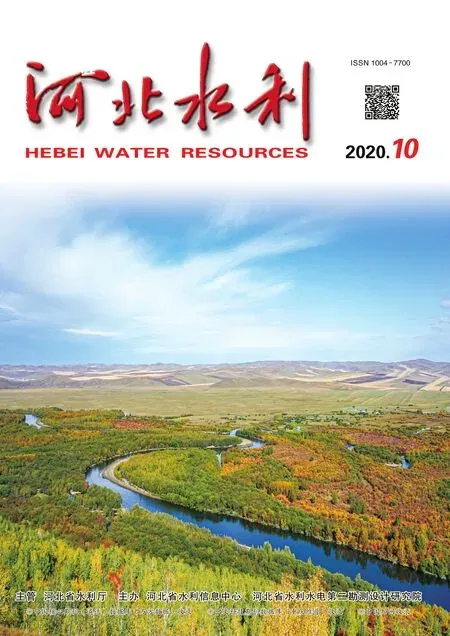家乡的麻池
2020-11-09温江水
□温江水
麻池,沤麻之池。麻,分生麻和熟麻,生麻脆而无韧性,且不易剥皮,而生麻经水浸泡沤过之后,把麻皮剥下来,纺麻、搓麻、织麻、编麻,在农村家家户户都离不了麻、离不了麻绳儿。尤其是在我们老家一带,除非你光着脚,只要穿鞋,男女老少清一色的麻绳儿纳成的“千层底儿”。
我们温和村,又名岗上,说是岗上,其实村子四周高、中间低,倒是一个“小盆地”。因为干旱缺水,先辈儿们从山西洪洞县迁徙到这里首先考虑的是用水问题。“小盆地”中间是生活区,所以就在村子的外围的南岭坡下挖了个净水池,拦蓄没有生活污染的雨水供全村人饮用。在村子下方建成一个大水池名叫麻池,留住雨水,沉淀“中水”,一水多用,灌溉全村。麻池下方筑有挡水墙,留有溢洪道,雨水小时悉数拦蓄,雨水大时就从溢洪道通过水茳沟流到清漳河,东流入海。
每逢下雨时,房上地下、院里街里流出来的雨水一股脑涌入麻池,整个村子的水一点儿也跑不了。夏天一场大雨就能把两个水池灌满,全村人吃用3个月没有问题。冬天下了雪后,村民们把场里地里不受污染的积雪填到净水池里,而把房上、院里等生活区的雪先扫到院里,再运到街上,而后或抬、或挑、或用车拉到麻池里,一时间麻池堆积如山成了我们村的“珠穆朗玛”。
麻池的水不能自流灌溉,只能肩挑手提,只要舍得力气,无论大集体还是自留地的小菜园一年四季时蔬不断。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离水近的人家和生产队用水比较方便。为了均衡用水人人共享麻池的福祉,村里把麻池边上或者离水近的地块重新分配,让4 个生产小队都能在麻池边上分到一块儿水浇园,供村民吃菜。每年到了红薯插秧、玉米点种等集中用水的季节,担水的人流排着队,麻池的水印儿落得快,越到水少时越抢着担,白天抢不上晚上加班担。麻池见了底,顽童们在浅水坑里抓蝌蚪,大人们还要在旁边挖泥坑淋水担。
就因麻池这点水,包括那些牛羊牲畜,出圈时或下山后,都要争先恐后往池边赶,生怕自己落了后。麻池岸边就那几个台阶,为了早饮几口水,个子大力气大的领头羊总是挤在前边,自己饮饱后,还要仗着自己的势力,拦着水道让自己群中的、沾亲带故的、有点眼法儿的先饮,那些头羊把能照顾的都照顾到了,才把水道让开。而那些弱势群体,要么被羊群挤着掉下水,要么悄悄地溜到外围耐着性子等待,等那些强势者饮饱喝足了,才能来到池边。其实,羊群里有多少只羊,每一只羊的脾气性格,乃至它的饥餐渴饮、身体力行,老羊馆是一清二楚。羊是这样,那骡马就不一样了,特别是那些刚下了套的牲口,主人还得紧紧的拽着笼头,来到池边再急也不能马上饮水,得让晾一会儿喘喘气,热身饮水容易伤风受寒,轻者伤了肠胃,重者大病一场。
老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如今,世道变了,时代好了,村子向外扩展,村民们大都在村外盖起了新房,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到城里住高楼大厦去了,全村实际常住人口已不足原来的2 了。村子成了“空心”,老房成了“空壳”,老街成了“空巷”,麻池成了“摆设”。每到雨季,虽然还能灌满,但除了必要的修房盖屋、红薯插秧外,也没人再去麻池担水了。再加之,随着“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村里少了“养羊户”没了“牛耕田”,牛羊成群、渴饮麻池成为历史。村民们吃上了机井水、水柜水,用上了卫生水、安全水,即使洗涤大块头的衣被也只是先在麻池涮一涮,回到家再用净水认认真真地洗干净。
村子的历史十分久远,人与麻池十分亲近。现在的麻池看起来“死水一潭”,但是关于麻池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生命、生态,以及人与水的故事,却依然装得满满登登,让人久久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