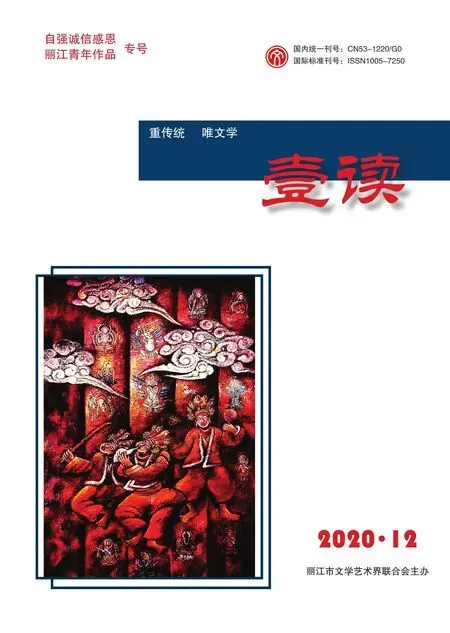村事
2020-11-05肖亚豪
◆肖亚豪
边哈
我从县城赶回月亮谷,去参加边哈的葬礼。
刚进入村口,大风扬起满地的黄土狂舞开来。在漫天的灰尘中,我看见一只乌鸦突然掠过远处的山坡,往村子的外围飞去。它速度极快,形如鬼魅,倏然不见。接着听得一阵炮仗声从附近处传来。我顿了顿,看见左侧山路边,一群吊客模样的人正在商讨着什么。有人问我死者家的具体位置。我顺手指了指便驱车离开了。身后传来妇女们拖着彝腔哭丧的调子。
说实话,我并不想回村。这阵子,新冠肺炎疫情那么严重。这时候去参加一位并无多少感情的邻居的葬礼,实在有些冒险。但思忖良久,还是决定回一趟。就当是回老屋看一看老人吧。
边哈其实是我家的老邻居了。二十年前,我家刚搬迁到月亮谷的时候,他经常来我家帮忙搭建木屋。他那时是一名出色的木匠,而且手艺极佳,村里需要做木活时往往都请他帮忙。他是个身材单薄的人,脸色腊黄,终日眯着眼睛,显得腼腆而谦和。他很少在家,春种秋收和过节的时候才偶尔见他回一次家。每年火把节前夕,他总是将家里的衣物拾掇一番并铺展在村口的红刺果上晾晒。接着翘起二郎腿,躺于屋外那株核桃树下,悠闲地吸兰花烟。除此而外,我的脑中再也没有留下关于他的任何印象了。
先回到老屋里,跟母亲打了招呼。洗脸,拍去身上的尘土,穿过屋后那片荊棘地,径直往边哈家走去。一路上,我的脑中不断闪过上个月的那个午后,当我们去探望重病中的边哈时的景象。当时他刚由昆明回来,准备在家里静候死亡的来临。此前,辗转几个地州医院,他仍不甘心,毕竟才活了56年。最后去了省城,由昆华医院诊断为肺癌。医生说他活不过二十天了。那天午后,当我走进他家院落时,觉得很冷清,只有两个人忙里忙外,进进出出地要为客人张罗食物。边哈躺在火塘边,他脸部肿胀,如蓬松的面团,用微弱的声音回答来客的问话。
翻过一座小山坡,拨开篱笆门,就进入边哈家了。屋前的斜坡上,人们或立或蹲,围着临时搭建的灵堂闲聊。灵堂布置得很庄重,黑、白、蓝、绿各色布料迎风招展。边哈穿着盛装,缩成一团斜躺在高高的木架上。周围堆垒着烟、酒、饼干、罐头之类的供品。我没有听到哭丧声。天空瓦蓝,风儿轻柔,只有屋后的寒鸦断断续续地哀鸣着。边哈的亲友们也穿着盛装从四面八方赶来送他最后一程,好像奔赴一场隆重的集体约会。
我看到我的二叔拎着一瓶泸沽湖白酒,摇晃着身子立在人群中,大声招呼吊客就坐。我劝他少喝点,他撇嘴,以不屑的口吻数落我。“人都有这么一天,怕个球嘛。”他说。我知道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医生嘱咐过不要饮酒,但他从未将其当作一回事儿。
呆了一会儿,我就折回家了。母亲正在老屋里忙着为我准备午饭呢。
当天傍晚,当我准备回县城的时候,夕阳早已染红了我家那几间老屋,狂风又卷着灰尘漫天狂舞开来,轰隆隆的声音响彻整个黄昏。母亲送我到大门口,听不清对我唠叨了些什么。我一下子觉得这几年死去的人特别多,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都在前赴后继地奔向死地。我突然发现,人其实是一批一批地走向死亡的,就像麦子,一年割一茬。人也一样,到最后,我们都终将成为时间的粮食。有时我怀疑,这世间,除非极端情况下,真的有人能看淡生死吗?所谓看淡,也许不过是面对死亡的无奈与恐惧时自我内心的适度调整罢了。
跟母亲道了别,接着驱车离开。透过车窗,我看见路边盛放着一树树洁白的梨花,都氤氲在夕阳晚照中,闪烁着梦幻般令人迷醉的光芒。我想,暖春大概要到来了吧。
万尼
关于万尼的死因,有多种猜测。其中最普遍的是鬼神引诱说。万尼所属的这一支家族中不得善终的人太多了。几十年来,各种天灾人祸搞得整个家族男丁凋零,万尼就是家里的独子。他其实有过一个只在人世活了三年的哥哥。村里开始通电那一年,电力施工队在村口挖了几个安电杆用的深坑,那时正是仲夏,雨水多,坑里积满了水,万尼的哥哥不慎跌进坑里淹死了。万尼的爹受了刺激,精神自此出了问题,疯狂的时候多,清醒的时候少。万尼的傻娘独立操持家业,大儿子死后,又拉扯大了一儿一女。万尼在县城读高中,妹妹在乡下读小学,都是毕业班,花销不小。家里每年卖点洋芋,养点家禽牲畜倒也能糊口。万尼两兄妹的学习都很优秀,特别是万尼,进入高中后,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而且万尼不是那种死读书的呆子,懂事、乐观,心思活泛,重情重义,是村里人人交口称赞的后生。村里人都说万尼的疯爹和傻娘居然生出这么好的儿子,真是虫豸生出龙种来了。只要再熬几年,等万尼大学毕业,找到工作就算熬出头了。倘若不是鬼神的引诱,万尼怎么会在此时选择自尽,一死了之呢?此前,万尼家里搞过一场法事,鸡骨占卜时,眼眶下有黑点,毕摩说是泪痕,为凶兆。眼看要到彝历新年了,按照当地的习惯,彝族过年时学校会放大约一周的长假。万尼的父母打算在孩子放假回家当晚做一场法事的。但万尼死在了放假前一晚。
万尼的爹是我的母亲的远房堂弟,幼年时,火把节和彝族过年后,我总要跟母亲去外祖父母处拜年。万尼的爹娘常来串门。万尼的爹叼着烟杆,穿一身破旧的灰色西服,脚上是石林牌胶鞋,人很瘦,一笑,露出满嘴焦黄的牙齿。他的女人戴着罗锅帽,挨着他坐着,脸上挂着一丝难以捉摸的神秘的微笑,整日不讲一句话。有人问候她时,总是习惯性地顿一顿,侧过身来,竖着耳朵问:“啥?”不等对方把问题复述一遍,她立马反应了过来,于是说:“哦,是的!”至于万尼,我已经记不起他幼年时的模样了。
彝族年过后,天气越发地冷了起来。有个周末的下午,空中飘起了微雪,寒风呼呼地吹着。我接到父亲的电话,说要我回家做一场法事。万尼死得不干不净,一瓶农药下去,口吐白沫,嘴歪眼斜。而且死在县城大街边的拐角处,死狗似的。按照传统迷信的说法,这样死去的人,灵魂会因回不到祖界而到处流窜,到谁家都会带来厄运。作为相关的亲戚,要通过法事和死者撇清关系,他才不会找上门来。
做完了法事,大家才觉得平安了,于是围着火塘闲聊开来。三婶说前几天随我的母亲去参加了万尼的丧礼,万尼的疯爹只是一个劲儿地傻笑,吃肉喝酒,满嘴流油。万尼的娘倚着墙角,面无表情地立着,望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出神。所有人都哭成一团。大家都为万尼的死而惋惜。万尼的几个同学也到了,说起万尼的事,也不胜感伤。据说万尼从来不愿透露自己的家境,更不愿主动地争取一份助学金。他的一日三餐都是两个馒头加一杯开水,偶尔才吃一份荤菜。万尼唯一的一位叔叔是村里有名的瘾君子。万尼死前曾留下一张便条,内容大约有三个意思。一是叫爹娘好好活,二是求叔叔戒掉毒瘾,三是说明自己的死与人无干,要求亲人不要去学校纠缠。三婶没念过书,但也和村里其他妇女一样爱玩微信,发朋友圈。她指着微信上的一张照片对我说:“喏,这个就是万尼。”我看到的是一张倔强的脸,瘦弱、清秀,眼里透着一种灵气。
“真傻,再熬几年,大学毕业了,有了工作就好了。”三婶说。
“也不怪他,是鬼神引诱他走向了死地。况且这年头大学毕业了又能怎样?还不是找不到工作?人活着都不容易。”母亲说。
夜深了,火塘边萦绕着呛人的松烟,我打开房门,灯光落在院落里,我发现雪已积了厚厚的一层了。
古布
刚回到老家,发小木嘎就告诉我,古布死去的那天傍晚,天边涌动着火红的云团。当时是隆冬时节,尽管晴了一整天,但万格火普山脚下的残雪还未消融尽,晚风一吹,整个村庄都冷飕飕的。在村口的集体院坝内,木嘎和一群吃过晚饭的村民们聚在一处,或立或蹲,束着披毡闲聊。猛然听到远处传来刺耳的哭喊声。大家愣了愣,听出是古布母亲的声音,紧忙往古布家赶去。
在木楞房左侧的屋檐下,古布的身躯悬在半空中,轻盈、单薄,如随风翻飞的纸片。一些白色的泡沫正顺着嘴角汩汩流淌。应该是先喝农药再自缢的。古布的母亲正在撕咬她的男人,古布的父亲推开女人。爬上榕柴堆,解下儿子的躯体。“这小子完蛋了。”村民们赶到他家时,他神情呆滞,反复念叨着。
古布从小就是个身体极其单薄的人,性子又懦弱,谁都可以欺负他。他不爱说话,又不讲卫生,整天蓬头垢面地挂着一条长长的鼻涕虫,大家嫌他脏,叫他“五保户”。我们做游戏,没人愿意同他一组,他一个人低着头,颓然踑踞于一旁,脱掉臭不可闻的石林牌胶鞋,低头抠脚趾头,或拿着一根树丫在地上瞎画。古布上学后,怎么教也不识数。老师问他一加一等于几?他答不上来,满脸通红地低头立着,不知所措。这几乎成了笑柄,一下课,大家都来逗他,问他一加一等于几?见他发窘的模样就哄堂大笑。我们村到学校大约有两公里多的距离,需要穿过大片松林地,春天的早晨,微雨濛濛,有雾,喇叭花绽开淡蓝色的小花朵,摇曳在山路边。学校上课时间晚,我们就去掏鸟窝。找到鸟窝后,大家总是把爬树的任务交给古布,我看见他脱了上衣,拼命往树顶爬去。雨丝落在他黑不溜秋的脊背上,形成一条条污黑的泥条。放学了,古布背不出乘法口决和生字表,每次都被老师关在教室里。我还隐约记得古布的左手(木嘎说是右手)上生有六根指头,他幼年时为此受过诸多嘲讽。他曾找来锯条,要求父亲将他多余的手指锯掉,他父亲找来手套给他戴上,他从此一年四季戴着一只手套。
我大约是八岁时搬离老家的。关于古布,我脑中只有这些零碎的印象了。至于成年以后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不过木嘎告诉我,在村里,古布从小到大都是一个多余的人,他唯一的价值是充当村民们无聊生活的笑料。也只有这个时候,大家才会记起村里还有这么一个人。木嘎说,当年同龄的伙伴都已成家,只有古布一直娶不到媳妇。有一年,同村的一个伙伴刚结婚不久,夜间总是听到屋后发出异响,起初以为是猫狗之类的动物。有一天深夜,这位伙伴刚从他女人的身上滑下来,突然又听到了响动,于是迅速起身,打起手电筒赶到屋后,看到有人跳过篱笆墙,拼命逃走。“那人是古布,他大概是憋出毛病来了。”木嘎说。
木嘎告诉我,不知从何时起,古布专门备了一把刀子随身带着,遇到欺负过他的人,甭管大人小孩,先不吱声,找机会从背后捅一刀。他先后用刀刺过十多人,但无一人毙命。家里穷得叮当响,儿子捅了人,古布的父母除了几只牛羊,没有可以赔偿的东西。吃了哑巴亏,整个村子的人都怕了古布,见他就躲。在初尝胜利的快意后,古布很快意识到这种胜利的可怕。所有人都不理他。有一次,他告诉木嘎说,他常常觉得整个村子只有他一人活着,其他的人都死绝了。他觉得自己活在一个只有他一个人生存的世界上。近年来,古布神情恍惚,每天拿着一把小刀在村里晃悠,让人整日提心吊胆。他成了鬼魅般无处不在的阴影。有时,他脱掉裤子当众摆弄生殖器,傻笑着大小便。
我搬离老家已经有很多年了,古布也算是我的远亲。此次回老家吊丧,我先去看望了古布的父母,说两句宽慰的话。古布的父亲对我说,一个人与其猪狗不如地活着,不如早点死去。尤其是像古布这样的人,活在世上是多余的,也是祸害,死了,于人于己都是解脱。
古布的父亲是个传统正派的男人,这是村里公认的。
那天正午,阳光刺目,酷热难耐,不似冬日。在户外的阴沟旁,古布的遗体怎么也火化不掉,古布的父亲往火堆里啐了一口唾沫,大骂儿子活着时混蛋,死了还不悔改。话刚说完,火舌翻滚,遗体立马化为灰烬。
拉莫
拉莫其实是死于艾滋病,但村里大多数人并不知情,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艾滋病,他们说拉莫死于肝病。一周前,我在一间小吃店里碰到拉莫的表哥,他告诉我拉莫患了肝炎,正在县医院传染科住院治疗,期间吐了整整一脸盆鲜血,大约活不久了。
在我的印象中,拉莫是个极健壮的汉子。2003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当拉莫第一次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时,就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当时我家刚搬到新营盘,村里有姑娘出嫁,拉莫是新郎,他身材高大壮实,脸膛黝黑,话极少,显得威风凛凛。那天傍晚,当太阳落山的时候,他俯下身子,脊背弓成一座山,在众人的呦喝声中将新娘背进屋,有人向他敬酒,他不讲客套话,接过搪瓷碗一饮而尽。来年春天的时候,拉莫就去外省打工了,那应该是宁蒗县第一批外出打工的人,我的堂妹学习成绩很好,但家境拮据窘困,为了供兄弟继续上学,小学没毕业就跟着拉莫两口子外出打工了。
当年火把节前夕,拉莫带着村里近十个青年男女回村过节来了。那时正是傍晚,夕阳悬在天边,在村口的集体院坝内,拉莫头一个下车,接着是一个个衣着时髦的青年男女。真的,我几乎认不出堂妹了,她已完全变了样,过去,她总是脏兮兮的,出去不到一年的时间,居然变成洋气十足的白天鹅了。当晚,二叔家杀了两只土鸡,我们围在火塘边,听堂妹说起城里的事,神往极了。堂妹说拉莫话不多,但其实是个好人,他关心每位他带出去的人,出门在外,又是乡里乡亲的,大家有什么难处,找到拉莫,他没有不帮的。据说当年邻村有不少人误入黑厂,但我们村的那批人有拉莫管着,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我对拉莫的了解仅止于此。我是在将近成年的时候才搬到新营盘的,这么多年了,一直在学校上学,只有假期的时候才会在家里呆一段时间。我至今还对村里的绝大多数人感到陌生。2016年冬天,一条公路从村口经过,将村子拦腰截成两部分,2019年冬天,又一条公路从村里经过,再次将村子拦腰截开,如今,村子一分为三,筑路施工队开着工程车来来往往,村里整日笼罩于漫漫黄土之中。有些农户田地或屋舍被征用,拿到政府补偿款,就地筑起了小洋楼。拉莫家也得到了一笔补偿款,准备建房的时候,拉莫死了,也就搁置了。一个月后,拉莫的父亲和母亲先后随儿子死去。有一天,三叔来我家,他告诉我,拉莫其实是患了艾滋病,他在外打工多年,不知什么时候沾上了海洛因,经常和人共用针管注射毒品。拉莫是独子,这么年轻就死去了,只留下一个女儿。村里人说,这真是断子绝孙了。
阿嘎
阿嘎的唇边长一颗黑痣,就像毛主席,大家都说那是福瑞的表征。阿嘎从小长得水灵,越大越标致,是村里公认的一枝花。阿嘎十五岁后,村里的后生们就络绎不绝地上门提亲,但阿嘎一个也瞧不上。阿嘎后来嫁给了邻村的一位教师。在村里,能够嫁给公家干部,意味着一生衣食无忧了,那是天大的福分了。最要紧的是,阿嘎的男人很疼她。
2009年,阿嘎和他的男人贷了款,又向亲友借些钱,在县城买了一套房。阿嘎的男人有一个弟弟,家里育有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儿子。那一年,他们将孩子寄宿在阿嘎家就外出打工了,两个孩子很乖巧,阿嘎视如己出。当年春节的时候,阿嘎带着男人和两个侄儿回村拜年,他们从我家门口经过,和我的母亲唠了几分钟,还顺手塞给我母亲一包夹心饼干和一把水果糖。我走出大门,看到的是一个美艳高挑的妇人和一个带着眼镜、矮小微胖的男人,身后跟着两个小男孩,约摸五六岁的年龄。母亲招呼我,让我喊婶子,我那时在上高三,正是羞涩的少年时期,不敢看对方,只埋头咕噜一声便走开了。
事后,母亲告诉我,那是咱们村嫁出去的女人,叫阿嘎。按彝家的辈份论,我得管她叫玛嘎。“多好的女人,可惜了”母亲叹着气说。母亲告诉我,不知什么原因,阿嘎成家多年,一直没有子嗣,有人说她身体有毛病,也有人说是男人的问题,具体什么原因,众说纷纭。
2017年春天,当桃花盛开的时候,我回了一趟村,发现大家都在讨论阿嘎的事。据说她杀了人,被抓走了。有一天夜里,她的男人去大理出差,阿嘎将两个侄子关起来,亲手割了两个男孩的生殖器,接着将孩子杀死。邻居听到孩子的哭喊声,也不敢进屋,立刻报了警,警察破门而入,见阿嘎已洗漱干净,换了一身干净的彝族服装,嘴角隐约挂着一丝微笑,正安详地坐在家门口。
补洛
补洛的婆婆过世早,公公是退休干部。1999年,补洛刚结婚一年,丈夫就死了。第二年,她嫁给了小叔子。补洛的小姑子去打工,由于有些姿色,跟了一个来内地做小本生意的台湾老板。有一年,台湾老板来村里,给补洛的男人买了一辆面包车。那时,村里的车还很少,男人学了车开着跑出租,收入很可观,没过多久就成了村里家境最殷实的人。
2010年冬天,补洛的男人开着一辆面包车撞在新营盘东风村口的一个坡地上,乘客都没有事,补洛的男人当场毙命。一根埋在坡道上的钢管被撞断,穿过前挡风玻璃刺入他的喉咙。路边有未消融尽的残雪,寒冬腊月,风一吹,结了冰,车胎压在冰面上,一滑,便撞上了对面的山坡。乘客纷纷下车,报警,通知司机的家属。大家闻讯赶来。补洛看到驾驶室里丈夫的惨状,立马晕倒,由路人抬到旁边,很久才醒过来,之后失声痛哭。
今年年初的一个午后,我听说村里出了丑事,补洛成了公公的女人。补洛属相、八字都不好,去跑马坪问过一个苏尼,说命很硬,克夫,没人敢再娶她。补洛不识字,哪里也去不了,公公是有文化的人,不信命,人老了,也无所谓了,于是便和儿媳妇一起搭伙过日子了。
瞎子
2018年9月25日傍晚,在万格广场偶遇一盲人按摩师。他身材颀长,穿白大褂,嘴叼香烟,昂着头,一副玩世不恭的高傲模样。这与我印象中凄凄惨惨的盲人形象大相径庭。甚异之,遂就坐,付费30 元,接受半小时按摩,与之攀谈。以下即为交谈内容。
我于1976年生于宁利乡白草坪村,今年42 岁了。我姓王,叫王富贵,我父亲给我取的名。他一辈子活得比牛马还低贱,希望生出一个富贵的种。但你看我,活得比他还低贱。解放前,我的父亲不知怎么流落到了宁蒗。他是四川人,汉族,据说他的家族原先在当地是名门望族,后来乡里闹兵灾,逃难过来了。在白草坪,他们十二个瘦骨伶仃的男人被当地的彝族土司捆住,成了家奴。其中有两个试图逃跑被砍了头,还有一个被绑在后山坡那株大松树上,活生生给剥了皮。我的父亲生前是个令人生厌的酒鬼,他爱扯谎,不知道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宁蒗解放后,他娶我母亲成了家。我母亲也是家奴,姓卢,是个聋子。五短身材,但体格健壮,干农活是把好手,我父亲喝醉了,她能拎小鸡似的把她的男人拎起来,夹在腋窝下带回家。
我是在七岁那年突然瞎掉的。我记得那年雨水很多,整个夏天都在下雨,草木绿得发亮,野花艳得晃眼睛。有一天傍晚,天下着大雨,我赶着牛羊回到家,发现少了一只羊羔。我父亲喝了点包谷酒,满脸通红地训斥我,叫我立刻回林子里找回羊羔。我披上一条山羊皮褂,冒雨翻过后山坡,往林子里赶去。那天傍晚我找到羊羔时,雨息了,我看到我的头顶凭空悬挂着一条彩虹,由于靠得太近,我觉得色彩艳得叫人窒息。当晚我就瞎了。我怀疑我的眼睛是被那道彩虹弄瞎的。
你看我的手法专业不?老实跟你讲,我可是专门去盲人按摩学校学习过的。那是十几年前吧,在大理,专门学了一年,又去店里实习了一年。回到宁蒗后,借钱开了个小店,我不奢望生意多火红,每天能赚点生活费我也就觉得自己活得有个人样了。你不知道刚瞎掉那会儿我有多痛苦,什么事也干不成,闲得发慌,眼前整天浮动着一片乳白色的海洋,辨不出东西南北,仿佛在漫无边际的牛奶里盲目地游泳一般。有时眼前还会闪过一圈圈彩虹状的光晕。真的,我觉得比起那些一出生就瞎掉的人来说,我的痛苦是双倍的。我见识过世界的模样,心中有更多的欲念,瞎掉后需要割舍更多的东西,承受的痛苦也就越多。当时,我老想我这辈子要完蛋了。想到起码连女人都没碰过就进了坟墓,我就觉得憋屈。哪个女人会看上一个瞎子呢?狗日的老天爷。
1999年春天,我结了婚。我的女人比我大十岁,是村里的寡妇,死了男人好几年了。我的酒鬼父亲那时还健在,他极力撮合我们,一来二去,也就成了。不是我吹牛皮,我年轻时长得仪表堂堂,器宇不凡。梳个大背头,就像领导。要紧的是,我会过日子,勤快、节俭又上进,那几年,我整个人都变得乐观了,不再怨天尤人,我知道那样不顶事。那阵子,我通过按摩,有了点积蓄。那时不像现在,可以去各地打工,我的女人命硬,克夫,没人敢娶,也没处去,于是跟了我这个瞎子。我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她善解人意,心思活泛,而且很能干,几十年来把家里布置得井井有条。你看我现在活得好好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命相这玩意真不靠谱,我女人克夫么?
其实我的眼睛也曾出现过复明的迹象。2000年冬天,有一天夜晚,我刚给女人下了个种,从她的身体滑下来的时候就不经意间看见肮脏的土坯墙上停留着一只硕大的黑苍蝇,我清楚地看见了它晶莹的眼眸和两根粗大的触角。我一翻身,仰面躺倒,发现月光正透过屋顶上那片透明的琉璃瓦,一束一束地泻在床边。我懵了一阵,随即惊呼了起来。不过当我的女人问我怎么回事时,我的眼前又形成一片乳白色的海洋了。
2001年3月,我儿子出生,第二年,我的酒鬼父亲死去,隔了一个月,我的聋子母亲跟着死去。我父亲生前已完全背叛了自己的四川汉人血统,他完全把自己当成了彝族人,尽管在彝区,他一直被视作低贱的奴隶,没有人瞧得起他,但他死后却转了运。他的遗体火化后的第二天,一只画眉鸟停在我家屋檐下叫了好一阵子,我的女人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端来一碗预先备好的荞麦粥去拜画眉鸟,按彝家的说法,那是我父亲魂魄的幻化物。同年4月,我母亲死去的第二天,一条带花斑的蛇嘴含鸡蛋,安详地卧在我家鸡埘里,我的女人怕得要命,但依然端来荞麦粥,硬着头皮拜了它。我真不愿意接受我的母亲死后竟幻化成了恶毒的蛇,她生前可没做过什么缺德事呀。我的酒鬼父亲尽扯谎,死后反而成了高贵的吉祥鸟。我们村里有些恶人死后幻化得更好呢。什么燕子、喜鹊、海鸥、布谷鸟都有,离谱得很。你说老天爷是不是眼瞎了?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都是扯淡的鬼话。
我儿子今年读高二了,就在你们民族中学。这小子会读书,今年还进了特尖班,明年考个一本应该没问题的吧。对了,我女人是彝族,跟我母亲一样,也姓卢,不瞒你说,按你们彝族的血统论,她也属于低贱的奴隶,我们一家都是低劣血统的杂交品种,可我不在乎。这都什么年代了,大清皇族爱新觉罗氏都与普通人通婚了,巴掌大的小凉山,还有人固守自以为高贵的血统,真是可笑。所谓血统,只是一种浅薄、狭隘、世俗的自以为是的偏见。我的人格不比谁卑贱。
晚风拂过,一些纸屑随风翻飞着。人们开始涌向万格广场。街边摆满了松果、樱桃和蜂蛹蠕动的蜂盘。广场中央,一群中老年妇女开始跟随音乐跳起了舞蹈。断断续续地聊了半小时,一转眼,按摩时间结束了,我起身,掏出一张50 元面额的纸币交给瞎子,他摸了摸,随即从左边的衣兜中摸出一沓钞票,熟练地补了我20 元钱。接着脱去白大褂,边顺手拿起一瓶水洗手,边随口吆喝道:“收工喽!”声音清澈、透亮。我怀疑他是否真是个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