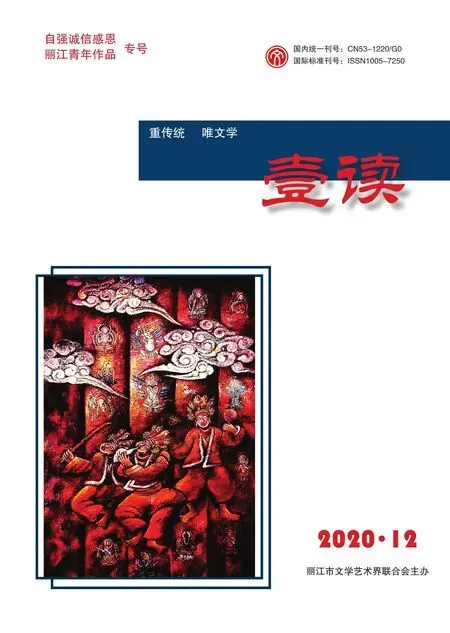有“根”的诗歌
——读《壹读》本期诗歌
2020-11-05马绍玺
◆马绍玺
丽江是一块有着独特韵味的土地。对丽江的认识,可以像大多数人一样,在旅游的人群中用双脚一步步去勘探,也可以在丽江诗人的作品中得到亲历。因为在这些诗人书写的一行行诗歌中,他们的灵魂与他们脚下大地的心跳已经合一。他们的诗所呈现的,是更真实、更集中、更可感的丽江,是他们用“最原始的字符,表示水/表示火,表示我爱你”(《天边》)的丽江。
阿卓务林已经在当下诗坛赢得了诗名。这位阅尽了“凉山雪”,拥有“飞越群山的翅膀”的年轻诗人,他的诗已经飞越了巍峨的小凉山,但是他诗歌的根脉依然牢牢盘扎在小凉山的群山沟壑中。因为常年与高大雄伟的山峰一起生活,阿卓务林获得了一种与群山会通了的精神世界和独特视角,他的诗也因为这种视角的独特而显示出独创性来:“云朵落下来/云朵长成了雪山/翅膀落下来/翅膀长成了森林//星辰落下来/星辰长成了古镇/雨水落下来/雨水长成了温泉”(《云南的云》)。在他眼里,山里的一草一木都是有情的、大美的:“多孤寂的一棵小树/它站在一座小山头/身边伴着仰天而卧的苔藓/和匍匐的草。一朵紫黄色的花/欲从树冠绽放/……而春天还在路上,黎明静悄悄/只有一只小鸟,在一遍遍喊/它的名字,喊得整座山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孤寂的树》)。这些诗句不仅让我们看见了日常中见不到的“整座山”的羞涩的“脸”——这是别的诗人没有写出来,而且呈现了让人为之震撼的属于大自然的和谐和秩序。因为本是同根生,所以所有源起于故乡的一切都包涵着无法舍离的情思:“仅仅一个岔口的迷失/雪莲花融化了雪/流入滚滚向东的金沙江/待我听见她的心跳/已是天涯海角”(《分别的海》)。那在时间的节奏中开放和凋谢的人事和物语,在他笔下都是满满的诗情:“雪,征服了整架山梁/那些高大的树木/和卑微的小草/一夜间,白了头/……而一株不起眼的腊梅/却赶在凋谢之前/抢先点燃自己的枝桠/并点燃了整个冬天的火绒草——/只要土地还有发绿的力量/纵使布谷鸟不在场/春天到了,绿色的河流/照样会从山下漫上来”(《腊梅》)。我想,只有把生命跟大山融为一体的人,才能有这样独特的生命体验。
诗人内在自我对自然山水的发现与会通,始终是丽江诗人灵感的重要来源。加撒古浪也是一位倾情于自然山水的秘语的诗人,他的诗就是他与群山河流对话的“凉山密码”(《凉山密码》)。在他的笔下,诗人就是“山坡上那棵孤独的树”,视野所及的一切都是他对话和书写的对象。他在自然之中感悟了人的时间性和与万物的统一性:“我爱着,爱着,就老了/然后死了。就像一朵雪的消融”。有时他真的想把自己融入到万古的群山中去,但又无时不感觉到有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让他体验着疼痛的分离:“那么多的群山,像天上的繁星/影影绰绰/不知是谁吹散了我们”(《截句》)。他从山脉河流宇宙的存在中感悟了生命的存在精神和向度:“选择仰望,是因为星空是海,我是一朵浪花/选择顶天立地,是因为山的骨骼,水的血脉//这么些年,我抱着山跑,水抱着我跑/一次次破碎,一次次相互重叠,相互撕扯”(《选择》)。在这种繁复的属于精神的对话和熔铸中,加撒古浪的那些优秀的诗呈现出了一种情感与知性融合的美。比如:“习惯了与一座山长久地对峙/不言也不语,不喜也不怒//青山一直没有白/白的只有稿纸,落满了雪/偶尔有鸟飞过/像极了路过的行人,各怀心事//那些互为峭壁的事物/此刻,正悄悄隐退//我没有理由怀疑——/我也是被时间刮过来的一只鸟”(《我是被时间刮过来的一只鸟》)。
与前面两位诗人相比,马海和付晓祺的组诗呈现的不是高蹈的意志和情感,他俩的诗更关注滇西北高原温暖的日常,但是依然清晰地呈现出人与高原对话的姿态和在万物中体味生命的意识。当诗人马海走进自然奇观金沙江虎跳峡时,突然变成了哑巴,因为面对自然的宏大,他突然顿悟,“在翻卷的巨浪中,说什么都是多余”(《岩壁上的鸣蝉》);当小小的自我闯入高原辽阔的世界时,他被眼前的一切震惊了:“哦,牦牛。一个个高原的标点。沉默,隐忍,彪悍。/大地的断章,在此铺开。牦牛就是不须呐喊的斗士/一对尖锐的角,在呼啸的高海拔上屹立”(《牦牛背上的风》);当高原的脚步落入秋天的季节时,他的内心像一片落叶一样脆弱和温柔,“几枚文字,怎么也码不出故乡的样子/凌乱的草垛,堵住回乡的路口”,让他无限伤情的,不仅只是回不去了的故乡,还有那不可抗拒的时间在人世显出的无情伤害:“爸妈给我一生的爱/我却给他们孤独的晚景/在我背离的这片故土上/面对说来就来的秋天/一生忙于收割的爸妈,毫无还手之力”(《又是一枕秋凉》)。这样的诗句,让人眼里湿润了泪水。
付晓祺诗歌的诗情更加温润柔软,但有时某一行又像一块烙铁一样,在你的心上烫开一个口子。这应该跟她女性的身份和体验有关。她喜欢通过写物来传达情感。在《很好的日子》里,古城里“在午后斑斓的阳光里舞蹈”的“金灿灿的桂花”,实际上是她内心里某些灿烂的“刻骨铭心的爱”的隐喻性存在。在普济寺相遇的那满山梨花和海棠,也是她“来不及说出的对世间的爱”,那梨花的白、海棠的红、杨柳的青,都是她与人世间最相思的人和事的情感关节点(《来到普济》)。她善于探寻事物中属于诗歌的秘密。在她的诗中,古城里古老的水井,“是慢时光里的眼”(《古井》);晚风中娉婷下落的变黄了的桦树叶子,“像极了转世的蝴蝶”(《夜》);那几经风雨在秋天成熟的玉米,其实是“劳作大半生的母亲/沉默的命运”(《沉默的玉米》)。我尤其喜欢她的《拉市鸥鸟》,这是一首较优秀的诗,在寻常的生活中写出了不寻常之美。诗中,诗人与海鸥融合,借海鸥之眼重新发现生活:“它们的左眼,看见/蓝的天空,蓝的湖面/右眼,看见/枯黄的落叶,灰白的芦苇/一些清晰而无法抵达的美//鸥鸟的眼,也是村庄的眼/在曦光日暮中凝望/连绵的群山,交错的田陌/时光的褶皱里/一些人离开,一些人留下/唯清风,在山岗里安睡。”这首诗平静、有控制的叙述,也与诗歌表现的情感相吻合,显示出了诗人对诗歌语言与抒情能力的把控。
阿别务机、阿甘凸浪、刘宁、佳桑四位是更年轻的诗人,是丽江诗歌新的生命力。他们有的刚刚参加工作,有的还在大学校园里读书。作为更年轻的生命,他们的诗歌体验更自由,也更自我。他们更执着于诗歌语言的构造功能,更相信修辞的力量。刘宁说,“如果我写一朵花/那便是在写我/如果我写一个在街角/舔冰激凌的男孩/那便是在写我/如果我写一把破旧的椅子/在地板上摩擦出尖锐的声响/那便是在写我”(《我的书写不为什么》)。她的诗就是要把这个隐藏的“我”点燃:“我把自己点燃/点燃这个令我不安的/令我痛苦的我”,然后在巅峰的体验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宁静”(《从我髋骨里撤退的人群》)。而在佳桑的体验里,“我时时刻刻都杂乱无章”(《液态素描》),因此他执着于对梦境的书写(《玫瑰与诗人素描》),对“颓败的废墟”和“颓败的花朵”的努力把握(《夜晚素描》),他的诗仿佛就是他在现实与梦境中插入的一把可以尽情旋转的钥匙,他想要告别那些“陈旧的抒情”,在语言的世界里,通过梦与思,与现实达成新的拥抱。
其实,如果说刘宁的一部分诗歌和佳桑的大部分诗歌代表了这些年轻诗人生命体验中飞翔的一翼的话,那么这些年轻诗人诗歌体验的另一翼,则依然扎根在脚下的丽江高原上。当刘宁安静下来,为母亲的日常“素描”的时候,她的诗在简单素朴中蕴含了一种源于独特的原生力量的美:“母亲围着绣有披星戴月图案的围裙/站在院子里的无花果树前/用纳西话叫我的名字/香樟树的影子覆在我身上/随着母亲的呼唤/树杈轻轻摇动”(《当我看见一棵香樟树》)。诗中,香樟树及其影子的意象的设置非常独特,充满了象征意味。诗歌不只是语言艺术,更不是一种为远方的写作,任何人的诗歌都需要有坚实的文化土壤和根基,就像阿甘凸浪所体验的一样,“总有一条河穿过我的胸膛/用它的平静流淌我生活的悲喜/总有一座山挺立在我的生命里/我背靠它的高度寻找远方的灿烂”(《我相信》)。阿甘凸浪的诗,是他对这条河这座山以及这山里与河边的人、事、情的书写:“我愿意在我的小村庄/和我最爱的人/过着加减法的生活/……我愿意就那样朴实无华地生活/朴实无华地在黄昏的屋檐下/写下我朴实的父亲和母亲/写下这两棵/站立在风霜雨雪中多年的树”(《加减法的生活》)。这其实是他的诗歌态度和诗歌追求。阿别务机的《慢下来》书写的是现代生活的“快”和个体生命渴望的“慢”之间的矛盾。他渴望时间和生命都能慢下来,因为只有在慢的状态里,才能发现美,才能拥抱丰富的人生。他的《一只鹰,从万格山飞过》是一首优秀的诗,它显示出了诗人敏锐的感受力,以及对诗歌语言的把握和抒情的控制力。诗歌分三节,每一节写的是鹰飞翔的一种情景,尤其第三节写鹰的飞翔“把我们塘山坪的云也赶到了天空的另一边”的感觉,最为敏锐独特。阿别务机的这首诗有美国诗人沃莱斯·史蒂文斯的著名诗歌《观察乌鸫的十三种方式》的味道。
丽江诗人的诗是有“根”的诗。我喜欢这样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