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上的气息
2020-10-24魏人彪
●魏人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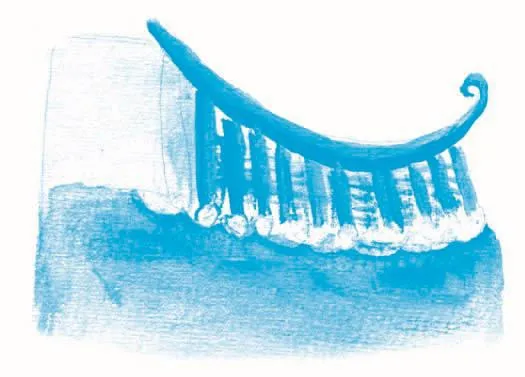
我站在屋檐下。
阳光在古镇一大片灰黑的瓦浪上流淌,不住地从檐头流泻下来,泼洒在我的身上,从头一直“淋”到脚。
我一下就闻到了瓦的气息。
瓦的气息温软香暖。因为瓦就是覆盖在人们温软香暖的日常生活上的,日复一日。
很久以前,那时我们家住的是公房。屋顶漏雨,房管所会派师傅来检修,宁海地方土话叫“捉漏”。一个捉漏师傅曾经告诉我,年代短的瓦片瓦腹和瓦背的气息是不一样的,只有久远的旧瓦,其气息才会浑然一体,浓厚、丰富、绵长。从那以后,若遇散落的瓦片,我会拿起一块,送到鼻子底下闻一闻。
刚刚铺上屋顶的新瓦,还带着砖窑中焦炭和高温烧烤的燥热气息,浅烟黑的瓦色,像未经世事的少年般稚气。四季交替,在一轮又一轮的曝晒、寒冻和风雨后,瓦们不再“青葱”,仿佛沉淀了岁月和经历,渐渐黝黑厚重。这个时候,在瓦背清新的气息里,有阳光和月光的味道,有冰雪消融、雨水浸透的湿润,有日夜兼程浩荡长风中的自然清气,也有生在瓦当瓦脊上的斑驳青苔、流苏瓦松那样一些绿植的青翠韵味……
而瓦腹温软香暖的气息却仍很薄很淡,似有若无。
那温软香暖中,最浓郁的气息自然是来自一日三餐的烟火气。第一蓬烟是带湿的青柴升上去的,那烟浓白似乳,呛鼻。灶膛里的柴火“噼噼啪啪”地燃烧得旺起来,烟淡了,火的焦灼感从灶口“呼呼”蹿出来,直逼脸面。一会儿工夫,锅水沸腾,米香随着锅沿“突突”喷溅而出的泡沫一嘟噜一嘟噜地从锅盖下钻出来,弥漫在空气里。少顷,煮熟的米饭的脂香渐渐显露,愈来愈浓。还有那些蒸在饭蒸上的咸菜咸鱼、土豆红薯的气味,也洋溢开来,把人肚子里的馋虫勾引得蠢蠢欲动。等到喷溅的泡沫没了,饭气里有了一丝丝焦香,就得赶紧扑灭柴火。这时,满屋子蔓延着刺鼻的烟火气,悄悄附着到了瓦上。
抢收抢种的农忙时节,女主人为了慰劳耕作辛苦的男人们,会将从烧饭灶膛褪出来的柴火随即塞入旁边的小灶,专门做几个下酒的、闲时舍不得破费的好菜。比如炒白蟹、小葱烤鲫鱼、红烧蹄髈、生炒鸡块,等等。于是,终日寡淡清汤的屋子里难得有了油腻。那些热烈翻滚的油腻的气浪趁机沾上屋顶的瓦片,久久不散。难怪过了农忙很长一段时间,进门的男人还吸着鼻子问:“今天什么日子,又烧蹄髈哪?”女人回道:“哪有啊?”男人东瞧瞧西瞅瞅,嘿嘿地笑,“我怎么又闻到烧蹄髈的味了呢!”
就这样,这温软香暖的气息,一年又一年地添加着,晕染着,在时光的流逝中不断地渗透着,直至透彻背负云天的瓦背。
有一次,闻着一块旧瓦,我突然觉得,那上面储存的气息,与日夜在瓦屋里操持的娘的拦腰布上、衣衫上的气味,没有什么不一样!
老屋如娘。
(和风朗月摘自《自然》2020年7月20日/图 雨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