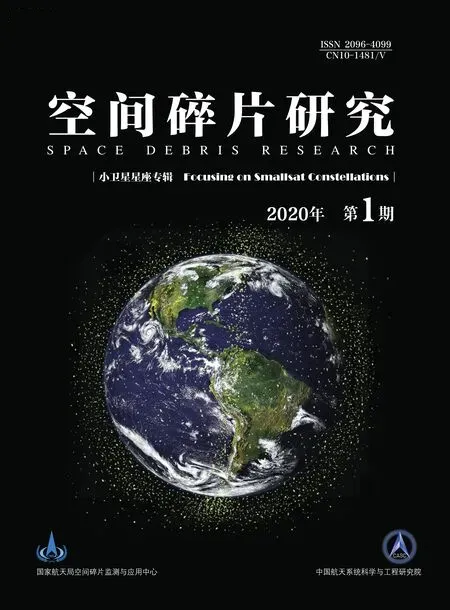空间交通管理概念研究
2020-10-22胡朝斌黄宇民郭世亮李帅任迪吴晓丹
胡朝斌 黄宇民, 郭世亮, 李帅, 任迪, 吴晓丹
(1. 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 北京100190; 2. 钱学森空间技术实验室, 北京100094;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研发部, 北京100037; 4. 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102206)
1 引言
自2009 年美国和俄罗斯的卫星发生人类历史上首次“空间交通事故” 以来, 在轨卫星的直接相撞由理论上的威胁变成了事实的存在, 空间交通管理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近年来, 世界各国在太空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 各航天强国不断调整太空安全战略, 加快发展空间军事化进程, 使得太空安全博弈局势日益复杂, 对我国空间资产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 同时随着太空技术的发展, 新型航天器数量迅速增长, 增大了在轨碰撞的概率, 给在轨航天器正常运行构成严重威胁, 空间安全问题愈显突出。
空间交通管理、 太空交通管理与外空交通管理在英语中对应的都是Space Traffic Management(简称STM), 只是因翻译的习惯和应用的领域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中文术语, 视为同一概念, 在本文中, 以空间交通管理为统一标准。
2 空间交通管理概念的演变
人类的太空活动首先是突破进入空间技术,实现科技创新。 在进入空间技术突破后, 太空的军事应用成为发展热点。 空间技术及其应用逐渐成熟后, 就全面渗透进入人类的经济、 技术、 社会、 军事等各个领域, 空间控制成为“新战场”。随着太空活动日趋频繁, 碎片急剧增多; 技术门槛逐渐降低, 低轨巨型星座的出现, 造成太空活动秩序的失序, 对空间交通管理的迫切需求随之而来。
2.1 概念的主要发展阶段划分
国际上, 空间交通管理概念的发展, 从时间上可以粗略分为三个阶段: 即萌芽阶段、 理论研究探讨阶段和实际操作的新阶段。 图1 是空间交通管理的概念发展时间标志示意图。

图1 空间交通管理的概念发展标志示意图Fig.1 Development signs for the concepts of STM
2.2 萌芽阶段
主要是指上世纪60 年代至1981 年期间。 空间交通管理概念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60 年代, 当时的提法是航天器交通管控, 通过信号和导引避免航天器在发射、 在轨和星际飞行中的碰撞。
在人类成功发射人造卫星并开始了大规模空间信息的应用后, 在许多研究报告中, 基于对未来发展的预测, 开始关注卫星安全问题, 陆续开始出现了一系列与空间交通管理类似及相关的概念, 主要为一系列对航天器及其行为的约束性概念[1,2](见图2)。

图2 萌芽阶段的概念系列示意图Fig.2 The concepts of STM for the budding stage
由于当时的发展热点是进入太空能力和应用空间的能力发展, 空间交通管理未成为当时的研究热点。
2.3 理论研究探讨阶段
以1982 年捷克斯洛伐克学者鲁博斯·帕瑞克在国际空间法学会论文中正式提出“空间交通管理” 一词为标志, 到2016 年为止。
以美国、 前苏联两国为代表, 虽然各国发射了数量众多的各类卫星及星座, 但由于太空的广袤, 最初几十年发射和在轨卫星数量少, 这些在轨卫星间碰撞和受到干扰的可能性小, 问题不太严重, 因此对空间交通管理的需求不十分迫切,各国主要针对空间碎片管理开展理论研究。
随着在轨卫星数量的增多及空间废弃物、 碎片的不断累积, 频率、 轨位等空间资源日渐短缺, 空间交通管理的需求日渐迫切, 各国的相关研究日渐深入, 空间交通管理的概念逐渐成形[3]。

图3 理论研究阶段的概念系列示意图Fig.3 The concepts of STM for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stage
2009 年美国和俄罗斯卫星发生的人类历史上首次“太空交通事故”, 标志着在轨卫星的直接相撞由理论上的威胁变成了事实的存在, 空间交通管理成为研究热点, 虽然在联合国的不同层面也开展了相关谈判和研究, 但由于各国的立场分歧严重, 各国对空间交通管理的概念没有形成共识。
理论研究探讨阶段的主要成果包括:
(1) 1992 年, 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原则》, 并体现在2009 年联合国外空委科技小组委员会通过的《外层空间核动力源应用问题安全框架》。
(2) 2001 年, 美国NASA 和国防部制定了碎片减缓标准。
(3) 2006 年, 国际宇航科学院(IAA) 发布《外空交通管理研究报告》。
(4) 2007 年, 欧盟提出“外空活动国际行为守则” 倡议。
(5) 欧空局发起“清洁外空倡议”。
2.4 实际操作的新阶段
以2017 年欧洲的白皮书 (三卷) 发表和2018 年6 月美国正式发布《国家外空交通管理政策》 为标志, 空间交通管理领域进入了各国实际操作及支撑系统的建立阶段。
随着空间技术应用的不断深入发展和技术门槛的降低, 人类正在面临一个空间系统建设爆发式发展的阶段, 主要标志就是巨型星座热的出现。 人类的空间资源面临着巨大的短缺, 空间环境面临着极大的压力, 各国为保护自己的空间资产、 维护各自的太空利益, 开始着手空间交通管理系统的实际建设与运行。
2019 年9 月2 日, 欧空局发布消息, 欧空局计算出其Aeolus 卫星与SapceX 公司刚刚发射入轨的Starlink -44 卫星存在潜在的相撞风险并预警, 与SapceX 公司沟通未获回应的情况下, 欧空局不得不对Aeolus 卫星启动机动措施, 避免与Starlink-44 卫星的碰撞。 此事件凸显了低轨巨型星座爆发式发展带来的对空间交通管理需求的迫切性问题。
实际操作新阶段的主要成果包括:
(1) 2017 年, 欧空局发表“实施欧洲外空交通管理制度” 白皮书(共三卷)。
(2) 2018 年6 月, 美国发布《国家外空交通管理政策》 (3 号令)。
(3) 2018 年6 月,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空间态势感知与实体框架管理法案》, 由商务部向民用和商业卫星运营商提供碰撞预警等交通管理服务, 由NASA 制定空间交通管理科技规划等。
(4) 2019 年, 美国依据3 号令, 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更详细的政策措施报告。
3 各主要国家的概念定义
3.1 美国
(1) 萌芽与理论研究阶段
提出了卫星周围“禁入区域”、 “空间试验范围” 和“卫星位置管理” 等与空间交通管理有关的概念和提法。 上世纪70 年代中期开始逐渐研发出将废弃卫星转移到废弃轨道上的技术。 1980年, 美国国防部计算出自己的两颗卫星很可能相撞, 一颗失控而另一颗尚在运行, 采用机动方式将废弃卫星转移至另一轨道上, 是为卫星位置管理。
1988 年7 月, 美国国会审议由美国空间科学和应用分会关于空间碎片的议题。 该分会主席提出一个极端的空间交通管理概念: 为了减少地球轨道上增加的空间碎片, 建议建立一个“零增长” 政策, 也就是在旧的碎片再入大气层之前不允许有新的空间碎片产生。 但如何来实现这一提议以及是否可以应用于美国卫星就没有下文了。
2016 年, 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为NASA 准备“轨道交通管理研究” 报告, 报告并没有空间交通管理或轨道交通管理的概念, 只有空间交通安全, 即“免于带来危害的在轨意外”, 危害包括宇航员和载人飞行参与人员的伤亡以及对航天器的损毁和干扰, 意外是指碰撞或解体。
(2) 实际操作的新阶段
2018 年6 月, 美国发布《国家外空交通管理政策》, 这是美国首份完整的、 综合性的空间交通管理政策, 旨在防范因日益拥挤、 竞争加剧造成的空间活动危险, 计划向国际推广管理标准和做法, 谋取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 引起广泛关注。
其中, 对空间交通管理定义是: 指为提高太空环境中行动的安全性、 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而对太空活动进行的规划、 协调和在轨同步工作。
2018 年6 月,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空间态势感知与实体框架管理法案》, 由商务部向民用和商业卫星运营商提供碰撞预警等交通管理服务,由NASA 制定空间交通管理科技规划。
3.2 欧洲
在研究阶段, 欧洲非常活跃, 提出了一些研究成果, 2007 年, 欧盟提出“外空活动国际行为守则” 倡议; 而欧空局发起了“清洁外空倡议”。
在实际操作的新阶段, 2017 年, 欧空局发表“实施欧洲外空交通管理制度” 白皮书(共三卷),认可空间交通管理的必要性。 白皮书是欧洲空间交通管理路线图, 突出了点对点亚轨道飞行。
其目标是在未来太空领域发挥作用并占有足够的份额, 同时, 必须通过国际协作确立欧洲空间交通管理的话语权和欧盟倡议的“外空活动国际行为守则”。
2017 年, 欧洲白皮书将空间交通管理界定为: “为确保安全的载人和无人的洲际飞行、 亚轨道飞行及穿越近地空间和空气空间的飞行, 实施所有必要管理、 监督和控制运行措施。”
3.3 俄罗斯
目前没有找到俄罗斯相关的概念研究报告。但2016 年, 俄罗斯在外空委员会上的会议文件的观点如下:
(1) 俄罗斯强调必须基于国际合作, 要求实现空间物体数据的共享, 特别是要建立联合国层面的信息共享平台;
(2) 俄罗斯认为没有有效的空间操作安全框架, 空间交通管理难以实施;
(3) 俄罗斯认为需要统一的国际层面基础设施支撑, 遵循“一致” 原则;
(4) 俄罗斯认为需要开展更多技术层面的研究和协商;
(5) 俄罗斯认为目前的国际谈判不能支撑空间交通管理的概念。
3.4 联合国层面
(1) 主要谈判过程及成果
在联合国层面, 大致经历了一个从零散的关注和谈判到磋商热点议题的发展历程, 目前成为空间治理和安全问题的重要方面。 空间交通管理是需要国际协调和统一规则的安全事项。
1978 年, 俄罗斯核动力卫星 “Cosmos954”再入并落至加拿大无人区, 引发国际社会对近地轨道的核动力源卫星的关注。 1992 年, 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原则》,目标是保护地面的人类和环境免受辐射影响。 此间讨论产生了“核安全轨道” 概念, 并体现在2009 年联合国外空委科技小组委员会通过的《外层空间核动力源应用问题安全框架》 中。 该框架试图在保护环境和不过分限制使用核动力源空间应用中寻求平衡, 建议各国减少在空间使用放射性物质, 但允许将核动力源用于非核动力源无法合理执行的航天任务, 且用于高轨道, 若用于低地球轨道, 须在航天任务完毕后将核反应堆存放至足够高的轨道上。
国际电信联盟(ITU) 主要负责各国卫星的轨位和频谱的登记协调, 防止射频干扰。
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法律小组委员会在2002 年、 2007 年和2008 年曾几次讨论过这个议题。 2008 年法律小组委员会会议期间曾有这样的观点, 为了建立更为安全和易进入的空间环境, 和平利用外空委员会应当考虑起草空间交通管理指导原则。 但各国讨论认为空间交通管理为时尚早, 无法接受限制自由的规则。
此外, 日内瓦裁军会议有关外空军控的谈判, 包括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有助于确保外空交通秩序, 2007 年 《空间碎片减缓指南》, 2013 年“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 政府专家组报告,2014 年“外空活动长期可持续性” 工作组报告以及有关谈判都与空间交通管理相关。
(2) 学术研究
国际宇航科学院 (IAA) 受联合国委托于2001 年成立研究小组, 启动一项关于空间交通管理的课题研究, 在2003 年提交到在德国举行的国际宇航大会上进行讨论。 该小组由16 位专家组成, 用跨学科的方法从科学技术和法律规范两个层面研究这个问题。 2006 年发布《外空交通管理研究报告》。 这份报告提供了全局的概念, 列举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核心观点是空间活动需要整体性的交通管理, 而不是隔离的分散活动。2014 年, 国际宇航科学院设立课题“空间交通管理——走向实施的路线图”, 2017 年发布报告, 在2006 年报告的基础上, 探讨空间交通管理的具体实施。
目前国际上获得比较广泛认可的概念是2006年IAA 报告中提出的。 主要内容为: 空间交通管理是指为了保障航天器进入空间、 空间运行和自空间返回地球的安全, 免受物质和电磁波干扰,而制订的一系列技术和法律规范[4]。 其目的是以恰当方式避免对空间活动的有害干扰, 实现《外空条约》 规定的自由进入空间。 在2014 年9 月的国际宇航大会(IAC 大会) 期间, IAA 批准“空间交通管理——走向实施的路线图” (Space Traffic Management-Towards a Roadmap for Implementation) 的课题研究立项。 IAA 此项课题研究是继2006 年IAA “空间交通管理研究报告” 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深入研究, 其研究目标是在2006 年《空间交通管理研究报告》 10 年后的2016 年, 再出版一份关于空间交通管理的研究报告。 2017 年路线图报告基本沿用了2006 年版的空间交通管理的概念, 但也有所调整, 以跟随空间活动的最新发展, 包括活动主体数量的增加和性质多样化。
4 各国的概念解读
4.1 各方概念比较
表1 是从立法形式、 发展目的、 行动举措、 管理对象、 管理方式等五方面对各方概念进行比较。

表1 各方概念的比较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concepts of main parties
从立法形式来看, 美国主要通过国内法长臂管辖来实现其国际管辖, 而欧盟和联合国主要通过国际法的形式来实现。
从立法目的来看, 美国主要是为了保持其技术领先地位, 形成对对手的技术代差; 欧盟主要是为了保持其在商业航天领域的市场份额; 而联合国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持太空和平及空间领域的可持续性发展。
从采取的举措来看, 美国是“对太空活动进行的规划、 协调和在轨同步工作”, 可以是双边或多边, 也可以是单边的, 且工作这个词非常基本和中性, 工作是否有结果本身也不重要; 而欧盟是“实施所有必要管理、 监督和控制运行措施”, 措施这个词本身就有一定的强制性和双边或多边协商后的共同遵守的意味; 联合国是“制订的一系列技术和法律规范”, 显然是在多边协商一致后制订的、 须强制执行和遵守的。
从管理的对象来看, 各方均为“所有太空物体及频谱”, 非常一致。
从管理的方式来看, 美国强调必须由美国主导; 欧盟和联合国则强调必须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实施。
4.2 各方概念解读
(1) 美国的概念解读
2016 年美国“轨道交通管理研究” 报告并没有空间交通管理或轨道交通管理的概念, 只有空间交通安全。 该报告明言“空间交通管理” 这个措辞的使用是有问题的, 因为暗示了集中命令和控制, 类似于航空交通管理, 将建议由国防部管理军事信息, 政府搜集、 管理和分享民用和商业信息, 并识别责任。
而“3 号令” 中的定义, 有了很大的进步,承认空间交通管理的必要性, 也直接使用了空间交通管理一词。 但是, 却将空间交通管理仅仅限制在宽泛的规划、 协调和在轨同步工作上, 仅为较低层次的、 广义上的管理行为, 且其目的是确立国内而非国际制度。
从中可以看出: 美国强调自身资产的绝对安全, 强调“他国对美的空间透明”; 美国拒绝任何国际(对美国资产) 共同管理的概念; 其目标是保持自身的太空优势, 确保美国航天技术的龙头地位。
(2) 欧盟的概念解读
从欧盟的概念中可以看出: 欧洲的概念比美国的更进一步, 定义成为“必要的措施”, 有协调、 决策并执行的意味。 强调基于国际协作, 确保欧洲的话语权; 强调共同管理、 监督及控制运行; 突出了穿越空气空间和亚轨道区域的飞行管理要求; 重点突出欧洲自身的要求, 确保欧洲的外空市场份额。
(3) 联合国的概念解读
2001 年, 国际宇航科学院(IAA) 在其2006年《空间交通管理研究报告》 中所使用的术语部分, 将空间交通管理界定为“空间交通管理包括进入外空, 在轨运行以及再入过程中保障安全和不受干扰的各种技术和制度规定的总称”。 这种表述并未界定什么是空间交通管理, 而是指出了空间交通管理的目标, 因此并没有提供一般意义上可以操作的概念。 新型航空航天器的发射是否应作为被管理的对象? 是否应为一些执行导航、通信和观测等任务的特定航天器在国家之间分配轨道资源? 再入问题是否应纳入管理的范围? 对这些问题国际社会尚没有答案。 在此份研究报告中, 对空间交通管理概念是否有新的发展, 我们仍需认真研究。
4.3 主要结论与思考
从上面的梳理、 分析和解读中,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 各方概念不统一, 概念仍处在发展阶段。
目前, 太空领域各方处在激烈的博弈中,面临发展瓶颈。 这就给了我们提出自己的概念、展示中国立场的机会, 我们把握这一时机, 在新的一轮空间利益博弈到来之际维护我国的太空利益。
(2) 各国(及联盟) 的空间交通管理概念是其太空战略的具体体现。
发展空间交通管理系统是我国推广全球太空公域治理的切入点和抓手, 我们需要加快有中国特色的空间交通管理概念研究, 体现中国特色的太空战略, 为我国的航天事业发展保驾护航。
(3) 各国(及联盟) 都强调空间交通管理是为了太空安全、 可持续发展, 但背后都隐藏着各自的利益诉求。
在新的一轮空间技术与应用的大发展到来之际, 国际上新的一轮空间利益的博弈即将展开,空间交通管理是未来人类突破空间环境的瓶颈制约、 实现航天技术长期可持续性发展的保障, 如何科学合理地在太空安全、 可持续发展的大旗下体现我国的利益诉求, 是目前空间交通管理研究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4) 话语权的争夺和太空博弈, 始终贯穿在空间交通管理的发展中。
从空间交通管理概念的发展历程来看, 各国的议题设置能力和空间技术的实力是其影响的主要因素。 我国是空间技术与应用的后发国家, 现在的议题设置能力和空间技术的实力与航天强国相比有相当的差距, “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治理” 理念为实现太空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创新思路, 如何在空间交通管理研究中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治理” 的思想,是现在争夺空间交通管理话语权的有力思想武器。
5 我国的后续工作建议
5.1 我国目前的研究现状
我国国内研究呈现出分散的、 点状的自发性特点, 缺乏专职、 统一的研究技术队伍。 目前已有部分装备可以实现部分能力支撑, 但缺乏一体化的整体需求牵引, 与未来建设目标严重不匹配。
目前, 我国主要从国际法角度参与空间交通管理的相关研究。 以被动的、 应对式的工作方式参与相关国际层面开展的对话, 缺乏自主研究成果的支撑, 没有提出适合自己的相关概念, 国际话语权、 议题设置能力严重不足。
表2 是不完全统计的(三年内的发表研究成果) 美国、 中国主要从事、 参与空间交通管理研究的单位。

表2 不完全统计的(三年内的发表研究成果) 美国、 中国主要从事、 参与空间交通管理研究的单位Table 2 Incomplete statistics of units engaged in and partaking research on STM in the US and China
5.2 后续工作建议
空间交通管理牵扯面广, 利益纠葛复杂, 会引起更加复杂的问题和挑战, 需要我国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具体的应对建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紧密跟踪研究
目前空间交通管理国际情况复杂, 技术、 政策、 法律、 商业等多领域都存在问题, 需要组织统一、 专业的研究力量, 紧盯国外发展情况和态势, 分析其内在动因、 目的、 技术水平和实际进展。 同时结合国内情况, 研究相关应对策略, 为决策提供参考。
(2) 突破现有的理论框架
目前, 太空领域面临着空间资源枯竭和空间秩序失序的重大危机, 现有的三“空” 能力模型框架(进入空间能力、 利用空间能力、 控制空间能力) 无法支撑危机的解决, 急需创新研究支撑后续发展、 体现国家重大利益的新模型框架。
(3) 开展空间交通管理顶层框架的深入研究
结合国际公域管理的概念体系[5], 依据我国的需求, 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空间交通管理的概念。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导下, 从有效管理太空的定位出发, 提出我国发展空间交通管理的定位、 必要性与发展目标, 进而提出我国空间交通管理的顶层框架、 法律法规体系、 发展路线图及管理体制建议。
(4) 建立协调机制, 加快立法进程
尽早研究出台我国空间交通管理国家政策,指导我国空间交通管理体系的发展和建设, 为相关立法奠定基础。 加快我国的空间立法进程,为尽快启动我国空间交通管理法规体系建设和后续的国际合作及国际立法提供法律基础和规则制定的实践经验。 在国内应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建设空间交通管理制度, 在国家层面进行统一规划, 从能力建设和制度建设两方面同步构建我国的空间交通管理体系。 先建国内机制,再建国际机制。
(5) 加大国际话语权的争夺
政府机构必须提升对我国参与空间交通管理领域国际博弈重要性的认识, 提升政府参与国际谈判的层级; 我国应积极参与空间交通管理领域相关法律规则制定的全过程, 在国际制度、 标准制定时争取有更多的话语权; 相关院校、 智库依据我国的空间交通管理概念定义, 统一相关表述, 主动参与国际层面的相关研究, 多渠道发声; 积极参与国际上已有的交会事件协调、 碎片信息共享、 碎片联测等常态化预警通报机制活动, 提升存在感。
(6) 建立统一、 专职的研究队伍
建议我国航天局牵头组织政府、 学界、 工业界、 军方等方面组成我国空间交通管理软环境领域统一的专业研究队伍, 持续、 深入开展研究,支撑我国未来的发展及国际上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