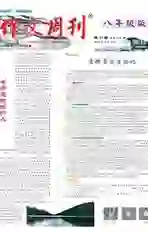艾草绒绒遍地青
2020-10-20
在初春,它是家常饭桌上的凉菜和青团;在暮春,它是驱赶蚊虫的浴盐;每到端午,它会被挂在门上或做成香囊,辟邪祈福。而除此之外,晒干了的它一年四季都可以拿来点燃了驱虫,或者做艾炙、泡脚。这种神奇的植物就是艾。
采艾草,做青团
清明采艾草,我常常提着竹篮随着母亲一起上山。正是春光明媚时,满面的清风,满眼的青翠,还有枝头啁啾不息唱着春之歌的不知名的小鸟,走在山野间,心早已像篮子里青青的艾草一样慢慢装满了。每当看到艾草了,母亲便弯下腰,用右手拇指和食指尖轻轻掐下艾草顶端的两三片叶子,从来不连根拔起,母亲说留下根子,来年还要发新芽。不大一会儿工夫,母亲手上就握满一大把青嫩嫩的艾草了。看着母亲采艾时利索的身影,我也禁不住手痒起来。对于并不认识艾草的我来说,想从山坡上庞芜纷杂的绿色植物中分辨出艾草来就更难了。母亲就会把她手上的艾草递给我,让我记住艾草的样子。真是一种普通的植物,锯齿状的青叶子上长满了绒毛,白茸茸的,尤其是叶子背面,绒毛更多,乍一看,泛白的似乎有些晃眼,凑上去一闻,一股浓淡有致的清香味带着厚厚的山野气息扑面而来。母亲说,风一吹,你看那些有泛白的地方肯定生有艾草。从此,我记住了艾草,记住了它特有的气味。
做青团时,往往只能看着母亲忙碌,我却很少能插上手。母亲将采来的艾草用开水烫过后切成碎沫,和上糯米粉和普通米粉,再加上一些清水拌匀揉透后,用手团成一个个圆形,整齐地码放在竹筛上。那时的米粉都是母亲用石磨磨出来的,透着粘口的糯香。母亲蒸青团时并不用蒸笼,而是在铁锅里加少量水,锅边烧热后,再把青团沾水捏成扁圆状贴满水线上的锅沿四周,锅上加盖,锅底添柴,不大一会儿工夫,青团就蒸熟了。记得帮母亲在锅底添柴,是我那时能做的仅有的活。而我也会边添柴,边想着青团熟了,母亲总是先铲一块给我,我会猴急一样地抓起来,赶着左手换右手倒腾的间隙,呲着牙趁热咬上一口,一面酥黄焦脆,而另一面则松软糯口,早已经满口生香了!
(节选自陈棣兵《青青子衿,青青艾》,题目为编者加)
心香一瓣
年年清明,年年艾香!寻艾,采艾;做青团,吃青团。人们是在用灵魂轻叩这种传承千年的大自然的草,而它依然还是山峦间从诗经里走来的样子,姗然而芳香。
艾蒿香
六月回乡,一进楼门,就看到了艾蒿,长长的一束斜插在人家的铁门上,暗绿的叶子微卷,露出银白的叶背。一层一层上楼,各家的铁门贵贱各异,可是大半都插了艾蒿。满楼都是微辛的艾蒿香,有人曾形容那是睡着了的花,屏住气息的嫩叶,还带着一股淡淡的烟味,像是谁忘记把篝火熄灭了。
我家也插了,妈妈说:楼下小菜市场就有卖的,五毛钱一把。——是快端午了。
艾蒿不是什么罕物儿,能放很久,叶杆越来越硬越来越脆,扑籁簌响。美女向来招蜂引蝶,我却不幸地招蚊子,打之不尽,赶之还有,没多久就咬一身包,我乱抓一气。我妈一看到就制止:“会抓破的。”去到厨房,我知道她是去煮艾蒿水了,渐渐闻到中药香。
常常在上网、看书、打电话,总要她千呼万唤才冲到卫生间,浴缸里,艾蒿汤影影的绿,我大白鲸一般浸进去,简直有春寒赐浴华清池的志得意满。真能止痒祛湿吗?难说。或许不过如小黄瓜贴脸或者何首乌洗发,象征意义高过实用。
有一年去周庄,吃人家的青团,很爱那初物的绿及淡香,不冒失不过分,问是什么。有人答是野菜,有人说是野草,到底有老婆婆给出标准答案:艾蒿。
艾蒿也就是草。艾特托玛夫曾形容他的祖国是一片长满牛蒡草、艾蒿和车前子的荒原;安房直子写过孩子们上山采艾蒿,被变成了兔子;张爱玲笔下的薄命小女佣叫做小艾,日子的确是野生野长。不过小艾是蒌蒿,倒不是艾蒿。
前几年我膝盖受过伤,也懒得打理,现在它却像痴心不改的初恋情人,时时跳出来骚扰,拍片子又说一切正常。武汉正是梅雨天气,膝盖又适时地疼起来,妈妈就给我几根艾条。我一惊,呀,艾蒿香是我永远不会陌生的。夏夜里,一天家务后,妈妈常常斜偎在躺椅上,膝弯手腕处,淡淡点一根艾条,炙她六十年劳顿的关节。现在轮到我了。——原来时序的沧桑不是诗不是文,只是一把燃著的艾条。
(作者叶倾城,选自《悬崖上的草莓》,有删节)
心香一瓣
艾蒿是一种极为普通的植物,无论贫富贵贱,家家都买得起、用得着;它的叶子有香气,可以入药,可以食用,又可以用来灼炙等;艾蒿还和端午节的家乡民俗联系在一起,被人们赋予象征意义。作者以艾蒿喻人生,平凡的人生自有意义,平平淡淡、快快乐乐地生活才是人生的常态。此外,其中也隐含着对故乡多年不变的风俗的眷恋和对艾蒿品行的喜爱。
母亲的艾菜
春节将至,母亲将晾在屋檐下腌了一个腊月的艾菜用水洗清,放在锅里用文火翻炒,加上她认为必不可少的作料,她亲自控制的炉火在她脸上飘动,母亲用双手捂住脸,我看到晶莹的亮点从母亲手缝间顽强地溢出来。我听到她说艾菜气味直辣得呛人。我看着她的眼睛,陷入了一种迷茫,我幼小的心灵还不能透过艾菜的辣味嗅到人生五味,但这也阻止不了我对艾菜初次麻麻的酸酸的感觉和记忆。那是一种甜蜜和苦辣的味道。
当最后一粒谷子将秋天毫不犹豫地收藏,初冬就会招引母亲把我的手牵到原野上,在天光微熹,星星开始淡化的时候,田野上的冷风就一个劲地拂动母亲的发丝。母亲很有节奏地起伏身子。如果找到艾菜,母亲就让我坐在她铺在地上的头巾上,让我看她怎样把艾菜激动不已地移到掌心。直到日沉西山,母亲小心而不厌其烦地将一棵棵透绿的艾菜放进精巧的菜篮,母亲就把我揽进怀里,我们就会在彼此温爱中吟唱那首她教我的儿时时常背诵的歌儿:“大青龙汤桂艾黄,杏草石掌姜枣藏……”我和母亲行走在归返的路上,小镇灯火就会簇拥着关押了一天的爸爸款款走来,再看我们的家园,也缥缈在夜灯之中了。
母亲的真知灼见是无懈可击的。清贫动荡的日子竟能让兄姐们健康平安地度过。我在大学图书馆曾翻遍所有的医科药典,始终没有发现与艾菜相关的文字,由此推论苦艾草只有母亲才能认识它,也只有母亲才有理由才有资格把它唤为“艾菜”。
当春光一次次逼迫冬日返青,母亲就把一粒粒收藏的艾籽播种到用甜杆围成的菜园里,艾菜发芽了,母亲就把芽蕊在早晨的阳光下重新编队,依次排序到她弹过三遍棉絮般的松暖湿润的土里。艾菜在她的希望里疯长,成为四季常绿的景观,母亲的技艺也传遍了村里村外,每逢腊月,风腊的艾菜就在各家庭院里的晾衣绳上窜来窜去,翻墙走檐。整个腊月,母亲的微笑在风中荡来荡去。
(节选自曹峰峻《故乡的艾菜》,题目为编者加)
心香一瓣
艾者,爱也。艾菜不管风暴和冰雪,总能坚忍不拔地点缀黝黑的泥土,很有耐心地独守一方风景;春夏秋冬,母亲的艾菜帮助作者一家度过了艰难岁月。艾菜虽然平凡、普通,而且有些苦涩,但在“我”心中却是甜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