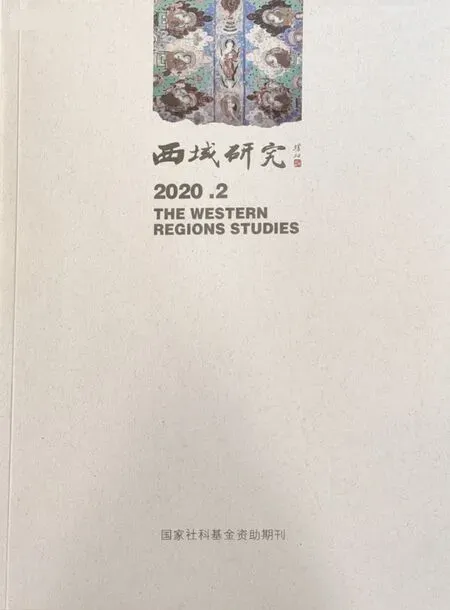隋封高昌王麹伯雅弁国公索隐①
——兼谈梁元帝《职贡图》的影响
2020-10-15米婷婷王素
米婷婷 王素
内容提要:隋炀帝曾封高昌王麹伯雅为弁国公,本文认为弁国指高丽国。炀帝大业八年带伯雅首征高丽不利,回到洛阳,封伯雅为弁国公,是准备二征高丽获胜,派伯雅镇守其地。炀帝有此奇想,是受梁元帝《职贡图》“高昌国使”题记称“面貌类高丽”的启发。炀帝大业九年二征高丽,因杨玄感起事撤兵,未能如愿;大业十年三征高丽,虽自称得胜,但其时,伯雅因进行“解辫削衽”汉化改革,导致“义和政变”,已逃到西突厥避难,炀帝的奇想终究没能实现。
隋炀帝曾封高昌王麹伯雅为弁国公,此弁国公之弁国,究竟指何国?又究竟有何用意?未见探讨,梁元帝《职贡图》的第四本子——清张庚摹本《诸番职贡图卷》的发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线索。
一 隋炀帝封麹伯雅弁国公的时间与背景
隋炀帝封麹伯雅为弁国公,最早见于《隋书·高昌传》,原文为:
炀帝嗣位,引致诸蕃。大业四年,遣使贡献,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来朝。因从击高丽,还尚宗女华容公主。八年冬归蕃,下令国中曰:“……今大隋统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齐向。孤既沐浴和风,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辫削衽。”帝闻而甚善之,下诏曰:“……光禄大夫、弁国公、高昌王伯雅识量经远,器怀温裕……”(1)《隋书》卷八三《西域·高昌传》,中华书局重印本,1982年,第1847~1848页。下引《隋书·高昌传》,不再注明。炀帝仅是在大业八年(612)冬麹伯雅由隋“归蕃”(返国)后,听闻麹伯雅在高昌进行“解辫削衽”汉化改革,特别下诏表彰,在诏中提到“光禄大夫、弁国公、高昌王伯雅”。何时封麹伯雅为弁国公?在什么背景下封麹伯雅为弁国公?均不明。据行文,很容易误认为隋炀帝封麹伯雅为弁国公,是大业五年(609)事。如《册府元龟·外臣部·封册》就说:“炀帝大业五年,高昌王麹伯雅来朝,拜左光禄大夫、车师太守,封弁国公。”(2)〔北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九六三《外臣部·封册》,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165页。《旧唐书·高昌传》云:“隋炀帝时(麹伯雅)入朝,拜左光禄大夫、车师太守、封弁国公,仍以戚属宇文氏女为华容公主以妻之。”(3)《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高昌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294页。虽然没有明确系年,但从“入朝”用词看,也是指大业五年。由于炀帝三征高丽,大业八年是首征,麹伯雅不可能大业五年来朝,就马上“从”炀帝“击高丽”,知前揭史籍均存在重大疏漏。
实际上,隋炀帝时,麹伯雅凡两次来中国:第一次始于大业五年六月十七日,系麹伯雅、麹文泰父子联袂入朝,终于大业六年(610)三月二日,麹文泰留在东都为质,麹伯雅独自返回高昌。第二次始于大业七年(611)五月四日后,系麹伯雅陪同西突厥处罗可汗入朝,终于大业八年十一月二日,麹伯雅、麹文泰父子一同返回高昌。其间,伯雅与处罗可汗曾陪同炀帝首征高丽。这就是《通鉴》大业八年三月条所说:“车驾渡辽,引曷萨那(处罗)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观战处以慑惮之。”(4)《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炀帝大业八年三月条,中华书局重印本,1976年,第5662页。炀帝首征高丽,不利撤兵,与麹伯雅等由涿郡经大同、太原、临汾,绕道回到东都洛阳。到洛阳后,才封麹伯雅为左光禄大夫、车师太守、弁国公,并以宇文氏二女为公主,妻麹伯雅、麹文泰父子。(5)王素:《麹伯雅、麹文泰与隋的交通》,《高昌史稿·交通编》,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411~422页。
隋炀帝封麹伯雅弁国公的时间与背景既已清楚,即可推知,此弁国公之弁国,必与高丽国存在某种关系。
二 弁国应指高丽国
说弁国与高丽国存在关系,首先想到的应该是三韩之一的弁韩。如《三国志·魏书·韩传》云:“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6)《三国志》卷三○《魏书·东夷·韩传》,中华书局重印本,1964年,第849页。《晋书·四夷·马韩传》云:“韩种有三: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7)《晋书》卷九七《四夷·东夷·马韩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533页。但传统认为,弁韩指新罗,并非指高丽。如《旧唐书·东夷·新罗传》云:“新罗国,本弁韩之苗裔也。”(8)《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新罗传》,第5334页。《新唐书·东夷·新罗传》云:“新罗,弁韩苗裔也。”(9)《新唐书》卷二二○《东夷·新罗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6202页。《辽史·地理志三》记三韩县更明云:“辰韩为扶余,弁韩为新罗,马韩为高丽。”(10)《辽史》卷三九《地理志三》中京道高州三韩县条,中华书局,1974年,第483页。马韩才指高丽。但是否弁韩就与高丽一点关系也没有呢?也不尽然。
按弁韩又作卞韩。如《后汉书·光武帝纪下》云:“东夷韩国人率众诣乐浪内附。”李贤注:“东夷有辰韩、卞韩、马韩,谓之三韩国也。”(11)《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建武二十年秋条,中华书局重印本,1973年,第72页。盖卞与弁原为一字,固可同音通用。如《左传·昭公九年》“豈如弁髦”陆德明《释文》:“弁,皮彦反,本又作卞。”(12)《春秋左传注疏》卷四五昭公九年陆德明《释文》,《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60页。《癸巳类稿·百家姓书后》:“卞为地名,又为弁。卞本弁官氏。弁、卞,篆、隶一字也。”(13)〔清〕俞正燮撰;涂小马等校点:《癸巳类稿》卷七《百家姓书后》,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45~246页。而弁韩作卞韩,指平壤。如《朝鲜史略》“弁韩”条注云:“弁一作卞,今平壤。”(14)〔明〕朝鲜佚名:《朝鲜史略》卷一“三韩”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至1986年,第369页。平壤是高丽首都,自然也就是指高丽。
卞韩又称卞国,也是指高丽国。近年新出著名的武周高丽人《高乙德墓志》,即称“卞国东部人也”。(15)王连龙:《唐代高丽移民高乙德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第32~35页;葛继勇:《新出高乙德墓志与高句丽末期的内政外交》,《郑州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144~149、161页。与麹伯雅封弁国公可以比较的是泉男生。泉男生为高丽权臣泉盖苏文长子,盖苏文死,男生继任,二弟男建、男产亦知国事,兄弟阋墙,导致高丽内乱。男生向唐求援,高宗派兵接应,顺势灭了高丽。男生随大军还朝,得“进右卫大将军、卞国公”。(16)《新唐书》卷一一○《诸夷蕃将·泉男生传》,第4124页。唐高宗封泉男生为卞国公,与隋炀帝封麹伯雅为弁国公,背景大致相同,用意也应近似。高宗虽然灭了高丽,占领其地,但未必有信心永远占领,一旦辽东有事,有泉男生作储材,自应可保无虞。炀帝凡三征高丽,首征不利,已准备二征,以麹伯雅为储材,有可能是准备二征获胜,派麹伯雅镇守其地的。
将泉男生与麹伯雅进行比较,泉男生是高丽人,镇守高丽顺理成章。麹伯雅是高昌人,高昌与高丽,西东悬隔,何啻万里,派他镇守高丽,太过匪夷所思。然则,高昌与高丽,是否就一点关系也没有呢?
三 《梁书·高昌传》之“面貌类高骊”
《梁书·高昌传》有一句很奇怪的话:“面貌类高骊。”(17)《梁书》卷五四《诸夷·西北诸戎·高昌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811页。高骊即高丽。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高昌人的面貌,长得很象高丽人。这句话曾被广泛引用。譬如:《南史·高昌传》:“面貌类高丽。”(18)《南史》卷七九《夷貊下·西域·高昌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983页。《通典·车师(高昌附)》:“其人面貌类高丽。”(19)〔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九一《边防七·西戎三·车师高昌附》,中华书局重印本,1992年,第5204页。《册府元龟·外臣部·土风》:“(高昌)面[貌]类高丽。”(20)〔北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九六一《外臣部·土风》,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132页。《通志·四夷·车师(即高昌)》:“其国人面貌类高丽。”(21)〔南宋〕郑樵:《通志》卷一九六《四夷传三·西戎下·车师(即高昌)》,中华书局,1987年,第3149页。《文献通考·四裔·车师前后王(即高昌)》:“其人面貌类高丽。”(22)〔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三六《四裔考十三·车师前后王(即高昌)》,中华书局,1986年,第2638页。
如果是隋炀帝看过《梁书·高昌传》,注意到“面貌类高骊”这句话,然后突发奇想,准备二征高丽获胜,派麹伯雅镇守其地,由于面貌相类,估计高丽人容易接受,故先封麹伯雅为弁国公,作为储材,以备不虞,应该是可以成立的。但炀帝不可能看到《梁书·高昌传》。
《梁书》《陈书》由姚察、姚思廉父子相继编撰。姚察在陈初先参加梁史的编撰,陈亡入隋,奉命继续编撰梁史,也一并编撰陈史。大业二年(606)尚未成书,姚察就去世了,“临终令思廉续成其志”,思廉遂接着编撰梁、陈二史。(23)《旧唐书》卷七三《姚思廉传》,第2592页。直到唐贞观九年(635)《梁书》《陈书》才同时完成。《梁书》共五十六卷,有二十六卷的后论署“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其中不包括《诸夷传》,说明《诸夷传》是姚思廉撰写的。《诸夷传》如果是姚察撰写的,姚察卒于大业二年,炀帝还有可能看到稿本;是姚思廉撰写的,恐怕无论在隋在唐,炀帝都是不可能看到的。
此外,还须注意的是,“面貌类高骊”这句话,很有图像感,在重文本的传统国史系列中,无论是“起居注”,还是“实录”,都不见类似表述,“二十五史”亦仅此一例。(24)《新五代史》卷一七《晋家人·高祖子重睿传》说“重睿为人貌类高祖”(中华书局,1974年,第185页),《明史》卷一一九《宪宗诸子·荣庄王祐枢传》云“祐枢状貌类高帝”(中华书局,1974年,第3642页),含义与此不同,又当别论。因此,可以推测,隋炀帝知道高昌“面貌类高骊”,不是来自《梁书·高昌传》,而应是另有所本。
四 梁元帝《职贡图》“高昌国使”图像与题记
实际上,隋炀帝看到的是梁元帝的《职贡图》。梁元帝《职贡图》旧有三个有图摹本,提供的信息都不完整:
1.唐阎立本摹本,原名《唐阎立本王会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清官修《石渠宝笈》卷三二著录。绢本设色,自右至左,依次绘有二十四国与蛮族使者立像,无题记。其中,有高骊,无高昌,无从进行比较。
2.五代南唐顾德谦摹本,原名《梁元帝蕃客入朝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清官修《石渠宝笈续编·养心殿藏》卷二著录。纸本白描,自右至左,依次绘有三十三国与蛮族使者立像,有高丽,也有高昌,但无题记。
3.北宋熙宁十年(1077)摹本,原名《唐阎立德职贡图》,原藏南京博物院,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清官修《石渠宝笈》卷三二著录。绢本设色,自右至左,依次绘写十二国使者立像与十三国题记,既无高丽,又无高昌。
顾德谦摹本,高丽与高昌分别排在第二十五国和第二十六国,高丽在前,高昌在后,两个使者立像紧挨着,仔细进行比较,会发现两个使者的面貌确实很相似(图1、图2)。但没有题记,缺乏提醒高昌“面貌类高丽”文字,很难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2011年,赵灿鹏公布了梁元帝《职贡图》的第四本子——清乾隆四年(1739)张庚摹本《诸番职贡图卷》,(25)赵灿鹏:《南朝梁元帝〈职贡图〉题记佚文的新发现》,《文史》2011年第1辑,第111~118页。首次披露了“高昌国使”的题记,终于使梁元帝《职贡图》“高昌国使”图像与题记合璧。现将题记全文迻录如下:
高昌国,去益州一万二千里。国人言语与魏略仝。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往往诵读。面貌类高丽。辫发为十条,垂肩项之间。著长身小袖袍,缦裆袴,金革莫靴,无裙履。女子头发辫而不垂肩,著锦缬璎珞环钏。婚姻六礼。其地高燥,筑土为城,架木为屋,覆土其上。寒暑与益州相似。有水田,备种九谷,人多噉麫、羊、牛。出良马、蒲萄酒、石盐。多草木。交关用布帛。有朝鸟(乌),集王殿前地,为行列,不畏人,日出然后散去。大通中,遣使献乌盐枕、蒲萄、良马、氍毹等物。(26)葛嗣浵:《爱日吟庐书画续录》卷五《清张庚〈诸番职贡图卷〉》,《续修四库全书》第108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线装书局,2002年,第546页。


图3 清张庚摹本“高昌国使”题记
题记中有“面貌类高丽”五字。经过中日学者多年探讨,《梁书·诸夷传》材料基本源出梁元帝《职贡图》题记,已经成为学界共识。(27)王素:《梁职贡图と西域诸国——新出清张庚模本〈诸番职贡图卷〉がもたらす问题》,《梁职贡图と东部ユーラシア世界》,东京勉诚出版株式会社,2014年,第45~66页;米婷婷:《梁元帝〈职贡图〉的形成》,《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41辑(待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这就是说,所谓“面貌类高丽”,是梁元帝画“高昌国使”图像时的联想。他将该五字写入“高昌国使”题记,然后才被《梁书·高昌传》抄录,后世史书广泛引用。梁元帝《职贡图》“高昌国使”题记是该五字的祖本。
题记中另有“国人言语与魏略仝”八字。其中“魏”,《梁书·高昌传》作“中国”,《南史·高昌传》作“华”。“中国”“华”,是站在南朝立场上的用词;作“魏”,则是站在北朝立场上的用词。梁元帝萧绎出身梁朝皇室,立场会更加鲜明,他撰写的《职贡图》题记,此处用词,只可能作“中国”、作“华”,而决不可能作“魏”。这反映梁元帝《职贡图》题记曾被北朝篡改,具体而言就是曾被西魏篡改。可以推测,西魏灭梁江陵小朝廷,将《职贡图》带回了长安,对其中一些国家的题记文字做了符合自己利益的改动。(28)米婷婷:《梁元帝〈职贡图〉的形成》,《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41辑(待刊);王素:《梁元帝〈职贡图〉“高昌国使”图像与题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41辑(待刊)。后来,西魏为北周所取代,北周为隋所取代,宫廷及其收藏一脉相承,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隋炀帝在长安宫中看过梁元帝《职贡图》,记住“高昌国使”题记“面貌类高丽”,是合情合理的。
五 梁元帝《职贡图》的影响
隋炀帝三征高丽,均为亲征:大业八年首征,不利而返;大业九年二征,因杨玄感起事,不得不撤兵;大业十年三征,两军尚未相接,其王就抢先遣使请降,炀帝自称得胜,班师。(29)参王素:《炀帝三征高丽》,《大河滚滚——隋代卷》,中国历史宝库丛书之一,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第152~158页。如前所说,首征不利,回到洛阳,封麹伯雅为弁国公,有可能是准备二征获胜,派麹伯雅镇守其地的。遗憾的是二征高丽,因杨玄感起事撤兵,未能如愿。三征高丽虽自称得胜,但其时,伯雅因进行“解辫削衽”汉化改革,导致“义和政变”,已逃到西突厥避难,炀帝的奇想终究没能实现。(30)按:隋炀帝大业十年(614)三征高丽,是二月征兵,七月到达辽西怀远镇,高丽王遣使请降,八月班师,十月经东都回到长安。高昌爆发“义和政变”,在麹伯雅延和十三年(614)十一月十九日前。即炀帝回到长安的时间,与高昌“义和政变”的时间几乎同时。如果炀帝遣使到高昌召伯雅赴高丽,则使者到达高昌的时候,伯雅早已逃到西突厥避难去了。参阅《隋书》卷四《炀帝纪下》,第86~88页;王素:《“义和政变”新探》,《高昌史稿·统治编》,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372~379页。
当然,梁元帝《职贡图》的影响并不仅此。北宋李廌《德隅斋画品》记所见梁元帝《番客入朝图》云:“此图题字殊妙,高昌等国皆注云‘贞观某年所灭’。”梁元帝所处时代早于唐代贞观近百年,不可能未卜先知记高昌被灭时间,故同书接着解释云:“又落笔气韵,阎立本所作《职贡图》亦相若。得非立本摹元帝旧本乎?或以谓元帝所作传至贞观,后人因事记于题下,亦未可知。”(31)〔北宋〕李廌:《徳隅斋画品·番客入朝图》,《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年,第942页。总之,高昌等国题记所注“贞观某年所灭”,是唐初画家临摹妄补固无疑问。这条材料,不仅证实前揭西魏改梁元帝《职贡图》完全可能,而且说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灭高昌在当时确是一件大事。
据《新唐书·东夷·高丽传》记载,唐兴,高丽新王亦初嗣位,有惩于前隋曾屡征高丽,与唐关系颇为微妙。高祖深明其理,谓左右曰:“名实须相副。高丽虽臣于隋,而终拒炀帝,何臣之为?朕务安人,何必受其臣?”太宗灭高昌后,高丽“遣太子桓权入朝献方物,帝(指太宗)厚赐赉,诏使者陈大德持节答劳,且观舋”。大德还奏,有言:“闻高昌灭,其大对卢三至馆,有加礼焉。”(32)《新唐书》卷二二○《东夷·高丽传》,第6187页。“大对卢”为高丽高官,他听说高昌为唐所灭,感到害怕,三次到大德下榻的宾馆探望,表示对唐使尊礼有加。这说明,高丽对炀帝曾欲派麹伯雅镇守其地记忆犹新,故对高昌之事十分关心,听说与中原王朝关系一向很好的高昌,也被唐朝灭亡了,感到自己与中原王朝素来不和,应该更加小心。高昌对高丽是否也会如此关心?史缺有间,难以断言。从情理推测,至少在麹伯雅被封为弁国公后,高昌对高丽也应该是很关心的。地处东西相距不啻万里的高丽、高昌二国,彼此关心,声气相通,追根溯源,应该都与梁元帝《职贡图》的影响有关。这是我们研究梁元帝《职贡图》所应注意的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