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于阗玉石的西传①
2020-10-15陈春晓
陈春晓
内容提要:玉,在中华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涵义和地位。玉石及其制品的外输带动了中华玉石文化在世界的传播。于阗玉石自上古时代就开始输入伊朗地区,被用于制作刀剑配件、带饰、戒指、杯碗等物件。中古时代以来,亚洲大陆上次第西迁的游牧部族将东方的玉石文化传至伊朗。波斯、阿拉伯语文献记载了有关于阗玉石种类、产地、用途及制造工艺的丰富信息。契丹人在中亚建立西辽政权后,中国的玉器风格也传入伊朗东部地区。至13世纪蒙古人征服伊朗,伊利汗国受元朝玺印制度的影响,将汉地玉石文化移植到伊朗,形成了“以玉为尊”的政治文化风尚。在多民族文化的交互影响下,中古时期的中国与伊朗之间,铺就了一条多元多彩的中华文化传播之路。
中国昆仑山一带自古就是玉石的出产地,其中尤以于阗美玉最负盛名。这里出产的玉石很早就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世界各方。向东,于阗玉大量流入中原地区,逐渐成为中华文明中不可或缺的审美元素。(1)关于于阗玉东传中原的研究有很多,较具代表性的有:程越:《古代和田玉向内地输入综略》,《西域研究》1996年第3期,第36~42页;杨伯达:《“玉石之路”的布局及其网络》,《南都学坛》2004年第3期,第113~117页;殷晴:《唐宋之际西域南道的复兴——于阗玉石贸易的热潮》,《西域研究》2006年第1期,第38~50、120页;张文德:《明与西域的玉石贸易》,《西域研究》2007年第3期,第21~29页;闫亚林:《关于“玉石之路”问题的探讨》,《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3期,第38~41页;荣新江,朱丽双:《从进贡到私易:10—11世纪于阗玉的东渐敦煌与中原》,《敦煌研究》2014年第3期,第190~200页。向西,在中、西亚地区及地中海沿岸公元前后的遗址中,都发现了玉石制品。(2)关于于阗玉的西传,西方考古学和艺术史学者有较多的研究,如:Robert Skelton,“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Indian Jade Carving Traditions”,in:The Westward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Arts from the 14th to the 18th Century,ed.by William Watson,London:University of London,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972,pp.98-110;Ralph Pinder-Wilson,“Jades from the Islamic World”,Marg,vol.44,No.2,1992,pp.35-48;A.S.Melikian-Chirvani,“Precious and Semi-Precious Stones in Iranian Culture Chapter I.Early Iranian Jade”,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Vol.11,1997,pp.123-173;而最重要的研究为Manuel Keene,“Old World Jades outside China,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Fifteenth Century:Section One”,Muqarnas,Vol.21,No.1,2004,pp.193-214.工艺方面,除中国外,古代伊朗尤其是东部伊朗,是加工和使用玉器最具规模的地区。中古时代以来,亚洲大陆上次第西迁的操突厥语部族和契丹人、蒙古人将东方的玉石文化向西传播,波斯、阿拉伯语文献中记载了有关于阗玉石产地、种类、用途及制造工艺的丰富信息。而在伊朗建立政权的蒙古人更是直接将中原汉地的玉石文化移植伊朗。本文将以多语种文献记载为基础,同时结合考古资料和艺术史的研究成果,考察中古时期于阗玉石在伊朗地区的传播历史,并探讨多民族文化影响下的中华文化传播路径。
一 释名
在跨地区、跨文化、长时段的物质交流历史中,名、物含混不清的现象很是常见。越是古老的事物,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越有可能发生名称的改换和含义的转变。因此,在探讨玉石西传问题前,首先需要厘清它在亚洲几种主要民族语言中的称谓。
汉字“玉”,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考古资料表明,自新石器时代开始,玉石便从各种石料中脱颖而出,用作礼器和装饰品。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解释说:“玉,石之美。”在近代矿物学诞生之前,“玉”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与其相近的玉髓、玛瑙、大理石、碧石等石料也时常混入“玉石”这一名称下。(3)干福熹:《玻璃和玉石之路——兼论先秦前硅酸盐质文物的中、外文化和技术交流》,《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年第4期,第6~17页。但古代中国人眼中最优质、纯正的玉,无疑是来自于阗的玉石。明代以后,翡翠被大量发掘出来,并成为于阗玉之外的又一种优质玉石品种。19世纪时中国玉器大量传入欧洲,法国矿物学家将于阗玉和翡翠统称为玉,并重新命名,称前者为nephrite(软玉),后者为jadeite(硬玉)。于是在今天,汉语狭义的“玉”指的是软玉和硬玉的集合。(4)卢保奇,冯建森:《玉石学基础》,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页。
值得注意的是,英语jade一词出现得很晚,约于16世纪由法语、意大利语演变而来。其词源来自古西班牙语ijada,原义是指一种能治愈腹部绞痛的石头。伯希和(Paul Pelliot)考证说,jade长久以来被误认为与札答石(Jada或Yada)有关,而实际上二者没有任何关系。(21)Paul Pelliot,“Cotan”,Notes on Marco Polo,vol.1,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1959,pp.424-425.英语jade一词出现后,专用于表示东方的玉石,逐渐与Jasper(碧石)区别开来。
二 波斯、阿拉伯文献记载中的玉石产地
(一) 闻名遐迩的于阗玉河
于阗玉主要产自今天和田东西两侧的玉龙喀什河(Ürüng qsh)和喀拉喀什河(Qarqsh)。波斯、阿拉伯语文献对此亦有很明确的记载。10世纪波斯地理书《世界境域志》记载于阗的河中出产玉石。(22)ūd al-lam:a Persian Geography,372 A.H.-982 A.D.,2d ed.,tr.by V.Minorsky;ed.by C.E.Bosworth,London:Luzac & co.,1970,pp.85-86.11世纪比鲁尼的《宝石书》《医药书》都对于阗玉河有十分具体的描述:
比鲁尼的著作影响深远,后来的波斯、阿拉伯作家持续沿用他关于于阗玉河的这一记述。(27)Nayshbūrī,Javhir-nma-yi ī,p.218.如12世纪内沙不里的《内扎米珍宝书》也记载说:“玉石出自和阗地区(nhiyat-i shahr-i Khutan(28)校勘本原作Chīn,但校勘记中显示有抄本为Khutan。显然这是由于音点错误造成的两个地名的混淆,根据地名前的限定词nhiyat(州、区)、shahr(城市)来看,这个地名应是于阗(Khutan)。)的两条河里,所处的镇子名叫Ajma,那里一条河叫‘哈失’(Qsh),另一条叫‘哈剌哈失’(Qarqsh)。”(29)Nayshbūrī,Javhir-nma-yi ī,p.218.

而汉文记载可见五代时《高居诲行程记》:
其国采玉之地云玉河,在于阗城外,其源出昆山,西流一千三百里,至于阗界牛头山,乃疏为三河:一曰白玉河,在城东三十里;二曰绿玉河,在城西二十里;三曰乌玉河,在绿玉河西七里。其源虽一,而其玉随地而变,故其色不同。每岁五六月大水暴涨,则玉随流而至。玉之多寡,由水之大小。七八月水退,乃可取。彼人谓之“捞玉”。其国之法,官未采玉,禁人辄至河滨者。(31)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三“玉屑”,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原刻晦明轩本,1982年,第81页。
高居诲所记出产玉石的三条河流中,乌玉河实为绿玉河的支流,所以他记载的也是两条主要河流。
上引几则史料显示,波斯语、阿拉伯语、突厥语和汉语文献关于于阗玉河的记载一脉相承,不仅对玉河的名称记载一致,而且对其所出玉石的色泽、种类,乃至“玉河捞玉法则”的记述也同出一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波斯、阿拉伯文献记载的玉河名称是突厥语,这说明当地人是通过说突厥语的人获知的玉河信息。由此可窥见亚洲大陆上知识从东向西的传播脉络,同时也显示出操突厥语部族在东西方信息传递中所承担的媒介角色。
(二)玉石产自中国
昆仑山的玉石产地,除于阗外,可失哈儿(今译喀什噶尔)是为波斯、阿拉伯人所知晓的另一个产地。艺术史家曼努埃尔·基恩(Manuel Keene)认为,最早在11世纪,最迟至13世纪时,可失哈儿就已成为了玉石的主要原料供应地之一。(32)Manuel Keene,“Jade:i.Introduction”,pp.323-325.不过文献记载显示,这个时间上限恐怕更早,在9世纪的阿拉伯语宝石书《宝石的属性》(Kitbal-Jawhir)中,就已有玉石出自可失哈儿的记载。(33)这是9世纪阿拉伯著名学者雅库布·肯迪(Yaqb ibn Ishq al-Kindī)撰著的一部宝石学撰著,全书共25章,记述了当时所能了解到的各种宝石及其属性知识。(Yaqūb ibn Ishq al-Kindī,Kitb al-Jawhir),埃及国家图书馆藏9世纪抄本,p.87.11世纪末的波斯赞美诗,描述了一位战士的手臂上佩戴着可失哈儿的玉石。(34)A.S.Melikian-Chirvani,“Precious and Semi-Precious Stones in Iranian Culture Chapter I.Early Iranian Jade”,p.132.13世纪密昔儿即埃及)宝石学家惕法昔(Abu al-Abbsb.Yūsuf al-Qaysī al-Tīfshī)撰著的《皇家宝石书》(Kitbal-Mulūkīt),沿袭了《宝石的属性》的内容,也记录了可失哈儿为玉石产地。(35)Abu al-Abbs b.Yūsuf al-Qaysī al-Tīfshī,Kitb al-Mulūkīt,埃及国家图书馆藏1554年抄本,f.113.
无论是于阗还是可失哈儿,历史上它们多处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因而波斯、阿拉伯文记载也常显示出对玉石出自中国的普遍认知。例如《世界境域志》就将出产玉石的于阗列于中国(Chīnistn)疆域下,又说可失哈儿也属于中国。(36)ūd al-lam:a Persian Geography,372 A.H.-982 A.D.,pp.85-86,96.比鲁尼则称于阗玉中最优质的白玉为“中国白玉īīnī)。(37)Bīrūnī,Kitb fī īrūnī,Al-Biruni's Book on Pharmacy and Materia Medica,English translation,p.341;Arabic text,p.382;Bīrūnī,Kitb īrūnī,al-Jamhir fīal-Jawhir,p.319.又如13世纪初波斯地理书《寰宇志》(Jahn-nma)记载说:“玉石矿藏位于中国(Chīn)。”(38)Bakrn,Jahn-nma:Matn-i Jughrfiy-yī,ed.by Amīn ī,Tehran:Intishrt-i Kitbkhna-yi Ibn Sīn,1963,p.98.

无论是对于阗玉河的描述,还是对玉石出于中国的记载,都反映出中古时代波斯人对玉石这种特殊石料来自东方的基本认识,同时玉石所承载的东方文化特质也逐渐为伊朗地区所了解。
三 波斯、阿拉伯文献记载中的东方玉石文化
(一)对玉石功效的了解
尽管从石器时代开始,玉石就已出现在中国以西直至近东的广大地区了,但受史料文献所限,中古时代以前西亚地区人们对东方玉石文化的认知情况,现已很难知晓。不过中古时代以来,波斯、阿拉伯语文献对东方玉石的记载多了起来,这些记载显示出西亚人民对东方玉石所具有特质、属性的了解和关注。
第二,玉石具有消灾避难的功能。内沙不里说,“随身佩戴玉石,能避开雷电,免受火灾”,(45)Nayshbūrī,Javhir-nma-yi ī,p.219.蒙元时代的徒昔、哈沙尼、迪马士基(Shams al-Dīīī)在他们的著作中也延续着这种说法。(46)Tūsī,Tansūkh-nma-yi Ilkhnī,p.121;Kshnī,‘Aryis al-Javhir va Nafyis al-Atyib,p.139;Shams al-Dīn ibn Abī Dimashqī,Nukhbat al-Dahr fī Aj'ib al-Barr īd īr,2003,p.103.这种认知的来源,我们可以从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中得到了解:“玉石,是一种光滑的石头,有白色和黑色,白色的玉石镶在戒指上,可以避雷、解渴和防火。”(47)ūd ī,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part II,p.226;汉译本参看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三卷,第147页。这再一次说明了波斯人的玉石知识来源与西迁的操突厥语部族息息相关。
第三,玉石具有医疗功效。这是波斯人对东方玉石最感兴趣和最为关注的方面,几乎所有关于玉石的波斯、阿拉伯文记载都提到了这方面内容。例如比鲁尼在其《医药书》中记录说:“有一种深褐色的玉石,能够缓解口渴;而把黄色玉石垂挂在人胃的位置处,可以增强胃功能。”(48)Bīrūnī,Kitb fī īrūnī,Kitb īrūnī,Al-Biruni's Book on Pharmacy and Materia Medica,p.341.内沙不里说:“玉石放入口中,能缓解口渴”,“把龙形玉佩用绳子穿起来挂在颈上,使玉佩垂于胃部位置,就能加强胃部功能,促进消化积食”;此外,他还提到“玉石能祛除眼疾”(49)Nayshbūrī,Javhir-nma-yi ī,p.219.。这几种玉石功用,一直到蒙古时代徒昔、哈沙尼、可疾维尼的著作中,还被不断提及。此外,哈沙尼书中还记载了妇女带上碧玉,可以促进怀孕生子;(50)Kshnī,Aryis al-Javhir va Nafyis al-Atyib,p.139.迪马士基则说玉石能“治疗乳汁不下和减少,治疗心痛、心闷,少精”。(51)Dimashqī,Nukhbat al-Dahr fī Aj'ib al-Barr波斯、阿拉伯语文献记载的这些玉石在医疗方面的功用,几乎全部可见于中国的医书。唐代《千金翼方》就记载了青玉、白玉髓“主妇人无子”、璧玉“主明目益气,使人多精生子”。(52)孙思邈著;李景荣等校释:《千金翼方校释》,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年,第74页。《证类本草》记载玉屑:“主除胃中热、喘息烦满、止渴”,需要注意的是,书中所言的玉石主要是蓝田玉,但也指出“外国于阗、疏勒诸处皆善”。(53)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三“玉屑”,第81页。根据书中对前代医书的援引,晋代的中医就使用玉石治病了。而这些汉地的医疗经验,随着玉石的西传也为波斯人所知晓。
(二)对玉石加工技艺的了解
物质流动的同时也带动手工技艺的传播,东方的玉石加工工艺也为波斯人所了解。内沙不里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契丹人玉石加工工艺的最细致的描述:
此外,内沙不里对契丹人的玉石审美情趣和价值观也具有相当的认识:
用这种玉石(青玉)制成各种器皿,在古代用以彰显文雅,这种说法十分著名。
在《宝石的属性》(Kitabkhawasal-Jawhir)一书中,玉石被称为“胜利之石”,因为契丹人把玉石佩戴在腰带、刀剑、工具上面,以求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也有一些人在他们的宗教仪式上使用玉石做卜筮,然后制成戒指、手镯和刀柄。(55)Nayshbūrī,Javhir-nma-yi ī,pp.218-21.
内沙不里所描述的契丹人的玉石文化,在辽代契丹人墓葬中得到了证实。根据考古发掘情况来看,辽代契丹人对玉器的使用具有相当的偏好,玉石工艺也颇具特色。于宝东、许晓东两位学者对辽代契丹玉器多有论述。(56)于宝东:《辽代玉器文化因素分析》,《内蒙古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第33~38页;《契丹民族玉器述论》,《内蒙古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22~27页;《辽金元玉器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许晓东:《辽代玉器研究》,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契丹人的金玉首饰》,《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第32~47页。据其统计,辽代玉器共出土三千余件,主要出自墓葬及佛塔。(57)许晓东:《辽代玉器研究》,第8~9页。他所定义的玉器为广义玉石制品,其中也包括水晶、玛瑙等类玉石料。其中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玉器最多,有玉銙丝蹀躞带、玉銙银带、玉柄银锥、玉砚、玉水盂以及造型丰富的玉配饰。(58)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45~46、59~60、74~86页;李逸友:《辽代带式考实——从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的腰带谈起》,《文物》1987年第11期,第30页。考古研究表明,契丹玉器除了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外,还吸收了汉地、中亚和佛教文化因素。其中玉带、簪、碗、杯以及龙凤、花鸟等纹饰造型,是仿自中原玉器。(59)许晓东:《辽代玉器研究》,第115页;于宝东:《辽代玉器文化因素分析》,第33~34页。内沙不里所描述的“彰显文雅”的玉器和价值千金的玉带,就是汉地艺术风格在契丹玉器工艺中的体现。
蒙元时代到来前,波斯人对东方玉石文化的了解,主要来自于西迁操突厥语部族和契丹部族的传播,这些部族因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对玉石的审美、应用及加工,也表现出汉地文化元素。这使得汉地玉石文化在此阶段是以游牧部族为中介,间接地被传介至伊朗。
四 玉石及其制品风格的西传
国内学者研究于阗玉石向西输送时,常常引用15世纪初西班牙旅行家克拉维约(Ruy González de Clavijo)行纪中的一段记载,所据版本多为杨兆钧先生20世纪40年代据土耳其语译本所译的汉译本。(60)如李吟屏:《和田玉雕漫谈》,《新疆地方志》1991年第3期,第44页;殷晴:《和阗采玉与古代经济文化交流》,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第1期,此据作者《探索与求真——西域史地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81页;张文德:《明与西域的玉石贸易》,《西域研究》2007年第3期,第22页等。其中对撒马尔罕城中外贸商品有这样一段记载:
自中国境运来世界上最华美的丝织品。其中有一种为纯丝所织者,质地最佳;自和阗运来宝玉、玛瑙、珠货,以及各样珍贵首饰。和阗所产之货,其极名贵者,皆可求之于撒马尔罕市上。和阗之琢玉镶嵌之工匠,手艺精巧,为世界任何地所不及。(61)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157页。
克拉维约的行纪,原文为西班牙文,近代以来被译为英、俄、土耳其等多种文字。对照西班牙文原文后会发现,汉译本将原文中的Catay错译成了“和阗”。Catay一词在全书中多次出现,其义为契丹,也就是中国。不仅如此,原文中也未出现“宝玉”“琢玉镶嵌”的表述。这段记述的准确翻译应当如下:
这座城市(撒马尔罕)的市场上聚集了大量的来自远方他国的商货。有来自斡罗思(Ruxia)和鞑靼(Tartaria)的皮革、亚麻制品,有来自中国(Catay)的世界上最优质的丝织品(paos de seda);尤其是一种不加刺绣的平织织物,最为上品。此外还有出产自中国的麝香(almizque);还有红宝石(balaxes)、金刚石(diamantes)在这里囤积得最多;还有珍珠(alxofar)、大黄(ruybarbo)及其他各种香料(especias)。从外国进口到撒马尔罕的货物中,中国的商品最为珍稀、名贵,因为他们具有世上最高超技艺的声誉。有这么一种说法:中国人每人有两只眼睛,摩尔人(Moros)(62)摩尔人是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的混血,是西北非的穆斯林。对西班牙人来说,摩尔人是他们熟悉的穆斯林群体,克拉维约用摩尔人代表所有穆斯林。斯特兰奇的英译本将Moros直接译作Moslem。是瞎子,拂郎人只有一只眼睛,所以中国人具有比世上其他人更高超的技艺。(63)Ruy González de Clavijo,Historia del gran Tamorlan,En Madrid en la imprenta de Don Antonio de Sancha se hallar en su librería en la Aduana Vieja,1782,p.191.
《克拉维约东使记》目前的最好译本,是伊朗学家斯特兰奇(Guy Le Strange)所作的英译本,(64)Guy Le Strange,Clavijo:Embassy to Tamerlane 1403-1406,tr.by Guy Le Strange,ed.by Eileen Power;Edward Denison Ross,London :Routledge & Sons,1928.学者若使用此行纪,当以斯特兰奇译本为佳。与西班牙文本一致,英译本也没有出现“和阗”和“玉石”这两个词语,因此这条材料不能作为于阗玉西传的证据。
虽然克拉维约的记载不能证明于阗玉贩运西方,但大量考古资料表明,从中亚至近东地区,在公元前就已使用玉石制品。不仅如此,近来的研究逐渐打破中西亚地区直到15世纪才从中国人那里学会玉石雕琢技艺这一旧有看法,(65)持这一看法的研究很多,如:Berthold Laufer,“Jade:a Study in Chinese Archeology and Religion”,Publications of 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Anthropological Series,vol.10,1912,p.3;Robert Skelton,“Islamic and Mughal Jades” in:Jade,ed.by Roger Keverne,London:Anness Pubilsillng Ilmited,1991,p.272.越来越倾向认为在公元前的东部伊朗地区,就已发展出区别于中国的玉石加工风格。(66)实际上中国的玉石加工工艺,也存在地域性差异。北方、南方与西域地区都有不同,参见邓淑萍:《从“西域国手”与“专诸巷”——论南宋在中国玉雕史上的重要意义》,《考古学研究》第9期,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408~456页。巴克特里亚地区拥有发达的琢玉技术,那里发现的玉器饰品带有浓郁的希腊化风格。(67)Manuel Keene,“Jade:ii.Pre-Islamic Iranian Jades”,Encyclopdia Iranica,vol.XIV,Fasc.3,pp.325-326.东部伊朗地区长期以来都是玉石加工的中心,而其中最重要的城市就是呼罗珊名城巴里黑(Balkh),此外也里(Herat)、加兹尼(Ghazna)也是玉石加工业的重镇,(68)Manuel Keene,“Old World Jades outside China,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Fifteenth Century:Section One”,pp.193-214.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近代。
从中亚、西亚出土的玉石制品来看,中古时代以前绝大多数为剑颚、护手、剑璏等刀剑具的配件。这可能是受到西迁月氏民族的影响,这种形制的刀剑及配具一直向西传至西亚及欧洲。(69)Manuel Keene,“Jade:ii.Pre-Islamic Iranian Jades”,pp.325-326.而7世纪之后的出土品中,带饰、戒指、碗杯更占多数,这种变化则是受到操突厥语部族和契丹游牧部族的玉石文化影响。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科威特沙巴(al-Sabah)以及美籍伊朗人哈里里(Khalili)的收藏中,皆可见伊朗出土的7世纪以后的玉带扣、带銙、带饰、玉戒指藏品。
需要格外指出的是,无论从出土实物还是文献材料来看,玉石在伊朗地区最广泛的用途都是制作戒指。这种戒指往往兼具印章的功能,戒面上多刻有文字图案。虽然玛瑙、水晶、贝壳、玻璃等材料皆可用来制作这种戒指印,但玉石凭借其柔韧的质地,成为制作戒指的优质石材。因此,在整个中、西亚地区,玉石被大量用于制造戒指。(70)Manuel Keene,“Jade:iii.Jade Carving,4th century B.C.E to 15th century C.E.”,Encyclopdia Iranica,vol.XIV,Fasc.3,pp.pp.325-326.内沙不里的书中写道:玉石工匠把青玉带到了波斯重镇贴必力思(Tabrīz,今译大不里士),用来制作戒面(nigīnh)。(71)Nayshbūrī,Javhir-nma-yi ī,p.111.12世纪伊朗地方史《拜哈黑史》(Trīkh-iBayhaqī)记载了波斯贵族佩戴玉石戒指的情形。(72)Abū Bayhaqī,Trīkh-i Bayhaqī,vol.1,ed.by ī & Mahdī Sayīdī,Tehran:Intishart-i Jughrfiy-yī,p.98.尤具说服力的是,在14世纪后期也门拉苏勒王朝(Rasulid)编写的六种语言分类对译辞书《国王词典》(RasūlidHexaglot)中,突厥语qsh(玉)所对译的波斯语nigīna和阿拉伯语意思皆为戒指上镶嵌的宝石,也就是戒面。(73)Peter B.Golden et al tr.& ed.,The King's Dictionary,The Rasūlid Hexaglot:Fourteenth Century Vocabularies in Arabic,Persian,Turkic,Greek,Armenian and Mongol,Leiden;Boston;Köln:Brill,2000,p.304.实物证据和文献材料都说明,玉石输入中西亚地区,最广泛的用途是制作戒指。
在伊朗地区,带銙是另一种较常见的玉石制品。传统的波斯带銙多是用金属铸成的,考古发现有金、银、铜、铁各种质地的带銙,尤以青铜带銙最为常见。而沙巴收藏中有四件乃沙不耳出土的玉带銙,为7世纪的玉石制品,玉带銙上有圆孔,用以悬挂佩饰。其中一枚背面成斜对角式地钻有成对的小孔,这是为了能使线绳牢固固定,相同式样的饰品在中国也能找到。(74)Manuel Keene,“Old World Jades outside China,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Fifteenth Century:Section One”,p.205.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一枚9~10世纪乃沙不耳玉带銙,与沙巴的藏品具有相同的式样,这枚带銙的材质为软玉,(75)Marilyn Jenkins & Manuel Keene,Islamic Jewelry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New York: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1983,p.33.而软玉正是于阗的特产。玉石带銙在伊朗的出现表明当地的琢玉水平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不过,尽管这些带銙的材质突破了金属范围,采用了东方的玉石来制作,但带銙从形制上来看,基本延续了中古时代以前的中亚传统风格。(76)Marilyn Jenkins & Manuel Keene,Islamic Jewelry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pp.33-35;Manuel Keene,“Old World Jades outside China,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Fifteenth Century:Section One”,p.205.
西迁契丹人在中亚建立西辽政权后,开始将中国汉地的艺术风格传至伊朗,这是伊朗玉石工艺汲取汉风的直接源头。西辽受中华文化的影响遍及政治、文化各个方面,(77)魏良弢:《西辽时期汉文化对中亚的影响》,《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第45~54页;Michal Biran,The Empire of the Qara Khitai in Eurasian History,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93-131.其统治区域内曾出土当地制造的带有中国母题的玉器。(78)Michal Biran,The Empire of the Qara Khitai in Eurasian History,p.100.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据称来自阿富汗喀布尔的鹤纹带銙,上面飞鹤的艺术造型,与宋、金玉器相仿;而玉銙背面的牛鼻穿数对,亦是中国玉带銙的传统固定方式。因此许晓东认为,这件中国风格的带銙当出自西辽。(79)许晓东:《13—17世纪中国玉器与伊斯兰玉雕艺术的相互影响》,《故宫博物院院刊》2015年第1期,第58页。
除戒指和带饰这两种主要形制外,伊朗人还用玉石装饰马具,制作棋子,雕琢饰品。(80)Bayhaqī,Trīkh-i Bayhaqī,vol.1,p.568.需要说明的是,古代伊朗一直拥有雕刻水晶、玛瑙、玉石等硬石的工艺传统,玉石只是作为一种较为优质的石料选择,而未像在中国那样被赋予崇高的含义。因此可以说,在蒙元时代到来前,中国对伊朗的玉石加工影响仅限于技术、造型等形而下层面,而形而上的文化影响是在蒙元时期发生的。
五 蒙元时代汉地玉石文化的西传


这一时期,汉地玉石文化对伊朗最重大的影响,体现在伊利汗国的印章制度上。古代波斯使用、制作印章的传统源远流长,护身符吊坠印、滚筒印和戒指印皆为其传统样式。据出土实物来看,波斯传统的印章通常个头较小(便于随身携带),材质多样,图案亦为多样。虽然用玉石制作戒指印十分常见,但玉石只是众多石材中的一种,未被赋予高贵、权威的政治含义,与中国的“玉玺”“玉宝”概念相去甚远。而伊利汗时期,蒙古人将中国的玺印制度带入伊朗,受汉地玺印文化的影响,玉石印章开始具有特殊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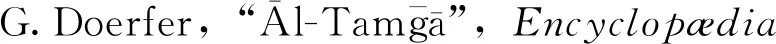

①〔日〕四日市康博:《伊利汗朝の印章制度における朱印、金印と漢字印》,第247页。
伊利汗国文书上出现的印文,反映出其受汉地印玺传统影响至甚,一方面无论是伊利汗的宝玺,还是政府的官印,汉字印文的使用并不罕见,另一方面印文内容既有“××之宝”,也有“××之印”。(90)〔日〕四日市康博:《伊利汗朝の印章制度における朱印、金印と漢字印》,第345页。四日市康博认为,印文为“××之宝”的印章不符合元朝印章印文书写惯例,定然不是元朝所赐,而应是伊利汗国自己铸造的。(91)〔日〕 四日市康博:“Chinese Seals in the Mongol Official Documents in Iran”,第218~219页;《伊利汗朝の印章制度における朱印、金印と漢字印》,第313页。然笔者认为,伊利汗国早期的大型印章,在当地铸造的可能性不大。例如阿八哈汗时代使用的“辅国安民之宝”(图3),最早可见于1267年的文书中,这也是目前可见最早使用汉字印章的伊利汗国文书。这一年是旭烈兀去世、阿八哈即位后两年,而元朝册封阿八哈的使团是在1268才到达伊朗的,所以这枚印章不是元朝赐给阿八哈汗的,而应是更早时候送来赐与旭烈兀汗的印章。汉文文献中有称旭烈兀为“辅国贤王”的记载,(92)〔元〕王恽:《大元故蒙轩先生田公(文鼎)墓志铭》载:“岁壬子(1252),辅国贤王定封彰德为分地,擢用贤隽,特授公为本道课税所经历。”参见《秋涧集》卷四九,四部丛刊本,第13叶。所以“辅国”二字应是对旭烈兀的特指。1264年忽必烈将伊朗之地封给旭烈兀,后派使团前来赐封。这方“辅国安民之宝”当为当时携来赠与旭烈兀的。旭烈兀不久后辞世,印章便留给了继任者阿八哈使用。
那么元朝为何会赐给旭烈兀一枚逾制的印章呢?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若这枚印章确实是1264年送达伊朗的,那么铸造印章的时候,元朝尚未颁布上述玺印制度。许多例子证明,忽必烈之前的蒙古贵族拥有“××之宝”印章的情况并不少见。如成吉思汗曾赐给次弟合赤温之子按赤台的“皇侄贵宗之宝”,(93)《元史》卷一四《世祖本纪十一》,第301页。窝阔台颁给察合台的“皇兄之宝”,(94)《元史》卷一三九《乃蛮台传》,第3352页。定宗贵由赐给东道诸王塔察儿的“皇太弟宝”。(95)《元史》卷一三四《撒吉思传》,第3243页。对于这些逾制的印章,忽必烈即位后曾收回过一些。另一种可能是,忽必烈赐给旭烈兀“辅国安民之宝”与阿里不哥之乱的历史背景有关。1259年蒙哥去世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间爆发了争夺蒙古大汗之位的斗争,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1264年才落下帷幕。在此期间,忽必烈为争取旭烈兀的支持,将原本交由旭烈兀代管的伊朗之地,封给他为独立汗国。1264年元朝使团来到伊朗,就是为了正式兑现这一承诺。对忽必烈来说,旭烈兀支持他取得了对阿里不哥的胜利,维护了蒙古帝国的稳定,堪称“辅国安民”;且无论血缘远近,还是政治向背,旭烈兀都是当时最尊贵的诸王,在忽必烈艰难平定阿里不哥之乱后,赏赐这样一方高规格的印章给旭烈兀,亦为合理。元朝还有一方逾制大印“移相哥大王印”,背印印文竟为“皇帝之宝”,令人匪夷所思。移相哥是成吉思汗幼弟哈撒儿之子,阿里不哥乱时他坚定地站在忽必烈一方,与阿里不哥作战。这方背印带有“皇帝之宝”的印章,或为移相哥出征时,代行皇帝之令的凭证。(96)照那斯图,薛磊:《元国书官印汇释》,辽宁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1~3页。移相哥印是目前可见到的元朝最大的印章,边长为12.5厘米。而“辅国安民之宝”则更为庞大,边长达15厘米,也是伊利汗国所有印章中最大的一方。这两方规格、印文都超出标准的印章,很可能都是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的时代产物。而在忽必烈稳定统治后,就再也没有新铸的逾制印章了。
据统计,目前已知伊利汗国宝玺及官印使用情况如下:

表1 伊利汗国历代宝玺、官印使用情况(97)摘译自四日市康博:《伊利汗朝の印章制度における朱印、金印と漢字印》,第345页。
从这张表格可以看出,中国的印玺文化在这一时期持续影响着伊朗。在不具备汉语环境的伊利汗国,国家的公文书上却有汉字印文的出现,这反映出伊利汗国作为元朝藩国对宗主国权威的认可,也体现了两国政治交往的紧密。表格还显示,伊利汗国前期公文中使用印玺的情况较少,除了上面谈到的“辅国安民之宝”外,只有乞合都时的官印“行户部尚书印”。(98)据四日市研究,“行户部尚书印”应当本为元朝所赐,而后在伊朗当地亦有打造。合赞汗即位后,对国家运行中的各项事务建立了严格的制度,文书制度的运行和玺印的使用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直至此时,伊利汗国的玺印制度才真正地建立起来。具体的规定被详细地记录在《史集·合赞汗纪》中:

这段记载反映的是伊利汗宝玺的使用规范。此外,伊利汗国对官印的使用规定是:宰相、财政大臣和必阇赤掌有朱印(l tamgh),为金、银材质,印色为红色,用于发布政令;怯薛掌有墨印(qartamgh),印色为墨色,用于确认文书。(100)Rashīd al-Dīīkh,Vol.3,pp.500-501;参见《史集》第三卷,第477~478页。可以看到,合赞汗时制定的玺印制度,受到了元朝制度的很大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印章皆为方形;(101)尽管伊斯兰地区过去也有使用方形的印章,但印章上的文字多为草书,且不受印章形状影响。而在伊利汗时代,波斯人所使用的方形印章上,方形的库法(Kufic)字体像汉字“篆书”那样充满整个平面。参见Yuka Kadoi,Islamic Chinoiserie:the Art of Mongol Iran,Edinburg: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9,p.89.二是君主处理不同级别、类型的事务,官员履行职责时,使用不同规格的印章;三是印章的材质标准与元朝制度一致,伊利汗的宝玺为玉石和金质,官员官印为金、银等材质。至此,玉石印章被赋予了高贵的政治地位,成为伊利汗国规格最高的印章,中国的“玉玺”概念被移植到了伊朗。
值得注意的是,合赞汗所制定的宝玺制度,突破了元朝对诸王印章规格的要求。不仅使用“××之宝”的印文,而且使用玉石材质。合赞汗以后的宝玺“王府定国理民之宝”“真命皇帝天顺万事之宝”,按照制度都应该是由玉石制成的。“王府定国理民之宝”直径约9.5厘米,“真命皇帝天顺万事之宝”直径13厘米,(102)Yasuhiro Yokkaichi,“Chinese Seals in the Mongol Official Documents in Iran”,pp.226-227.两者都属于处理国家重大事务时使用的“玉石大印”。(103)“王府定国理民之宝”用于合赞汗致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ius VIII)的书信中,“真命皇帝天顺万事之宝”盖于完者都致法国国王腓力四世(Philippe IV le Bel)的信上。
文献对伊利汗国玉石印章的使用记载得很详细,但遗憾的是,考古方面尚未发现伊利汗所使用的印章实物。日本的门井由佳博士研究蒙古时代中国艺术风格对伊朗的影响,她认为伊朗的玉石业受中国影响不大,可能是由于玉石原料不足。(104)Yuka Kadoi,Islamic Chinoiserie:the Art of Mongol Iran,p.109.她的研究是基于考古资料和实物材料进行的,所以未关注到当时的文献对玉石印章的记载。从伊利汗国玺印制度和公文中呈现的印文来看,伊利汗的玉玺是非常大的,且不止一方。这说明伊利汗国并不缺乏玉石储量。而我们还能从《元史》中看到不赛因向元朝进贡玉石的记载,(105)《元史》卷三〇《泰定帝本纪二》,第672页。尽管进献之人可能只是假称使臣的回回商人,但他们能以玉石贡献,至少说明伊朗与中国之间的玉石之路是通畅的。至于为何伊利汗国的玉石工艺品,不像同时期传入的其他类型的中国工艺品那样多见,恐怕与蒙古人的审美旨趣有关。蒙古人传统上崇尚金银,在征服了西域后,对回回人进贡的各种绚丽的宝石亦喜爱异常。蒙古人对玉器的审美是受汉人的影响形成的,并逐渐接受了儒家“礼制用玉”的观念。但对于早期西迁至伊朗的蒙古人来说,他们缺乏汉地“玉石文化”审美情趣的熏陶。玺印制度所体现的“以玉为尊”观念,仅是附着于汉地政治制度,被整体移植到伊朗的。因此,在这种制度之外,伊利汗国的蒙古人缺乏对玉石的审美情趣,其对玉石的使用和推崇就远不及汉地了。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中华文化对世界的传播和影响也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玉石,对古代中国人来说,是身份、地位、审美及权力的象征。中古时期,伴随着于阗玉石的向西传播,中国的玉石文化也逐渐影响着西方世界。本文在考察玉石西渐伊朗的历史过程中,揭示了古代操突厥语部族和西迁的契丹人、蒙古人在文化传播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为我们研究中华文化向外传播之路径提供了一种思路,即中华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多个民族的共同参与和多元文化的交互影响下,历经数个阶段、一步步地衍射至域外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