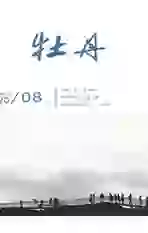论加缪作品中的荒诞主义
2020-10-12章杰
加缪是法国小说家、剧作家,也是荒诞主义文学的代表,他的荒诞思想可以浓缩为他在散文《西西弗神话》中的一句话,“世界是荒诞的,人生就是幻灭”。在小说《局外人》中,他对主人公默尔索形象的刻画深入人心。小说开头轻描淡写地说默尔索猜测“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用这样荒诞的一句话将主人公默尔索的平淡性情和对世事的无所谓的态度呈现给了读者。加缪笔下的默尔索冷漠地看待这个世界,以一种决绝的态度漠视荒诞。小说《鼠疫》中的里厄却用一种无畏的姿态和精神来对抗这个世界,他相信这个世界仍余温未尽。这些作品开启了读者对荒诞的概念,并向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荒诞生活中,人该何去何从?
本文主要以《西西弗神话》《局外人》《鼠疫》为例,通过作品中西西弗、默尔索、里厄医生这些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探讨加缪作品中所体现的荒诞主义。笔者通过探寻加缪作品中的生命哲学和其所热爱的足球运动,分析他独特的哲学精神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和启示。
一、加缪作品中荒诞主义的具体体现
(一)加缪作品情节的荒诞性体现
在《局外人》中,加缪通过赋予默尔索一份出色的感知能力,塑造了一个特立独行的默尔索,他会主动追求身心的愉悦体验。对牛奶咖啡的钟爱能让他在母亲的灵堂里照样安心品尝,享受味觉上的舒适。觉得灵堂气氛压抑,他便去抽烟来摆脱那份令他感到不适的气氛。在葬礼之后的第二天,默尔索毫不顾忌,感受到生理上的悸动,就与玛丽做爱。而后在床上,他依旧能安心地体会在静谧夜晚的夏天的气息。从默尔索的社会关系来看,在工作上,默尔索拒绝了老板让他去巴黎主持新业务的要求。常人求之不得的升职机会,他兴致缺缺,只因为不愿打破自己平静生活的美好。他认为爱情到最终是无垠的虚无,没有意义。因而,他对玛丽所提出结婚的要求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不难看出,他很难再融入世俗的生活。
失手杀人之后,在狱中,默尔索看了无数遍报纸上店客的故事。故事中的店客隐瞒身份与妻儿衣锦还乡,被母亲与妹妹谋财害命,第二天,妻儿来询问,报上了店客的名字,母亲与妹妹悲伤不已,双双自尽。默尔索觉得“人生在世,永远也不应该作假”。秉持着这种态度,他对世事看得通透,将生老病死视为必然会发生的事。因而,在世俗观念的肆虐下,成为判定他死刑的第一大罪状的不是案件本身,而是他在母亲葬礼上的冷漠态度。在他上法庭之后,世人对他的厌恶与案件无关。正如作者笔下所描述的,众人听完养老院院长证词之后,默尔索看到检察官投来得意的眼神,“让我感受到了生平第一次愚蠢地想哭的念头,因为我感受到世人对我的厌恶”。再等到门房的证词“他说我不想看见妈妈的遗容,说我在灵堂里抽了烟、睡了觉、喝了牛奶咖啡”说完之后,默尔索觉得,“我感到有某种东西激起了全大厅的愤怒,我第一次觉得我真正有罪”。但默尔索仍不愿去故作悲伤,违背本心。因而,在世俗观念中公平公正的司法机关的运作下,一件原本只不过是过失杀人案,被定性成了“丧失人性”的“预谋杀人”,表面上严禁客观、周到细致的法律程序中却发生了这样一件荒诞至极的事。从预审、开庭、起诉、审讯、辩护到宣判的整个过程中,默尔索被置于“排除在外”的局外人地位。加上一系列庸常的生活细节,默尔索被精心设计、描绘成了一个无恶不作的罪犯。一步步看着自己被妖魔化的默尔索,不仅深切地体会到被世俗观念肆虐的滋味,也感受到了司法机构的荒诞。换句话说,默尔索的死,不是因为杀了人,而是挑战了当时整个社会的伪善矫情,挑战了谎言堆砌的现代文明,戳穿了皇帝的新衣。
一系列叛经离道的行为出现在温良随和的默尔索身上,人们或许难以理解默尔索的心态和言行举止,这却是他用来逃避生活、逃避荒诞的方式。在生活无穷无尽且无处不在的荒诞中,默尔索逐渐走向了虚无的状态,慢慢丧失认真生活的动力。以一種“遗世独立”的态度活着的默尔索,反映了加缪观念中对于荒诞生活的一种态度:面对荒诞,漠视之。自顾追求生命的自由即可,这就是“身体即天堂”的概念。
二、加缪作品中的荒诞所蕴含的哲学
(一)加缪作品中的生命哲学
1.知悉荒诞而不陷入虚无
1913年,加缪出生于处于战乱状态的阿尔及利亚,当时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殖民地。他的父亲在战争中受伤,不久病逝,他就跟随他的母亲和祖母生活在贫民窟里。贫困而疾苦的出身也造就了加缪的哲学——在这荒诞的世界里永不停止他对这个世界荒诞的反抗。西西弗是幸福的,他在推石上山时明确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为目标不断努力奋斗着。而现实中那些下山或者在山腰停滞不前的人则是悲哀的,他们认为无法逃离荒诞,因而在荒诞中陷入了虚无。但荒诞的世界有着许多美好,《鼠疫》中的里厄医生、塔鲁等在鼠疫的荒诞中不断斗争、追求着美好生活。他们就是现实中的西西弗。但这“荒诞中的美好”又因为人拘于肉体的限制而没办法全部体验,因此也就有了《局外人》默尔索那样“身体即天堂”的生活态度。
《局外人》中,默尔索对一切世事都漠不关心,陷入了虚无主义。他明知世界的荒诞,选择了与世无争,事事顺心即可。他的结局是悲惨的,温良随和的默尔索在法庭武断且咄咄逼人的判决下被判处死刑。法庭上的观众带着恶毒的喜悦,欣赏着一个“十恶不赦”的人被处决。而被妖魔化的默尔索也明白了“为了不让自己感到另类,我期待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来看热闹,他们都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这是默尔索与这个冷漠且存在诸多不合理的世界所进行的最后的斗争。这之中蕴含了在《局外人》中加缪所想要展现给读者的一大核心主题,在这样冷漠的世界里,每个人的生活都如同一个小世界,而人们互为对方生活里的局外人,又都是世界的局外人。鲁迅曾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这方面,加缪和鲁迅表达的都是一份世人皆披着冷漠外衣的意味。
《局外人》深刻地揭示出人在异己世界中的孤独。小说最后也展现了一种看透世界荒诞的同时又不绝望的态度,默尔索躺在监狱床上,“现在我面对着这个充满了星光与漠视的夜,第一次向这个冷漠的世界敞开我的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有爱融洽,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依然是幸福的”。默尔索向死而生,真正意义上体会到了幸福的滋味,回归了自我。沐浴在星光中的他意识到自己从没离开过这个世界,也不是一个彻底的“局外人”,完成了和这个荒诞世界的圆融统一。他看穿了世界的虚无本质,面对世人的漠视,原谅了世界,这也正是加缪在荒诞生活中的生命哲学。正如诗人北岛的《无题》所写:
“对于世界,
我永远是个陌生人,
我不懂它的语言,
它不懂我的沉默,
我们交换的只是一点轻蔑,
如同相逢在镜子中。”
2.在荒诞中的救赎
加缪通过默尔索、西西弗、里厄医生等角色形象,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份超脱庸常善恶观的悲悯和人文主义情怀以及他所坚信的在荒诞生活中要不断反抗的生命哲学。
在《西西弗神话》中,西西弗泄露天机,被惩罚终身推石上山、又被石碾压的无尽轮回,西西弗却从未放弃,毕生都还在为之倾尽所有气力。加缪通过西西弗想要传达的精神内涵是:人在荒诞境遇中实现信念与肉体高度一致,秉持永不后退的气魄,进行不惧艰难的斗争,保持在极度困难条件下的乐观精神,实现人生的自我充实,从而获得荒诞绝境中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就像加缪所说:“爬上山顶所要做出的艰苦努力,就足以让一个人心理感到充实。”西西弗也是一个失去故土,没有祖国、永被流放的个体。加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之后体会到了难以排遣的流放感和陌生感,还有不知何去何从的孤独。在这样的境地下,加缪选择像西西弗一样“举起巨石,蔑视诸神”,既然逃脱不了生活的荒诞,那就直面它。这实际上是一种崇高但却悲怆的格调,加缪感受到了世界和命运的残酷,仍选择对生活充满热爱,迈出自己在荒诞中自我救赎的第一步。
在《鼠疫》中,奥兰多疫情爆发之后,人们被关在城市里,终日空闲,沉浸在死气沉沉的氛围里,日复一日地陷入令人沮丧的回忆里。鼠疫带来的孤独感让人幻想美好的过往,让人沉浸其中,不愿相信残酷的现实。当内心空虚、无所事事的时候,过去的事情会占据人的脑海,使得回忆的种种被无限放大,勾起人们的各种情绪。此时,里厄的人物形象反映了加缪身上的反抗哲理。他没有怨天尤人,追忆过往。哪怕知道现今医学力量有限,依然默默扛起了奥兰多抗疫的大旗,不知疲惫地奔走在鼠疫肆虐的奥兰多。因而,他的积极态度也感染了群众,从一开始的塔鲁,到后来的朗贝尔,越来越多的小人物加入了抗击疫情的战斗中。最后战胜了鼠疫的奥兰多小城,昭示着当时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因此,完全有理由说,《鼠疫》是20世纪人性力量战胜邪恶势力的史诗,加缪自己也明确指出“《鼠疫》显而易见的内容是欧洲对纳粹主义的抵抗斗争”。以里厄医生身上这份更为坚定的抗争精神,加缪完成了对荒诞生活的自我救赎,认为在荒诞中竭尽此生就是幸福。
3.加缪的荒诞哲学中的足球元素
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加缪回到阿尔及利亚,出租车司机认出他是当年RUA的守门员,而不是作为某位作家的身份被认出,加缪为此十分欣喜。笔者相信,加缪也无时不在怀念,曾经有着那么一段岁月,在那令人费解而棘手的荒诞生活中有着足球相伴。与其说是足球赋予加缪了解人与人之间灵魂的能力,倒不如说是加缪的一生在足球的荒谬中得到心灵的慰藉。对于足球荒诞的体验,加缪将他身上的荒诞主义所蕴含的哲理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
加缪曾说:“所有我对人类道德与义务的笃定,都归功于足球。”通过足球与文学的融合,他创造了其独特且极具魅力的精神哲学。细细看来,不难发现足球的元素或精神几乎贯穿了加缪的每一部小说。他的自传体小说《第一个人》,文中名为雅克的年轻人,同加缪一样,酷爱足球,在少年时期,足球便是他们的“王国”。青年的加缪开始为这项运动“着了迷”,在阿尔及利亚空旷的田野上踢着“用破布做成的足球”。荒诞主义者加缪曾是一名职业球员,但18岁时因患上肺结核不得不告别足球运动,转而专心研究哲学与文学。而在足球的荒诞中,加缪好像找到了精神的栖息地。在这别样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历程中,加缪形成了他独居特色的矛盾思想与性格。正如同他不同作品中人物在荒诞生活的不同选择,是选择对自我的虚无放逐还是在荒诞中永恒地斗争?而足球运动中的一对对矛盾,狂野与理性、竞争与友谊、欢笑与泪水、胜与负,将足球爱好者加缪的青春线条描绘得淋漓尽致。
《西西弗神话》中,西西弗的精神则是加缪对于足球运动中胜负观的最好诠释,将西西弗的一个又一个轮回看作一场场球赛,如果输了,那么就得从山底重新将巨石滚上山;就算赢了,总会有输的一天。在《局外人》中,默尔索看到当地球队凯旋归来,“引吭高歌着球队的永不衰败”。默尔索认为他们终会有衰败之日,而在那时,仍需要继续将巨石推上山,如此往复。这并不只是关乎是否会赢,而关系到在下一次球队又需要推巨石上山时,球员和球迷们是否还能怀揣着最初那份无法阻挡、同样易碎而又如同孩童般纯粹的热爱?即“世界以痛吻我,我还能否报之以歌”的心态。
在小说《鼠疫》中,加缪生动地描述了比赛时球场里的火爆场景:球迷们挤满了看台,球员们鲜艳的球服同黄褐色的场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场休息时的柠檬水是最爽的,它给球员们干燥的咽喉重新注入活力。描写的篇幅虽短,却已勾起听者身临其境般的兴奋感觉。
加缪还刻画了文学作品中很少出现的足球运动员形象——朗贝尔和贡萨雷斯。他们一起讨论法国甲级足球联赛,评论英国职业球队的优点,分享传球的技术。通过足球,两人产生了深厚的友谊。书中有一个场景极为动人:贡萨雷斯望着被用作鼠疫隔离营的球场,轻叹道:“可惜了,这么好的天气,不太热也没下雨,要是能踢球该多好!”书中的贡萨雷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在街上踢空易拉罐的机会,这也正是加缪对自己后半生无法继续进行足球运动的遗憾所进行的叹息。贡萨雷斯说:“球赛中,要经过多少配合,推进,传球,才能造成一次破门。”朗贝尔也表示同意,却叹息道:“可是一场球只有一个半小时。”加缪用这样简洁的一段对话,完美诠释了足球这项运动中所蕴含的哲理和团结、拼搏、坚持等宝贵精神。同时,以身处鼠疫肆虐的奥兰多却仍熱爱足球的贡萨雷斯和朗贝尔这两人的形象启示着人们:生活就是一场球赛,人们在活着的时间里,即处于球场的一个半小时的荒诞中,是选择自怨自艾,还是不断去战斗呢?而加缪推崇的则是,哪怕身处鼠疫这样的困境,永远不要放弃。足球是圆的,人们不坚持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生活也是如此。
而一场足球比赛,哪怕只有短短的九十分钟,也能让人们通过足球暂时忘却鼠疫、隔离营所带来的阴郁,足球能够为原本暗淡无光的生活赋予希望和意义。正如成功打入非洲国家杯的利比亚队,原本内战中的敌人在球场上团结一心,共同向自己的命运斗争。在其他时候,足球也总能让人们忘却忧愁,让队员们在球队和球迷的爱戴中找到家一般的温馨,人们的情感也因此而紧紧相连。而这一切都不需要金钱的介入。当加缪热爱的事物丰富地蕴含着他所主张的荒诞主义时,加缪将他身上这份有关足球的独特精神哲学作为其作品里的一份元素,传达给世人。
三、荒诞主义对后世的启示
不论是漠视世界的默尔索,还是做出斗争的西西弗和里厄医生,永远无法逃脱或者战胜荒诞的生活。不论是小说还是现实,人本身就是一个荒诞的个体,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始终存在着一系列的分歧和冲突,但又相互依存。人们对生活、对社会、对自然总抱有各种各样的诉求,如物质、理性、和谐、永恒、公平等。但这些东西存在于荒诞且不合理的现实生活,许多事到头来只会事与愿违。人们永远也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局外人”,这便是加缪通过小说所展现给世人的一个真理——存在即荒诞。马克·吐温也曾说:“有时候现实比小说更加荒诞,因为虚构是在一定逻辑下进行的,而现实往往毫无逻辑可言。”以《鼠疫》为视角来看,现实生活中,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可以说比鼠疫更加严重,但是依然有无数人奔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前线。对祖国的热爱、坚韧的意志让他们不畏死亡,毅然前往,他们就是现实生活中的里厄医生、塔鲁。中国人具有在危难关头团结一致、敢于牺牲的精神。因此,中国的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有效控制。与中国不同,有些国家的领导人怀着像鼠疫初期时朗格尔一样自私自利的态度,导致疫情在一些国家愈演愈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也告诉人们,新冠肺炎疫情并不只是某个国家或某个民族的敌人,而是全人类的敌人。以前听人说读不懂《鼠疫》,但现在笔者相信读不懂的人应该很少了。在人类历史上,瘟疫一再发生,但也一再地被人们遗忘。《鼠疫》的伟大就在于以文学的方式,让人类记住它、重温它并反思它,从而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
对读者而言,加缪的作品犹如一把直击灵魂深处的利剑,命中要害。读者合上的是书,揭开的是内心对于生活荒诞的认知。这把利剑直截了当地挑破了掩盖着存在诸多不合理的荒诞生活的面纱,带着真挚,照见这个时代人类良知层面的种种问题,并在这些不合理上深深地刻下了“荒诞”二字,这也是加缪面对这个荒诞世界所表达的态度。
无论生活多么艰难,人们都要勇于反抗,在荒诞中捍卫自身的权利。要同加缪一样,知悉世界的荒诞而从不绝望,在荒诞中实现对自我的救赎,做自己荒诞生活里的英雄。
(浙江樹人大学)
作者简介:章杰(1999-),男,浙江温州人,本科,研究方向:外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