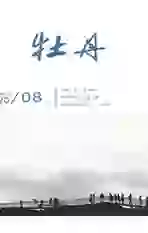行走的艺术
2020-10-12黎荣亮
黎荣亮
生活是一门行走着的艺术,它有着人的感性、意象世界的精神诠释,还有着现实上的审美思辨、哲学上的灵魂救赎。喜、怒、哀、惧、爱、恶、欲是它的艺术基调,它源自人的行为艺术,忠于文化传统,又循于生活美学,筑起了生活中的匠心。
喜是人生常态,人生中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世俗中的小欢喜。久旱逢甘霖是得偿所愿的欣喜,他乡遇故知是久别重逢的适意,洞房花烛夜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怡悦,金榜题名时是欲一朝大展宏图的称心如意。田园有真乐是田野农夫之喜,诵读有真趣是学园学子之喜,山水有真賞是天涯旅人之喜,吟咏有真得是文坛墨客之喜。所喜由心生,心乃道之本源,拥有着大千世界的至理,之于喜,其是“立心”上的至悟、情感。在喜浇灌的蜜糖里,一惊一喜皆风景。有人转山转佛塔,等待着与它的下一次邂逅,也有人沉溺在它的糖衣里,这一次喜成了人生中唯一的风光。
《礼记·中庸》记载:“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怒和喜、哀、乐同为情,是生活偶尔的小脾气,它有时与你四目相对,感受着你的情绪波动,聆听着你的呼吸,模仿着你的一举一动,和你若即若离、忽远又忽近。有时,它惦记着你,和你形影相随,期望自己变得透明一些,再透明一些,直至贴着你的心跳,点燃心中的火苗。中庸的人,排斥怒,挚爱自然和谐、安居正道,走着走着,怒就成了胆小鬼,生活恢复了顺遂生长的宁静。颓废的人,追求怒,喜欢把怒藏于心,表于情,怒就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相由心生,一言一行皆心境,怒与喜仅一墙之隔。
哀为愁、悲、痛所化,情之所至,往往不能自已。每个人在人生的舞台上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喜剧演员,他们恪守着作为一名演员的职业修养,学会了十八般武艺,吹拉弹唱无所不能。极少数时间里,他们化着浓厚的妆容,戴着形似恶魔小丑模样的面具,和搭档们讲着双簧小品,既要取悦观众,又要逗乐自己。结果,总是逗着逗着自己就哭了。更多时间里,他们孤身一人唱着独角戏,嘶哑的声音中在抽丝剥茧般诉说着故事中的前尘往事,初闻不知剧种意,再见已是剧中人。众生皆苦,佛说,生苦、老苦、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各苦皆哀,放下即是自在。
惧是黑暗设计的魔咒,它专挑弱小的人下手。胆怯的人因犹豫而惧,迷信的人因愚昧而惧,虚度光阴的人因拖延而惧,恶贯满盈的人因死亡而惧。一切惧,都来自对未知事物的恐慌,惧极则生悲,悲极则生恨。罗素在《真与爱》中曾说“凡有恐惧的地方,就不会有快乐”,摆脱惧的密钥是无畏。墨翟因百挫无反顾、力拯时世而无畏,辛弃疾因勇猛彪悍、忠义之心而无畏,王阳明因彪炳显赫、豪气凌云而无畏,谭嗣同因不屈不挠、铮铮誓言而无畏。当人不敌惧时,惧就会无处不在,随时寻找偷走人意志的可乘之机,当惧与无畏势均力敌时,惧就会主动退缩。你躲在角落等待恐惧,恐惧便会在前方无声无息地等你,恐惧照亮了你的内心,你也装点了恐惧的梦。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能心有向阳,即可世事洞明,固守本心,无所畏惧。
爱是古老的艺术素材,孕育着发自内心的渴望与期盼,有四个境界。第一境界:“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爱是情窦初开的懵懂,是心扉敞开,种下相思树,只待情花开的憧憬。第二境界:“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爱是携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相守,也是彼此惺惺相惜的承诺。第三境界:“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爱既有着心若止水、清心寡欲的执着,又有着曾经拥有过的怅然释怀。第四境界:“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原来,爱有时不必浪漫和海誓山盟,和你同饮一江水,两颗心便可一脉遥通,一解相思苦,这是平实之爱的真谛。
性善说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人有着和社会道德相适应的从善天性。与之相悖的是,性恶说否定人生而善良,需要后天教化使得人崇德向善。性善说、性恶论中所认为的善与恶是一种天性、伦理上的行为符号。这些符号或表现为谩骂、暴力、侵害等恶行,或表现为偏执、冲突、强迫等人性隐忧。唯愚者心生邪念,扰乱心智,助长恶性。而智者心怀豁达,自愿与恶分道扬镳,可得不惑。仁者心怀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与恶为敌,兼济天下,可得不忧、不惧。
欲由贪生,贪而往复,滋长眼耳鼻舌身意六欲。欲是高悬明镜,可正纲纪、明是非,可感事理,悟大道。欲又带着希望,是活力、朝气和拼搏向上的象征。另外,欲又是邪恶的代名词,知足常乐可得岁岁安好,得陇望蜀反可坠入深渊。
生活这门行走的艺术,有时深奥得难以理解,有时又简单得一目了然。它是我们人生中不可思议的学问,也是我们人生最好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