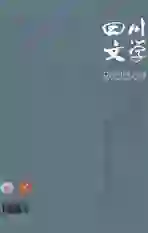多多
2020-09-27张运涛
张运涛
1
还没开口呢,她就被人认了出来。
贝贝?是贝贝吧?
她使劲点头——这应该算是最佳的反应吧?再配以嗯嗯两声,礼貌,又不乏热情——少说话,话多了,就有漏洞。
是贝贝,贝贝回来了!那个大胡子朝里面喊。
那是一个小卖部,面对着公路。里面有人打麻将。
出来几个人——应该是看牌的,里面的麻将声依旧。
校长闺女回来了。
贝贝回来了。
这么多年,你咋没音信啊?
早回来一年也能见上你爹一面了。
大胡子,还不赶紧给你婶打电话。
……
她怯怯地问,有开水不?
有,我给你接,大胡子殷勤地接过她的水杯。
剩下杯盖在她手里。杯盖外面嵌着的白色金属片被宝宝摔掉了,露着狰狞的粗糙内里——她常常不由自主地将这种狰狞与自己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也想过换一个,水杯又不贵,但这个保温好。
大胡子没打电话,他要送她们回去。
我爸……她知道是死了,想问他怎么死的,他应该还不到七十。
去年割稻子时走的,肝癌。发现不到半年就不中了。
这个,真没想到。她收起表情,但心里松了一口气,家里只有一个人,还是个女的,更容易对付了。
宝宝闹着要她抱,大胡子抢着将她抱过去,宝宝身子硬着,不要他抱。她接过去,这么大了,还认生。大胡子只好接了她的箱子和包。
我是你哥啊,小水,不像了吗?
她特意扭头看看他。别怪我(按计划应该先叫一声哥的,却又担心过于殷勤,引起怀疑),医生说,我是失忆。
失忆?大胡子也看她。
想不起来了。过去的事都想不起来了。
还有这样的事?
嗯。我被车撞了一下,醒来躺在医院里,就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现在叫李淑丽。
王畈并没有贴着公路,从公路下来还得走四五百米的田间小路。村头有个水塘,李淑丽记得贝贝说这水塘比学校操场大,夏天她能从这一头一口气钻到那一头。是因为岁月的侵蚀还是因为当时年龄小?反正这个水塘没有她之前想象的大。
村里房子虽然也有新的,但大多破败不堪。有的大门和窗户都用檀条或砖头堵死了;还有的像地理书上楼兰古城的照片,院墙颓了一半,里面杂草比人还高。李淑丽好多年没见过内地的村庄了,既歉疚又失落——歉疚是因为好像这种破落是她的责任,她没有为村庄出过力。失落当然也是因为村庄的破落,不过二十年,怎么就这样了呢?也许是人给她的感觉吧,到此刻为止,除了这个大胡子,她见到的几乎都是老人。
贝贝是第五家,不是第三家——外面那两家应该是别处搬来新建的。一个过道,过道边上一个耳房,进去是一个长方形的小院,后面三间起脊的砖瓦房。李淑丽由此想起贝贝那些零零碎碎的讲述——她还真像一个失忆者,正一点一滴地恢复记忆。房子很旧,一看就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建成的。李淑丽放下心,他们没有建新房,手里应该还有积蓄。
婶!大胡子站在院子里喊。
一个老婆子应了一声,走到门槛那儿,愣愣地看着李淑丽。
是校长。贝贝的妈。她见过她的照片,印象中昂首挺胸,有校长的范儿。但眼前这个人,身子像塌了,手腕上还戴了个俗气的镯子,耀眼得很——不是闪亮得耀眼,是因为她袖子挽了起来,小半截胳膊光秃秃的。别说校长了,连老师都不像。李淑丽中止了上前拥抱的计划,装作因长时间不见而生疏的样子。
好一会儿,校长才反应过来。我的儿啊,你咋这个时候才回来啊?……
她的眼泪被她的颤音激出来——之前她还担心自己临了没有眼泪呢。宝宝见妈妈哭,也跟着哭,扯着妈妈的衣衫。
一只白猫跑过来,对着他们喵喵喵。李淑丽这才想起来,贝贝喜欢猫。她跟她讲过很多猫的趣闻,她都没用心听——连人都养活不了,还顾得了猫?!她还想起一个细节,贝贝家的猫喜欢臭美,喜欢对着镜子跳舞,左转一圈右转一圈。李淑丽当时还不相信,猫还会照镜子?
校长看着正跟猫对视的宝宝,问,这是外孙女吧?
李淑丽嗯了一声,叫宝宝。宝宝,快叫姥姥。
我叔我婶去深圳找了你好长时间,还报了案,大胡子一旁说,公安说很可能失踪了……
出车祸伤到头了,李淑丽面向校长,醒来什么也不知道了。上个月,上个月我才想起来个大概:家在哪儿,你们的名字……
校长点点头——校长比大胡子见识多,知道失忆。电视里演过,失忆就跟黑板擦一样,过去的事儿一下子被擦得干干净净,啥也不知道了。
哦,大胡子像是也明白了。
屋里很快挤满了人,老的,少的,都来看贝贝。二十年了。也有更精确一点的,说是十九年整——西头老铁热死那一年嘛,送走老铁回来校长又去深圳找贝贝……
他们说的是2000年,李淑丽当然知道。厂里新进了一批员工,有一个跟她长得一模一样。她不信,中午吃饭的时候特意找过去,跟她挤到一个桌子上。
你哪里人啊?她问。
河南。贝贝说。
做什么?
缝纫工。你呢?
裁断工。
工资多少?
300。你呢?
350。加班多不?
不多。
……
新元鞋厂差不多有三万人,大家见了面都这样,哪里人,做什么,工资多少,很少问名字。李淑丽也没问,但她记住了她的胸牌,王貝贝。
还真像,个头,眼睛,鼻子,嘴巴,脸,连牙都像——两个人左边都长了一颗小虎牙,李淑丽的略大些……不过,还是有不同,李淑丽微胖,没有贝贝白。贝贝手腕内侧还有个暗红的痣,指甲盖那么大,一般人不会注意。
两个人就好了。女人的好跟男人的好不一样,男人的好是经常聚到一起吃喝,一起作恶,女人的好则是无话不谈,家长里短就不用说了,甚至包括哪个男生给自己写信,哪个男生亲过自己……
出来进去的,人家问起来,她们都是骄傲地说,嗯,亲姐妹!
放年假,李淑丽送贝贝坐上去火车站的小巴,她没想到,贝贝侧着身子跟同事挤在车里的场面是她留下的最后一幅剪影。几个小时后,李淑丽也跟老乡挤上回老家的大巴。
李淑丽的人生从此拐弯。父母开着平时载客用的三轮去镇上接她,拐弯时被一辆货车碾压。葬礼结束不久,又接到警察询问,贝贝失踪了。四个多月后回鞋厂,她的工位被取代,只好重新找了厂。
2
校长几乎一直在跟她讲贝贝的爸。一个清瘦的老头,眼睛深陷。遗像就摆在供桌西头,框上缠了一圈黑纱。
见她一直在看遗像,校长问,想起来没?
大样还在。这是一个颠扑不灭的回答,李淑丽相信,用在任何人身上都行。
你爸在深圳找了你一个多月,贴寻人启事,到电台、电视台打广告……回来大病一场,跟变了个人一样,话明显少了。不能见酒,见了酒谁都挡不住,非得喝醉。醉了就哭,嗯嗯嗯的,像个娘们儿。医生说他的肝癌就跟喝酒有关系。在医院住了不到一个月,死的时候还不到70斤……那段时间,听他念叨最多的就是你……后悔怪了你,后悔非要逼你去上学——老说他没上几年学,不也一辈子?啥大学不大学,能活蹦乱跳的,守着我们,不比啥都强?想想也是,咋样不是一辈子?要紧的是,活着……院子东南角那个土堆,你看到没?那是你没见第三年,他挖的坑,里面埋着你的衣服……对外人,说是菜窖。一到你过生,他就会在那儿给你烧几页纸……我心硬,每次都是看着他烧。有人烧就好,反正我不想让人看到我后悔……
李淑丽早已泪流满面。除了感动,主要是觉得愧对自己的父母。这么多年,竟然没去他們坟上烧过一张纸。过几天吧,等这事了了,先回去看看父母——哥嫂可以不见,父母不能忘。
咱家贝贝回来了?!外面一个大嗓门喊。
你黄婶,校长说,大胡子他妈。
黄婶停在门口,眼睛越过校长,盯着后面的李淑丽看。
校长替她解释,贝贝被车撞了,失忆了,啥也想不起来了。
怪不得,黄婶说,小水跟我说我还不信,还有这病?好好,人回来就好。可怜他叔,到死还在念叨他闺女……
明儿个就去跟他爸见个面,校长说。
那只白猫爬到李淑丽腿上,竖起两个黄金三角耳朵,警惕地瞪着她。它身上的毛异常柔顺,滑溜溜的,像天鹅绒。眼睛是浅蓝色的,晶莹剔透,像镜子,里面映出自己。李淑丽向它喵了一下,又眨了一下眼睛。猫解除戒备,也喵了一声,像是回她——它还以为她在向它放电呢。
多多的崽,校长说。
多多?李淑丽不明所以。
想不起来?还是你起的名字啊。
多多?贝贝也许说过,她没印象。怎么不显老啊?李淑丽不知道猫的寿命,过后从网上百度了一下,猫比狗活得长一些,十五年左右。
这是多多下的崽,我捡了个一模一样的留在家里。
哦。
还叫多多。
多多不知道她们在说它,侧头静静地看着她,像一个八卦记者。
电视里热闹得很,相声大赛,一会儿笑,一会儿鼓掌。李淑丽没心思看电视,黄婶和校长也没那个心思。背后墙上是个相框,贝贝的照片都还在。黄婶见她扭头看,也站起来指点,这张是你满月照,这张是你周岁照,那一张……
小学毕业照,校长说。这一张,我们三口一块儿去武汉拍的。那张,你初中的毕业照。这个认识不?
李淑丽摇头。校长手腕上的那个镯子映入眼帘,有点暗黑,不像是银的。
你大胡子哥,黄婶替她答。他那时候还没有胡子。越长越老了……
看你说的,谁不是越长越老?校长笑,又指向一个合影照片。那个穿扎独角辫的,是你。这一张呢,能想起来不?
怎么想不起来?贝贝站在新元鞋厂大门口,身上是鹅黄色的连衣裙,身子微侧,日光打在她嫩黄的脸上。贝贝当时还送了李淑丽一张,她保存了几年,到底还是扔了——死人的东西毕竟不吉利。李淑丽相信贝贝肯定是死了,那些年,经常有女孩子失踪,不是被弄去卖淫就是被人先奸后杀。也只有父母才如此保存着她的照片吧?想到这,李淑丽的眼泪又来了。
夜里,李淑丽和宝宝就住在过道边上的那个耳房里。那是贝贝走前的卧室,不过不像电影或电视,屋里并没有保存着她生前的样子,这会儿更像一个储藏室。这跟她老家的风俗一样,人死了嘛,都沾着晦气,衣物之类的都要烧掉。还有一个借口,怕活着的人睹物思人,徒添伤悲。桌子和床应该还是那时候的,没舍得扔。样子都笨,家里的木材做的,二十年肯定有,桌子刚收拾过,没有书,也没有文具,更没有女孩子化妆用的东西。靠墙地上一堆铁家伙,扳手、电笔、开口钳子、小锤……床是平板床,床上的用品已经换了新的,床单、枕巾、被罩——上面的折痕清晰可见。
躺下后,她回忆自己当天的表现,觉得还算完美,相逢、解释、拥抱、眼泪,自然流畅,恰如其分。唯一惊心的是黄婶特地看了她的右手腕。她不担心,尽管做上去的痣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毕竟隔了二十年,大小、形状,即便亲生父母也不可能记确凿。
李淑丽比贝贝大两岁。安顿好父母,她去县城给人家带了一个多月的孩子,不自在,又回了深圳。模具厂、油漆厂、马达厂、方向盘套厂,都做过。一个保安追她,他们同居了三年,直到那个男人的老婆找到厂里来。再没有朋友——她其实分不清同事和朋友的区别,反正再没交过像贝贝那样亲近的朋友。最长一份工作做了六年,卖茶叶。余大智就是那段时间认识的。他是个赌徒——当然是她后来才发现的——工资赌完了,还偷李淑丽的钱。到后来,发展到抢。不给,就打。李淑丽开始还怀着希望,有宝宝在,余大智会改的,直到李淑丽的钱被赌光,肩胛骨被踢折。反正也没领结婚证,李淑丽悄悄辞了工,带着一万多块钱的提成去了惠州。宝宝太小,李淑丽做不了工。在一个以前的同事家借住了三天,朋友的老公趁老婆出门,骚扰她。李淑丽走投无路,一夜没睡。她不想回老家,不想见哥嫂。肇事方当年赔了他们10万块钱,哥嫂背着她签的谅解协议。她没有和他们争,但越想越伤心,手足之情啊,竟然连10万块钱都不值!
是的,她想到了贝贝。她跟她讲过,她母亲是小学校长,父亲在路边开了个小卖部,不算大富大贵,但也不缺小钱。她决定冒充贝贝,假装失忆,骗了钱就跑——骗不到也无所谓,权当出去散散心。李淑丽其实没见过失忆的人,但她在一本法国小说里读到过。又上网恶补了一下,中国也有这样的病例。小学校长算知识分子,应该知道这种病。她们长得那么像,又有二十年的岁月隔在中间,谁敢肯定她不是贝贝呢?
外面除了风细抚树叶的声音,死一般寂静。画着斑马线的城市街道,汽车、电影院、超市,好像与王畈不在同一个世界。二十多年,李淑丽第一次睡得这么踏实。
3
第二天,不断有亲戚来,大姨二姨、舅,还有两个姑。他们拉着李淑丽细看,跟校长感叹,啧,二十年了……昨天都预演过了,李淑丽并不觉得多难。她在厨房帮着做饭(既少露破绽,又有主人的感觉),当下手。黄婶是主厨,校长忙着应付来客。
一有空闲,黄婶就跟她讲亲戚们的大事、趣事。你姥得了喉癌,吃不下东西,生生饿死了。你大姑父,前年,在路边解手,一个车轮胎飞过来,砸死了。你表哥,你小姑的儿子海旺,结婚,女方那边时兴送活猪。车到一个镇上,逢集,猪跑了,一车人在街上找了一上午……李淑丽等她笑停下来,问,找到没?黄婶愣了一下,哪能找到?临时又买了一头。
吃饭的时候,大姨拉她坐身边,说小时候最疼她了,以为再也见不到了呢。舅在一旁劝,回来就好,喜事,都别哭都别哭。李淑丽陪着掉眼泪,偶尔看看校长,并没有盯她,放下心。
晚上还有客,朋友,还有近门几家亲戚。正吃着饭,又来了一个,带了箱酒,还有挂面。校长介绍,胡坤,你們同学。李淑丽懵懂地摇头。校长又抱歉地跟胡坤解释,贝贝出车祸撞着头了,失忆了。胡坤笑,听说了听说了。变化不大,还那个样。校长将他朝堂屋让,回来又跟李淑丽介绍,胡大头,想起来没?你们同学给他起的外号。
李淑丽轻笑,想不起来。
你这是啥病啊?多熟的人都想不起来,校长叹气。在王畈,你们一个班。到镇上上初中,还是一个班……
他当过兵?李淑丽突然想起来。贝贝跟她讲过这个男人,她的初吻就是被他夺走的。还说他高大威猛,像演员张丰毅。哪儿像呢?除了个头,李淑丽看不出来哪儿像。
对对。校长炫耀似地拉着李淑丽去堂屋,对着一屋人说,贝贝想起来了,她说坤儿当过兵。
李淑丽红了脸。
贝贝讲过他,是因为他是她的初恋。胡坤要当兵,来向她辞行。好像是个雨天,但没有打伞,说明雨并不大。他们出去的时候天还没有黑。胡坤将她挤到一棵树上吻她的时候,村里有人在唤小孩回去吃饭。李淑丽至今听到有人高声呼唤小孩仍会想到贝贝跟一个男孩的吻。那时候他们都不会接吻,胡坤只知道亲她,紧紧地亲,嘴唇都被他咬出血了……她呢,因为害怕,一点儿也没觉得美好,更不用说甜蜜了。相反,倒是很失落。
这一点,她相信,会大大减少他们的疑虑——如果谁还对她有怀疑的话。
收拾完了,人也散尽了。李淑丽舒了一口气,正要给校长的杯子添水,宝宝在西屋哭起来。李淑丽把她抱出来,晃一阵,宝宝又睡了。
放下孩子,李淑丽又去拿拖把。多多嗖地一声跳开。
多多怕拖把,校长说。
多多跑得卖力,浑圆的肚子,拖着尾巴,身影一耸一耸的,像要逃避追杀。它活得真认真啊,李淑丽忍不住笑,一个拖把,有什么好怕?
贝贝,校长招呼她,过来坐一会儿吧,说说话。
她喜欢她叫她贝贝,让她感觉自己真是贝贝,贝贝就是她。
校长喝口水,贝贝,我们就你一个孩子,也不瞒你,钱呢,也攒了一点儿,不多,在镇上买了一套房子。没敢跟人说,你大胡子哥巴着眼儿盯着我们呢。那个小卖部,校长说,你大胡子哥说是租用,一年给我们5000块钱。一到过年他们就喊着赔——赔你还干那么欢?2000块钱都没合到,有一年只给了1600块钱。到处跟人说,老了养我们,给我们送终摔老盆……
校长这么一说,李淑丽想起贝贝也讲过家里的小卖部,她走那年刚建好,王畈在路边的第一座楼。
等这两天过去了,你要是乐意,你大姨、二姨、你舅、你姑、你大伯,各家转转,多少年没见了。亲戚不就这样嘛,越走越热。
嗯嗯,李淑丽点头。
外人,哪个都指望不上。我自己有闺女,不指望他。校长喝了两杯酒,说话比平常底气足。
我还有个外孙女呢,校长像是突然想起来还有宝宝,站起来,从李淑丽怀里接过沉睡的宝宝。姥姥搂一会儿,让你妈歇歇。回来就没闲过……
李淑丽抬头撞上校长端详的目光,心下一紧,妈……
校长转身回到自己座位上。妈的钱也不多,房子还没装修呢……人老了,事儿也多,今儿个腿疼,明儿个眼睛又看不清,还有红白事儿随礼……你放心,我不用你养活,不是还有退休工资吗?你好好过你的就中了。再找个人——最好还跟宝宝他爸过——屋里这房子你们尽管住……
嗯。
王畈你也待不住,年轻人谁愿意圈在农村?回来住一段也好,宝宝我可以替你照护,你想出去尽管出去。宝宝可以上幼儿……
园字还没说不出口,噗的一声吐了一片。李淑丽觉得不太对劲,小声叫了一声,妈?校长没忍住,又吐了一次……
4
第二天上午,校长醒过来,看着旁边的输液支架,问是在哪儿。李淑丽说医院,校长追着问哪儿的医院,大胡子抢着表功,说是县医院,咱们来得及时,要是晚一两个钟头,危险。医生说没事了,幸亏送来得及时。
我这是咋了?
李淑丽没敢说脑出血,只说太激动,再加上喝了点酒……
问题不大,出血少。不是安慰,医生也说,出血很少,不碍事的,再观察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第几天了?校长又问。
昨天晚上才来。
校长不信,李淑丽两个眼睛里都有血丝。
大胡子说是的,昨晚上的事。
等他出去吃早餐,校长让李淑丽回去拿银行卡,衣柜底层,衣服下面,密码是贝贝的生日。
李淑丽一惊,贝贝?我不就是贝贝?旋即释然,校长病了。
校长说了一组数字,跟你大胡子哥说你回去拿你的包,取钱。
李淑丽会意。
当晚她陪夜,给大胡子在医院旁边的宾馆开了间房。大胡子要轮班,一个上半夜,一个下半夜。她说不用,换来换去都睡不安稳。真困很了,我可以跟我妈挤一会儿。
李淑丽一夜没睡,很难过。不是装的。她只是想来弄点钱花,无论如何也不想弄出人命。
白天闲些时,大胡子说,你爸就是喝酒喝坏的。
他好像以前不太喝酒吧?
你想起来了?大胡子问,你想起来我没?
你是不是老欺侮我?李淑丽故意问。
没有,我老是保护你——胡坤见了我就怕。
李淑丽不好意思起来,好像自己真成了贝贝。我爸什么时候开始喝酒的?
大胡子想了想,也就是这一二十年前的事儿。对,好像就是你失踪之后。
2000年?
具体哪年谁记得着?大胡子说。原来我叔多喜翘的一个人啊,你没见后他就变了。话还多,脸上的笑却少了。唉,你那年突然就走了,到底为啥啊?
能为啥?我妈非让我复读。贝贝跟她说过,她一看到课本就头痛,一刻也不想在教室里待,复读还不是浪费时间?
不是因为你谈恋爱?
李淑丽嘁了一声,真谈恋爱了,舍得离开男朋友?!
谁说,谁说你……大胡子吭哧吭哧不说完整。
说我什么?
说你跟胡坤……我婶气急了,才骂你。
李淑丽明白过来,大胡子的意思是她和胡坤上床了。上了又怎么样?李淑丽为贝贝鸣不平,没有跟男人睡过,总归遗憾。是我妈逼我上学逼急了,骂得难听,我一气之下才跑的。
……
王畈在县城的学生陆续过来看校长。李淑丽想,还是当老师好,她爸妈下葬的时候也就几个亲戚朋友,哪像校长,生个病就有一大堆学生探望。有两个跟贝贝上下届,见了李淑丽,免不了又是一番唏嘘。李淑丽惯了,面无表情地再重复一遍,失忆了,对不起。
第三天,大胡子要回去,家里一摊子事,小卖部你嫂子一个人应付不过来。李淑丽说好,我自己能行。等出院时,哥再来。大胡子说,出院怕也来不了。屋里一大家人,老的老少的少,哪个没点事儿?你回来了,这边就用不着我了……
李淑丽讲给校长听,校长说,让他去吧。你爸活着的时候许过他,东头大路上的房子给他——你爸喝了酒许的。现在你回来了,他觉得没指望了,不愿守了……
李淑丽左右不是,表态给他吧,有点心虚,自己好像还没有这个权利。反对吧,明显给校长添堵。唉,没想到,贝贝父母这边也一堆事儿。谁都不容易啊。
也不能怪你爸,你那时候不是……
给他就给他吧。李淑丽鼓起勇气,我不在,大胡子哥也不少辛苦。但有一个条件,只能您百年之后。她想给校长一个保险。
过几年,咱去镇上住。怕校长怀疑,李淑丽又补了一句。
5
回王畈的第二天,李淑丽起床很晚。外面早亮了,院子里一老一少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
它是白的,为什么叫多多啊?
你也白,为啥叫宝宝呢?
我妈给我起的名儿。
多多也是它妈妈给起的啊。
多多。姥姥,还有吗?
还有啥?
猫啊。
没了,就这一个。你喜欢它吗?
喜欢。它妈妈怎么没见啊?
它媽妈老了。
老了在哪儿啊?
老了就去睡觉去了。
睡完觉不回来吗?
不回来。
它不想多多?
想啊。
想怎么办啊?
多多去看它啊。
什么时候去?
一早一晚。
早晨还是晚上啊?
它还没确定吧。
为什么还没确定?它也跟妈妈一样,很忙?
没妈妈忙。
那怎么不现在去?
……
宝宝问得随意,校长答得却用心。李淑丽想象着校长坐在外面屋檐下的椅子里,宝宝背对着她,在院子里玩那一堆准备修厨房用的黄沙。这就是家的样子吗?李淑丽想象不出自己父母六十多岁的样子,他们不到五十露头就没了。即使活着,也没有校长这般优雅,人家毕竟是老师。但他们肯定也会喜欢宝宝的——哪个老人不喜欢外孙呢?
手机响了一声,垃圾短信。顺便看看时间,6:37。夏天,天亮得早。十三天了,李淑丽算了算。要按她原先的计划,不能超过五天的。时间越长,越容易露出马脚。现在不用担心这个了,她有信心,戏演得意外的好,她都觉得自己可以当演员了。
吃早饭时,校长突然问,你有没有绝望的时候?
李淑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这样的对话,大大出乎她的意料。
那种不想活下去的绝望。
怎么没有呢?她想,好多次吧,父母死的时候,知道哥哥瞒掉那笔赔偿金的时候,余大智打她的时候……她没有自杀的勇气,怕自己受不了死之前的痛苦,更怕死不了成残废。
两次,校长自问自答,我有两次撑不下去了,觉得跟同事跟亲戚跟家人都到了极限。
李淑丽点头,她眼下也是这种状况。
我这辈子,太可悲了,竟然在一个小学校窝了一辈子。
小学校也得有人啊,李淑丽终于找到一句安慰她的话。事实上,她觉得校长有点矫情,在一个小学校窝了一辈子也叫可悲?那她父母早逝,哥嫂不待见她,找了个男人又不成气,想来王畈弄点钱又碰上这事,算不算?
年轻的时候,我有机会。上面要调我去镇上,他不同意……
为什么?
怕我到了大地方,嫌弃他。要是去了镇上,兴许我还能进县城。教课、当校长,哪样我都不服。
李淑丽嗯了一声,有点心不在焉。
唉,啥都没做好。
李淑丽又嗯了一下,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心跑远了,强行拽回来。没有啊,您是个好老师,我看出来了。好校长。
好党员,校长笑了。要是再加上一个好老婆,像不像悼词?
李淑丽一只手摁到校长的手上,她能感受到她的真诚——这些话,她肯定没来得及跟贝贝说。
不是一个好妈妈,校长说,这是我最遗憾的地方。女人嘛,好老婆好妈妈才是最重要的。
是,李淑丽说,您是学生们的好妈妈。
学生毕竟是学生,校长摆了摆手。说实话,我真希望那天没醒过来。我可不想像你爸那样,在床上躺着让人家伺候得烦烦的。
当着宝宝的面,李淑丽忍着,眼角鼓出两泡泪,没有掉下来。她握紧校长的手,心里问自己,将来我死了,悼词里能写上好女儿吗?显然不能。一个十几年不去父母的坟头烧纸的人,算什么好女儿?贝贝更不能,她连父亲的葬礼都没参加。
换个杯子吧,校长看着她们面前的茶杯。
嗯,是该换了。换个好点的,既保温又好看。她喜欢喝热水,胃不好,不敢喝凉的。她其实有些迷信,以为父母早逝跟她从深圳回老家走了一条从没走过的小路有关,从此不敢再做改变,比如换一样东西。她怕变得更不好。
唉,校长叹了一声。人老了,尽是麻烦。
不麻烦,妈。这一声妈,发自内心,她真想留下来给她送终——不是替贝贝,她希望自己至少算一个好朋友,贝贝的好朋友。
你什么时候走?校长从兜里掏出银行卡,递给她,拿着吧,你挣钱也不容易。
李淑丽没有伸手接,直到校长塞进她手里。她想好了,不管卡里多少钱,一定要先给校长装个空调,再在院子里建个带马桶的厕所。厨房也得改造一下,再建一个简易浴室……越快越好,最好明天能开工。
在医院照顾我这么久,谢谢你,孩子!
谢谢?一家人哪有说谢谢的?李淑丽又是一惊,身子坐直,手自然缩回来。
其实,那天晚上我就知道了,你不是贝贝。
李淑丽没有辩解,眼睛无辜地看着她——之前有过这样的预案,最好不解释也不反对,真被识破,也比强词夺理少些尴尬。
贝贝头上两个旋。校长反过来拉住她的手,这不要紧,孩子,要紧的是你的这份心。你跟贝贝以前是朋友吧?
停了会儿,李淑丽才点头。是的,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贝贝是个好闺女,我不是好母亲。校长取下自己的手镯,这个,贝贝为遮掩手腕上的那个痣买的。她放假回来,碰上我过生,就取下这个镯子送给了我……我知道是地摊货,但闺女有情意。
校长脸上有两滴泪珠。
李淑丽低下头。贝贝没跟她讲这一出,这是她不愿示人的地方,即便对好朋友。看来,每个人心中都有柔软的地方。
贝贝早恋了。整个夏天,她都是半夜才回来。我装作不知道,也没跟她爸說,怕他急。我就是受不了她不愿复读……
顿了一下,校长说,其实,贝贝不是我们亲生的。
李淑丽忍不住啊了一声。
我生不了孩子,她是我们从医院捡回来的。
她自己也蒙在鼓里?怪不得在医院里大胡子问她多大了,她说三十五,比他小四岁。我婶六十六,大胡子当时自言自语,又像是故意说给她听。她还觉得蹊跷,不知道他是在提醒她:母女这样的年龄差,在农村不正常。
你要真是她,多好!去吧,孩子,这儿不是你们待的地方。不用担心我,我有退休金,不多,但在农村足够了。校长另一只手揽过宝宝,宝宝,留在这儿陪姥姥好不好?又转向李淑丽,你要是放心,让她在我们这儿上幼儿园。
不知不觉间,太阳从院墙外溜了进来。阴凉小了,暑气弥漫开来。李淑丽去厨房洗刷,想避开尴尬,也平静一下自己。
宝宝在堂屋喊着要看动画片,随即就传来《熊出没》里熊大夸张的嗷嗷声。
李淑丽在厨房里发呆,校长会同意她也留下来吗?镇上的房子要是位置好,她哪儿也不去了,就在那儿开一家茶室。天热,卖信阳毛尖;冷了,就卖红茶,卖普洱。王畈的房子不改造了,都搬到镇上——镇上正好有房子——孩子上幼儿园方便,校长看病也方便。
好,她想象着校长的答复。外面有什么好,贝贝可是出去了。
多多跳到厨房窗台上,头伸到窗户的缝隙处。缝隙太小,猫钻不出去,爪子扒得嗞嗞响。李淑丽看看窗外,没什么特别的,除了两棵树——一棵是寻常的椿树,一棵是广玉兰。多多知道扒不出去了,停下来,两爪依然前伸,身子前倾,极其努力的样子,像是……
多多,喵,宝宝在堂屋找它。
此刻,多多多像那个踮起脚尖吻自己深爱男孩的贝贝啊。
责任编辑 杨易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