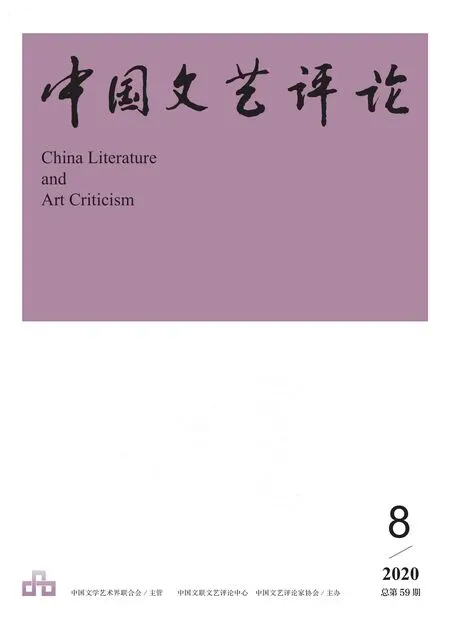新世纪历史题材纪录片的艺术魅力
2020-09-18李国兴
王 锋 李国兴
欧阳宏生教授认为历史题材纪录片“是指利用影像形态对历史遗迹、历史文物、文化景观等的记录,刻画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反映一个地区、一个时期的历史文化,并以此来折射当代人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刻认识、体验与反思,具有十分明显的文化意味”[1]欧阳宏生主编:《纪录片概论》,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6-97页。;而学者徐舫州和徐帆则指出,其概念为“以纪录片的形式,反映当代人们对于历史的看法,并体现学术界对于历史的最新研究结果以及历史观念”[2]徐舫州、徐帆编著:《电视节目类型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8页。。以上说法分别从文化和史学的角度对历史题材纪录片本身的内涵进行了有效读解。而本文认为,在现阶段的评价范畴内,历史题材纪录片作为一种重要的记录介质和手段,以虚构的推演方式再现历史情节为表现手法,依靠摄影机专业技术操作等进行艺术式影像复原。它并非是对繁复历史的单一线性表现,而是对具体的历史事件进行宏观或微观的样貌呈现和艺术探索,天然具备丰富的历史文献功能,以及完整的审美意义和艺术价值。
与此同时,历史题材纪录片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创作本身纳入国家及民族浓厚的历史氛围和价值意义中,随着历史语境和文化观念的更迭,其表现对象的范围愈加广泛,包括了某一特定历史阶段中的历史遗迹、文化遗事、人文景观、历史事件或重要人物等,因此界定范畴不断与时俱进,呈现出新的艺术态势。本文对历史题材纪录片的界定,更多地站在其展现已逝的历史以及与历史接续的当代现实的角度,因此人文历史纪录片、历史文化纪录片等更为细化的类别都在本文探讨的范围内。
本文旨在厘清新世纪国内历史题材纪录片的文化认知价值、美学特征和创作新观等,在理解其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历史关系的基础上,把握历史的整体面貌和局部细节,寄予历史题材纪录片具备更多人文精神的传达诉求,实现创作方式和理念的革新,更加注重表现人在历史中的位置,并承担起回溯历史、传播文化的重任。
一、历史题材纪录片的文化认知价值
纪录片是人们真实再现历史时空,把握现实世界的视听形式,兼具认知价值和审美属性,既带有历史的底色,又深具文化的基因。历史题材纪录片以现代化的视听画面挖掘历史题材中蕴含的文化思想和精神内涵,这些内容历经千百年的积淀和酝酿,对于当下的观众来说,具有醇厚的美学韵味和恒久的认知价值。
新世纪以来,历史题材纪录片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创作主题和表现形式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大型历史纪录片《故宫》《中国通史》《敦煌》,以及近十年来拍摄的历史文化纪录片《颐和园》《景德镇》等,浸染于我国悠久的历史脉络和深厚的文化血液,在历史影像中抒写本民族的影像质感和审美特质,锻刻着深沉的民族烙印,同时不失人文追求和艺术表达,以影像的力量为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理念助力加码。历史题材纪录片作为影像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是对历史的再现和翻新,是传播本民族文化、构建文化认同的重要形式。事实证明,受创作者所处的历史生态环境和文化语境的影响,历史题材纪录片的艺术实践环节发生着悄然改变,而诸如历史纪录片等大众传播媒介又会反向作用于公众对纪录片影像本身和社会凝聚力的理解,并对公众认同产生重要影响。
1. 历史文化的影像建构
纪录影像本身是最直接、最基本、最先被观众接收到的画面信息源,获取真实有效的信息是人们认知活动的基础,从此意义上讲,理解纪录片所建构的影像成为我们探究历史题材纪录片文化认知价值的重要路径。而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影像建构加深了观者对于本国历史文化的认识,唤醒了自身对已发生的过去的文明的无穷想象力,其中的文化力量激励创作主体对历史宏大传统展开新的系统性认知,以更为真实而细节化的影像建构起传统意义的历史文化奇观。创作者在真实的基础上呈现共有的集体记忆影像,所记录的画面构成了本民族恢弘绵长的史诗,传达出一种严肃的历史观,表现出对人文历史的尊重以及对受众群体的观照。毋庸置疑,建构一种悠远而从容的历史影像体现了创作者的初衷与纪录片的客观要求,在不断累积的过程中日渐发掘历史题材纪录片深厚、广泛的文化价值。

图1 大型历史纪录片《中国通史》剧照(图片来源于网络)
大型电视历史纪录片《中国通史》基于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史实,以其极具广度和深度的艺术编排,全面讲述中国境内的从人类起源到清王朝衰落的全过程,无论是大秦帝国、魏晋风度,或是敦煌遗古、宋金和战等,都展现了华夏大地各民族之间的分流、碰撞与汇合。纪录片各个专题相互独立又上下承继,历史事件的梳理完整而详尽,历史逻辑系统而缜密,较好地呈现了历史真相,为那些被曲解、被忽视的断代史和王朝将相正名,完成了真正有骨架、有血肉的历史面貌的影像书写。《中国通史》在还原历史画面真实的同时,更通过旁白引述、史学专家评说等加以佐证这种真实,以一种故事化的叙事方式提升了纪录片的魅力,吸引了更多受众的目光。《中国通史》播映后,不仅在电视频道收视率不断攀高,而且在投放到哔哩哔哩网站后,口碑呈现良好的上升势头,受到年轻网友们的热烈追捧,从而实现了在全年龄段之间的广泛传播,使得这种历史文化影像的传播范围得以扩容和延展,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彰显了大众普遍的文化心理诉求。诸如《中国通史》这样的历史纪录片以其兼具专业化和通俗化的表达打破了观众的心理接受范围和认知边界,缩小乃至缝合了他们对历史纪录片的期待落差,在受众面前开辟了另一条通往历史的崭新道路,真实、广阔而悠远。这一路径越来越成为观众对本民族历史的知解方式和消化途径,也是认识和承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至关重要的一环。
2. 历史记忆的当代认知
纪录片以影像的方式对历史文化进行全面梳理,而接受主体则以纪录片为介质,以基于文明底蕴的历史记忆为对象,对其中所包含的文化意味进行自我诠释和深入反思,在新时代中激发新的辨识和认知。一个国家的文化记忆首先建立在民众集体记忆的基础上,一个人对自身民族特定历史的记忆,构成了他的个体身份和处于群体中的相对位置。而纪录片创作者作为公众的一员,更有责任在艺术创作中明确这种经验意识,以文化为切口,既对宏观历史的时间线索进行串联,又将与历史具体环境拥有共生关系的人推向大众视野,加深文化记忆在纪录影像中的色彩和编码。纪录片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介形式,以其先天的优势担负着记录真实的集体记忆亦即文化记忆的历史性角色,在相对稳定的尘封历史中灵活把握创作契机,从而强化记忆的流动性和延续性。尤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记忆与文化认知彼此关联愈加紧密,两者依靠不断增强的媒介属性,促使历史纪录片的传播视阈发生深刻变化。在不断接纳外部信息和他者世界的过程中,纪录片以其艺术化的形式和表达有效而广泛地输出其本身的文化认知,使公众对彼此共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背后的文化属性、精神意蕴展开深入挖掘和再现。历史题材纪录片具备较为丰沛的历史表现力,成为构建认同心理的重要媒介和艺术手段,也是民众表达自身价值观、历史观、国家观的出口。这种双向性不仅体现在视角的转变上,更在叙事层面寻找到新的创作可能,展现出个体的人如何看待一个国家在时代浪潮中的激流勇进和厚积薄发。
《电影传奇》作为献给中国电影百年诞辰的电视专题纪录片,回顾了中国电影史上经典电影的创作过程及幕后故事。作品以真人扮演、档案解说、主创访谈等兼具娱乐性和艺术性的形式,让观众跟随讲述者一同进入电影的历史叙事中,与电影直接对话,激发了观众对中国电影过往影像文化的无穷想象,引发其强烈的思想共鸣。《河西走廊》是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创作而成的人文历史纪录片,以更为民族化的叙述视野,多维度讲述丝绸之路的黄金地段“河西走廊”的异域文化,发掘出一段鲜为人知却神秘悠长的古代文明记忆。此外,作为国际合作的典范之作,其精致的内容脚本、摄影、配乐等使其整体的艺术价值颇高。《1937南京记忆》不同于以往讲述宏大历史的作品,以其独具巧思的私人叙事和多维结构,探讨了个体与历史、民族和国家之间紧密的脐带关系;以其独特的记录功能,把握了一个国家的命运与个体生命之间彼此牵连的力量和深刻意味,以及个体如何唤醒强烈的自省意识。纪录片中有很多镜头对准了张纯如本人和她的家庭,同时展示了张纯如寻访南京幸存者时所拍摄的珍贵影像。在多方的回忆和追述中,该片所记录的影像画面反而愈发私人化,兼具痛感与诗意。在多面向记录、呈现历史本身之外,对自我身份的深度自省成就了一段个体历史的抒写,揭露真相的过程正是为本民族历史正名的过程,更是向观者呈现中华民族过往记忆的过程。纪录片中所传递出的最为重要的信息是,那些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全体国人的记忆,绝不会随时光的流逝而褪色,那些禁锢在数字墙背后的亡灵以及尘封于历史迷雾中的冤魂,都能成为沉淀于历史深处的不能忘却的记忆。纪录片呈现的正是这种历史记忆,而当代认知则发生在观看纪录影像的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漫漫历史被层层追溯,一个国家、民族共有的文化记忆、时代体验、人类良知被逐渐唤醒了。
3. 文化精髓的历史传承
伴随着对纪录片历史记忆和文化意味的认知不断强化和深入,如何以自身的微弱力量、以精神的索引和行动的意义较好地继承历史浪潮中的文化精髓,成为纪录片创作者和接受者都应思考的问题。时代的更迭使得一个国家的历史土壤和社会文化推陈出新,并在延续和发展中不断强化自身属性,而当文化的抽象意味附着于具体的指代物体之上时,文化的语意则与现实语境更加贴合。作为传统文化重要载体的历史文化遗产无疑扮演着此类角色,无论是纪录片《故宫》《圆明园》,还是《景德镇》,通过对中国古代建筑群、手工瓷器等城市符号的细致展现,雕刻出一座城市的历史纹理,挖掘了其中的文化内蕴,捕捉到城市现代化背后的靓丽风景线。历史题材纪录片因对传统的秉承和对时代的追问,成为记录这些艺术瑰宝存在价值的重要媒介,凝聚起人们和当代社会、地域城市之间的重要纽带联系。历史题材纪录片是在文化视野中深思城市化的精神向导,也是一种将内心对影像艺术的思考付诸时代改革进程的文化试炼。

图2 纪录片《景德镇》剧照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3 纪录片《景德镇》剧照 (图片来源于网络)
纪录片《景德镇》以“瓷器”为载体,从城市手工业的兴衰中摸索中国传统工艺文化的渊源和肌理。“起城篇”中,景德镇作为世界范围内仅存的单一手工业城市,制瓷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汉代,而它早在数百年前就已成为全球瓷器艺术中心。在此生活的制瓷工匠们一代代守护着制瓷艺术,碎片化拼凑景德镇的“身世”,这种对历史的碎片记录,即使缺少完整的文化概况,也依旧充满追溯的可能性。这样的纪录影像充满了艺术自觉和文化魅力,激发了观众基于本民族的文化诉求而形成的文化力量源泉。而今的景德镇实际是建立在近千年的瓷片堆积之上的,每块瓷片都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同样被湮没在景德镇历史中的制瓷工匠们,以超乎寻常的想象力投身于制瓷艺术,正是他们让“瓷器”这样的城市符号真正落地,让历史可以真正地被触摸、观看,他们以不断延展的毅力构成景德镇这座手工业城市的人文历史篇章。景德镇的制瓷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已久的工匠精神,对青白瓷“薄如纸,声如磬,白如玉,明如镜”这般完美艺术的追求,足以让世界对景德镇瓷器刮目相看,瓷器本身的艺术价值也随着时代变化日益被重视。与之相适应的是紧跟景德镇瓷器繁衍而生的市井文化——鬼市,一种持续数百年的交易形式,即常说的古玩市场。各种各样的瓷器在鉴赏中完成买卖,瓷器艺术或在有识之士的目光中传承下来,或消解于日夜交替的颠簸之中,这样的轶事或许只有在景德镇才会发生,在文化的互融中才会碰撞出艺术的火花。
二、历史题材纪录片的美学特征
从历史题材纪录片文化认知价值的探讨中可以看出,其创作根源上带有政治属性,深刻影响了其创作的美学特征,成为既定范围内必然要考虑的“胎记”和“烙印”。但这并没有从本质上影响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创作初衷,它仍旧以表现对象的特殊性、内容创作的真实性、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为主,为人们带去至臻至美的艺术享受。景观式的历史呈现拓宽了客观的存在边界,人文式的历史脉络提升了人性的情感浓度,成就了纪录美学的艺术价值,使得历史题材纪录片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史诗性”。所谓“史诗性”,是指史、思、诗的统一,即史的真实性、思的深邃性、诗的感染力的辩证统一。
1. 真实表达:影像现实的托举之力
纪录片是一种如实反映社会生活的影像记录形态,尤其是历史题材纪录片,更应该尊重历史,准确把握历史的真实维度,立体式呈现物质复原的结果。但其所表现的影像里的现实世界并不能简单等同于真实的历史发生经过,其中夹杂着创作者的主观判断成分,包含创作者对于所展示的特定历史段落、特定社会生活、人物背景等内容的理解。一旦创作完成进入审美环节,纪录片便成为相对稳定的审美对象,必然会带来评价的簇拥以及观看者的情感投放,逐渐演化为一种建立在历史真实基础之上的现实性的表达。纪录片是经过主题的反复确认、素材的筛选细化、创意架构后而形成的一种认知意义的叙事力。历史题材纪录片经过深思熟虑的编排,在历史语境的叙述中投射现实话语。尤其在历史真实影像资料严重不足的条件下,更考验纪录片创作者的编导意识。如何在保有真实性的前提下展开对历史的丰富想象,无限复原历史的本质面貌,如何平衡好历史真实与影像现实之间的顺承关系,都是在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创作过程中需要悉心思考的问题。
历史纪录片《颐和园》抛弃面面俱细的陈词,另辟新径,以微观视角叙述历史君王和景观轶事,为观众展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乾隆皇帝,补足了观众对乾隆的认知成见,在君主身份之外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心思细腻的人,让纪录本身呈现出强而有效的叙事张力和人文魅力。“昆明有乾坤”篇中,乾隆特意为母亲祝寿而修筑清漪园,昆明湖的形状正如一颗寿桃,不仅蕴含“百善孝为先,以孝治天下”的心意和理念,更是乾隆作为一代君王的政治姿态,以此将自己对儒家文化的推崇彰显于世。考虑到园林景观设计,清漪园中只在文昌阁至西宫门一带筑有围墙,一方面是通过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中的“借景”方式,使得园林的光景与周边自然景物有机地融为一体,在整体上达到一种无限延展的效果;另一方面则是遵循中式园林讲究的道法自然,去人工化、雕琢化,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境界。
“清漪出锦绣”篇中,不仅有对园林景观的细致描述,其中还潜藏着诸多历史旧闻谜团,在浩荡真实中激涌出丰富的文化想象。乾隆曾在《圆明园后记》中写道,由于修建圆明园人力、物力消耗巨大,从此往后将不再修建皇家园林,以示帝王勤俭爱民之心。但仅仅六年之后,大规模的清漪园建设又开始了。乾隆为何出尔反尔?纪录片以悬疑化的处理引起观众对历史谜团的兴致,又以娓娓道来的口吻为观众解惑答疑。因为违背诺言修建清漪园,乾隆为自己定了一个特殊的规矩:园虽成,过辰而往,逮午而返,未当度宵,犹初志也,或亦有以谅予矣。这一次,乾隆没有违背自己的承诺,因此欣赏不到清漪园的夜景,这成为乾隆永远的遗憾。而这与我们在历史课本或者影视剧中看到的似乎大有出入,观众在此看到的乾隆是一个颇为矛盾的君王形象,对于其“食言”和“立信”之间情感互搏的情由亦能感同身受,这是一种建立在历史真实之上的现实观察和文化体谅。
2. 时空思辨:技术于历史的“在场”
相比其他类型纪录片,历史题材纪录片呈现的是更为宽广的历史经纬,更为复杂的时空环境,更具艺术探索意义的纪实试验。它所呈现的历史与现实不是一种时空的对垒关系,而是一种表达场域。不同的人在同一时空坐标下对同一事物可以有不同的说辞,表达发生在一种历史对外开放的空间场里,纪录片实际建构了一个自由的发声场所,由于现实的人在历史中的缺席,历史纪录片在处理好人与特定历史时空的关系上用力颇深。“维尔托夫对‘现实’近乎偏执的忠诚,对‘时间’重构的迷恋,对蒙太奇的多层次理解,对观众参与的高度重视——与他卷入其中的历史进程不无相关。他的电影追求从一开始就不只是艺术上的,也是技术上的,还是道义上的。”[1]刘红梅:《回到未来——吉加·维尔托夫的先锋电影理论与实践》,《当代电影》2018年第11期,第83页。正如维尔托夫所主张的,对于时空的诸多思考更多聚焦于技术,技术正是搭建这种表达场域的“武器”。历史题材纪录片不仅记录影像,也记录技术在历史中的位置,在历史真实的外围看到技术的“在场”,因为无论是情景再现或是记忆修复都离不开技术。客观来讲,历史题材纪录片应严格恪守艺术创作的真实性原则,在不违背史实的前提下,通过技术手段复原存在于历史舞台上的重大事件,抓取历史中的重大戏剧时刻,使得原本处于历史环境中的人物“复活”于眼前,而叙事情境则不断向观者渗透一种对于历史的逼真想象,这是人对所谓真实的加码。
历史纪录片《中国通史》传递的直观信息是历史文献资料、电脑合成技术做旧的历史影像、留存至今的古画图景以及人物雕像建筑等。片中《人文初祖》关于“龙的图腾”的讨论本质上是中华民族对植根于历史土壤已久的文化信仰的追崇,《“夏”家天下》借助现存的遗迹和历史文献的记载,全景展现夏王朝的荣辱兴衰,试图全面认知那段远去的历史,创造一个真实感十足的历史世界,在直观感受之外,于战乱纷飞的过往中读解镌刻在沧海桑田的史学符号。历史纪录片《海上传奇》采用第三类叙事手法,既不同于搬演,又不完全是历史时空的产物,而是针对同一个“上海”母题,间歇式嫁接经典电影作品(如《红柿子》《苏州河》)中的上海片段,使得不同历史时空下的“上海”具有某种连续性和继承意义,这是剪接技术的无穷魅力。同时,通过电影《海上花》导演侯孝贤、电影《小城之春》中“周玉纹”的扮演者韦伟等人的讲述,串联起上海和台北、香港等地的情感线,延伸了“海上”的地理意义。若从视觉影像的角度将纪录片纳入电影艺术的范畴,历史搬演的内容其实正是电影中的闪回部分,两者均借助一种情景再现的方式,从无到有,从记忆到模拟过去的现实,将观者脑海中的画面事实化。实际上,影片中演员赵涛个人的介入对于纪录片完整展现历史情节和细节造成了间断式的阻力,实现了电影艺术中“打破第四面墙”的间离功能,使观众从历史的演绎中跳脱而出,重新站在旁观者的视角,思考故事背后潜存的社会关联和历史渊源。
3. 诗性缔造:平民视角的发掘切入
历史题材纪录片受到新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思潮的影响,其创作主题、叙事主张、呈现形式的选择维度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主题逐渐向多元日常和个体参与过渡,注重发掘纪录片创作中的平民叙述视角,重新确立了人在历史中的位置。无论是历史中的人,还是站在历史外围的观看者,都以一种崭新的面貌被书写和对待。历史题材纪录片在历史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之间建构起关联,使观众在近距离观看影像时不会无所适从,主动且自由地释放情感、情绪,乃至评判态度,缔造出不同凡响的况味与诗性。历史题材纪录片以人作为表现的核心,创作视角的下沉实际是将个体的情感脉络和命运走向微观切入对历史的宏观审视之中,在人和历史的关系中判定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关联、边界,搭建起现实与历史互为勾连的桥梁,捕捉到掺杂于其中的情感张力与理性、真实的表现力。
纪录片《幼童》书写的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幼童留学生,他们远渡重洋,克服文化障碍和语言难关,适应异国生活,获得优异成绩,投身各行各业的前沿阵地。然而随着清王朝的衰落,这些留学生被迅速召回国内,他们的命运波澜起伏、千回百转,经历了中国晚清政坛的跌宕起伏,目睹了近代中国的兴衰荣辱。纪录片以微观视角展现了被深深掩盖在历史一隅的特殊群体,向观众揭开了他们不为人知的过往经历,一幅幅黑白照片串联起“人所以为人”的刻骨记忆,带给观众剧烈的震荡感。纪录片《海上传奇》中的演员赵涛站在历史和口述者之外,充当着观众的身份,穿梭于上海的建筑和人潮之中,以观看者的视角感受上海已然褪去的萧瑟和当代的风华,进行着前所未有的纪录实验,在影像内外的互动中实现纪录片的自反,在情节插叙中感受一座城市的温度,以及其中内蕴丰富的诗意和感染力。纪录片《玄奘之路》则返璞归真,剔除《西游记》的神话枷锁,直接让“表演”成为了主角,由演员扮演玄奘,沿着取经线路跋涉千里,在面目特写中呈现出人的疲惫、不安与笃定,以剧情化的戏剧感引领观众进入玄奘的内心世界,成就了一段巍然浩渺的史诗。纪录片抛开那些盖棺定论的评价,重新赋予人物以灵魂,回望一个拥有至深信念和魄力的人如何开始并完成他的生命之旅。在对于历史的解构和对于历史中的人的重塑方面,《玄奘之路》显然走得更远。
三、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创作新观
随着越来越国际化的传播,越来越深厚的艺术交融,以及纪录片导演自省意识的不断强化,不少历史题材纪录片试图在创作观念上寻求突围,展现出美学流变的诸多迹象。在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创作导向日趋明朗的同时,我们需要在某些艺术边界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辨析。
1. 创作的个性化
个性化创作是指从选取题材、切入角度等出发,做到推陈出新,在把握时代导向的同时,扼住历史的脉搏,呈现创作者的个人维度思考和艺术审美的自觉。这种建立在纪录片生态语境上的创作转型,首先来自创作者对本国历史视野的态度转变,是影像创作身份的变化,作者性日益被视作个性化创作的一部分。贾樟柯践行了这种作者性,所拍摄的人文历史纪录片“艺术家三部曲”另辟新径,实属众多历史题材纪录片中包括纪录电影在内的“异类”。
“艺术家三部曲”分别是《东》《无用》《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在创作伊始,创作者便试图以跨时段、跨维度的综合形式,呈现当代历史的风貌,以及“在历史中行走的人”的心境,在对不同身份的艺术家展开各自位置的发问之间摸索出统一的历史根脉。贾樟柯的纪实美学风格为其创作纪录片提供了先天优势,尤其是在书写“小人物大历史”的叙事内容上,展现出一位艺术创作者高度的责任意识和悲悯情怀。“电影《东》中导演与画家的深度合作,促成了两种艺术媒介结成了一种异质同构的互盟关系。”[1]李华强:《盲人的寓言 艺术之悲悯——纪录电影〈东〉中的个体生存影像》,《新闻大学》2009年第3期,第67页。“画家与导演借助绘画和电影两种不同的介质,站在二十一世纪初重新阐释了一个古老的艺术母题:盲人的寓言。”[2]李华强:《盲人的寓言 艺术之悲悯——纪录电影〈东〉中的个体生存影像》,《新闻大学》2009年第3期,第67页。《东》在画像中展现了三峡移民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刘小东以12名拆迁民工作为写生模特,在与其交流的过程中彼此产生观念与情感的碰撞。片中,曼谷影像与三峡库区相对应,都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谋求生存与发展,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存在认知的盲目,那些身处其中的人更像是彼此扶持的盲人,等候把握自己命运时机的到来,由此可见导演在纪录片创作中深切的反思意识。《无用》中,贾樟柯拍摄设计师马可如何创立服装品牌“例外”,见证设计师如何将自己对时尚文化和历史变迁的知觉融入服装设计理念之中。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山西汾阳的个体行业此时正遭到服装工业化的强烈冲击,“散户们”的生存空间被时代的浪潮无限挤压,被边缘化的他们无疑成为时代的“例外”。导演将镜头对准巴黎和汾阳这两座天壤之别的城市,抓取历史的地域性差异,由此建构起两者之间微妙的互文关系。《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是“艺术家三部曲”的最终篇,来到山西汾阳一个小村庄的几十位作家,以叙述者的口吻共同回溯自1949年至今的中国往事,将视角放在了动荡时局和社会变迁中的个体精神与历史截面上。贾樟柯试图站在纪录片的维度,拍摄一部以文学一隅窥见历史全篇的“中国往事”。
“艺术家三部曲”虽是三部独立的纪录影片,但内里具有创作意识的整体性、情感的包容性以及内容的延续性。在以纪录形式讲述历史的同时,自身又构成一个导演的纪录片史实和史诗,拓宽了纪录片创作的边界,在不断变化的时间概念中寻找记录现实的可能性,在复杂的历史框架中打开一幅不为人知的丰盈社会图景。诸如此类的种种尝试,让观者与被拍摄对象之间产生一种思考关系,在素人真实记录和演员角色扮演的相互交替中,观者以主观的眼光观察到历史的物理属性,并在历史中照见自己的位置,实际上与导演达成了一种观看默契。贾樟柯正是以不惧呈现纪录片伦理问题的态度,赋予纪录片“与时代共行”的宽阔胸襟和历史体感,在个体身上开启通往历史的漫长旅程。其作品充满了历史日常和时代哲思,这种“与被拍摄对象共同经历历史”的私人化创作视角,传递出一种更为宏阔的历史反思,使得观众同样能够在纪录片中投入持久的专注力,真正为历史的真实魅力而无限动容。
2. 现代性视野的介入
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的摄影影像本体论强调影像对于客观物质的再现功能,认为无论是电影或纪录片都应当呈现一种原始面目,强调所拍摄时空的完整、真实和不容篡改,在既定事实上排除创作主体亦即人为因素的干扰。以纪录片作为观察对象,这里所说的“现代性”有两个面向,一是观察主体是现代的人,二是现代人观察动作的主观现实意味。纪录片创作是创作主体的本能创作,在当代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创作语境下,题材选择、形式表现以及风格化呈现等日益融入创作者的主体精神,逐渐形成一种“主观的艺术”。当创作完成之后,观看的结果则由观众赋予,观众观看时的身份和位置、彼时和此时的不同观看心态,促使其建构起自己心目中的历史概况,以一种介入的态势,让纪录片的历史视野范围渗入人的现代性读解的意味。创作者和观众所释放的认同感和认知碎片,共同塑造了历史题材纪录片的艺术全貌,使其具备张力十足的美学内蕴。

图4 动画纪录片《我的抗战》剧照(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的抗战》以动画纪录片的形式,大胆挑战纪录片的创作传统和艺术伦理,作品拥有形式的先锋性,内容的主观建构性以及本质上的假定性。臧飞认为:“动画纪录片的创作主体一方面需要对现实的事件进行主观改造,另一方面需要在呈现事件的影像方面进行主观改造,由此产生的双重主观介入性,颠覆了以往人们对于纪录片或真实的基本认知。”[1]臧飞:《动画纪录片的认知及美学思辨》,《视听》2016年第3期,第39页。动画纪录片实际上是对现实的一种提炼和简化,加深观者对其中的历史事件概貌、人物形象、动作细节等全面的认知难度,由于摄影的参照物和表现对象发生了实质的变化,所以挑战了镜头表现物质现实的权威性。《我的抗战》的创作过程是不断调和的过程,创作主体在动画的基础上,嫁接口述历史的传统纪录片模式,以平衡由此产生的种种创作争议。抛掉对历史原型的固有印象和稍显迟滞的观看形式,观者在动画纪录片中获得了一种崭新的视觉体验。虽通往客观现实的手段和路径有所差异,但表达真实和回溯历史的诉求与纪录片的创作初衷不谋而合,使其呈现出一种值得深入思虑的现代特性。那些生动丰盈的旧日抗战动画图像从历史长河中慢慢被打捞上岸,天然附带着历史的余温。观众在新颖独特的艺术形式中感受到历史激荡的回音,从纪录片的影像中感到时间的流逝——人类的局部抗战史已然结束,如今留存于心底的,既是新旧交替着的战争记忆,又是一段难以湮灭的世界近代史。观众正是在种种情感依附和凭借之中产生共情,在历史中的人事和现实的人的历史记忆之间寻得某种认同感。历史题材纪录片正是在这种基于客观真实的技术尝试中不断拓宽自身的外延边界。
3. 历史的公众化消费倾向
与历史题材纪录片的现代性相关联的,是历史的公众化消费倾向,而这种倾向本身也有其历史根源。伴随着互联网尤其是自媒体的兴起,大众开始从封闭的话语中解脱出来,历史纪录片的创作语境发生转向。权威性的姿态被打破,画面加解说的单一样式无法适应当前文化市场的消费诉求,艺术创作理念呈现出具体化、个人化和多元化的特点。在信息扩张与消费社会的环境中,历史存在成为日常谈资和消费对象,乃至可供分享的文化资源,灌注其中的是一种特有态度、接受方式和消费嗅觉。大众文化的不断扩容要求历史题材纪录片能够以更为通俗化、亲民化的方式进入大众视野。
媒介融合催生纪录片以短小、高效的叙事模式适应大众的传播与共享。近年来的“文化热”让历史题材纪录片着眼于历史洪流中的小时代,如何以崭新的视角进行题材的深入发掘,使得与大众距离甚远的历史在当前的文化消费中建立更为有效的作用机制,是当下历史题材纪录片创作的新方向、新机遇。电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借助哔哩哔哩网站等网络平台,实现了对跨阶层、跨年龄段的受众的吸纳。紧接着同名纪录电影被投入大银幕的市场运作,获得了媒体、民众和研究学者们的一致赞赏。故宫题材纪录片的火爆,进一步催生了“故宫热”等一系列的文化产业的萌芽,比如《上新了·故宫》等纪录式文化真人秀电视节目,以及故宫文创、故宫淘宝等衍生品和衍生产业。公众在文创产品以及各类文创活动中认识到历史文物深藏的文化底蕴,并在其衍生产品中获取一种日常的实用价值,进而在一种极为轻松的消费语态中达成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内在认同,这无疑是文化自信重要的组成部分。
四、结语
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纪录片的创作语境发生着深刻变化。历史题材纪录片要兼顾市场性和艺术性,无疑要求创作者不断革新创作方式,使纪录片的模式和风格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互融、吸纳和创新,不断向着平民化、公众化、市场化的方向迈进。除此之外,历史题材纪录片必须对过往历史作出相对客观的叙述和阐释,增补纪实美学的创作认识,在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中寻得认同,在与世界各国的影视合作中开拓视野,在历史性、艺术性及现代性的多重思辨中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人文对话,以此来把握纪录影像本身独具的真实性、厚重的力量感与蓬勃的生命力。

图5 电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剧照(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