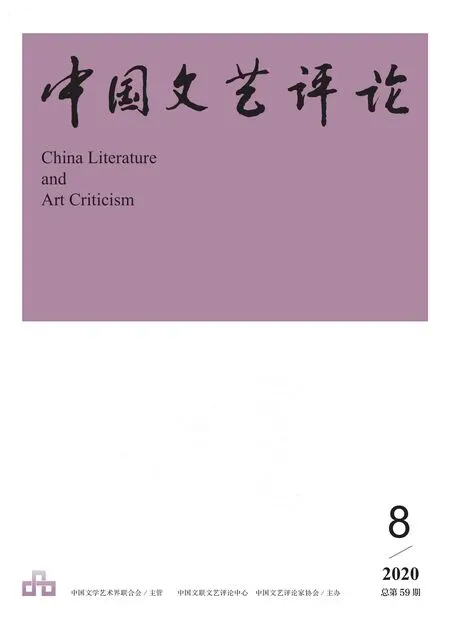大美:中华美育精神的意趣内涵和重要向度
2020-11-17金雅
金 雅
一
大美是中华美育的重要命题之一,它与和谐等命题共同构筑了中华美育精神的核心谱系。中华美育精神聚焦以真善为内核的美的人格涵育,标举美情高趣至境的主体生命涵成,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民族意趣。
中华美育与美学同根同源,离不开民族文化的滋养。与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叩问“何为美”的认识—科学论命题相映衬,中华民族自先秦以来就探寻“美何为”的价值—人生论命题。自前学科的古典思想形态始,到学科意义上的现代理论形态,美与人的生命、生存、生活的价值关联,在中华美学中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崇扬大美,是中华文化与中华美学的重要价值旨趣。中华之大美,既是对象的刚健超旷之美,也是主体超越小我之束缚、与天地宇宙精神往还和合的诗性美。中华大美之意趣,究其根柢,乃“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1页。的浩然正大之美。“大”,不能简单将其等同于体积之大、数量之巨等形式化因素,它与西方美学中的“崇高”也“并不是同一的范畴”[2]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4页。。西方式的“崇高”美,追求“理性内容压倒和冲破感性形式”,与内容形式统一的“和谐”美往往“是对立的”。中华之“大”美,建基于中华哲学天地万物相成化生之“大道”,深具中华文化的独特印记。“‘大’者,也是‘道’(天)之义”,“在古人的观念里,‘大’是最美的”。[1]仲仕伦、李天道:《中国美育思想简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15页。“大”是刚健正大与超旷高逸的统一,是物与我、我与他、小我与大我的诗性关联及审美生成。它并不破坏事物要素间的内在联系与整体和谐,而是通过以整体涵融局部的诗性化成,达致新的更高的更大的正大之美。“大”可以是“压倒和冲破”的超拔浩然,也可以是“和谐的统一”的诗性正大,其要义是冲破一切、升华自我、直抵大道的大无畏、大涵融、大自由之美。
王国维曾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中说:“美之为物,不关于吾人之利害者也”[2]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55页。。这里的“吾人”,即“我”,即审美主体,后人据此常常把王国维解读为审美无功利论者。实际上王国维谈的是审美主体应超越美之于“我”的利害判断,而不是否定美之于人的普遍价值。“利害”作为偏正结构的语词,内含了辩证的尺度。以实用尺度的功利考量来替换利害考量,并不切于王国维的本义。在该文中,王国维又说:“无利无害,无人无我,不随绳墨而自合于道德之法则”[3]同上,第157页。。“无利无害”指审美主体超越“我”之一己利害判断,而达“无人无我”的道德境界,实现美的道德目标。因此,王国维的美的无利害并不是康德意义上的审美无利害。在中华文化中,“道德”的最高境界乃是合于宇宙自然之大道,亦即抵达“天地之大美”。所以,中华美学的核心命题乃“美何为”,而非西方式的“何为美”。中华美学必然要走向美育,以人的审美生成为最高目标。可以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国维又说:“观我孔子之学说”,“其教人也,则始于美育,终于美育”。[4]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57页。如此,“之人也,之境也,固将磅礴万物以为一,我即宇宙,宇宙即我也”。[5]同上。我与宇宙万物融通之大美,超越了美对于“小我”之利害。唯此,大美与那些“逐一己之利害而不知返者”正相反对,是超越“有用之用”的“无用之用”。[6]同上,第158页。前一个“用”,对“小我”言。后一个“用”,对“无我”言。“无我”之“我”,也就是“宇宙即我”之“我”,是突破了个体与宇宙之对立、实现两者和合的诗性“大我”。
对诗性大我的体悟与涵育,是中华哲学精神之灵魂,也构成了中华大美命题之神髓。道家的大美,乃宇宙自然之道。老子以“大道”论之,庄子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应之。[7]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63页。大美乃“大方”“大器”“大音”“大象”,乃“大成”“大盈”“大直”“大巧”。[8]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57页。老子概之:“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9]同上,第449页。儒家的大美,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之“大德敦化”,[1]陈戍国点校:《四书五经》上册,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第13页。是由自然之道贯通人伦之德。孔子以“仁”释之。闻道知命,尽善尽美;乐山乐水,立人达人。是以“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2]同上,第32页。而“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3]同上,第55页。儒道均强调主体之我应循天地、百物、人伦之规律德性,而达大道,而成大美。天地物我和合,小我才有来处,大我方具进路。大美之刚健超旷,才可行可味。诗性之快乐,才与纯粹的愉悦同一。
“大”之天地物我往还和合的宇宙根性、立人达人无利无害的道德根性、超越小我宇宙即我的诗意根性,潜蕴了与美与艺术的天然关联,也潜藏了与生命与人生的深层关联。中华美学对大美的追求及其刚健超旷的精神意趣,在对普遍超越的至美追求上与康德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美学的无利害性是相通的,但中华美学的大美意趣又有别于康德美学为代表的偏倚以美论美的纯思辨循环,而是主张美向现实人生的开放,主张真善美的实践贯通,主张创美审美的动态统一,主张美学美育的知行合一,倡扬天地运化之美、艺术创造之美、生命化育之美的融通无悖。中华大美之意趣不停留于对艺术、对形式的有限的、静态的、优美的观照,而从美的艺术教育、美的知识教育、美的技能教育走向大美人格涵育和大美人生创化,使美育开掘出广阔的视野,升华出形上之维,激荡着浩然正大之辉光。
二
在中华美育视野中,小我和大我,在大美的终极追求和理想涵成中,可以道通德成,天人合一,成就“大人(我)”。这个“大人(我)”,既是中华哲学的范畴、道德的范畴,也是审美的范畴。
“大人(我)”构成了中华美育“大美”精神的人格构像。艺术并不是中华美学的终极归宿,中华美学最终要走向人,落到人的涵育上,贯通于主体的生命、生活、生存实践中,这就是生命的审美化、人生的艺术化。中华美学不局限于唯艺术而艺术的小美唯美,而是通向人的美化和人生的美育,由此,美学与美育密不可分。对大美人格的美趣致思,在20世纪上半叶生成了一定的话语谱系,如梁启超的“大我”、王国维的“大词(诗)人”、丰子恺的“大艺术家”、方东美的“大人”等,它们和现代启蒙思潮相呼应,突出体现了中华美育精神的民族传承与现代推进。
梁启超的“大我”,是对其趣味精神的形象诠释。梁启超把趣味视为美的本质与本体,即以“知不可而为”和“为而不有”相统一为内核的不有之为的大美生命意趣。趣味的人乃大化化我之人,是“大我”“真我”“无我”,是实现了个体众生宇宙“迸合”的艺术化的人,是将人生的外在规范转化为主体的情感欲求的达致生命胜境的大美之人。1918年,梁启超发表了《甚么是我》一文,专门讨论了对“我”“我的”“我们”“小我”“真我”“无我”“大我”之理解。在他看来,没有“无我”,就不可能超越“我的”。但他的“无我”,又不是不要“我”,也不是无视“我”,而是倡扬“大我”,准确地说是不执成败不忧得失的大化“小我”之“大我”,这与他所主张的“迸合”论统一了起来。梁启超吸纳佛学智慧,以佛化儒道,认为肉体的“我”是最低等的“我”。“我”可以通过文化化育,不断“迸合”,层层升华,最终实现自我超越。故“化我”之“大我”才是“真我”,是“我”的生命本真与终极归宿。他说:“此‘我’彼‘我’,便拼合起来。于是于原有的旧‘小我’之外,套上一层新的‘大我’。再加扩充,再加拼合,又套上一层更大的‘大我’。层层扩大的套上去,一定要把横尽处空竖来劫的‘我’合为一体,这才算完全无缺的‘真我’,这却又可以叫做‘无我’了”。[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67页。无我的趣味精神是梁启超的美之基石,也是梁启超美育思想的核心命题。在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史上,梁启超第一个明确提出“趣味教育”的概念,强调以艺术美育为主要途径,辅以自然、劳动等多样方式,涵养趣味化的人,实现生活的艺术化。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的“趣味化”的“大我”,是兴味与责任相统一的“我”,是个体与社会、自我与宇宙和谐和合的“我”,也是创造与欣赏在实践践行中直接同一的“我”。梁启超曾说:“人类固然不能个个都做供给美术的‘美术家’,然而不可不个个都做享用美术的‘美术人’”。[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2页。20世纪初年,梁启超以“美术家”与“美术人”的对举,富有远见地提出了人人成为“美术人”的美育愿景,突出了美育的人文底蕴和价值向度,也突出了对生命审美化的“大我”意趣之期许。
王国维较早从域外引入与绍介美育。王国维一直被看作是中国现代无功利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实际上,他虽受叔本华、尼采、康德、席勒等的影响,以艺术形上学为人生之解脱,但他从未把唯美化的超然物外看作艺术和美的终极追求。他以真情、德性、胸襟、人格等为前提,标举“境界”,弘扬 “大文学”“大诗歌”,推崇“大诗人”“大词人”,探索艺术之美与人生之美的融通。何谓“大词(诗)人”? 王国维以为,“大”不仅是拥有艺术的技巧技能,关键是有着生命之境界。他以东坡、稼轩为例,认为若“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3]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52页。他把艺术视为生命的写照与存在方式,艺术的美境乃生命追求之标杆。他以“三种之境界”来比喻艺术和生命不断追求、层层奋进、渐次提升的三个阶段,以此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必由之径,而“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4]同上,第147页。王国维慨叹:“美之为物,为世人所不顾久矣!”[1]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58页。他痛惜国人缺乏“审美之趣味”,只知“朝夕营营,逐一己之利害而不知返”。[2]同上。因此,他对艺术与美的思悟,也是他对学问与事业、对生命与人生的感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孔子思想的美育底蕴与席勒的美育理想,在对美的“无用之用”和“有用之用”的联系上,是有相通之处的。“大词(诗)人”不仅是王国维心中伟大的艺术家,也是实现了有我与无我、出与入的自由超越的审美化的人。
丰子恺是中国现代美育的重要倡导者与践行者。他提出“最伟大的艺术家”,就是“胸怀芬芳悱恻,以全人类为心的大人格者”,[3]丰子恺:《丰子恺文集》第4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6页。这才是“真艺术家”[4]同上,第403页。。他最鄙夷“小人”。“小人”不是指年龄之小,“小人”也不是那些尚存天真的“顽童”,而是那些爱美体美之心蒙垢的“虚伪化”“冷酷化”“实利化”的成年人。丰子恺说,生活是“大艺术品”,绘画、音乐是“小艺术品”。他主张通过艺术审美教育,把美的精神贯彻到生活中,涵育“生活的大艺术品”,涵育趣味化的真率的“大艺术家”,实现“事事皆可成艺术,而人人皆得为艺术家”的美育理想。[5]同上,第293页。
方东美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美育思想突出体现了传统儒家以文化人的大美育理念。他说,“天大其生”,“地广其生”,“合天地生生之大德,遂成宇宙”。[6]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9页。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说”,就是把“宇宙和人生打成一气”,“这种宇宙是最伟大的、最美满的”;“人的小我生命一旦融入宇宙的大我生命,两者同情交感一体俱化,便浑然同体浩然同流”。[7]同上,第161页。方东美以“广大和谐”来阐释宇宙精神和生命精神,倡扬“大人”之涵成。“大人”是方东美理想中的“全人”(Perfect and perfectied man),是“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的“至人”。[8]方东美:《方东美先生演讲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6页。他引《周易》之“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9]陈戍国点校:《四书五经》上册,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第143页。认为“大人”乃知性人、德性人、宗教人、艺术人合一的行动人,是真善美和融的诗意化的“时际人”和“太空人”,也是与天地同心之“大诗人”“大音乐家”“大艺术家”。“大人”“大诗人”“大音乐家”“大艺术家”,词异而意通,诠释了方东美以精神美成践形于世的美育致思。
三
大美之根本,在于对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与天地大化浩然同流的生命气韵与精神气象的激扬赏会。中华美育的大美意趣,最终体现在对大美生命的涵育上,体现在真善美和融正大的人格化成上,体现在小我大我汇通迸合的自由升华上。但“大”在中国古典美育中,因为与道德、天道等的纠缠,其作为美育范畴的功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20世纪上半叶,伴随中国现代美学的理论自觉,“大”的话语建构和理论内涵得到了丰富推进。特别是与“新民”的时代命题相结合,在确立情的核心地位的基础上,“大美”阐发聚焦主体人格刚健、精神浩然、生命正大等美趣意向,突出了美育的道德向度、崇高向度、自由向度等。
大美弘扬了美育的道德向度,是对主体共情能力的激发。审美主体对道德律的体认,是对自然律把握的道德升华及其情感体认,大美的生成须由主体从道德体认超向情感体认,即由道德知性通达道德美感,而生成刚健超旷的情感认同和浩然正大的情感愉悦。朱光潜指出,“道德家的极境,也是艺术家的极境”。[1]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77页。大美基于大爱。小我之展拓扩张,援物入我,援他入我,爱我及他。身之小我,爱披众生。通宗会源的大美至情,俱兴于纵横灿溢的高趣艺象,迹化于生生不息的生命爱境。梁启超独具慧眼誉杜甫为“情圣”,认为他常把“社会最下层”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1页。,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至情,抒写了大爱之美的正大辉光。丰子恺的画作将满溢的爱意和清致的美感相交糅,“物我无间,一视同仁”,处处洋溢着美与爱的主题,浸透着对人和生命的最深切的关怀[3]参见何莫邪:《丰子恺》,张斌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体现了绝我不绝世的清雅超旷的大爱大美。
大美弘扬了美育的崇高向度,是对主体共情能力的锤炼。刚健超旷的大美,激扬着崇高的意趣,但不能把大美与崇高美直接画等号,也不能将大美与和谐美截然对立。大美、崇高、和谐,既有对立要素的冲突与超越,也有多元要素的融通与升华。中华文化之“大”,乃万源归一。中华文化之“和”,乃和而不同。大有根,和存异。没有矛盾冲突,就没有同一和谐。没有相辅相成,就没有诗意升华。有限之小我与无限之大我,在大美生成中冲突与和解,最终实现了小我的超越与诗性。梁启超以“迸合”来诠释“大我”的这种超越与升华,高度肯定了悲剧精神的崇高品格与大美意趣。他高度赞赏屈原“All or nothing”的人格美,指出屈原“最后觉悟到他可以死而且不能不死”,是拿自己的生命去殉改造社会的高洁热烈的“‘单相思’的爱情”,“这汨罗一跳,把他的作品添出几分权威,成就万劫不磨的生命”。[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7页。在他笔下,屈原既是伟大的诗人,也是大写的人。
大美弘扬了美育的自由向度,是对主体共情能力的升华。大美是纯粹之大无畏大涵融大自由的美。“大雄无畏”[5]方东美:《生生之德》,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31页。。“惟大英雄能本色”。[1]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92页。美的实践主体,纯粹刚健而自由辉光。他向最高本体提升又践行于生命自身,非彼无我,一体俱化,同情交感,至纯至善。空灵超脱的艺术世界、巍然崇高的道德世界、澄明莹彻的真理世界,迹化于鲜活烂漫的生命世界。即小而即大,至实而至虚,无所不容而无所不可容。健进通贯,至真至纯,无畏自在。这种纯粹大美的境界,也是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向往的生命审美化、人生艺术化的自由境趣。正如朱光潜所言:“伟大的人生和伟大的艺术都要同时并有严肃与豁达之胜”;[2]同上,第94页。“‘无所为而为的玩索’是唯一的自由活动,所以成为最上的理想”。[3]同上,第95页。唯纯粹而至大,唯无畏而至大,唯涵融而至大,唯自由而至大。创造与欣赏,看戏与演戏,出入自如,是谓“谈美”。朱光潜感叹,在最高的意义上,美与真与善并无区别。走向大美,正是走向伟大的人生,走向生命的纯粹与自由。
四
在当下实践中,传承弘扬中华美育的大美意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针对性,对于培养艺术家高洁的审美趣味和刚健的精神境界具有积极的引领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艺创作时,批评了“调侃崇高”“低级趣味”“形式大于内容”等现象[4]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页。。文艺界的有识之士也呼吁当前艺术活动要正视“喧嚣、浮躁、浅薄化、空心化、形式化、游艺化”等现象,反对“奴颜媚骨”“市侩气息”“拜金主义”诸情状,关注“中华民族精神的矮化,中华民族风骨的软化,乃至中华民族生命力的退化”之忧患。[5]陆贵山:《刻画新人形象 树立时代典型》,《中国文艺评论》2020年第6期,第8页。弘扬大美,是对艺术风骨精神的呼唤,是对旖靡媚俗、追名逐利、形式至上的反拨、超越、审思。
大美是对旖靡媚俗的反拨。先秦汉魏,中华文化不乏雄健之风。初唐盛唐,亦多雄健气象。但很久以来,西方世界包括我们自己,渐渐忘却了中华文化的阳刚之美,放大了温柔敦厚、蕴藉柔美的气息,甚至渐成民族文化的标记。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曾漫衍出种种褊狭和病态的趣味。梁启超曾指出,中国韵文的表情法历来“推崇蕴藉,对于热烈磅礴这一派,总认为别调”。[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3页。而就中国文学对女性审美的病态,他更是予以了辛辣批评:“近代文学家写女性,大半以‘多愁多病’为美人模范”,“以病态为美,起于南朝,适足以证明文学界的病态。唐宋以后的作家,都汲其流,说到美人便离不了病,真是文学界一件耻辱”。[7]同上,第127页。这种病态趣味,在当代并未根绝,“娘炮”等称谓,就是对当代性别审美的病态异化的嘲讽调侃。文艺创作要“存正气”“讲品位”“有筋骨”。“有筋骨,就是作品要表现崇高的理想信念、非凡胆识和浩然正气”,“这种精神上的硬度和韧性,正是伟大的作家艺术家之所以伟大的根本所在,也是一切伟大作品之所以伟大的艺术质地”,“一部堪称优秀的作品,都应该有大胸怀、大格调、大气度”。[1]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年,第30页。习总书记先后提出“中华美学精神”和“中华美育精神”,高屋建瓴地指明了以民族美学和美育的优秀精神传统引领当代艺术实践发展提升的深刻意义。王元骧谈到,席勒美育的内容包含“融合性的美”与“振奋性的美”,前者“在紧张的人身上恢复和谐”,后者“在松弛的人身上恢复张力”。[2][德]席勒:《美育书简》,徐恒醇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4年,第96页。他认为,“美育问题近年来已引起学界普遍的重视并在研究上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也存在某些认识上的不足”,其中之一就是“以能否直接引起人的精神愉悦为标准,把美育等同于‘美’(优美)的教育”,而“美育并非只是‘美’的教育”。[3]王元骧:《艺术的本性》,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50页。他引席勒的观点“假如没有崇高,美就会使我们忘记自己的尊严”[4][德]席勒:《席勒散文选》,张玉能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09页。,进而指出“崇高感的审美价值以及它在美育中的地位一样,目前还很少为人们所认识”。[5]王元骧:《艺术的本性》,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62页。这类褊狭的认识,不仅影响了我们对美育的全面理解,也影响了我们对优秀民族美育资源的发掘。推动中华美育精神的传承弘扬,发掘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大美意趣,对于拨正提升当代艺术实践的精气神,夯实提振艺术家“精神上的正能量”,在艺术创作中展现“大真大爱大美”,具有切实的意义。
大美是对追名逐利的超越。当代社会,商业化、市场化的冲击,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滋生,使得有些艺术家、评论家失却了艺术的情怀信仰,作品粗制滥造,评论吹捧抬轿,把创作和评论“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6]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2015年,第10页。,投机取巧、沽名钓誉。有些艺术家只抒写一己悲欢,有些评论家脱离现实大众,他们的创作和评论缺乏大情怀大格调,难以与民族同脉搏、与人民共呼吸,丢失了追求君子人格、鄙弃追名逐利的美好情操。大美要求艺术家具有博大的胸怀、高洁的情趣、高远的境界。“自我价值的过度膨胀、个人私欲的过度放纵,缺少理想和爱,难以与文艺的崇高追求合拍,也不符合人民的审美意愿,最终只能停留在粗鄙的境界之中”。[7]同上,第104页。当代文艺创作应积极回应时代发展的新态势,深入结合新的时代生活,创作出体现大胸襟、大情怀、大格调的生动文本,发挥好艺术审美教育的独特作用。[8]同上,第115页。
大美是对形式至上的审思。从古典到现代,中华之大美从不以形式为要。孟子曰“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1]陈戍国点校:《四书五经》,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上册,第134页。,他的“大”就是“充实”之内质与“光辉”之气象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现代形式主义思潮对我国文艺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冲击。特别是“当前我们的一些文艺作品,沉醉于玩弄形式技巧,缺乏表现‘心灵’的深度,致使作品沦为单纯的炫技表演”。[2]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年,第33页。在文艺创作中,“单纯地、片面地、不问其他价值因素地去一味求‘美’,作品就容易变得苍白、流于形式、丧失精神”。[3]同上,第103页。西方现代美学中的“美”,很大程度上是指形式性的美,偏于感官观审的美,与之相联系的美感通常指单纯的愉悦。这与康德美学将情与知意相区分所构建的判断力命题相联系,所以形式论者常将自己的鼻祖溯至康德。而黑格尔的艺术哲学,主要将“美”导向了艺术领域。他们的思辨,强调了美与艺术的独立品格,却有意无意疏离于美与人的现实关联,疏离于美向人生开放的实践品格,使得美在走向鲜活的人和鲜活的实践时,难以完全发挥其深刻的美育效能,难以充分发挥美反哺主体、涵育心灵的独特作用。
今天,对包括大美在内的民族美育资源的梳理、发掘、辨析、阐发,是传承弘扬中华美育精神的重要基础工作。我们一方面要积极梳理这些资源的发展演化脉络,摸清自己的“家底”,挖掘自家的宝贝;同时要积极推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推动优秀民族理论资源走向艺术实践、引领艺术实践,在介入实践中推动其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