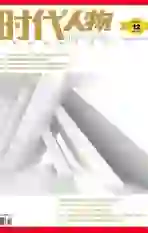男权社会下的悲剧生存
2020-09-17张翼
张翼
在对历史观念进行消解与重建的过程中,女性这一叙述的盲点终于被受到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影响的男性作家所重视并将其作为了表达的主要对象。中国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刚柔并济,在女性形象身上能够以一种优美与崇高的形式展现出来。女性以一种精神上抚慰与回归的角色无形地成为了家园的根本,也具有了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特质的地位。而在对这样一类形象的设定与描写上,正是出于对女性地位的肯定,很多作家不约而同地呈现出了对女性形象的强烈关注。
正如《红楼梦》里所说,女人都是水做的。从江南烟雨中走来的苏童,也给了女性一种轻灵与流动。他笔下的女性群像,从个性张扬的三太太梅珊,到精明强干的皇甫夫人,再到瓦匠街女孩织云……每一个女性,都有着自己的独特个性与行为方式。每一个女性的身上,都闪动着聪慧的灵光。而与之相对应的男性世界,则是一个布满金錢、肉欲、心理阴影的黑暗之地。在这样的男性世界的衬托下,女性世界显得更智慧、更有灵性。而恰恰是这样的女性,在社会及家庭伦理秩序中是被统驭的对象,时时都受制于猥琐阴暗的男性,这本身就是一种无法消解的悲哀。苏童通过建构这样一种理想与现实的不均衡,展示女性不断向自身命运挑战与挣扎的过程,以及在这样的过程中失去话语权的女性逐渐失去自我的现象,预示了男权社会中女性无法摆脱的悲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家族没落命运。但是,也正是通过这种悲剧,将历史无意识下的盲点聚焦,女性无名又无言的悲剧也被上升为了一种历史悲剧。
在这里,根据悲剧的形成原因,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完全依附男性而产生的受制悲剧。这种女性悲剧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女性完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觉醒。虽然其中大部分的女性都是近现代社会的女性,正在逐渐接受着新的思想,但是并没有改变男性的主导地位。而这种现象,不单是在近现代时期没有得到改善,即使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时期,在女权主义逐渐盛行的情况下,我国的大部分女性,仍然习惯性地接受着男性的主体地位。而很多女性仍然身处于此而不自知,根本没有自我意识,而是习惯性地接受并参与男权社会中对女性的定位——依附男性,这就是女性的悲剧所在。这一批女性,基本上都遵循着寻找依附——竞争——牺牲的链条。作为弱势群体,她们如果希望在男权社会中求生存,依赖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做到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她们必须要寻找一个依附点。而这个依附点,只能是男人。而女性对男性的依附,经常会以家庭关系来体现,因此,这也成为了苏童家族叙事中常见的女性悲剧。即使如皇甫夫人这般精明能干,地位这般尊贵,也不能得到大臣的拥护,必须依赖于一个男人作为支撑点,即使这个男人弱智得如端白。那就更不用说《逃》中我婶子千山万水地寻找叔叔刘三麦、《妻妾成群》中雁儿将讨好老爷作为了拯救自己的方式。而这种依附关系的悲哀就在于是在依附双方处于不对等的条件下产生的。在男权社会里,女性永远只能处于被选择的地位,而男性则牢牢掌握了选择的权利。女性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在竞争之余,为了取得所谓的胜利,不惜采用各种手段。但不管女性怎样努力,因为最初男女地位的不均衡,女性的道路最终仍然只能走向牺牲。这一类牺牲一般来说都是精神与人格角度的牺牲,但正是这类牺牲使得女性悲剧更为突出。苏童从人性审视的角度,在展示女性聪慧与灵性的同时也深刻地展示出了女性为求生存而不得不具备的恶毒、妒忌、乖戾、残忍等等心理,当这两种互相矛盾的极端特质都集中在女性身上时,就形成了一种人性悲剧。如《妻妾成群》中的大太太、二太太等女性,只是把竞争看作是为保住自己在陈家的地位而下意识地做出的行为,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受制于男权的同时在戕害同病相怜的姐妹。雁儿为了争取地位采用巫术诅咒颂莲,卓云也带着和善的笑容戕害梅珊肚里未出世的孩子。而《我的帝王生涯》中后妃也将自己的未来寄放在懦弱的端白身上,为争宠残忍地互相残害,甚至当宫变之时菡妃仍然以为怀孕是她的法宝而闯进囚室避祸,遭到了黛娘的疯狂踩踏而死。正是在这种争夺过程中,女性也逐渐变成了男权社会的牺牲者,失去了女性的灵动与自我,变成了男性的工具。
第二种悲剧的形成则是稍稍觉醒的女性在男性地位的压制下逐渐绝望而自我崩塌。这一批女性大多都接受了新的思想,但改造不彻底,仍对男权社会抱有幻想。这使得女性的自我人格产生分裂,当面对男权社会中毫无温情的男女关系时,不断使她们清醒地认识到女性的地位,甚至为了提高女性的地位而不断努力,但最终因为自我意识的觉醒、无法承受残酷的社会现实而产生精神上的自我崩塌。如《妻妾成群》中稍微觉醒一点的三太太,因为戏子的出身而相对来说性格更自由、真实,但是最初还是对男性抱有幻想,认为陈佐千对自己的宠爱是感情的一种表现,所以当颂莲进门时她经常称病而引陈佐千去,她不愿与更多的一个人分享丈夫。而后来便逐渐发现自己在他眼中不过是玩物而已,于是在绝望之余开始追寻新的爱情,但终于死在对华丽爱情的追逐之中。而颂莲作为一个接受新思想教育的女学生,在父亲死后考虑自己的生活时毫不犹豫地选择嫁人,这也是长久以来男权社会思想对她的影响。进入陈家后,她也逐渐卷入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去,甚至用尽手段,即使自己不爱陈佐千,但是不允许威胁自己地位的人存在。从她对待雁儿的手段来看,似乎她也接受了女性的依附地位。但这毕竟不是一个真实的她,内心存留的善良与纯真使她也因为自己的残酷而逐渐产生恐惧感,精神上的自我压力使得她必须要找到一个精神寄托。而从她的内心来说,她毕竟有自己的个性与人格,有一定的女性自我意识,她需要的是爱情,需要的是人格上的尊重。陈佐千视她如玩偶的做法逐渐使她对他失去希望,而适时出现的飞浦则成为她转移感情的一个很好的目标。可是当她知道飞浦的不正常心态后,这样的家庭使得她完全绝望,这种囚笼似的环境也逐渐对她产生了精神上的折磨,时常产生幻觉、醉酒等,最终自我崩塌,被逼成疯。甚至《罂粟之家》中的刘素子,以财主女儿的身份仍然无法逃脱女性的悲剧。有着绝世容颜的她,也具有一定的自我意识,有奇异的秉性,也曾因为父亲将作为三百亩地的交换被卖给驼背而对父亲表示抗议,但是在土匪进犯时,她又因为女儿的地位而被父亲拱手送出,最后甚至成为了长工的猎物。她最终无法承受男性社会对女性的压制而杀死了自己,杀死了那个眉宇间有洞穿人世的散淡之情的刘素子。
第三种悲剧则来自于完全觉醒的女性以一种极端方式来表达的对男性社会的抗争。在对历史的重写过程中,苏童特别关注并展示了一群对男性社会背离与反拨的女性。在不平等的家族地位下,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安于男权主宰的命运。即使是在绝对的男权下,仍然有少数女性有着与生俱来的自主意识与叛逆精神,她们拒绝男性中心文化对女性做出的价值定位,挑战男权社会对女性设定的各种禁忌,虽然这些禁忌已经潜移默化地植入她们同时期的大部分女性心底。而正是因为社会环境对她们种种不利因素,她们微弱的力量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于是她们以一些极端的方式来给社會敲响着警钟,同时也给她们的人生染上了悲剧的色彩。这种女性的存在贯穿了封建社会的全过程。《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金瓶梅》中的潘金莲等女性人物,都是这些具有叛逆特质的女性在文本上的折射。苏童也以他细腻的笔触,深入地描绘了这一批女性的心理状态,以及她们所采取的不同极端方式。有些女性是以放浪形骸的方式表达对男性的极度蔑视。以《米》中的织云为代表。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判断经常以女性的贞洁与端庄作为评判标准。女子要遵循三从四德,以各种规矩约束住女性,而男性却没有以同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一点其实很多女性都产生过质疑与不满情绪。但是有一些女性被社会的所谓规矩蒙蔽后认命,而有一些女性则奋力向这样的社会规范发起冲击,向所谓的贞洁挑战。织云在瓦匠街上无疑是放纵的坏女人形象,连自己的父亲也骂她“小妖精”,她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贞洁概念,她只要自己的快乐。她既依靠六爷,同时也阿保有私情,当她被六爷打后,再企图诱惑五龙来满足对男性的挫败感。看到五龙惊愕的表情,她不屑地骂“没出息的货”。她葬送了阿保的性命,而自己无动于衷。在别人眼中,是她被男人玩弄,而在她自己的眼中,她以自己的方式玩弄着男人。而可惜的是,作为独特存在的生命个体,她的野性与放纵是不被社会认可的,而她不屑与蔑视的态度也招来了男权社会对她的放逐,她无法在瓦匠街立足,不得已委曲求全开始了依附男性的生活,最终以悲剧收场。织云悲剧的形成,不仅仅在于男人,更在于遭到了女性的唾弃。而与此不同的少数女性则是以直接挑战的方式撼动着男权社会的基石。最典型的代表是《才人武照》里的女皇武照。可以说,武照是中国历史上能够撼动男权社会的唯一女性。当她在天子那里受到几次耻辱后,“常常在天子之躯上闻到一股平庸的汗味”。她以非凡的思维逐渐意识到男性的平凡,而后宫红粉的灿烂与消逝也使她看清了女性在男性社会中的地位。她以她的智慧逐渐掌控了国家,以一种果敢地态度挑战并且颠覆男权社会中的种种规范,甚至压制住了自己的几个儿子,建立了自己的朝代。可以说,她已经逐渐接近成功。她不仅仅是女性形象,更代表了一种强者形象。她如此凌驾于男性群体之上,正如以前的男性群体凌驾于女性之上一样。但是她没有意识到,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男性凌驾于女性被认为是天经地义,而虽然现在她掌握了天下,但仍然是一个男权思想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她并没有建立一个女权社会,经受了千年封建思想熏陶的女性群体也并不是她强大的后盾。即使大家对她的才能心悦诚服,但并不代表能认同她至高无上的地位。可惜的是,身处高位的她,也被权利迷住了眼睛,并不能很清楚地认清形势。她也具有了男权社会掌权者的一些通病,过于强调自我意识,而忽略了其他群体,她的目的不是改变女性地位,而是不顾一切地稳固住个人地位。当她以如此盛的气焰操纵一切的时候,必将把男性群体的反抗意识推向最高峰。即使没有告密铜箱,没有张氏兄弟,她最终也只能以孤独的身影退出历史舞台。
相对于从感性角度对于女性的歌颂与认可来讲,苏童更倾向于因为女性弱势地位形成的家族女性悲剧生存而引发更为冷静的历史思考。女性之所以在长时期在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除了男权的压制之外,女性群体自身的原因也无法排除。作为男权社会中强势的一分子,苏童用超然而冷静的眼光认识着男权社会中的家族女性悲剧,在为她们扼腕叹息的同时,也不由地流露出一种悲凉。
参考文献
[1]赵树勤.找寻夏娃——中国当代女性文学透视【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199页。
[2]苏童.苏童作品精选【M】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3]陈龙.从解构到建构——论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渊源【J】当代外国文学,1995(03)
[4]林丹娅.女性话语的文学境遇【J】东南学术,20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