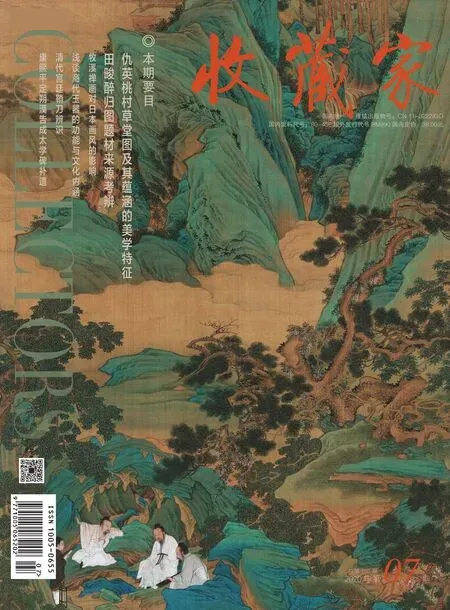融合之美
——北朝青瓷
2020-09-12姚颖
□ 姚颖
南北朝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段。这一时期,陶瓷工匠们通过不断改变釉料的配方,使得在早期并未完全成熟的“青瓷”得以成功烧制。相比较而言,河北地区制瓷业的发展较南方稍晚。北魏孝文帝494 年迁都洛阳之后,大大促进了北方民族的融合,吸引了大批南迁工匠的回归。东魏和北齐先后建都河北,这些回归工匠带回了南方地区越窑先进的青瓷烧造技术,这也迎来了北方青瓷烧造的辉煌时代。北方地区的巩义窑、相州窑、邢窑、磁州窑、淄博窑等窑口均成功创烧了北朝时期的青瓷,并在造型、釉色、装饰技法等各个方面形成自身鲜明的时代特色,取得了非凡成就。
2010 年初,南水北调文物考古发掘工作中,在河北省赞皇县西高村南的岗坡地,考古发掘了北朝赵郡李氏家族墓群,出土了随葬青瓷数十件,纪年明确,组合清晰,为北朝青瓷的典型代表。此外,河北景县封氏墓中出土的青釉瓷也为北朝青瓷中不可多得的精美器物。可为研究北朝青瓷研究提供例证。
工艺特征
北朝青瓷的坯体成型,主要是用快轮拉坯,底足部位采用旋削工艺,因技法十分纯熟,故器物造型普遍规整,足端削棱,形成倒角造型,制作干净利落。此外,还采用捏塑、模制等成型方法制作的坯体,注重实用性与艺术性的有机结合,无论是碗、杯、盘、豆、钵、盆等日用器皿,还是罐、瓶、尊等盛储类器物(图1、图2),皆呈现出厚重浑圆、粗犷质朴的风格,与南方青瓷那种清新、秀美的艺术面貌形成鲜明对比(图3)。纵观北朝青瓷,造型的设计理念和图像表现受到浓郁的域外影响,有些器物本身即是舶来品,有些则是吸收了域外设计因素的中国制品,均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贵实物证据。

图1 北朝晚期 葡萄纹双系扁壶
北朝青釉瓷器主要承袭了南方青瓷技术。但因原料产地不同,瓷胎与釉料含铁量不同,并受工艺配方、烧成技术等因素影响,北朝不同窑场烧造的青釉瓷器在釉色上也呈现出细微的差别。大多北朝青瓷的胎色深灰,釉面青翠晶透;邢窑胎色浅灰,釉色青绿;巩义窑因胎体原料的含铁量较低,故胎色白,釉色淡雅,釉面光润纯净,也称白胎青瓷。共性是普遍存在着积釉和开片现象。积釉部位往往釉层较厚,色调较深,甚至呈现黑褐色,带有强烈的玻璃质感。釉面开片现象较为明显,可见这一时期的胎釉结合不甚紧密,被认为是北朝青瓷典型的时代特色。(图4)
装饰上主要是胎装饰为主。所谓胎装饰,是指直接施于胎体表面的装饰。从使用的工具以及装饰技法上看,可分为刻划、浮雕等,图案清晰,布局规整,风格朴实。此外还有剔釉等装饰,技法娴熟,工艺独特。
刻划,是利用竹木类工具的尖端将图案花纹勾划在陶瓷胎体表面,然后罩釉烧成。因线条在釉下,故也称暗花。北朝早期瓷器上刻划装饰多为弦纹。较为多见的是在碗、盘、钵、盆的口沿部位刻划一道弦纹,而在瓶的颈、腹部位刻划数道弦纹。北朝后期开始出现刻划仰莲瓣纹与覆莲瓣纹,刻工精细,线条流畅,图案清晰。莲瓣纹的出现,说明佛教文化逐渐流行。

图2 东魏 青釉四系盘口壶

图3 南朝 青釉覆链唾壶

图4 北朝 青釉多足砚

图5 北朝 青釉鐎斗

图6 北朝 青釉长颈烛台

图7 北朝 青釉刻花莲瓣纹碗

图8 北齐 青釉唾壶

图9 北朝 青釉覆莲座插器

图10.1 北齐 磁州窑青釉刻覆莲纹盖罐

图10.2 北齐 磁州窑青釉刻覆莲纹盖罐顶部

图11 北齐 磁州窑青釉覆莲纹六系罐
赞皇李氏墓群出土的青釉灯、青釉盘和青釉唾壶都用到刻划的装饰工艺,器表只有简单的弦纹,其中青釉灯由灯台、灯柱和底座三部分组成,灯台呈碗形,中心立有一圆形管状灯柱。灯柱中空,外表装饰有一圈圈凸棱的弦纹。底盘为敞口平底,灯外施青釉,釉面开片,造型新颖美观,端庄大气。蜡烛大约在东汉前后出现,烛台就是伴随蜡烛而出现的,到三国时期开始出现了瓷质的烛台。这件青釉覆莲座烛台,釉色清亮,造型精美,莲花圆润饱满,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是表示纯净和断灭的一个主要佛教象征,代表“净土”,象征“纯洁”,寓意“吉祥”。(图6 ~图8)
同时出土的青釉盘,器形较小,盘腹较深,盘内底饰花叶暗花纹,胎体厚重,粗犷质朴,盘子的口沿部位刻划一道明显的弦纹。青釉圆盘的内壁满釉,釉层有强烈的玻璃质感。唾壶呈盘口束颈,扁圆腹,圈足呈外撇,颈、腹,肩部各有两道弦纹装饰。
浮雕装饰也在北朝青瓷中常见,浮雕是指凸起于瓷胎表面的立体图案雕刻。根据图案深浅程度的不同,又可分为浅浮雕和高浮雕。以青釉仰覆莲花尊最为典型,浮雕莲瓣纹普遍流行于北朝后期的磁州窑与淄博窑。除封氏墓出土的莲花尊外,赞皇李氏群墓中出土的青釉仰覆莲座插器(图9),也采用深刀雕刻,具有强烈的立体感,座上置一方托,拖上有长方形横梁,上承五个长方形的敛口深腹杯(残缺一个),胎为浅灰色,坚致细腻,釉色清脆,釉层薄而透明,有细密的开片纹,造型别致,底部浮雕的莲瓣圆润饱满,雕刻刀法流畅,工艺精湛。莲瓣精雕细琢,朵朵圆润饱满,如雨氤氲里在水一方的冷美人,“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简单的构图,却生出丰富意蕴,让人称奇回味!雕刻的实与虚之间,多种对比手法的运用,不仅使其形式变化丰富,其审美意蕴亦非常充盈,极有张力。
河南偃师市杏园村北魏孝昌二年染华墓出土的蟾蜍插座,与其年代相同,上半部分几乎完全一样,只是器座不同。另外,1978 年磁县大冢营村东魏武定八年(550)茹茹公主墓出土的仰莲瓣纹器盖及1982 年淄博市淄川区龙泉镇和庄石室墓出土的青釉莲花尊也比较典型,莲瓣凸起,呈现立体状态,凝釉处釉色碧绿,十分美观,显示了高超娴熟的装饰工艺技巧。
剔釉,是指器物成型挂釉后,在未干之前勾勒出图案,然后剔掉多余部位,再经高温烧制而成。如青釉托盘,托盘中的莲花图案采用剔刻法,剔除掉莲花周围的泥坯,留出莲花的图案,这种因剔釉露胎而形成的凹弦纹,与北魏洛阳大市遗址出土瓷器的装饰技法完全一致,也与西方玻璃器有着相似之处,独具匠心,颇具北朝釉色特色。
寨里窑、相州窑及其他
北朝青瓷烧制广泛,存量也不少,但是能确定其窑口的并不多。目前唯有淄川青瓷产品可确认其窑口。1976 ~1977 年,淄博陶瓷史编写组及省市博物馆对淄博寨里窑的复查和试掘中,发现了一件贴花器的残片,推测为尊的上腹部,装饰堆贴花,纹样有莲花、宝相花、宝塔、双系处联珠人面等,因此,与此尊出土地相距10 公里处的淄川寨里窑可认定为莲花尊的产地。
寨里窑位于淄博市淄川城东约10 余公里,年代为北齐时期。它是在以北沈马遗址为代表的古代陶器数千年烧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我国北方最早的青瓷窑址。寨里窑器物造型优美,装饰典雅,全身施青釉,釉薄而均匀,釉色青中泛黄,光亮莹润,华贵之气盎然。出土的青瓷莲花尊花纹趋于细密,莲花纹和其它花纹并重,莲花为一叶双瓣式,宝相花、忍冬花纹与莲瓣争雄。以花纹精细,雕刻与模印堆贴等装饰方法共用的特征,与其它莲花尊相比,纹饰更加精美。国家文物局鉴定其为国家一级文物。
此外,相州窑也是北方青瓷窑口。北齐时期,河北地区佛教非常兴盛,磁县响堂山造像、邺城造像都是那时期的。相州窑,在河南安阳与河北交界处,北魏和北齐时曾经辉煌一时。当时佛教兴盛,寺庙林立,民间里很多百姓信仰佛教,因而促成大量佛教色彩的器具和雕塑品出现。陶瓷鉴定专家丘小君就认为,相州窑烧制的也有青釉莲花尊。
磁州窑也出土了一些青瓷制品。如北齐青釉刻覆莲纹盖罐,质粗厚重,施青黄釉,盖上有桃形纽,盖面有覆莲瓣八片,下有凸弦纹二道,罐口侈,沿外卷,肩部有覆莲八片,下有凸弦纹二道。东魏时期的青釉覆莲六系罐,则通体施青釉直口,口颈相连,口以下渐广至腹部内收,肩部有六系,腹部中央装饰有覆莲花瓣,莲瓣微翘,釉不到底。将这些青釉瓷与赞皇李氏墓出土青釉瓷比较研究,发现釉的发色和施釉的方法有明显不同之处,虽有专家猜测为同为磁州窑烧制的产品,但仍需进一步考古资料来印证。(图10、图11)
再如河北境内的邢窑也在北朝时期开始烧造瓷器,在邢台内丘出土的青釉龙柄壶,由出土地层推断,年代为北朝后期到隋代。壶身整体施半釉,胎体呈灰色,与赞皇李氏墓出土的青釉瓷的特征不太相符,由相近器型的鸡首龙柄壶比较可以看出,不能为同一窑口产品。故此关于这批青釉的确切窑口产地问题,仍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及研究考证。(图12、图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