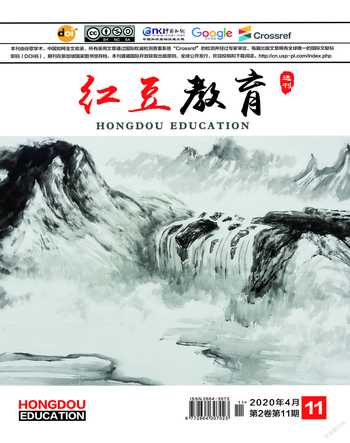聚讼纷纭
2020-09-10鲍相志
一、研究的历史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别号为香光居士,是明代松江华亭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从一品)。为明代著名书画家,其著有《容台集》、《画禅室随笔》等。
作为我国艺术史和艺术理论方面无法回避的人物,对董其昌的研究一直是中国艺术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在清代董其昌的艺术因为康熙皇帝的喜爱与推崇,凡有志于科举的士子无不学习董书。董其昌的门人后学通过著书立说、鉴赏题跋、交游唱和等活动,不断继承、阐发董其昌的艺术理论。直到戊戌变法以前,董氏的书画理论都基本居于主流地位而未受到大的质疑。
董其昌第一次真正受到大的冲击是因为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康有为继承了包世成对董其昌书法的批判,以碑学中兴旗手的身份,认为董其昌虽然名声显赫,但是书法软弱无力,缺乏大气象和丈夫气,名不副实。从此,伴随着西风东渐和社会变革,董其昌的艺术和理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判。
当时,由于国运衰败和西方艺术的传播与影响扩大,董其昌的艺术理论和艺术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攻击与质疑。在这一片讨伐声中,以徐悲鸿的意见最具代表性,也最为激进。他认为其实天分极为普通,他的艺术理论和作品的推崇,实际上把中国画带入到难以为继的境地。之后又有滕固、童书业、俞剑华、启功等等一批学者相继著文批判“南北宗论”,他们大都从实证的角度,指责“南北宗论”不符合画史的史实,有相当大的主观臆断成分。同时期的宗白华、徐复观等学者却比较客观地评价了董其昌的艺术成就,指出了董其昌的理论在中国艺术史上的非凡意义,为其辩护,但当时对董氏理论的批判已成主流。
然而在此期间,由于中国艺术品和艺术书籍的对外传播,董其昌的艺术和理论引起了海外学者的极大兴趣,尤其是在日本,出于对中国文人画的欣赏,出现了内藤湖南、田中丰藏、古原宏伸、神田喜一郎等等一大批研究董其昌的学者,他们大都汉学功底深厚,有比较出色的鉴赏水准。而在欧美艺术史研究圈中,像高居翰、方闻、张子宁、傅申等学者都对董其昌有過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哈佛大学东方艺术史系的李慧闻博士更是倾毕生之力专研董其昌近四十年之久。还有杜维明、张少康等学者虽非这一领域的专家,但也偶有独辟蹊径的卓见。
改革开放以后,董其昌的艺术和理论重新得到重视,王伯敏、薛永年等老一辈学者开始把董其昌放到大的历史环境中去重估他的理论价值。国内于1989年在上海松江(董其昌的故乡)举办了“董其昌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大批海内外著名学者。此后每隔几年便会在世界各地举办有关董其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议。最近一次影响比较大的国际会议是2008年由澳门艺术博物馆与上海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联袂在澳门举办的董其昌国际讨论会。
二、研究的方向
纵观国内外几十年来的有关董其昌专题研究的论文,所讨论的问题多围绕以下几个方面:
1、有关《画说》作者的归属问题,即有关中国绘画史上“南北分宗”说的首倡者问题。这虽然是自民国以来就争论不休的历史遗留问题,然而却至今悬而未决。由于董其昌其他有关气韵、笔墨等等的艺术观念都建立在“南北宗论”之上,所以首倡者是谁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直接影响到董其昌在中国艺术史上的理论地位。
余绍宋最早在1932年出版《书画书录解题》时为《画说》一书的作者指出了两种可能。他认为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其实董其昌和莫是龙都有可能是南北宗论的提出者,而且两个人处于同时代,关系又很亲密,实际上很难判断到底是谁先提出了这样的风格分类学说。
后世学者由此分为两派,早期学者大都持莫是龙首创,董其昌发扬光大的观点,代表人物有童书业和俞剑华两位学者。童书业在《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新考》考证了是莫是龙提出,后来俞剑华在1963出版的《中国山水画的南北宗论》一书中亦采用此说。
徐复观在其1966年出版的《中国艺术精神》中首次反驳了前两位学者的观点,他经过详细的比对,认为莫是龙的《画说》全部抄录自董其昌收入在《容台集·别集》里的《画旨》,而且《画说》很可能是后人东拼西凑假借名目以求销售的伪书,分析得十分透彻。
当代的傅申、汪世清和古原宏伸三位学者是将南北宗论的创说权归至董其昌名下的代表人物,尤其是傅申先生治学严谨,考订周翔,遂使“南北宗论”为董其昌首创的说法逐渐成为主流。
2、董其昌的美学思想和艺术主张及其影响研究。这类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⑴、董其昌艺术思想的渊源和内涵研究。有的论文从阳明心学和禅宗观念的角度探寻董其昌艺术思想的来源,如姚东一的《论禅宗思想对董其昌山水画的影响》、朱良志的《论董其昌画学的心学色彩》、贾云娣的《董其昌书画禅实践与理论研究》;有的论文则分别从董其昌艺术思想当中的某一点切入,如陈靖的《淡董其昌书法艺术的特色与境界》、王志伟的《董其昌的“明暗”说研究》、何毅的《董其昌“以书入画”现象研究》等等。
⑵、董其昌的生平、家世、政治活动、交游等等方面的实证研究,并通过这些方面的史料来考察董其昌的思想理论来源、影响及其传播。这类研究多通过文献资料、传世作品等来考证董其昌的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如吴耀明的《董其昌的生平和家世述论》、颜晓军的《董其昌杭州诸问题综考》、江雯的《董其昌与公安派的交游》等等。
⑶、董其昌艺术思想与其书画创作、收藏等活动之间的关系研究。这类论文主要运用形式分析和图像学的方法,从作品入手,归纳董其昌的书画艺术风格并将之与其艺术理论相印证。如颜晓军的《宇宙在乎手董其昌画禅室里的艺术鉴赏活动》、胡颖冰的《董其昌山水画抽象性研究》、姜畅的《行云流水下的温敦淡荡谈董其昌书画中的笔墨情怀》等等。
三、董其昌艺术理论研究的难点及局限性
虽然近40年来,有无数的相关领域的学者针对董其昌进行了各方面卓有成效的研究,但从目前的相关成果来看,董其昌研究呈现出研究难点与研究局限性互相交织的特点:
1、先入为主,有过主观价值判断以后再来寻找资料求证自己的观点
这类研究误区比较常见的原因是,几乎所有的研究董其昌艺术理论的研究者首先面对的就是“站队”问题,这在有关“南北宗论”的研究中尤为明显。研究者究竟如何看待“南北宗论”,如果你不先进行立场选择就几乎无法继续研究,从而导致此类的研究陷入了一个这样的怪圈,那就是双方学者都有自己的理论和事实依据,永远争论下去,没有定论。站在文人艺术发展立场上的学者和站在技法至上主义一方的学者永远难以达成共识。
比较明显的例子比如知名董其昌研究者古原宏伸的《论后世对董其昌的评价》一文中,他引用王石谷《清晖绘言》和王原祁《王奉常题跋》当中对董其昌忽视的段落,来证明这是董其昌的传人对董其昌艺术无言的批判。然而古原宏伸也一定知道对董其昌最过誉的评价“犹文起八代之衰”就是王原祁说的,而且大量的文献可以佐证“四王”一派对董其昌的推崇备至。他同样应该知道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当时的情境、作品等因素都会影响艺术家对画作的题跋。历史的终极目的是要“复活”人类的往昔,作为一个艺术史家尤其应该谨慎的是,我们运用任何言论性的文献佐证自己观点的时候,都应该抓住言论的“主流”而非“支流”,同时还要把这些言论还原到当时的情境当中去,以体察其本意,如此我们的观点才显得有说服力。
2、学者们大都重视文献考证而轻视图像研究
尽管瓦尔堡的图像学方法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但我国董其昌研究者重文轻图的倾向依然没有太大的改变。董其昌研究重文轻图的背后其实是这样一个研究难点,即董氏传世的绘画和书法作品当中有太多是代笔和伪作,这使得研究者不太情愿引入图像的证据,因为一旦引用失误,即使有生花妙笔也难以挽回其研究不入行家眼的结局。例如颜晓军的博士论文《宇宙在乎手董其昌画禅室里的艺术鉴赏活动》中就收入了一幅明顯为伪作的董其昌书法作品。
四、董其昌研究的展望:
回望整个20世纪的董其昌研究,无论是中国的学者童书业、滕固、薛永年还是西方的方闻、高居翰等,他们其实是都把董其昌艺术以及其理论的出现看作是中国艺术史上的典型的转型个案来论述的,在董其昌之前,没有如此的艺术风格和理论,而在董其昌以后的书画艺术,又很难不受他的影响,也就是说无论是批评还是认同,对于他本人的影响力都给予了承认。这样的研究其实已经人为地把董其昌当成一个节点,忽视了他之前的各种文人画理论所做的铺垫。董其昌在明代后期提出了南北宗论,而晚明是一个文人士大夫审美逐渐成为主流的时代,比如汤显祖创作的文人戏剧“临川四梦”和文震亨的园艺代表作《长物志》等,文人开始自觉积极地参与到艺术作品的创作和改造当中,并把他们的艺术理想付诸实践。尤其是书画艺术,无论是苏轼的绘画理论还是元四家的技术成熟,都成为了董氏理论提出的思想和物质铺垫,他的理论完全反映了时代脉搏和方向,所以自然而然地能够取得统治地位。
对于董氏理论的文献研究已经相当成熟,但显然我们对文献和图像文本的综合研究还很不够。董其昌除了他和同时代以及后学留下的巨大文字资料以外,那些流传作品和相关的题跋、收藏活动、笔记的互文关系,还鲜少有人探究。这些资料是如此丰富和鲜活,可以反映时代艺术思想的流变细节。对这些资料,我们应该充分梳理,董其昌的研究不应该局限于他本人和他的时代,而是应该把视野扩大到董其昌之外来阐释他的意义。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考察董其昌艺术理论的传播,包括对其传播者、传播方式、途径和场景的研究,是想通过这样一个经典的个案,来考察艺术理论是如何被接受从而影响艺术发展的,即他的理论的“赋权”过程。这样的问题值得被重视。传播不仅仅传达意义,在传播过程中也会产生新的意义,事实上董氏理论的每一次传播都留下了传播者的精神轨迹。比起董氏的理论是不是“正确的理论”,我更关心它是如何成为“正确”或“谬误”的。没有任何一种艺术理论可以完美无瑕地解释所有艺术现象,但有一些理论为什么格外流行,这恰恰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参考文献:
[1]潘运告编:《明代画论》,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
[2]黄专、严善錞:《文人画的趣味、图式与价值》,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
[3]范景中:《图像与观念》,岭南美术出版社,1992年。
[4]阮璞:《中国画史论辨》,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
[5]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
[6]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
[7]张连、[日]古原宏伸编:《文人画与南北宗论文汇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年。
[8]俞剑华:《中国山水画的南北宗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
[9]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
[10]任道斌:《董其昌系年》,文物出版社,1988年。
[11]滕固:《滕固艺术文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
[12]《朵云》编辑部编:《董其昌研究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
作者简介:鲍相志,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职称: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书画鉴定。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