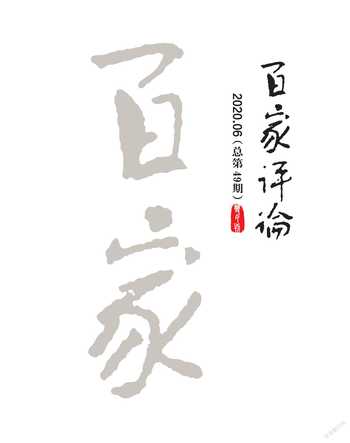死亡——消失的力量
2020-09-10梁翠丽李焯炜
梁翠丽 李焯炜
内容提要:东涯诗歌如同站在海岸线上的修行人,以冷静的视角从海平面掠去,在对生命感知的基础上,透出其深层体认与感悟。她诗歌体现出较为鲜明的“死亡”意象。这些意象有“生”艰难,有“死”的悲悯,更有冷静地觉察与思考。诗歌以沿海渔民生活为基础背景,扩大到生命各个层面。不同事件,同一母题——死亡。诗歌中的“死亡元素”就像一幅黑白木版画一般,令读者在静置的画面中,思考生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死亡意象 向死而生 死生同体
东涯,山东荣成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26届青春诗会成员。山东省诗歌创作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研讨的“山东青年诗群”代表诗人,以其海边和海边岁月为背景的写作探索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著有诗集《侧面的海》、《山峦也懂得静默》、《泅渡与邂逅》等。作品散见《诗刊》等报刊,每年均有 作品入选中国作协创研部、诗刊社、《诗探索》杂志以及国内多种机构编选的年度诗歌精选和跨年度选本,曾获泰山文学奖、《青年文学》诗歌奖、新世纪山东优秀诗集奖等奖项。
注意到她的诗歌,源自她诗集《侧面的海》。诗歌浓郁的死亡意象,透过生活表面的真实直抵内在,构建了独具特色的个体智慧,呈现出生命异质性的思索,生发出迥然不同的生命力量,令人叹为观止。
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说,东涯诗歌的“死亡意象”呈现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对死亡事件的体认,强烈的疼痛感是诗歌的主要特点;二是向死而生的生命关怀,在揭开死亡真相的同时,给予了生的力量;三是挖掘了死亡的诗性内涵,采用时间与空间的轮回与停顿、梦境与现实的转换、死亡与生命共时存在,呈现一种万物共生的阔达的精神走向,实现了哲学高度的精神返乡。
一、死亡事件的体认
东涯诗歌首先从触碰到死亡事件入手,表达了死亡给读者带来的最为真切的情感体验,实现主客体共鸣。
“在不幸的源头,总有一桩意外——/海浪的舌尖吻过弄海的人/ 这是一种古老的接纳/飞翔的海鸥因真相而悲鸣”
“捡浮水的女人多了起来/修假坟的女人多了起来/海水苦咸,浪花漂泊/哪一朵,才是无家可归的水手”
“海水茫茫,不断上身的雾气/模糊了海岛的眼睛——/等候的名单上,失踪者/还会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
——(《侧面的海》第13页)
这是一个典型的“海难”场景。诗人用“海浪的舌尖”、“吻”意象反转的语词,表达死亡的无奈、沉郁、伤痛。用语简介,情感内敛,画面感却极强,所有的悲伤都浮现眼前。那些逝去的鲜活的生命,可能是诗人的邻居,也可能是熟悉的陌生人,诗人见证了生命瞬间即逝的事实,却无力改变,心中难免生发生命无常的伤感,这是作者对死亡带来情感颠覆的最真切体认。
疼痛的疗愈,需要时间,更需要面对的勇气。诗人为了安慰那些痛失亲人的渔民,写到:
“其实他们只是去长途旅行/当海潮褪尽,螃蟹/吐着泡沫穿梭在沙滩上/他们趟着渔火,与我们擦肩而过/却不为我们所知”
——(《侧面的海》第13页)
以海为背景,用“螃蟹”作为意象,表达了死亡玄幻而神秘体验,反射的是死亡创伤之后情感的牵绊,并从中寄寓自我剝离。这种剥离,是个体的,也期冀于群体。
诗人也意识到:与消失了的生命一同消失的不仅有寄予了所有喜怒哀乐、寄予了情感意义的亲人,还有鲜活的爱与温热、彼此存在的时间。这些非常真实的疼痛,诗人感同身受。
“说起忧伤,海誓山盟/不再属于爱情,过世的亲人/他们!流水一样从山脊消失/留下刀切的断面——/我必须持续地忍住疼痛/忍住被拿走的虚空”(《侧面的海》第9页)
诗人用“流水”表达了失去,“刀切的断面”表达的是感情断裂,“虚空”则极言内在力量的缺失,表达了情感剥离时锥心的疼痛。
每个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都是从一件事一件事始,从一个情绪一个情绪中辨识。强烈的情感冲击带来的必定是思想波的高速运转,运转的结果,因思考个体不同而产生千差万别的外部镜像。这些景象的出现,必定暗合了思考者某些固有的意识。
带着死亡带来情感体验与心理恐惧,作者将思考深入了更渺远的内在,诗歌有了明显哲学意义。
“来吧,我的爱/让我们在寂静的冬天唱一首歌/献给大地上的流浪者,老人和孩子/献给太平洋的海水、船只/葬身海底的生命/献给落日,献给旗帜,献给/折戟沉沙的心灵。也献给你,我的爱/时光如流水不舍昼夜/我们什么也没有失去,只有拥有”(东涯:《献歌》《侧面的海》第42页)
诗人以“爱”为礼物,给予生命所有的存在。用“寂静的冬天” 表达出死亡静默的忧伤;用“大地上的流浪者、孩子、海水,船只、落日、旗帜,折戟沉沙的心灵、不舍昼夜的流水”等意象,面对时光,背对死亡,进行了内外的辩证统一,给出了思考后的结果:消失的也是我们拥有的,生命从来不增不减。这已经颇有禅学意蕴了。
在原生态的世界中,各种生命都被赋予了种种力量。死亡,融合了生命的潜力,是世间存在的模式之一。有生必定有死,有幼必定有长,自然界彼此观照,此消彼长,生命因此多元而饱满,死亡具有与生存一样灯亮的价值与力量,没有什么会真正消失,所有存在都值得珍重以待。
对于死亡的多重理解与体认,东涯诗歌呈现出阔达、清亮的意识走向。死亡作为参照的生活,是人类有限生命的最好见证,她因之实现了死亡在时间意义上的生命推演,化腐朽为神奇,以充满力量的平实,接纳生命中劈面而来的种种,在持续前进中转换心智模式,提升个体维度,调适个人情感,接纳与拥抱各种生命境况。
“谢谢你,人间的爱/从无到有,从此岸到彼岸/从赶小海的女人 到海上孤魂/你抚慰每一滴水,每一颗破碎的心/也谢谢你,无常的灾难/使世上生命变得具体起来”
——(《侧面的海》第24页)
“无常的灾难”,恰好是“生命具体”的对镜。东涯的感谢中蕴含了对“永生”概念的解读,“永生实际上是另一种死亡,另一种更彻底更本质的死亡,只有死才能赋予生以意义和价值。”如此,这“感谢”既是对逝者的“安魂”,也是对生者的鼓舞。
“一切使我们变大的感情都在世界中安排我们的处境。”东涯以诗歌为舟,泅渡生命的汪洋,并获得了具有面对风浪的涌起和信心。
“章鱼:一截截被斩断的腿/在习惯的跑道上惶惶然地蠕动/它肯定隐隐作疼仿佛地震后的废墟说不清哪里塌陷仿佛废墟下活过来的人/生的灯火曾由死来点燃”
——(《侧面的海》第65页)
“生的灯火曾由死来点燃”,显然,她已经获得了某种确定的力量。
二、向死而生的生命关怀
死亡,是时间有限性的表达。人们往往感知到存在结束时,生命的本真才彻底凸现出来。然而,真实的情况是,每个人都知道属于自身生命的限制,却并不知道确切结束的时间。生命的隐秘里,暗藏着人们对自身时间拥有长度的恐惧。拒绝谈及死亡或者回避死亡,不能改变人类消逝的命运。人们痛苦,往往因为消逝了的事物带走的不仅仅是事物本身,还有赖以存在的情感体验。抽走了那部分情感,成为心灵创伤,长久地捆绑着失去亲人的人们,甚至为此丢掉自己一生拥有的有效时间。
东涯起底生活,以诗歌搭起生与死的桥梁,不规避死亡,不漠视存在,单刀直入,把所有外向的指证主动转化为自身生命思考,在自我端详中,对生命困惑进行了纾解,主动选择承担“此在”命运的种种,面对、接纳、珍惜。
“谁的心里没有苦涩呢/生活在海边的人/早已学会对自己心怀敬意/必须向岩石学习抗击技术/像海浪那样承受破碎/学会忍受想章鱼那样白纱似的眼皮/享受风浪过后的宁静”
——(《侧面的海》第32页)
用“岩石”表达了坚强,用“海浪”表达破碎的现实,用“章鱼”暗喻生活的不幸,诗人告诉人们“学会对自己心怀敬意”。这些意象,都带有强有力的抚慰色彩,为悲伤的人们拓宽了视野,注入再生的心流,诗歌昂扬的生机,扑面而来。
生活中很多烦恼并不是事情本身,而是对事情未知结局的恐惧。东涯诗歌的魅力在于用文字做出先行的决断,帮助人们直面死亡的现实,领悟真实的此在,承担了真实的世界里所有的喜怒哀乐。这时的个体,相比于那个曾经沉沦于日复一日重复生活又遗忘了本真的自己来说,是慈悲,是双重的真。
她说:“海岛周围泊满船只,有人从这里启程/带走海草暗昧的气息/很多年了,他们中一些人再也没有回来……/白鹭在海面低飞,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虚无随着云雾升腾——/小镇浮在海面上/我们浮在人世间”
——(《侧面的海》第7页)
“小镇浮在海面上/我们浮在人世间。”这就是我们最真实的生 命状态,虚实并存,如梦似幻,“就像露易·哈斯所说,在一个无穷无尽的时间里,所有的事情都会发生在一个人身上。”
她理清了这样一种关系:死亡,是确准的存在,一个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存在,是时间线上的一种状态描述,与生存一样具体可感。
认清这种真实,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从死亡的背影中跳脱出来,坚强而温和地面对生活。
“大雪铺满道路又有什么关系/倚窗望雪,或者/堆一个无所不能的雪人/戴高帽,以凛然之态睥睨天地万物——”
“不幸的生活变得幸福起来——/羊群,蚂蚁,苜蓿草……/这些活在低处的/朋友,与我一起守住落日/守住一个温厚发光的词”
——(《侧面的海》第71页)
诗句使用“雪”表达了生活中的不幸,而应釆取的态度是“堆雪人”、“睥睨天地万物”,这样的态度,即使遇到生活的不幸,也可以“变得幸福起来”;用“羊群,蚂蚁,苜蓿草”等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存在,表达了生命并不孤单,天地间的一切,都会与自己一同面对“落日”——日渐走向消亡的事物,要保有的心态是“温厚发光”。
诗歌流淌出坦然面对的冷静,虽有死亡的印记,却没有死亡的消沉,这是东涯诗歌心灵重构的重要通道,是生命维度增加和密度提纯的方法。在死亡背景中注视着生,她已走出时间的局限,走向更广阔的空间。
于此,她扩大了死亡的边界。生活中小小的伤害,偶然的失明现象,梦的中断与缺失等,都意味着断流与消失,是死亡的另外一种形式。对这样的现实,有了更多的体谅与包容。“何必对这些心怀暗疾——/既然生活是伟大的失眠/既然生活对一切都犯有过错”《侧面的海》第45页);对掌中的风景——现有的生活,有了饱满的热望,尽管死亡的信息,就好像飞鸟一般,划过天空,时时出现在眼前,而鲜活的生活更让她珍惜与期待。因为每一种存在都“仿佛杜尚的/日用品,放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每一个,都是孤品”(《侧面的海》第30页)存在的价值,不言而喻。
“我依旧喜欢我们的黄昏和海水/可我刚写到黄昏,黄昏/就已远去,随着飞鸟的翅膀消失在隔壁的群山中
新的生活需要新的规划/在你复活之前,我要遍访世界各地/让我们的海岛再没有幸与不幸的符号”
——(《侧面的海》第65页)
向死而生,东涯诗歌有了质的飞跃。精神的沃野借助死亡的肌理,走向多向度。生命的温热在掌中延伸,成为心灵诗意的聚居地,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生命浪潮,说生活在人世间,最合适的方式依旧是敞开怀抱,“抱团取暖的方式/只能是,用心地爱,无心地伤害”(《侧面的海》第59页)
三、发掘死亡的诗性内涵
詩性是世界的本体。海德格尔说,诗化并不把人带入想入非非,遁入幻想或梦境,相反,诗化把人引入大地恬然悦乐地栖居。
东涯解构了生命的内在本质,从精神上对个体进行了超高的解读。她诗歌的高空之气,似一剂清凉剂,带着读者俯瞰人世间的繁华与衰败,看到生命的局限与广阔,高纬度地呈现了诗性内涵。
首先,有了死生同体的生命觉知,这是涵盖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表达。每一样事物当下就是事物的全部,芥子藏须弥,就可以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爱心珍视当下。长天莫及,当下易见。
“阿婆在藤椅里打盹/正午的阳光/把她的灰布棉衣/洗得像晚年一样发白/
她撑开松垮的眼皮/脸上皱纹堆积如山/一片落叶飞过/她曾经汹涌的河床”
——(《侧面的海》第16页)
诗歌里的“阿婆”是寄予了“过去-现在-未来”概念的实体,“灰布棉衣”“松垮的眼皮”“堆积如山的皱纹”都是时间的表征。
“阿婆”并非初生婴儿,是个体生命走向消亡的标志,承载了生与死, 存在与消失,意象叠加,一体两面,合二为一。
诗人情感内敛,控笔严格,只是勾勒了一幅画面,告诉人们所有事物都如“阿婆”一样,走在死亡或者正在死亡的路上,事物即生即灭,存在的本真便是如此。在这个基础上,人生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消弭。人,可以诗意栖居。死亡,也是诗性的一部分。
二是冲撞带来相生相克的和谐。东涯诗歌语境中的冲撞意象比比皆是,这些意象表达的是,无论是内在冲突还是外在冲突,都是自然性的本真表达。个体省察到的痛苦与哀伤,是内在冲突的外在展示。基于自然本体属性,冲突是运动与生长的动力,是万事万物运行的法则,是事物最本质的存在。这些存在,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是最为普通不过的日常。死亡,是以冲撞的对立面现身的,没有死亡的提醒,没有疼痛的觉知,生命如同虚幻,很难感受自身存在。
东涯诗歌表达了这样的宇宙观。
“照片上的女人,年轻清秀/男人的悲伤弥散了/整个屋子,三岁的儿子趴在地上玩弹子/笑嘻嘻地看着每个人/在这间屋子里,死亡/黑色的尖刺/与童年的幸福不期而遇”
——(《侧面的海》第52页)
诗歌用“黑色”、“尖刺”指向了死亡,与之对立的是三岁孩童“玩弹子”、“笑嘻嘻”这些属于孩子生机勃郁的意象。镜像式的冲撞被安排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好像一幅画的正反两面,生死视觉的对比,带来强大的冲击。读者看到的是,死亡的悲伤与生命的继往开来,都只是宇宙最自然不过的存在。画面并不突兀,反而有一种说不上的平静与和谐。
诗歌中也有这样的冲撞:“我喜欢这个词 横空/出世。/像银色的鞭子/把黑暗的天空抽成破裂的蛋壳/——孵化出真理”
——(《侧面的海》第55页)
如果说“横空出世”是一种再生的力量,那么这个力量的源泉来自力的运转:天空被抽成破裂的蛋壳,却因此孵化出“真理”。
“哦,我喜欢入殓师/的表情,世俗中最后的慰藉。/多么温暖——/我喜欢所有温暖的事物:牛车上的阳光。母亲/在村头的凝望/亲人的 拥抱/爱情里小小的阴谋/垂暮时光/临终的眼……就像我”
——(《侧面的海》第17页)
“入殓师”是死亡的符号,与之相对应的是人世间的温暖。这些温暖就像“垂暮的时光”,就像“临终的眼”,以死亡的意象表达了生的愿景。
诗人以内在的驱动力,冲破了生死局限,用对比冲撞的力量,平和地挂出世相图,道出生命本质不过是生死相克中的和谐生成。生生之谓易,恒存之谓道。以此,为活着带来温暖,为死去抚平伤痕。
三是变异生成的意识重构。人,只有从内心深处重新组建个体意识,才能对外界产生新的认知;同样,外在世界的磨砺也是产生内在变化的动力。它们互为表里,对人的思维及行为产生关键性的影响。
东涯诗歌主动接受生命中的变异现象,就像迎风而起的海潮一般,顺势而为,借力打力,通过生活的体验,实现了自我蜕变与重生,也昭显了诗歌的力量。
变异,实际上是改变正常路径,是以打碎后的重组为前提的再生。死亡意象,对于人们如常的生而言,本就意味着变异。在东涯诗歌中,变异只是手段,突围是策略,重生才是目的。东涯的重生,是基于哲学意义上的生命思考,表现出来的则是物我两忘的超然与旷达。
“人世间已没有什么我想拥有/明天,我就是这山,这水/这自然的 一部分/那条清澈的河流等在大地尽头”
——(《侧面的海》第92页)
诗人把自己当做山,水,当做自然的一部分,同归于天地间。由人的诗性,转化为超自然的神的诗性。意识的跃迁,显而易见。
“我不悲秋。就是想看看/我最后的美丽是什么样子:看看星子/落下来燃烧的表情:就是想听听/秋风吟唱安魂曲”
——(《侧面的海》第103页)
心平气和地说话,本就是一种气息带动、情绪抚慰,对于生命中无法规避的苦难而言,无疑是一曲“安魂曲”。
心灵的转换,对日常存在的关注便有了别样的感知。温暖,如坊间的太阳,从诗人的笔端流出。而渔村的生活,再次成为诗人的关注点。小而暖的人间况味,如一副画面挂在了读者面前。
“遮阳帽上,粉红的碎花/极弄着她此刻的心情/女人一边织网,/一边怀想/
她偶尔扰一下露在外面的头发/抬头看看蓝天,碧海/身边的小狗, 远处的渔船”
——(《侧面的海》第11页)
诗歌借助“遮阳帽”、“碎花”、“织网的女人”、“小狗”、“渔船”等沿海生活的景象,表达了诗人实现了自我突破与意识躍迁之后,感受到的日常生活的温暖与恬静。
东涯诗歌从死亡入手,经历“体认死亡、认知死亡面对死亡、超越死亡、蜕变重生与善待生命的圆形逻辑路径,最终以热爱朴素之美,“抵达了精神与诗歌世界的辽阔,几乎呈现为海平线上无限的潮涌”。
——(《侧面的海》第5页)
东涯通过诗歌死亡意象触摸了生命“存在”的本质,内在日愈深邃、笃厚,实现了以内在统摄外在,达到了智知凝于内、引心以化外物的哲学高度,以诗为舟,“驶向心灵的乌托邦”,而终于至“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生命境界。
(作者单位:山东威海海洋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