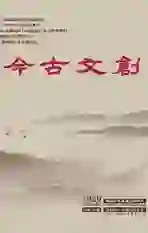奥登《见证者》细读赏析
2020-09-10谌盼
谌盼
【摘要】 20世纪英国著名诗人W · H · 奥登创作的诸多诗篇风格独特,其“诗体实验”吸引了诸多研究者的关注,本文主要使用新批评提倡的“细读法”来理解《见证者》这首内涵丰富的诗,对其进行语义和结构的分析。在细读过程中发现了奥登诗歌精炼的叙述中具有很大的阐释空间,其主题上也有着新批评学派主张的“张力”的美学特征。
【关键词】 奥登;见证者;张力;细读
【中图分类号】J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9-0015-02
一、被“见证”者:被动和不安
诗人在首段中,用“不安分的头颅”这一具体意象,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年轻人”有心事而难以入眠的焦灼不安,枕头本来只是被动地充当人的寝具,诗中却特别指出,卧枕“无法安顿”头颅,仿佛这客观存在的物体对人的失眠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接下来,“抽签”的主体被省略,更凸显了人的不知所措,关于即将到来的命运,“年轻人”什么也做不了,只能被动地等待宣判,这些解释并加剧了开头所说“辗转反侧”的状态。面对离家远行时那可想见的“危险和痛楚”,他们一遍遍追问不幸是否会降临在自身。诗开篇的“年轻人”既可能是一个一般泛化的指称,也可以是有具体的指称对象的,可能是指诗人看到自己年轻的伴侣陷入对未知的彷徨时欲表达的关心和理解。“会是我么?会是我么?”以不同字体呈现,从戏剧独白诗的角度来看,相当于合唱队功能,把人类看作舞台结构中的受话对象和背景,针对前文做出提问。
接下来诗人却揭示,所谓的抽签、疑问都不过是掩人耳目的烟幕弹,命运的走向其实就在他们各自的内心。这里用到了几个巧妙的比喻:心灵如聪明的魔术师或舞者——魔术师有许多变戏法的手段,他最擅长的就是用障眼法迷惑观众,使其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至于舞者,则需编排好一系列舞蹈动作,表演时也常常给人以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之感,这些都是经过选择的形象,如果心灵想隐藏某些秘密,同样需要想出各种合理的解释和借口,去说服自己,也使别人信服,于是就会出现“欺骗”行为。这几行诗具有复义的效果,“欺骗”“奇巧花招”自然能指魔术师或舞者的魔术、舞蹈的表演性质,但同时也能阐明当人想掩饰内心真实欲望想法时的自欺欺人。诗人紧接着以“动机如偷渡客”转入了一种无情的讽刺,即任你如何用尽心思,多么冠冕堂皇和理直气壮,也只是欲蓋弥彰,你那不愿为人所知的勃勃野心和“犯罪动机”,就像非法偷渡的行径,不可能永远不被人发现。结合上节对恋人关系的猜测性理解,这部分可理解为不安分的人迟早下定决心做出改变,而互相依恋的关系也面临着解体。这节诗末尾,仍然可看作是合唱队旁观着代替人类进一步地发问。
然后,诗人用一个个“应该”似乎给了那辗转反侧的“年轻人”一些建议。 一般来讲,如果想要让“内心的感觉更麻木”,首先不是应该追求心如止水、不为所动的境界吗?可是诗人却说应“抵抗他的平静”,这不就是恰巧打破了平静吗?毕竟“麻木”是“平静”更深程度的“冷眼相看”,而激情却是“麻木”的反面,以上就形成了一个悖论。而接下来的诗句更令人读来费解:为何要羡慕呆鸟本禽?原来鸟禽虽呆笨,但它们却是属于“家里的花园”(at home in a garden),得以享受在家的怡然自得,步履轻松。所以,如果出走者的前路是踏上离开的旅途,遭受颠沛流离的折磨,那他自然是会羡慕家禽呆鸟的这份悠闲自如。那么前文所说“抵抗平静”就可理解为不去留恋那有关家和故乡生活的舒适、安逸、满足之感,“麻木”(harden)也有了“坚硬”的另一层意思,当人们对“平静”钝感甚至麻木,让内心坚硬起来,才能褪去柔弱,有力量“自此起步”,“踏上虚伪、自私的旅途”——这就是诗人对“远行”的看法,“在路上”越是不堪,越是流露出诗人对“家庭”“婚姻”及其所代表的稳定、安全之感的渴望。外面世界那处于“风险”和“安全”之间的地带,“永久安全”很有可能就是指死亡的结局,毕竟死亡象征着一种终究,它也确实是相对稳定的状态。这饱含了旅行者无尽的挣扎和不安。末尾依然叩问未来的归属,不确定感也进一步加剧。但是,人们也应看到,呆鸟本禽不会思考,它们对现状是很知足的,而人类却是会思考的,因此才会反抗,所以这个高高在上的隐藏的发声者并不像其言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完全掌控受话者,这种思考和反抗就与他的绝对权威地位之间构成了一种逻辑上的张力。
克林思 · 布鲁克斯所提出来的诗歌语言的悖论,原本指的是表面上荒谬而实际上真实的陈述,他把悖论视为诗歌区别于其他文体的最本质的特征,赵毅衡主编的《 “新批评”文集》中写道:“科学家的真理要求其语言清除悖论的一切痕迹;很明显,诗人要表达的真理只能用悖论语言。”诗歌的悖论语言从本质上讲还是诗歌创作的一种艺术手法,诗人所真正要表达的内容在悖论语言似是而非的逻辑外表之下得到了一种修饰,变得含蓄却更有感染力了。布鲁克斯认为,“如果失去了悖论特质,失去了悖论的两个伴随物:反讽与惊异。”唐恩的《圣谥》的题材就松散成生物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事实”,而失去了悖论,奥登的这首《见证者》同样地会丧失许多百转千回的思想深意和诗味,沦为平铺直叙的说教。这节末尾留下了巨大的悬念——这个(这些)高高在上的掌控者、发声者到底是谁?伴随着合唱队将人的这种疑惑唱出,这首或创作于1934年的诗也戛然而止,这个第一次出现的复数人称“我们”,或许就是《见证者》前后两部分诗文的联系所在。
二、现身的“见证者”:主导与播弄
在这之后还有一部分内容,长达48行的诗句被当作《见证者》这首诗的剩下部分,或创作于1932年12月。背后的人物终于现身,并且势不可挡。
这两位神秘的人物(The Two)自比城镇的时钟和把门洞的守护者,无时无处不伴随人们而存在,时钟标记时刻,象征着一种标准和权威,它守卫着时间的精准。燕卜荪《朦胧的七种类型》中讲到,朦胧的第三种类型表现为,一个修饰性的比喻不是用一件事物来阐明另一件事物,而是用来同时阐明两件事物,而且使这两者互相阐明对方。这里,诗人为了说明见证者的身份地位既是护卫又是权威,将其喻为忠实可靠的时钟、门洞守卫,同时也是令人胆怯的“双煞”(The Two),将其特征描写融入了一组有着某种共同点又可以互相印证说明的形象当中——漩涡、礁石、噩梦、伤心事、玫瑰。“左”和“右” “白天”与“黑夜”分别是相对的概念,诗人这样来写相比“我们日夜守在你的左右”明显更能营造出一种悬疑、神秘的戏剧性效果,“双煞”的形象也塑造得更加立体、生动。“漩涡”的特点是能将周围的物体飞速卷入,“礁石”坚不可摧,遇到二者中的哪一个都是航行中的极大危险;这个比喻渲染了“见证者”能使人如做噩梦般恐惧,像遇到“伤心事”一样悲痛。
到这部分,旅行者似乎已经完全丧失了主动权,即使他们在外历经各种艰难险阻,饱经挫折和荣辱,回到了原点还是得任由“见证者”的摆布,他们可以以消遣的眼光斜睨归来的游子兴奋地讲述游历,但决不允许人们自作聪明地隐瞒真相,挑战其权威。“学水手的说话做派”,只是“学”,而并不就是如此,读来似能发现在见证者看来,旅行者所说都是谎言,反过来看,人是不是也在试图努力挣脱见证者的压制?
“见证者”又一次提出警告,他们虽无影无形但能明察秋毫,哪怕是“花园”,他们也能长驱直入。然后这节诗突然以对天气异象的描述结束,又留下悬念——那如雨点纷纷落下的到底是什么呢,而且它还被特别说明绝非鲜花这样一般意义上明亮、美好的意象。
诗人在最后将其营造的戏剧氛围渲染至高潮,“见证者”的神秘面纱并没有掀开,但更严重的警告,加之刻意强调的死亡象征让人深深感受到了威胁。回到具体语言运用上,诗人做了一个奇喻,“葱绿田野如盖子般被揭离,露出了那件藏得好好的物件”,别忘了前文,来自双煞的警告,再看这里,诗人在说:“任你用尽心机意欲瞒天过海,其实一切花招早已被看在眼里,谎言假造的宁静随时可能会迎来疾风骤雨般的严惩,届时,等待你的就是一命呜呼了。”死神来临的威胁就像电影画面真实:门闩在锁槽滑动,窗外赫然停放着黑色灵车,连原本可能救死扶伤的医生都让人觉得不那么可靠。那屋内的人目睹这些,恐怕早已吓得不轻了。“外科医生”(surgeon)工作时的状态一般是手持手术刀械,和“死神”(scissors man)手执刀斧的形象非常相似,这里也可看作诗人用的双关手法,渲染“见证者”或者说“双煞”的恐怖气息。
三、结语
《见证者》中,人穷尽一生,出发、前行,踏上生命旅程,经历临行前的好奇、不安、恐惧和哀伤,旅行途中的风景和故事使我们内心一片虚无和彷徨,前途未卜。不同于人的纠结、渺小,见证者是很嚣张的,他或许象征着死亡,守卫着死的期限和规则,掌控着人类,自比上帝般无所不知。人生老病死,自然荣枯更替,终将归入尘土,所以人类既然躲无可躲,藏无可藏,不如坦然面对。我们看到,受话者在安定的室内状态被见证者诱惑、刺激外出,自以为已经实現了自我价值,却遭到其无情的讽刺和嘲弄,从见证者的角度来说,人是完全被动的,但实际上人难道不也是在反抗的吗?见证者一再禁止的“耍花招”和欺骗的谎言,就可看作人对一种不可抗的强大力量的反抗,也正是因为人的难以掌控,见证者才需要反复进行恐吓、威胁,这也许就是整首诗的一个中心悖论。人生依然苦短又漫长,要经历多少孤独时刻,于绝望之中想象茫茫宇宙有一道关注着自己的目光,如影随形,这或许可以说是迷茫的现代人孜孜不倦地追寻归属、追问答案的体现。
参考文献:
[1]W · H · 奥登.奥登诗选:1927-1947[M].马鸣谦,蔡海燕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2]李梅英等.“新批评”诗歌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3](英)威廉 · 燕卜荪.朦胧的七种类型[M].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
[4](美)布鲁斯特.精致的瓮[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5](英)勃朗宁.勃朗宁诗选[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