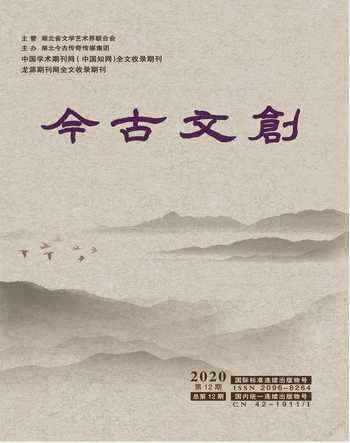《道格拉斯自述》福柯式解读下的教育图景
2020-09-10凌源
【摘要】 以福柯的权力理论为视角研究,《道格拉斯自述》呈现的教育图景处在极权主义奴隶制的权力场中,多层次权力维度的叙事中教育成为争夺的焦点。在美国奴隶制体系下,白人与黑人的关系类似于环形监狱中监视者与囚禁者的关系,而这个权力机器的钥匙则是教育。奴隶制用权力规训控制身体和思想,试图將黑人塑造成温顺的主体,从而进行奴役和剥削。道格拉斯通过对善恶两种教育体系的叙事,揭露了奴隶制权力规训的非法性,促进了废奴主义运动的开展,加速了美国南方种植园神话的破灭。
【关键词】 权力规训;道格拉斯;福柯;奴隶叙事;教育叙事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2-0037-04
福柯的权力理论指出,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动态而紧张的权力关系网络之中,无处不在的权力规训在个体、肉体和行为各个层面复制出一般法律和政府的形式[1]29。作为规训权力的集中体现,环形监狱的设计理念意在不留死角地监控每个犯人的活动,最终实现个体的自我规训。在美国奴隶制体系下,白人与黑人的关系类似于环形监狱中监视者与囚禁者的关系,而开启这个权力机器的钥匙则是教育。运用福柯的权力理论观察《道格拉斯自述》(以下简称《自述》)发现,奴隶制用权力规训控制精神和肉体,试图将黑人塑造成温顺的主体,从而进行奴役和剥削。道格拉斯通过对善恶两种教育体系的叙事,揭露了奴隶制权力规训的非法性,促进了废奴主义运动的开展,加速了美国南方种植园神话的破灭。
一、权力规训:戴上奴役的枷锁
话语是内在秩序允许我们说的话,与特定历史的制度和规则紧密相关。权力规训着话语,而话语则书写着身体和思想[2]27。在《自述》中,教育是话语和权力角力的主战场。奴隶制运用禁令、谎言和惩罚的程序阻止黑人获得教育,以便对黑人进行控制和奴役,迫使黑人的话语符合奴隶制运转的需求。
(一)用禁律剥夺黑人的教育权利
奴隶制切断了道格拉斯获取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主要渠道。奴隶主剥夺了黑人接受教育的正常权利和机会,试图将黑人置于人为的、有目的的无知状态[3]145。奴隶主故意让奴隶如同牲畜无法知晓自己的年龄和身世,从而加强对他们的控制和压迫。道格拉斯从出生就被禁止与自己的母亲见面,更不知道父亲是谁。黑奴被明令禁止询问这些信息,奴隶主坚信“奴隶提这种问题不合适、不规矩。这就是不安分的证据。”[4]8奴隶制体系中,无知是黑人安分、听话和守规矩的表现,而求知则是不规矩和不安分的证据。白人奴役黑人的秘密正是在于将黑人置于精神的黑暗之中。
教育是黑人继承文化传统和学习白人文化的重要途径,禁止黑奴获得教育是为了扼杀黑人发展的机会。对书面文本的读写能力是衡量努力要在西方书写文化中定义黑人作者人性的最终标尺[5]149。奴隶主不仅禁止黑人主动获取教育,而且禁止任何人给黑人提供教育机会。当奥德先生发现他的妻子教道格拉斯英文字母和基础的英语单词之时,立刻进行了制止。奥德太太在认识到教育与奴隶制水火不相容之后,也加强了对道格拉斯的监管。除了强调教奴隶识字“非法性”之外,奥德先生还说“黑鬼除了懂得服从主人,照主人吩咐的去做之外,别的是不必知道的。学习只会惯坏世界上最好的黑鬼。”[4]37这番话让道格拉斯发现了奴隶制的核心秘密,察觉到白人正是通过剥夺黑人的教育机会来达到奴役黑人的目的。从此以后,道格拉斯认识到教育是从奴役通向自由的途径。
(二)用命令强化对黑人思想控制
奴隶主用命令来禁锢黑人的思想活动,桎梏黑人的精神世界,试图让黑人变成具有人形却失去人性的劳动机器。奴隶们受尽了各种不公正待遇,却不能做出任何回嘴,必须服从任何命令。监工高尔将奴隶的任何回嘴和辩解都曲解为傲慢无礼并进行惩罚。在高尔那里,他说奴隶有罪就是有罪,有罪就得受罚;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便是下命令,一下命令奴隶就得服从,否则就得受罚[4]27。奴隶主还对奴隶私下谈话进行严密监控。有个奴隶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说了真实想法,就被监工卖到远方,从此再也见不到他的亲朋好友。奴隶主和监工是奴隶制的化身,服从他们的命令是维持奴隶制权力秩序的基石。奴隶制试图让黑人变成牲畜,失去发言的权力和意识,而“白人说的一个字就足以使最要好的朋友、最亲近的亲戚、最亲密的联系割断”[4]48。奴隶主还经常派密探混进奴隶当中来监控他们的思想活动,奴隶们只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对种植园生活很满足。当白人劝道格拉斯逃到北方去的时候,道格拉斯假装不感兴趣,并装作听不懂,用欺骗来避免上当受骗,因为有些白人靠抓捕逃亡的奴隶来赚取赏金。面对无处不在的命令规训,黑人不得不表现出绝对服从,否则就要受罚。命令监控着黑奴的公共活动和私下生活,黑人必须隐藏自己真实想法才能生存下去。
(三)用体罚规训黑人的身体行为
身体是自我意识的外在表现,也是思想的载体,蕴含着巨大的潜能和价值。奴隶制下的黑人身体成了奴隶主剥削的对象,通过权力规训让黑人身体产生经济价值,维持种植园的存在和发展。奴隶主说话时,奴隶不仅必须站直身子乖乖地听着,还得装出胆战心惊的样子。久而久之,很多黑人的身体被驯顺了,形成自然的条件反射,这正是奴隶制下身体规训想要达到的目的。奴隶主的妻子也经常体罚黑人。汉弥尔登太太总是坐在一把大椅子上,挥舞着又粗又重的牛皮鞭打得黑人鲜血直流,同时骂到“你不爱动,我来让你动!”[4]39皮鞭能解决问题,他们绝不用嘴巴。奴隶一个小小的眼色、半句话、一个姿势都会被曲解为傲慢无礼,并加以惩罚。奴隶主经常把道格拉斯的赫斯特阿姨捆在梁架上,打得她浑身是血才住手。目睹这样可怕而血腥的场景,道格拉斯叙述了他的感受:
“我当时还很小,但是印象却很深,而且只要我记忆力尚存我就绝不会忘掉它。这是我注定要成为见证人或当事人的一系列同类暴行中的第一件。它以一种可怕的力量震动了我。这是一扇沾满了血的门,是我即将进入的通向奴隶制地狱的入口。这是一个最最可怕的景象。”[4]12-13
这种残暴的罪恶深深震撼了道格拉斯的心灵,塑造了道格拉斯对种植园生活的最初印象,规训了道格拉斯早年的行为和思想。在这里,黑人除了忍受奴隶主的鞭打暴行,还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危险。一个奴隶为了躲避鞭笞跳进了河里,监工高尔在三声警告之后毫不犹豫地开枪打死了他。在《自述》中,类似事件比比皆是。道格拉斯的背上也留下了被鞭打的伤痕。在蓄奴的马里兰州塔波特县,“白人杀死一个奴隶或任何黑人,在法院和社会的眼里不算犯罪”[4]29,这一桩桩恐怖而邪恶的谋杀案的凶手既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也逃过了社会的谴责,却给黑奴身心留下磨灭不去的印迹和创伤。
二、反抗规训:身心解放的钥匙
规训权力并非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控制、稳定的关系。作为处在紧张、活动状态中的网络关系,规训权力体系存在“无数冲撞点、不稳定的中心,每一点都有可能发生冲突、斗争,甚至发生暂时的权力关系颠倒”[1]29。因此,权力规训必然遭到反抗。在《自述》中,道格拉斯获得教育的过程正是反抗奴隶制权力规训的过程。
(一)命名:颠倒主奴权力关系
道格拉斯用命名策略对奴隶生活悲惨处境进行了形象化的描述,对奴隶制的运行机制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反抗了奴隶制的权力规训。通过将标准英语概念中能指的意义清空,将自己的概念和意义填充进去,黑人作家秘密地、有意地用黑人传统和意义体系融入甚至代替西方传统和意义体系,从而打破了意义=所指/能指的公式(the signification=signified/ signifier equation),服务于颠覆白人霸权和权力的意图[6]51。在奴隶制中,很多白人都在名字后面加上代表权力等级的称谓,道格拉斯第一个主人叫“安东尼船长”,他的女婿名叫“托马斯·奥德上尉”,“安东尼船长”是“劳埃上校”的秘书兼监工,也是所有监工的监工。奴隶们将劳埃上校所在的种植园称作“大宅子农场”,因为这里外表上像一个村庄,“是繁忙的事务中心,是所有二十个农场的‘政府’所在地”[4]15。相比之下,很多黑奴在称谓上表现出一种主奴的从属关系,还有不少黑奴连完整的姓名都没有。例如,黑人纳德·罗伯兹属于劳埃上校,因此被称为“劳埃家的纳德”。这一系列称谓之间的层级关系表明奴隶制是等级森严的权力体系,如同军队、政府和监狱一样。
起绰号是命令策略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将原有的名称赋予了新的意义。道格拉斯将监工帕林茂起了一系列绰号:“无可救药的酒鬼”“骂人的能手”“野蛮的魔王”[4]12。 道格拉斯认为监工西维亚先生(Mr. Severe)的姓名名副其实,因为他心狠手辣,对黑奴冷酷无情。另一个监工爱德华·科维是出了名的“黑奴驯师”,但奴隶们称他为“蛇”,因为他经常像毒蛇一样悄悄地匍匐着爬到正在劳动的奴隶中间,然后猛然跳起来呵斥奴隶们抓紧干活。与西维亚和科维不同,监工弗里兰先生相比之下还有些教养和人性,因此奴隶们从不给他起绰号。当道格拉斯萌生对自由的渴望时,他说他不仅要和弗里兰(Freeland)一起生活,还要在自由的土地上(freeland)生活[4]82。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文字游戏和双关,让道格拉斯对奴隶主的虚伪残暴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加深了道格拉斯对自由的信念和憧憬。在实施逃跑计划的前一周,道格拉斯用奴隶主的口吻和书写格式给每个同伴写了一张通行证,并签上了奴隶主的姓名。这种模仿与改写破除了白人对知识和话语的垄断,暂时颠倒了奴隶制下的主奴关系,进而解构了奴隶制体系得以维持的根基:黑人无教育因此适合当奴隶。
(二)批判性思维:为获取自由做准备
面对白人严密的权力规训,道格拉斯正是通过获得教育从而得知并揭露了奴隶制的权力机制。教育获取的知识打破了白人社会的知识/权力体系,进而激发了道格拉斯争取人身自由和精神自由的主动性,从被奴役的客体转变为自由游走的主体。然而,美国黑人在信任白人教育力量的同时又心存疑虑[7]156。在应对这种复杂而矛盾的心理和文化反应过程中,道格拉斯培养了批判性思维能力。批判性思维打开了道格拉斯获取教育的大门,让挣脱奴役的枷锁成为可能,也促进他种族意识的觉醒,帮助同伴获得教育并争取自由。
通過掌握读写能力,道格拉斯证明自己并非牲畜和机器,而是有思想的人。道格拉斯抓住任何机会拼命学习,因为知识既是奴隶制奴役黑人的权力也是黑人摆脱奴役的途径。他用奴隶主的面包作为交换,让穷白人孩子帮助他认字。他通过摹写船舷上的字、与白人小孩进行写字比赛、将《韦氏拼音课本》作为字帖练习写斜体字、临摹托马斯少爷的笔迹等方式,来练习书写技能。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道格拉斯学会了看书写字,掌握了读写能力。教育激发了道格拉斯种族意识的觉醒,通过将自我(“我”)与黑人种族(“我们”)的命运紧密结合,道格拉斯将自我与废除奴隶制、解放黑人作为终生使命。道格拉斯是一个教“我们”的“我”,一个组织“我们”的我,一个“超”我[8]57。《哥伦比亚演说家》中有一篇主奴对话启发了道格拉斯:奴隶主所有支持奴隶制的论据都被奴隶驳倒了,辩论的结果是主人自愿解放奴隶[4]42-43。这段话不仅让道格拉斯认识到真理和理性的力量甚至能激发一个奴隶主的良心,还让他认识到奴隶主本质上是将黑人从非洲家园掳掠到陌生国土并让他们沦为奴隶的强盗。教育让道格拉斯产生了种族意识和种族觉悟,将争取族群自由作为自己的使命[9]196。自从道格拉斯阅读报纸时理解了“废除”(abolition)和“废除主义者”(abolitionist)的意思之后,每当听到这两个词的时候总会仔细去听,期待获得争取自由的信息和机会。在他的影响下,几个黑人同胞产生了学习念书的强烈欲望,他们凑了几本旧的识字课让道格拉斯开个主日学校教他们识字,之后道格拉斯每周抽出三个晚上教同伴学习。在这些学习团体中,道格拉斯和同伴们暂时摆脱了奴隶主的管束,可以相对自由地学习、思考和讨论[10]20。这种教育过程是对自由生活的练习和准备。
(三)言说的主体:揭露奴隶制的非法性
到了北方之后,道格拉斯积极著书立说,用主流话语写作和演讲,传递出黑人群体想要表达的信息。《自述》将“黑色信息装在白色信封内”,展现出“黑皮肤,白面具”现象。为了反抗奴隶制的话语权力规训,向白人读者呈现自己的经历和思想,道格拉斯必须掌握白人的话语体系,而教育则是打开这道门的钥匙。
作为逃出奴隶制压迫的幸存者,道格拉斯也是奴隶制的罪恶和残忍的见证者。通过叙述自身的见证和经历,道格拉斯向公众揭露了奴隶制对黑人和白人犯下的罪行,揭露了奴隶制的非法性,为争取个人和族群自由而不懈奋斗。权力不仅控制话语,也存在于话语之中。对权力的争夺最终都转化为对话语的争夺[11]208。道格拉斯模仿了宗教和法庭的见证模式,以真实的处境和文件式的证据,提供了叙事的真实性。从社会话语的角度来看,《自述》提供了一种先前不为人所知的一个群体生活境况的知识。《自述》不仅提供了道格拉斯亲身经历的事件,还提供了他亲眼所见或亲耳听到的周围的亲戚、朋友遭受非人待遇的事实,成为一份“目击证人”报告。因此,道格拉斯揭露奴隶主和监工们的罪行,就是揭露奴隶制的非法性。道格拉斯更多地围绕南方奴隶制来叙述他自己的故事,利用一切机会来抨击奴隶制的惨无人道,叙述的着眼点在于揭露南方奴隶制对黑人肉体和灵魂的摧残[12]38。道格拉斯对奴隶制罪行的见证和批判,为他通过反抗手段争取自由提供了合法性,证明了黑人通过教育可以和白人一样并且甚至比白人更优秀。
作为一种恶的教育,奴隶制不仅对黑人犯下滔天罪行,也扭曲、异化了白人的人性,使他们沦为奴隶制权力机器中的零件和齿轮。奴隶主随意杀害黑人而不受法律制裁和道德谴责,这种罪恶行径笼罩下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深深毒害着白人小孩和妇女。白人小孩坚信“花半分钱就能要一个‘黑鬼’的命,再花半分钱就能把他给埋了”[4]30。奥德太太从虔诚、热情、心地善良的家庭妇女变成了铁石心肠、残忍恶毒的女人。托道格拉斯儿时的朋友和玩伴托马斯少爷,长大后却堂而皇之地声称自己蓄奴完全是出于“照顾好奴隶”的“慈善”目的[4]58。道格拉斯运用相同的叙述策略和类型化归纳将奴隶主和监工刻画成同一个类型,只有残忍程度的不同,没有个性和本质的区别,深化了这个群体罪行累累的主体性阐释[8]55。《自述》在叙说奴隶制下黑人斗争故事的同时,让奴隶制下恶的教育与道格拉斯所追求的善的教育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小结
以福柯的权力理论为视角观察,《自述》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叙事图景:恶的教育和善的教育。恶的教育是奴隶制下白人实施权力规训的核心体系,而善的教育则是黑人奴隶颠覆主奴关系、争取自由平等的主要途径。这两种教育叙事之间的张力正是奴隶制中权力流动的动力。道格拉斯在获取教育的过程中认识到奴隶制赖以生存的根基只不过是一个谎言:黑人无教育因此不是人。教育让道格拉斯由被规训、被物化的个体转变成自我意识觉醒的主体,在争夺话语权的斗争中用善驱逐着恶,用主流话语占领了道德和人性的制高点,揭开了奴隶制的遮羞布,加速了美国南方种植园神话的破灭。
参考文献:
[1]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2]杨晓莲,黄燕娇.权力规训下的生存图景—— 《诚惶诚恐》的福柯式解读[J].外国语文,2017,33(03):26-30.
[3]John D. Cox. Traveling South: Travel Narrativ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Identity.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5.
[4]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道格拉斯自述[M].李文俊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
[5]盖茨.意指的猴子:一个非裔美国文学批评理论[M].王元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6]Henry Louis Gates Jr. & W. J. T. Mitchell. The Signifying Monkey: A Theory of African 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7]Robert B. Stepto. “Narration, Authenticating, and Authorial Control in Frederick Douglass’ Narrative of 1845”. William L. Andrews and William S. McFeely (eds.), A Norton Critical Edition: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 an American Slave, Written by Himself.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1997.
[8]赵白生.美国文学的使命书—— 《道格拉斯自述》的阐释模式[J].外国文学,2002,(05):52-57.
[9]庞好農.“潘多拉的魔盒”开启之后——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个美国奴隶的生平叙事[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4,第20辑.
[10]Wincent L. Wimbush. “Interpreters—Enslaving/Enslaved/Runagate”.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No.1(2011).
[11]刘晗.福柯话语理论中的控制与反控制[J].兰州学刊,2010(4):204-208.
[12]许德金.叙述的政治与自我的成长——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两部自传[J].外国文学评论,2001,(01):33-40.
作者简介:
凌源,男,安徽合肥人,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和西方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