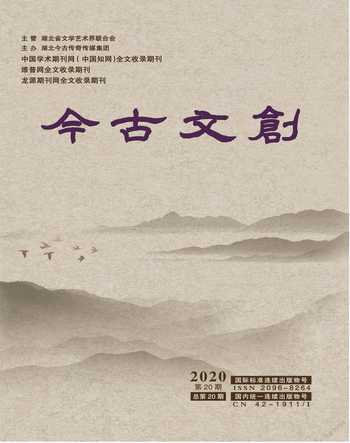《三个高个子女人》中的伦理困境之“结”与“解”
2020-09-10杨思扬
杨思扬
【摘要】 爱德华·阿尔比的晚期代表作品《三个高个子女人》于1994年获得普利策奖。其中的女主人公做出的各种伦理选择让她多次陷入不同的伦理困境中。本文拟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以文本细读的形式深入探究女主人公陷入伦理困境的成因以及她挣脱出困境之泥潭的过程。阿尔比对女主人公倾注的关切与期盼同时凸显了阿尔比对其刻画的人物的终极人文关怀。
【关键词】 《三个高个子女人》;爱德华·阿尔比;文学伦理学;伦理困境;伦理结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0-0019-02
爱德华·阿尔比(Edward Albee,1928-2016)是美国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家,是二十世纪的美国剧坛中最具影响力的剧作家之一。他关注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各种问题,表现出对于个体的异化和个体间疏离的担忧,同时更致力于对人类前途与命运的关怀。[5]《三个高个子女人》是他晚期的代表作,于1994年获得普利策戏剧奖。
在《三个高个子女人》中,作为同一个女人人生的不同阶段,92岁的A,52岁的B和26岁的C分别分享了她们现阶段对于自己人生经历的感悟和对同一事物不同的理解,从起初的激烈争吵到最后的彼此认同,最终与自己和解。剧中A在不同的时期做出的伦理选择在后期都让她深深陷入伦理困境中,而最后她在自己的回忆中一一细数在当时的道德观念和伦理环境中所做的各种选择,却恰好“解”开了当时的“结”,完成了自己人性的救赎。本文拟运用聂珍钊教授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以文本细读的形式细数女主人公陷入的各种伦理困境,探究她是如何挣脱出各种伦理困境的泥沼的。通过剥丝抽茧般的梳理,各种事件得以清晰地再现,而其中蕴含的剧作家的人文关怀也清晰地展现出来。
一、家庭成员之“结”与“解”
在《三个高个子女人》中,女主人公A与自己的家庭成员之间存在诸多的矛盾。她的父母是虔诚的清教徒,于是对她十分严苛,让她想起父母来都只记得他们的严厉;她对妹妹有着诸多抱怨,同時暗暗与妹妹较劲;她和丈夫之间没有什么感情,两人双双出轨;她接受不了自己的儿子是同性恋,儿子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各种被扭曲的家庭伦理关系在女主人公的回忆叙述中被重现。文学伦理学中强调“寻找和解构文学作品中的伦理线和伦理结”[2]20通过寻找这些家庭关系中呈现出的伦理结,女主人公的伦理困境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A从小接受的是父母极为严厉的清教徒思想的教育:“我母亲一直对我说这句话:别不懂规矩……让我们上床睡觉前把前天晚上穿的所有东西都洗干净,用手洗。有时妹妹不愿洗,我得替她洗。她让我们做淑女。”[1]97母亲竭力将自己两个女儿塑造成淑女的样子,教育她们禁欲:“记着,别把它给出去,妈妈说,别把它轻易给出去。他们会因此不尊重你,别人会认为你是个放荡的女孩儿。那样你还能嫁给谁呢?”[1]104剧本中没有正面描写她对于自己受到的这种教育的看法,但是根据后文中她和男人交往时产生的报复性的快感可以看出这是她对她年幼时受到的禁欲教育的挑衅和反叛。她对于自己高挑的身材甚为满意,时常把自己与妹妹相比较:“我个子高,相貌端庄;她个子高,模样可爱,个子高但比我矮,没有我现在高……没有我过去高,” [1]99“我是个好姑娘。我知道如何吸引男人。我个子高,惹人注目。我知道怎么做。妹妹懒洋洋地没有精神,缩脖猫腰的;我个子高大,昂首挺胸……我在走廊里一走,别人就知道有人来了,或是有人在那儿。”[1]104对于妹妹的才华和美貌,她是嫉妒的,于是她对她十分刻薄:“我妹妹是个酒鬼。(不友好地)她比我聪明,不,是更伶俐,比我小两岁。”[1]98指责她酗酒成性,还强行给她找了个四十岁的意大利人和她结婚(此处她用的“意大利佬”,有贬义)。她的丈夫是个有钱的花花公子,风流成性,她和丈夫之间仅仅只有金钱和性的联系而没有真实的感情。而两人被兽性因子所支配,肆无忌惮的出轨行为就造就了恶劣的家庭伦理环境,使每一个家庭成员都陷入深深的煎熬中。当她发现了自己的儿子是同性恋后愤怒地要教训他,儿子却当场揭穿她出轨马夫的事情,并离家出走,连他父亲的葬礼也没回来参加。
以时间顺序展开的伦理线将女主人公的各种伦理困境一一铺陈开,将家族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敌意描写得淋漓尽致。而每个“结”,都对应地迎来了它的“解”。女主人公在叙述对妹妹负面回忆的同时,又用轻松欢快的语调表露出她对妹妹的喜欢:“我想我们彼此喜欢。我们过去说很多知心话,经常在一起笑。”[1]98并且对于酗酒的妹妹她并没有不管不顾,她将她接来,让她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悉心照顾她。她举例她自己最幸福的时刻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和妈妈、妹妹在一起的欢乐时光:“举个例子,看看这是不是幸福的时刻:妈妈给我做了件白色连衣裙,妹妹又嫉妒又激动,蹦来跳去,同时又生着闷气。” [1]111对妹妹和妈妈从排斥到接纳,两种相反的情绪从碰撞到融合,也是她走出伦理困境的“解”。同时,她与儿子的关系也从冰封变得缓和。她们之间的缝隙曾经是如此之大,“是的,是的,他是这样,他穿着那件外套。他说,我走了,拿着个包。(停顿)把一切都带走了。”[1]107时隔多年,母子再次相聚,两人尴尬的如同陌生人一般。她因为他的冷漠和敌意而悲伤不已,却一直询问着今天是星期几,琢磨着他什么时候会带着小苍兰来看她:“他来的时候有时会给我带些。或者给带些花——当令的小苍兰。他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他知道这个。”[1]98“你带给我花,你带给我小苍兰,你知道我喜欢小苍兰,所以你带给我这些花,因为我喜欢它们。”[1]111她不知道自己是否爱他,他又是否爱自己:
A: 他不爱我!他爱他的……他爱他的那些儿子。你不知道!他不爱我,我也不知道我爱不爱他。我想不起来了!
B:他爱你。
A:(快哭了)我想不起来了,我想不起来想不起来什么了。[1]102
他爱她吗?答案在他赶来医院看她的时候就已经很明显了。儿子细心地带了她最喜欢的小苍兰,送到了她的病床边。握着A已经冰凉的手,他先是愣住,然后整个人开始发抖,泪如雨下。A以灵魂旁观者的角度对这段记忆进行了极为细节的描述,轻柔的语言充满了母亲的慈爱和关怀。这一段解开了她与儿子的“结”,解开了亲子关系的伦理困境。
二、社会环境之“结”与“解”
文学伦理学重在分析文学作品中的伦理事件,“为人类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提供不同的生活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启示,为人类的文明进步提供道德指引”[3]9而作为一个旁观者,文学伦理学批评本身并不会评判观察的对象的对错,而是提供了一个思考和对话的途径。剧中的女主人公A对金钱和物质的态度正是值得我们用文学伦理学探讨的对象。
在《三个高个子女人》中,A年轻时的时代背景正好是美国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时的美国正在从农业社会迅速转变为工业社会,垄断资本主义大行其道,美国经济迅速发展。从小习惯了清贫的清教徒生活的A来到城市中,内心顿时受到极大的冲击。她被纵横享乐、物欲横流的世界所吸引,对自己先前所受的节约和禁欲的教育产生了怀疑。于是她在两种文化巨大冲突的作用下迷失了自我,开始追求金钱和性带来的刺激。高挑漂亮的她选择嫁给一个矮如企鹅的独眼男人,只因为这个男人有钱,能给她优渥的物质生活。“他们的婚姻关系实则是互相利用的关系:她需要物质的满足,而他则渴望一位美丽的异性填充精神上的虛无。婚后,他们的夫妻关系一一被商品化,金钱被等同为感情,变成可以买卖的商品,夫妻双方最在乎的也只是对方的交换价值。”[4]174对财富的追求几近痴迷的A认为所有人都惦记着她的钱:“所有人都想骗我的钱,我又不是钱做的。”[1]96“你要是不注意,他们就会骗取你的钱:佣人、商店、市场,还有那个给我做皮服的犹太小女孩儿,她叫什么名字来着?她倒不错。他们甚至在你一转身的时候都会骗取你的钱财。他们所有的人!”[1]96,“每个人都在抢我的钱——到处都是。每个人都偷窃。每个人都偷东西。”[1]100从文本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人欺骗她的证据,只看到她对财富不懈的追求与病态的保护欲。她被困在金钱造就的“结”中,越陷越深。然而,她身边的人一个个离去,父母、丈夫、妹妹、儿子相继离开,家族也没落了,所有东西都被拍卖掉了,连银行金库里存的珠宝首饰也都换成了假的,用来至少撑撑门面。A对着自己剩下的假珠宝发出叹息:“全都华而不实。”[1]110这既是指她虽然一生富足享乐,最后却沦落到孤身一人躺在病床上,也是指自己一味追求金钱的物质人生看似充实,却在精神上感到无比的空虚。通过最后对生命的彻悟,她挣脱出了盲目追求物质的伦理困境,找到了她的“解”。阿尔比对A这种繁华落尽后只感到无尽空虚的人物形象提供了他的思考,也倾注了他的人文关怀。
三、结论
爱德华·阿尔比在《三个高个子女人》中塑造了一个与亲人矛盾重重,疯狂追求物质的女主人公形象。笔者从家庭和社会两个方面出发,深入探究了A是如何摆脱伦理困境,如何化“结”为“解”的心路历程。阿尔比对女主人公A的同情和思考可谓贯穿剧本始终,同时也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提供了自己对社会现象的思考,让身为读者的我们在意识到各种伦理问题的同时也对伦理存在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
参考文献:
[1]爱德华·阿尔比.三个高个子女人[J].于海阔译.戏剧之家,2012,(12):90-112.
[2]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12-22.
[3]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4]姚瑶.“我怎么变成这样”——浅析《三个高个子女人》中的“异化”世界[J].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5,(8):174-175.
[5]Bottoms, Stephe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dward Albe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