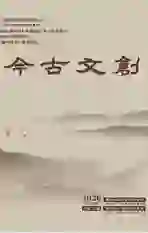《老妇还乡》中个人被牺牲剧情的合理性解读
2020-09-10崔羽欣
【摘要】 《老妇还乡》是瑞士戏剧家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的代表作之一,故事叙述了一位贵妇衣锦还乡,向旧情人复仇的故事。全剧突出体现了人在金钱诱惑下逐渐臣服于趋利本能而放弃道德底线的斗争主题,并最终引向由群体迫使个人牺牲以换取物质利益的结局。通过心理分析、文学阐释以及伦理呼应的手段,对其个人被牺牲情节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以期受众能够对故事情节有更高的情感接受度。
【关键词】 《老妇还乡》;迪伦马特;被牺牲;剧情合理性
【中图分类号】I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2-0008-03
一、引言
站在人道主義立场来看,以一人性命换取多数人的安定富足并非是符合人性教化的正确抉择,然而在弗里德里希 · 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所著戏剧作品《老妇还乡》(Der Besuch der alten Dame)中,坐拥亿万身家的富婆克莱尔 · 察哈纳西安却背倚财富带来的无上权力,借凭群众的声援力助,实现了对昔日情人伊尔的“围捕”和成功的复仇。
《老妇还乡》剧作的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伊尔最终死亡的结局有违人伦信念,是对资本与现实的讽刺”。而老妇复仇成功有其特定条件及合理性,可从集体无意识角度、作品讽喻角度以及现实情境角度进行解读。
二、集体无意识下的个人被牺牲合理性
资本、复仇与“正义执行”无疑是《老妇还乡》中极为突出的、推动情节走向的表现性因素,但正如迪伦马特在剧作后记中所言,“我描写的是人,而不是傀儡;是一种有动作的情节,而不是一则寓言;我是在呈示一个世界,而不是要进行道德说教”。
迪伦马特作品中描写的城中居民对克莱尔回乡之举以及用十个亿换取伊尔性命的交易可以说是在思想上各有考量,在实践上却又奇妙地趋向一致。与此同时,迪伦马特对于剧作情节及内在世界的构建虽然不必“跟现实进行对照”,但却在某种程度上负载着各种“原型(archetype)”和“原始意象”。
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认为“艺术家都以为自己的创作是自由的,那只不过是幻想,他的创作实质上受着集体无意识的束缚”,荣格在弗洛伊德个体无意识的基础上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理论,并以此作为其进行文学批评的基础。
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认为“集体无意识的形成是个潜在的过程,刚开始集体感觉不到这种无意识的存在,但客观上却已经以某种形式存在着”,所以作者笔下的作品也便不单纯是个体欲望的升华,而是集体记忆的体现。
无论作者还是读者,在面临举城穷困潦倒的处境和处死一人换取生存生活资本、并且需要被牺牲之人原为有罪之人的条件下,是否会遵从人性道德的指引对其进行赦免其实是未知数。
作品给予读者的结局是伊尔死亡,居民最终无法抵抗内心欲望而违背人伦的定论,且由于人类社会在原始和封建时期长期推崇牺牲个体换取族群安定的“原型”普遍存在于人类集体记忆之中,导致相似情境出现时,人们会做出印刻在历史族群记忆中的心理反应。
由此可见,对于居伦城民众行为折射于现实的道德评判不可单一认定为资本侵蚀了人性,居民为了财富夺取了伊尔的性命,而是当从群体角度无法做出唯一正确标准的评判时,个人的被牺牲存在其合理性。在这一层面上,剧作可以激活读者内部的集体记忆,从而引起读者共鸣。
三、喻体形象下的个人被牺牲合理性
(一)“非人化”的加害者喻体形象对个人牺牲的影响
剧作第一幕中,克莱尔来到居伦城,携带着搬不完的箱子、一只关在笼子里的豹子,还有一口棺材,先后向牧师询问死刑和葬礼主持事宜,向医生询问他是否会开死亡证明书。
教师初次见到这样的克莱尔,心生恐惧,说道:“我觉得她就像是罗马神话中的命运女神,就像是希腊神话中的命运女神。因此与其叫她克莱尔,不如叫她克罗托”。
在希腊神话中,莫伊莱(Moerae)是命运三女神的总称,掌管万物命运的三位女神分别是克罗托(Clotho)、拉克西斯(Lachésis)和阿特洛波斯(Atropos)。克罗托掌管未来和纺织生命之线,拉克西斯负责维护生命之线,最年长的阿特洛波斯掌管死亡,负责切断生命之线。迪伦马特以剧中人物口述的方式引入神话中的命运女神形象,并细节性地将老妇的名字与克罗托进行关联。克莱尔干涉了居伦城中所有居民的命运,居伦的窘迫潦倒由她一手造成,并以此作为铺垫,换取她想要的公道。她需要维持自己表面的清白体面,而非直接通过自己的手切断伊尔的生命之线。最好是在众人的助推下取走伊尔的性命,又能让每一个人都在内心背负杀死伊尔的罪名。最终让居伦人明白,他们抱有的希望不过是妄想,“少数人坚守的人道信念毫无意义,他们的一生都是浪费”。
(二)社会公职人员喻体形象对个人牺牲的影响
第二幕则是全城追捕克莱尔逃跑的黑豹和坐立不安的伊尔向市民寻求帮助双线并进的剧情走向。居伦人因长期的贫穷渐渐经受不住金钱的引诱,选择赊欠消费,与此同时,良心也逐渐为克莱尔所收买;全城人沉浸在身心需求得到满足的极致愉悦中对伊尔来说更是让他惊恐不已。伊尔以挑唆谋杀的理由向警察提出要求逮捕克莱尔,代表着公正与司法的警察形象虽然声称会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秩序,保护公民生命财产,行动上却同其他居伦城民一样,穿着赊欠来的鞋,镶着赊欠来的大金牙。司法的堕落为伊尔的死亡埋下伏笔。
随后,伊尔选择向市长寻求帮助,代表着政治力量的市长形象先将保护市民伊尔的责任推诿至警察局,又在得知警察决定束手旁观后以话术安抚伊尔——“居伦是个有着人道主义传统的城市,民众不会辜负传统的价值”。政府为资本所腐蚀无疑成为了伊尔死亡的催化剂。
最后,伊尔去教堂寻找牧师,代表着宗教神圣性的牧师形象更是直接劝告伊尔不应该惧怕死亡,应当战胜内心的恐惧,检点内心,好好忏悔。宗教的软弱无法拯救陷入众人无形围捕的伊尔。被枪打死的黑豹躺在伊尔的小百货店门口,每个人手中都握着枪械,无人知晓究竟是哪一个人射杀了黑豹,便是每一个人都射杀了黑豹。黑豹形象从被追捕直至死亡伴随着伊尔的心理状态从心存希望到极度紧张,再到精神完全崩溃,最终也喻示着伊尔的无奈丧命。
(三)社会文教人员喻体形象对个人牺牲的影响
第三幕体现了居伦城中极少数人出于对仁义道德的坚守与资本力量做着斗争,代表着知识分子的教师形象对居伦城仍抱有希望,希望居伦城能够重放光彩,恢复昔日的繁荣。但他既无法说服克莱尔,也无法阻碍其他市民,甚至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想要在记者面前说出人命与金钱交易的真相时,也被意识到自己罪过的、心灰意冷的伊尔所打断。
又有代表媒体传播力量的记者形象一味追求富人们的风流史和花边新闻,无法揭露社会中存在的黑暗现实。知识分子的懦弱无能和大众传媒的闭目塞听让伊尔的死亡愈发临近。教师在试图说服克莱尔时请求道:“您在我面前就像古代那位女英雄——美狄亚。然而……请您抛弃这种要不得的复仇思想,不要把我们弄得无路可走……求您发扬您的纯洁的人性吧!”
在第一幕的描写中,“克莱尔的假腿挂着链条,白嫩冰凉的手也是由象牙制成,此时克莱尔的形象已经趋于非人性、非自然的物体”,对于教师所要求的人性,克莱尔也自然是难以满足。
迪伦马特在作品后记中也指出,克莱尔的形象是“可以像古希腊悲剧中的一位女主人公那样行动,专横、残暴,近乎美狄亚。她可以为所欲为”。
对于说出“这个世界曾经把我变成一个娼妓,现在我要把它变成一座妓院”的克莱尔而言,复仇不仅是对于伊尔的复仇,她还要让整个城市的道德彻底沦丧。
美狄亚的形象更是希腊神话中女性复仇的代表人物,她被复仇的情感所控制,最终的结局也是非理性的胜利。以美狄亚的形象来呼救克莱尔,可以预计她的回应必将是贯彻到底的成功复仇。
四、功利主义下的个人被牺牲合理性
《老妇还乡》的故事发生在穷困破败的居伦城。从前的居伦城多地通衢,经济发达,文化繁盛,却在五年前开始逐步衰落:工厂倒闭、公司破产、冶炼关停,居民只能靠失業救济艰难过活。如今,小城终于在哀苦中迎来了转机:“亿万富婆要回家乡来看看,这可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市民们怂恿着伊尔去说服克莱尔为她度过青春年华的小城做出贡献,让工商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恢复正常运转。在居伦,贫穷是最大的罪恶。伊尔因为贫穷抛弃克莱尔,否认了年轻的克莱尔的父权控告,娶了经营小百货店的玛蒂尔德,克莱尔沦落为妓女;柯比和罗比因为贫穷,在伊尔一升烧酒的贿赂下面对法庭做出了伪证,后被克莱尔寻得,变成了瞎眼的阉人;居伦城民因为贫穷用赊欠的方式提高生活质量,逐步落入克莱尔设下的圈套,他们共同完成了一起谋杀,用一具尸体换取了全城的繁荣。
美国科幻文学作家厄修拉 · 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在其短篇小说《离开欧麦拉城的人》(The Ones Who Walk Away from Omelas)中描绘的欧麦拉城人也面临和居伦城人相似的抉择。与居伦城有诸多不同,欧麦拉城市民的欢乐情形难以描述,他们在明媚的阳光下举行盛大的游行,在海滨城市的绿地上分享美味的食物,奏响动人的乐章。成年人都富有智慧,充满激情,孩子们都天真快乐,所有人都过着不错的生活。“他们的社会既不存在君主制与奴隶制,同样也没有股票交易,没有商业广告,没有秘密警察,没有原子弹”,“还有一样东西我确知是欧麦拉城所没有的,那就是罪恶”。然而在欧麦拉城某幢漂亮公共建筑的地下室里,却隐藏着一个众人皆知的“秘密”:一个被幽禁在此、不知性别的低能儿。他(她)所在的地方没有窗户,结满蛛网,拖把立在墙角生锈的铁桶里,散发着臭气。“他(她)每天只能靠半碗玉米粉和一点动物油维持生命,臀部和股部是一大串化脓的疮,因为他(她)老坐在自己的屎尿里。”生活在欧麦拉城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她)的存在,却无一人敢对他(她)说一句关切的言语,展现一点不忍和友善,遑论将他(她)带出污秽之地,让他(她)也看一眼欧麦拉城的美好景象,体验一次欧麦拉城的富足生活。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所拥有的一切繁荣和睦与欢乐都依赖于那孩子所遭受的苦难。“为了做那一件微不足道的善事而牺牲善良的欧麦拉全体众生,为了给一个人创造幸福的机会而破坏千万人的幸福,那无疑是将罪恶引进欧麦拉城”。
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边沁(Jeremy Bentham)是功利主义思想的奠基者,所谓功利,就是指“一种外物给当事者求福避祸的那种特性,由于这种特性,该外物就趋于产生福泽、利益、快乐、善或幸福;或者防止给利益攸关的当事者带来祸患、痛苦、恶或不幸”;“当事者可以泛指整个社会,也可以指具体的某个人”。功利主义认为个人利益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动因,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是个人行为和社会活动的准则。
相反,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 · 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则对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进行了批判,认为实行这一原则的代价是对少数人的不公正,而“我们之所以容忍某种不正义,也仅仅是因为我们必须避免一种甚至更大的不正义”。
欧麦拉城人虽然能够意识到囚禁孩子是非正义的,却又声称自己的城市不存在罪恶,认为停止孩子的被牺牲才是对全体众生犯下了罪恶。欧麦拉城的孩子与居伦城的伊尔同样作为为了社会趋于繁荣安乐而被牺牲的对象,前者受难以防止给欧麦拉城带来祸患、痛苦、罪恶与不幸,后者赴死便能为居伦城产生福泽、利益、快乐、善与幸福。与欧麦拉城的孩子无辜受难的情形相对比,伊尔年轻时犯下的罪恶成为他被牺牲的条件之一,他意识到自己的罪过并最终以用生命来赎罪的悲剧收场。迪伦马特认为伊尔的死“是很有意义的,同时又是毫无意义的”,市长在剧作的结尾宣布了克莱尔向居伦城捐赠十个亿的喜讯,并宣布这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主持公道,是良心之举,必须铲除罪行免得灵魂受侵害、被玷污。在居伦城民众眼中,杀死伊尔逐渐从不正义变为了正义,拿不到克莱尔的捐赠才是更大的不正义,从而奠定了伊尔的死亡走向。
五、结语
正如迪伦马特在《老妇还乡》后记中所言,“克莱尔 · 察哈纳西安既不是代表正义,也不是代表马歇尔计划”“她仅仅是她而已,世界上最有钱的一个女人”,对于伊尔在剧作中个体被牺牲结局的合理性探讨限于剧情合理性而非现实合理性,也并非意味着在现实情形下剥夺他人财产生命权利有绝对的正确性。从作者心理角度、作品讽喻角度以及现实情境角度对个体被牺牲现象进行较为合理的分析有助于剧作读者和戏剧观众认识剧情走向的大体逻辑,在意识上能更好处理这一出以悲剧收场的喜剧。
参考文献:
[1]吴海涛.论迪伦马特悲喜剧《老妇还乡》中的资本、复仇与正义[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7,(16):31-32+42.
[2]弗里德里希 · 迪伦马特.老妇还乡[M].叶廷芳,韩瑞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3]朱志荣.西方文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杨镇源.集体无意识视阈下翻译价值理论的归结性反思[J].外语学刊,2020,(05):112-116.
[5]次晓芳.试析《老妇还乡》中的女性形象[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3(01):51-53+100.
[6]zdwdyx665.离开欧麦拉城的人译文[DB/OL].2020-05-28.
[7]叶立煊,郝宇青.西方政治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作者简介:
崔羽欣,女,陕西师范大学翻译硕士研究生在读,专业为英语笔译,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