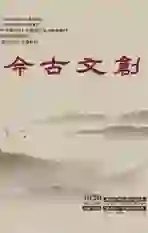试论娄烨电影《推拿》色彩的使用
2020-09-10焦天骄
焦天骄
【摘要】电影色彩的使用一直是电影创作者始终关注的问题,从一般意义上来讲,一部优秀影片中的色彩能够强化导演的表达以及观众对于人物的主观认知,本文从作者型导演娄烨的电影《推拿》出发,尝试分析色彩在本片中的象征与非象征性,对于电影创作者在影片色彩的使用方面提出一定的建议。
【关键词】电影色彩;娄烨;电影创作;象征;非象征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3-0060-02
一、电影的色彩
2012年,娄烨拍摄了一部探索盲人世界的影片《推拿》。必须要注意的是,在《推拿》这部影片里,我们可以隐约的发现娄烨对于色彩的应用开始进入到不同的层面,一个开始用电影色彩探索未知世界的领域,用色彩探索盲人“非色彩”的领域。归根结底,影片中出现的色彩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问题,它涉及到电影摄像的技术、电影创作者的美学意识及对于电影本身的认知,因为色彩在电影中始终以一种动态的方式进行呈现,对于色彩的控制与进行创作者式的表达就变得十分困难。(电影《推拿》以下简称“推拿”)本文认为娄烨导演在推拿中对于色彩的使用同时具备象征性与非象征性,下文将从影片中截取一些关键的片段对色彩的两种性质进行简要论述。
二、电影推拿中色彩的象征性
电影从诞生之日开始,并不涉及到色彩的问题,一切都是黑白的影像,摄影师面对眼前事物进行选择时所需要考虑的因素也较为简洁,以至于一开始电影创作者关于电影本性的争论仅仅涉及电影是物质现实的客观复原,还是利用眼前的事物进行一种主观表达的问题,也才有了这样一种观念的提出:“重要的是如何把他们的现实主义倾向和造型的努力正确地结合起来”。
当电影开始获得色彩权限之后,原来对于电影的探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动摇,如何利用色彩创作出如复制一般的现实,以及表现最新观点仍然备受关注,但人们很快就意识到色彩并非仅仅起到完全的还原现实作用,当我们看到电影屏幕上的绿色草原时,并不同于在实际生活中所看到的草原那样,而是会自然而然的受到情节的影响,当主人公兴奋的奔跑到绿色草原时,草原象征着一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希望;当主人公悲愤的跑向草原时,此时的绿色便象征着一种浩瀚的迷惘与人生不可寻,这也就是说,色彩可以跳脱普世的意义,来到一种具有象征性的境地。视觉感知是一种非常不确定,极容易受周围环境和人主观个体经验影响的知觉,极容易形成一种暧昧意味,当暧昧的感觉发生后,色彩便会发生一种象征意义,即色彩的使用符合某一种独特的意味时就会形成象征性,于是我们可以很自然地得到一个色彩象征的等式,即:色彩变化+特定时刻/人群/情景所需要的色彩经验=象征。
在推拿中有两种对于色彩的使用形成了“盲人”的视点,让普通观众能够产生一种“盲”的象征性感知。第一种为色彩对比形成盲人视觉效果,例A:在影片开头,小马在医院摔碎吃饭的碗,用碎陶瓷割喉,在该段影像中,现场明亮的白炽灯色与灰黑色模糊前景构成的色彩交叉剪辑,其实在开始阶段,看到这两种色彩首先会让人产生一种疑问,即为什么电影中的一个情节会产生两种不同的颜色,疑问过后,作为非盲人的观众首先会将白炽灯色的片段当作正常性视觉感知加以理解,因为这符合我们日常生活的真实感知经验,伴随着画外音的介绍,观众开始意识到眼前的这个人物“小马”是盲人,所以片段中的另一个灰黑色片段被观众自然地理解为一种盲人式的色彩象征。
第二种为稳定色彩的突然阻断形成盲人视觉感知的象征,例B:影片中沙复明第一次见别人介绍的对象小向,两个人坐在凳子上开始介绍自己,但是每隔10s就有跳舞的人从两人的面前走过,也就是说观众对于眼前色彩的感知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阻碍,首先要说明的是這是用一个长镜头完成的对话拍摄,只有跳舞的人从前景闪过,观众从前景里闪过的人中得不到任何的信息,所能产生的唯一作用就是对于之前色彩的阻断与消抹,我们假定两人坐在凳子上产生的色彩感知水平为1,当有一组人从前景走过时,观众对于该对话场景的色彩感知水平瞬间变为0,也就是说,观众在这个完整的长镜头中总共有五次从1变为0的感知过程,这样经验与盲人的视觉体验极为相似,当观众经过了五次的色彩出现与消失的过程后便会理解面前所做的那位盲人是如何感知面前的世界的,也就是说观众的代入感变得更强,观众能够真正地通过象征具备人物的主观视角。
三、电影推拿中色彩的非象征性使用
实际来说,电影中对于某一种色彩的使用同时具备象征性与非象征性,只不过象征意义的产生更加的依赖观者主观的视觉经验,如果观者不能拥有一般意义上的感知经验,我们认为这时象征意义是不存在的,具体的颜色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究竟象征着什么,意味着什么将变得不再重要,颜色成了一种十分具体的信息刺激,在此时一切色彩变得缺乏象征,非象征性的色彩使用将展现其规律。
从色彩学的角度上讲,衡量一种色彩有三个十分具体的尺度:色相、明度、饱和度,当三个维度的表现拥有一个数字的时候,便认为这种颜色是独一无二的,在这种情况下的色彩将不再具备所谓的意义,仅仅把其当作一种生物学上的刺激,电影创作者对于色彩的非象征性使用将不再体现其创作意图,而应当去让色彩符合影片本身所具有的色彩顺序与信息强度,也就是说观众观看影片时对于色彩的处理将不再需要观后思考,对于影片色彩的反馈是伴随着观看行为同时发生的,此时的观看行为产生另一个等式,即:色彩变化+观看行为=理解。
在这种状态下的观看,观众无须进行任何深入的思考,色彩变化本身就代表着一种理解。现在来分析影片中的一个对话段落,例C:小马与都红坐在椅子上谈论着对于爱情的定义,都红说“马路上撞着一个人是爱情,撞着一辆车是车祸”,之后小马站起来离开。在这个片段中(两人坐在凳子上聊天,小马离开)总共用了四个镜头,C1:固定变摇镜头,小马和都红两人肩并肩坐在凳子上,都红穿着白色的衣服,小马穿着蓝色的衣服,都红在讲话,镜头最后落幅到都红身上。C2:摇镜头,镜头从小马身上摇到都红。C3:都红伸手拉着小马,小马准备离开,只有胳膊入境。C4:都红脸部特写。
对于上面一个片段对其中出现的人物进行命名,将都红设置为a,小马设置为b,在C1镜头中的一开始,a与b反馈给观众的信息刺激是处于同等地位的,C1单个镜头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都红(a)与小马(b)处于画面左右两端,占据同等的位置进行对话,这样的过程持续了1分59秒,在这之后,C1镜头逐渐摇向a,b具有的色彩将逐渐提供较少的信息量,直至零。C2继续重复了C1的过程,镜头再一次从b(2秒)摇向a(5秒),直至C3镜头中b的色彩减少,完全在a身上停留8秒,C4采用特写镜头展现a的面部表情6s。从这四个镜头的安排上,我们可以发现a与b在影片一开始所展现的信息量是完全相等的,但是b在本片段末端是带着离开任务的角色,因此其在色彩安排上也就理所当然的需要进行消色,所以C2再一次快速的展现C1色彩变化过程实际上是对影片即将到来的变化所做的无声的说明,当C1与C2镜头累计叠加,突出a所能够展现的最大信息量,降低b的色彩信息量时,此时C3对于b的减色处理是极为理性的,而C4镜头又用了特写镜头强化a色彩所产生的刺激,总体上呈现出一种a色彩逐渐上升直至最强,b色彩自然撤出的过程。
在实际的观看过程中,甚至丝毫不觉得镜头的切换有任何不妥之处,因为导演通过对于镜头的安排已经展现了一个自然的减色与增色的过程,这样对于色彩的处理实际上是极困难的,是一种对于色彩表现的极致把控。
再看一个例子,例D:在这个片段中小马穿着蓝色的衣服与同样身穿蓝色衣服的小蛮在楼道里对视,位于影片结尾,该片段由五个镜头组成,D1:移动镜头,小马走到楼道,看着正在楼道里正在洗头的小蛮,D2:摇镜头,从小马半身摇到小蛮半身,D3:固定镜头,小马脸部特写,D4:固定镜头,小蛮走过来,脸部逐渐变大,D5:固定镜头,特写,小马闭上眼睛。
仍旧对于上述片段中出现的两个人物进行命名,给小马命名为c,给小蛮命名为e,在片段D1镜头的结尾,c位于画右,e位于画左,两个人物给予观众的色彩刺激处于相同的地位,即全部都十分的少,此时便认为两个元素所提供的信息量是相同的,而在D1的开头c占据着主要的位置,镜头一直在呈现c的信息,镜头D2从c的半身摇到e的半身,并在e停留较长的时间,对于e的信息量提供了一定的补偿,此时D1与D2成功地将c与e的信息提供量放到相同的位置,之后D3、D4是同等程度的色彩信息量提供,双重色彩刺激在D5镜头产生了色彩亢奋点。在这个例子中我们能够看到其不同于例C的一个属性是构建双重色彩刺激量,其中并不涉及某一个元素的减色过程,而是两个元素此起彼伏的同时强化自身的颜色刺激,在结构关系上到达一定的强度。
通过以上两个例子的分析,可以清楚看到,在对于影片色彩的非象征性使用过程中,往往不涉及主观的一种经验考量,更多地需要电影创作者对于色彩刺激的强度与频率进行深入的思考,同时根据情节进行缜密的安排,才能在单纯的视觉上形成一定的美感。
四、結论
对于电影的探索将是没有止境的,对于电影色彩的探索也将是没有止境的,就电影色彩而言,对于色彩的象征性使用将更多的涉及观看影片的主体所具有的某种特殊经验,而这种象征意义的形成也将受制于此,如果个体没有反馈,则象征无效。而对于电影色彩的非象征性使用将是一种更高级的对于电影色彩的表现方式,它可以被电影创作者把控,可以根据具体的情景进行理性化思考,从而制定应有的色彩表现程度与频率。
参考文献:
[1]王小华.《推拿》:艺术电影的群体性探索[J].电影评介,2015,000(015):6-8.
[2]朱薇.论娄烨导演艺术风格[J].电影评介,2015,(04):7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