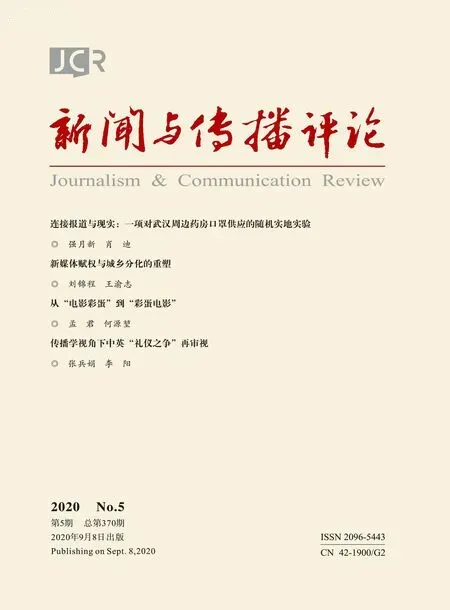从“电影彩蛋”到“彩蛋电影”
——基于超文本结构的电影再媒介现象考察
2020-09-02何源堃
孟 君 何源堃
电影中置入“彩蛋”的现象滥觞于美国。该方式经过长期发展成为好莱坞电影的一种商业策略和话语范式,并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流行起来。电影彩蛋(film Easter-egg)一词源自西方的“复活节彩蛋”(Easter-egg),复活节彩蛋原指纪念耶稣复活的基督教节日传统中的一种象征性食物,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在彩蛋中藏入礼物制造惊喜的节庆游戏。寓意惊喜和玄机的“彩蛋”被挪用至电影文本中即被称为“电影彩蛋”,它是对隐藏在电影文本中有待观众挖掘的惊喜元素的统称。电影彩蛋包括正片结束后的拍摄花絮,片末终场前附加的额外剧情或影片主体部分埋入的谜题式隐蔽线索,等等。无论以何种方式出现,观众都能从蓄意设置的彩蛋中找到惊喜,对置入和寻找彩蛋的互动乐此不疲,片尾彩蛋的魔力可以让观众继续留在座位上坚持看完乏味冗长的片尾字幕,久而久之电影彩蛋成为召唤观众的一种电影现象和文化行为。
由于电影彩蛋通常被视为一种单纯的娱乐手段和营销策略,而非电影本体意义上的结构元素和审美对象,因此学术界并未对这种似乎只是商业伎俩的电影文本变异体进行深入考察,只是基于电影营销的角度对“电影彩蛋的作用”和“电影彩蛋的设置方法”进行了研究。如尹鸿和李天语的《关于电影创作中“彩蛋”运用的若干思考》[1]主要对电影中彩蛋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分析,然后对在电影创作中的彩蛋使用给出了一定的建议;詹娜的《当前国产电影“彩蛋”研究》[2]主要分析中国当下电影彩蛋的特点和产生条件以及彩蛋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功能,并对电影彩蛋的设置给予一定建议;周獴和薛寒婓的《电影彩蛋:暗藏玄机的观众福利——以漫威电影宇宙为例》[3]则主要分析电影彩蛋对电影叙事与电影营销的作用。这些研究既没有回溯电影彩蛋诞生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也没有对电影彩蛋的本体属性进行探讨。
然而,在电影彩蛋尚未被给予特别关注和认真考察的同时,具有彩蛋集中化和文本类型化特征的“彩蛋电影”(Easter-egg film)却已经出现,并成为一种瞩目的电影现象。2017年,中国动画片《十万个冷笑话2》(OneHundredThousandBadJokesII,2017)首次汇聚了许多经典影视“梗”,受到中国动漫迷狂热追捧,被称为“脑洞系”电影代表作;2018年,美国科幻片《头号玩家》(ReadyPlayerOne,2018)内嵌数百个向流行文化致敬的彩蛋,催生了全球观众找彩蛋的热潮;同样在2018年,匈牙利动画片《盗梦特工队》(RubenBrandt,Collector,2018)因片中隐藏有大量艺术经典作品的转喻,使影片在文本的故事层读解之外,还具有考校观众艺术史知识的智识深度。这些彩蛋电影将电影彩蛋的运用拓展到不同的电影类型中,上映后俘获了大批观众,普遍形成较好的市场反响和口碑评价,表明电影中彩蛋的设置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媒介实践,鉴于电影彩蛋的传播效果和彩蛋电影的文化效应如此显著,对它们的研究无疑是必要且紧迫的。
彩蛋电影是在电影文本中集中设置电影彩蛋的一种电影形态,各种艺术或媒介的文本共同出现在某个电影文本中,形成一种电影再媒介现象。彩蛋电影具有符号堆栈和媒介融合的外部表征。电影文本融合了以超链接方式结构起来的来自电影、文学、绘画、音乐、建筑、漫画、游戏、广告、网络(如手机、博客、论坛、社交平台、线上社区)等各种媒介的文本,这种由复杂的超文本(hypertext)结构形成的彩蛋电影与采用封闭式叙事结构的传统电影存在根本区别。为了探究彩蛋电影再媒介现象的性质、成因及意义,笔者将在梳理从电影彩蛋到彩蛋电影的历史演变的基础上,分析彩蛋电影的超文本结构和再媒介化属性,并客观认知其价值功能,以此考察作为时代文化浮标的电影彩蛋热潮及其潜隐的文化逻辑。
一、从经典彩蛋到现代彩蛋:历史演变、定型与释义
电影彩蛋近年来才被观众所熟知和认可,然而追溯电影史可以发现,电影彩蛋的起源远不止于此,目前可以查证的最早的电影彩蛋在电影诞生不久后就已经出现。虽然早期电影彩蛋的设置目的与今天相比存在差别,甚至有的只是一种无心之举,但是电影史上的早期彩蛋已经具有了如今现代彩蛋的某些雏形和初级功能。
(一)早期电影彩蛋:从“莫名其诧”到策略自觉
电影彩蛋诞生于1903年,埃德温·鲍特(Edwin Porter)导演的影史经典《火车大劫案》(TheGreatTrainRobbery,1903)中出现了最早的电影彩蛋。这部仅有12分钟的短片讲述了四个劫匪抢劫火车后逃跑,最终被警察击毙的故事。鲍特在片尾有意追加了一个额外情节——当四位劫匪已经尽数伏诛,故事圆满落下帷幕后,画面中突然又出现了已经死去的劫匪头目,他面向银幕,将枪口对准观众方向连开三枪。这个额外情节便是影史上第一个电影彩蛋,它以“斯丁格”(1)Stinger原指蜜蜂尾部的针,后来被用来形象地指称电影片尾彩蛋。(stinger)的形式出现在结尾处,形成了出人意料的惊奇效果,这是早期电影导演为了突破电影表现可能性进行的摸索和尝试,但却在无意中具备了电影彩蛋的外部表征和奇观效应。
像《火车大劫案》这样在正片结束后追加一个或多个情节的“片尾彩蛋”(2)片尾彩蛋还具有tag,stinger,coda,button,mid-credits scene,after-credits sequence,end-credit scene,secret ending or credit cookie等不同的译法,主要指“在电影、电视或游戏的全部或部分字幕结束后或者在出品商标放映完之后出现的附加片段,通常用来制造幽默效果或揭示故事的续集”。详见Post-credits scene.Wikipedia,2019-11-12.[2019-12-09]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st-credits_scene。(post-credit scene)一直是最为流行的电影彩蛋设置方式,电影制作者常以这种方式在故事主体之外为观众呈上一道“餐后甜点”。在重新审视早期电影中“火车进站”式的电影原初神话时,汤姆·甘宁(Tom Gunning)认为,在电影初生的十余年间,在叙事性开始主导电影之前,早期的电影都可以被看作是“吸引力电影”(the cinema of attraction),“吸引力电影通过各种形式手段,使得影像突如其来,造成一种直接冲向观众的动态画面”[4],其目的在于对观众形成直接作用于感官的冲击性体验。《火车大劫案》片尾追加额外情节的奇观正是汤姆·甘宁所称的“莫名其诧”(cinematic dé paysement),“莫名其诧”的“吸引力”目的在于刻意制造震惊效果,虽然这种策略与现在所说的电影彩蛋在形式上非常相似,但两者的目的和功能有一定的差别。比较而言,《火车大劫案》中的彩蛋是诉诸感官“吸引力”的“火车效应”变体,现在的片尾彩蛋则完全是出于娱乐大众和商业目的所设,因此其目标不仅诉诸视觉感官刺激,还包括扩展故事、放映花絮、致敬经典、推广明星、宣传续集等。正因为早期片尾彩蛋的功能较为单一,这种不自觉的彩蛋形式被迅速抛弃,虽然后来在叙事性电影中偶尔使用,但直到1979年才以商业自觉的方式出现在《布偶电影》(TheMuppetMovie,1979)中。在《布偶电影》的片尾字幕结束后,画面中又突然出现了一只布偶,向观众大叫:“该回家了!该回家了!拜拜!”这个彩蛋与《火车大劫案》的片尾彩蛋的区别在于,它被字幕分隔后与影片主体部分完全分离,可以看作是对坚持看完字幕的观众的额外犒赏,因此具有了鲜明的商业诉求指向。
电影彩蛋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节点是从片尾彩蛋的单一形式向片中彩蛋等多元形式的转变,希区柯克标志性的“希式客串”(Hitchcock cameo)是最早的“片中彩蛋”(Easter egg in film),它是电影彩蛋从“莫名其诧”的无心之举走向策略自觉的开端,也是彩蛋设置方式多元化的起始。在希区柯克的第二部影片《房客》(TheLodger,1927)中,他以客串的方式饰演了一名在报刊收发室背对观众打电话的记者,自此以后,几乎在希区柯克导演的所有影片中他都会以这种方式出现在电影中不经意的角落。希区柯克在与特吕弗的对谈中承认了这种设置策略的自觉性,他说:“严格来说,这是功利性的,我们必须要填满银幕。后来这就变成了一种执念,并最终成了一种噱头。”[5]中国早期电影中也有类似的电影彩蛋,例如在孙瑜拍摄的《小玩意》(1933)中,著名作曲家聂耳就在其中客串了一个卖臭豆腐的小贩的角色。在袁牧之导演的《都市风光》(1935)中出现的片中彩蛋则具有更强的指涉性,在这部影片的片头部分出现了几组石狮子的镜头,包括狮子的俯卧、抬头与吼叫,这一段内容明显是对爱森斯坦《战舰波将金号》(Броненосец Потёмкин,1925)中以石狮子醒来寓意人民觉醒的蒙太奇镜头的有意借鉴,可以看作是“致敬式”的片中彩蛋。但是在当时《战舰波将金号》没有在影院公开放映,只在“南国电影剧社”小范围放映,因此《都市风光》中的这个彩蛋很难被大多观众识别,没有实现“彩蛋”的真正功能。此外,在《马路天使》(1937)中有一些因无心之举形成的片中彩蛋,这些彩蛋出现在糊墙的报纸布景上,以电影宣传广告的形式出现,如《孤城烈女》(1936)、《生死同心》(1936)等。这些彩蛋并非是有意置入,所以大多比较隐蔽,观众往往也难以察觉。总的来看,早期“片中彩蛋”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与观众之间约定俗成的设置和寻找互动游戏为观众带来了捉迷藏一般的乐趣,使电影彩蛋真正产生“惊喜”而非“惊诧”的效果。同时,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使电影彩蛋从片尾游弋至影片的主体部分,激活了彩蛋设置的无限可能性,给予后来的电影彩蛋设置极大的启发性。
(二)游戏推动和电影彩蛋的现代转向
无论是《火车大劫案》的片尾彩蛋,还是希区柯克式的片中彩蛋,都属于早期的经典电影彩蛋。受制于早期电影产业的商业成熟度,经典电影彩蛋大多缺乏明确的商业意识,受制于早期观众较为匮乏的知识素养,经典电影彩蛋往往难以被一般观众发掘,加之经典彩蛋的设置大多没有超越文本自身的叙事话语范畴,只要联系故事的整体情节就能理解彩蛋的意义,因此早期电影彩蛋始终处于断断续续的不稳定发展中。随着广播电视网络等现代媒介的发展,信息传递的地域被逐渐打破,人们的知识储备更加丰富,这为彩蛋的理解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文化土壤,在此基础上现代电影彩蛋才得以诞生并普及。与经典电影彩蛋相比,晚近的现代电影彩蛋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娱乐手段,其设置和寻找更为复杂,此时观众不仅要在电影文本中寻找彩蛋,还要在超出电影文本范畴之外的众多泛文本中读解彩蛋。
经典彩蛋和现代彩蛋有不同的起源,经典彩蛋始于电影,现代彩蛋则来自另一种视觉媒介——电子游戏(3)美国电影《洛基恐怖秀》(The Rocky Horror Picture Show,1975)中出现的“彩蛋”常被认为是最早的现代电影彩蛋,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读。笔者通过资料查证发现,该片的拍摄时逢复活节,剧组便在片场举行了寻找彩蛋的节庆活动,但是节庆结束后被藏起的彩蛋没有被完全找回,剧组继续拍摄时有彩蛋意外进入电影画面中。这一轶事被Behind The Scenes Stories From The Rocky Horror Picture Show等文所记载和传播,遂被误认为在这部电影中出现了最早的现代电影彩蛋。笔者对电影文本进行细读后发现,影片中所谓的彩蛋全是鹅蛋般的白色物体,没有设置和意义的指向性,只是单纯的隐藏元素,与电影的穿帮镜头没有实质区别,因此不能算是真正的电影彩蛋。。现代彩蛋会诞生于电子游戏并不令人意外,因为电影彩蛋的原型就是宗教节日游戏。游戏的基本特征是互动性,彩蛋不过是游戏用于强化自身互动机制的一种策略,事实上互动性后来也成为电影彩蛋最主要的特征,而游戏也善于借鉴电影的某些优长,“常常利用电影的各个层面,为玩家所进行的活动制造更多的意义并促进共鸣”[6]。
1977年,电子游戏尚处于初生期,具有自觉性和互文性的现代彩蛋就已经出现在游戏《星际战船》(Starship1,1977)中。在这款由雅达利(Atari)公司发行,基于JUL-77型号街机运行的游戏中,玩家通过特定的操作触发“HI RON!”(4)“RON”是游戏《星际战船》的设计师Ron Milner,他将自己的名字设计成特定的代码置入游戏中,并附加10条命作为玩家发现这个彩蛋的奖励。详见Chasing the First Arcade Easter Egg,edfries,2017-03-22.[2019-12-10]https://edfries.wordpress.com/2017/03/22/chasing-the-first-arcade-easter-egg/。字幕便可以获得10条免费的命,这个简单的互动环节是第一个游戏彩蛋,也是第一个现代彩蛋。游戏彩蛋后来能够得到推广和普及,得益于雅达利公司的游戏设计师沃伦·罗宾耐特(Warren Robinett)的抗争。1979年,缺乏游戏开发经验的雷·凯萨(Ray Kassar)被提升为雅达利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他主张在雅达利的游戏盒带上删除游戏制作者的名字,只留下公司的标识。设计师罗宾耐特为了反抗这种非人性化的要求,在自己设计的游戏《冒险》(Adventure,1979)中设置了一个隐藏关卡,当玩家无意闯入就能发现“Created By Warren Robinett”(沃伦·罗宾耐特制作)字样的字幕,从而留下了游戏制作者的署名。正是罗宾耐特的这一叛逆行径真正将彩蛋推广开来,此后无数的游戏和影视作品效仿这种潜藏式的彩蛋设置方式制造惊喜和互动效果,大量的著名电影彩蛋也相继出现。譬如,《夺宝奇兵》(RaidersoftheLostArc,1981)中印第安纳·琼斯抬起法老的棺盖时旁边柱子上雕刻的“C-3PO”和“R2-D2”(5)该彩蛋指向电影《星球大战》(Star Wars,1977),C-3PO和R2-D2是电影《星球大战》中的两个机器人角色。;《电子世界争霸战》(Tron,1982)中隐藏在雷达四周网格线间的“吃豆人”(6)该彩蛋指向游戏《吃豆人》(PAC-MAN,1980),吃豆人是万代南梦宫(Namco)公司推出的经典街机游戏《吃豆人》中玩家操控的角色。;《玩具总动员》(ToyStory,1995)中出现在卧室钟表上的“米奇”(7)该彩蛋指向“米奇动画片”,米奇(Mickey Mouse)是迪士尼经典动画角色,首次出现是在《汽船威利》(Steamboat Willie,1928)中。;《冰雪奇缘》(Frozen,2013)中在艾尔莎加冕礼上混在宾客中间一闪而过“乐佩和雷德”(8)该彩蛋指向电影《魔发奇缘》(Tangled,2010),乐佩(Rapunzel)和雷德(Flynn Rider)是这部迪士尼动画电影中的两位主角。等等。正如福斯特所言:“各种艺术越发展,互相交流定义的机会也越多。”[7]从1979年开始,作为一种效果明显的游戏策略,“彩蛋”随着电子游戏的蓬勃发展被逐渐运用到包括电影在内的其他媒介域。在电影中,彩蛋的设置发展得更为复杂,开始溢出影片原始文本的内容,形成超文本链接关联起巨大文本网络,指涉当代文化场域中诸多媒介的内容,这就是电影彩蛋的现代转向。

(三)电影彩蛋的概念释义和文本间性
基于以上对经典彩蛋和现代彩蛋的历史梳理可以发现,电影彩蛋经过长期发展已成为一种日渐自觉的和成熟的电影现象,据此对电影彩蛋做如下概念界定。所谓电影彩蛋,就是有意设置的、居于故事主体之外的、有待观众挖掘的惊喜元素的统称。具体来说,电影彩蛋应具备如下特征:电影彩蛋的设置是一种商业策略,这一策略具有游戏性和互文性;彩蛋的发现与否并不影响影片的叙事,对彩蛋的寻找和捕捉必须在电影故事的接受之外“有所付出”;彩蛋的发现和读解能带来惊喜和成就感,但受到彩蛋数量和能指形变程度的制约,还受到发现者的感知能力和既有知识经验的制约;惊喜元素必须居于影片主体之外,是故事的边缘或话语的外延。
在上述特征中,电影彩蛋的本质特征是具有“文本间性”或“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里所说的文本间性是指彩蛋的意义必须指向阈限性文本,即某个单一文本或者多个关联文本,并与之发生意义指涉。有的彩蛋指向自身的单一文本,例如《火车大劫案》中劫匪复活的片尾彩蛋指向自身文本,通过对自身符码的揭示起到了麦茨所说的“自我反思”[8]作用。更多的彩蛋指向其他单一文本或多个关联文本,例如《复仇者联盟3》(Avengers:InfinityWar-PartI/II,2018)的片尾彩蛋指向的是漫威随后推出的衍生电影《惊奇队长》(CaptainMarvel,2019);《乐高大电影》(TheLegoMovie,2014)中的蝙蝠侠乐高人指向的是处于互文本网络中的一系列“蝙蝠侠”(Batman)漫画、影视和游戏;《天龙特攻队》(TheA-Team,2010)中莫多克大喊的“Freedom”指向的是电影《勇敢的心》(BraveHeart,1995)。当然,也存在与上述案例相反的情形,一些在文本中设置的情节不具有文本间性,比如《小银幕大电影》(TheKentuckyFriedMovie,1977)中嘲弄好莱坞类型片的一些情节就不能算作彩蛋,因为它指向的是不具有明确定位的泛文本,无法建立实质上的互文关联。
此外,读解电影彩蛋的基础和必要条件是观众的感知能力和知识经验,来自诸多信息源、覆盖广泛知识面的电影彩蛋能否被观众准确理解必然受到观众感知和理解能力的制约。无论是单一文本的简单关联还是多个文本的复杂链接,彩蛋只有被观众感知的状态下才具有价值,如果只是置入文本之中,却没有被观众所感知或者感知后未能识别文本间性的意义指涉,那么彩蛋的设置就成为无效的策略。事实上,电影彩蛋通常只能与部分观众产生互动,年龄、职业、爱好等因素都会对彩蛋的传播效果产生影响。因此,电影彩蛋与观众的知识经验必须匹配,否则彩蛋的设置会失效。
综上所述,从1903年至今,电影彩蛋的发展历经早期的经典彩蛋时期和晚近的现代彩蛋时期。早期的经典彩蛋包括片尾彩蛋和片中彩蛋两种较为简单的形式,经过游戏设计和推广后实现现代转向,变成现代彩蛋,由此彩蛋的形式和功能稳固下来,最终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电影现象。电影彩蛋的内涵和属性都已十分明确,现代转向后的电影彩蛋是一种自觉的和成熟的商业策略和话语范式,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彩蛋电影”这一新的电影形态。
二、作为“理想类型”的彩蛋电影:超文本结构与再媒介属性
“彩蛋电影”(Easter-egg film)是聚集了大量彩蛋的电影,21世纪以来出现了许多典型的彩蛋电影,譬如《惊声尖笑》(ScaryMovie,2000)、《我的巨型独立电影》(MyBigFatIndependentMovie,2005)、《史诗电影》(EpicMovie,2007)、《乐高大电影》(TheLegoMovie,2014)、《港囧》(2015)、《缝纫机乐队》(2016)、《十万个冷笑话2》(2017)、《头号玩家》《无敌破坏王2:大闹互联网》(Wreck-ItRalph2:RalphBreaksTheInternet,2018)、《盗梦特工队》《死侍2:我爱我家》(Deadpool2,2018)等。从电影产业维度来看,彩蛋电影是电影彩蛋的集中化,它体现出彩蛋在电影制作和电影营销中的运用已进入成熟阶段;从社会发展维度来看,彩蛋电影的出现体现了整个社会文化取向和审美趣味的变化,碎片化和互动式的娱乐习惯让观众能够把握到彩蛋电影中一闪即逝的隐蔽线索,网络时代信息的海量增长则使观众能够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去理解所捕捉到的电影彩蛋。由于“彩蛋电影”是一种处于发展初期和急剧变动中的电影现象,笔者将彩蛋电影视作具有相对性和暂时性的“理想类型”(12)“理想类型”是马克斯·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书中提出的研究社会行动的方法。理想类型主要起到作为一个立足点和坐标系启发研究者进行现象观察的作用,它可以是片面、纯粹的,没有对错之分也没有严格界限,主要价值在于激发后续研究。参见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xix-xxiv.安东尼·吉登斯,菲利普·萨顿.社会学基本概念.王修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38-41。(ideal type)加以研究,“理想类型”是韦伯提出的“文化科学认识经验实在的特有方法”,笔者借用此方法以探究其结构和属性。作为电影活动的一种“理想类型”,彩蛋电影借由超文本结构和再媒介属性与其他电影现象区别开来,它以电影彩蛋作为基本元素,通过超链接的方式对彩蛋文本进行结构,并具有再媒介化的媒介融合属性。
(一)超文本:彩蛋电影的文本网络结构
在彩蛋电影中,大量彩蛋的积聚在一起并不只是发生量变,而是产生意义的质变,这既是彩蛋电影对电影彩蛋的超越,也是彩蛋电影与电影彩蛋的本质区别。在严格意义上,电影彩蛋不能算作超文本,由于数量有限、分布零散,电影彩蛋只是具有超文本特性的独立存在的文本,而彩蛋电影中的彩蛋是高度灵活且可自由读取的文本符码,因此是能与其他互文本构成文本网络的超文本单元。超文本最初是用以建构一个非线性的文本网络供读者进行互动式的分享和选择,是一个“连接语言信息与非语言信息的信息媒介”[9],当彩蛋在单一文本中大量聚集,彩蛋和彩蛋之间就摆脱了独立性,以互文的方式超越电影文本在泛文本中建构关联性的文本网络,形成“影像超文本”这一彩蛋电影的“理想类型”。
对具有超文本结构的彩蛋电影来说,彩蛋必须在单个电影文本中大量出现并且彼此联结为网络,才能实现从文本向超文本的飞跃,因此超文本是彩蛋电影形成文本网络的结构方式。超文本是一种复合物,它既是实存的文本聚合域,也是复杂网络的一个节点。超文本具有鲜明的结构特征,它“基于自身的互动性形成了树状分支结构和如同被许可的选择一般的多线性”[10],彩蛋电影也有树状或多线性等结构。譬如《无敌破坏王2:大闹互联网》中出现的彩蛋,除了大量迪士尼影视作品外,还有《街头霸王2》(StreetFighterII,1991)、《VR特警》(VirtuaCop,1994)、《太空侵略者》(SpaceInvaders,1979)等电子游戏,以及微博、天猫、猫眼、谷歌(Google)、亚马逊(Amazon)、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维基百科(Wikipedia)、油管(Youtube)等互联网公司,还有“不爽猫”(Grumpy Cat)(13)不爽猫(Grumpy Cat)原名塔妲·索斯(Tardar Sauce),是美国亚利桑那州一只天生“臭脸”的杂交猫,在2012年因为被主人将其照片上传而在Reddit网站贴图区而走红。经过经纪人本·拉希什(Ben Lashes)的经营,不爽猫参加了各种节目,并衍生出许多周边产品,至2014年其身价达到6400万美元。、“吼叫山羊”(Yelling Goat)(14)吼叫山羊(Yelling Goat)出自Youtube博主Smooth Feather在2007年11月30日上传的名为Man Goat的视频,视频中一只山羊被绑住不停地咩咩叫,后来这段视频被无数视频制作者用来制作搞笑视频,其中最为知名的是美国歌手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的歌曲I knew you were trouble的MTV恶搞版本。、“甩手舞”(The Floss)(15)“甩手舞”(The Floss)出自2017年5月21日的美国电视综艺节目《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在节目中,歌手凯蒂·佩里(Katy Perry)对自己的新单曲Swish Swish进行宣传,为其伴舞的一个背包男孩凭借“魔性”的甩手舞蹈意外走红,随后被无数人竞相模仿。、“魔鬼辣椒挑战”(Ghost Pepper Challenge)(16)辣椒挑战(Hot Pepper Challenge/Ghost Pepper Challenge/Chili Pepper Challenge)是在美国社交媒体上流行的一项挑战游戏,始自喜剧网站Rooster Teeth2011年11月5日上传的“魔鬼辣椒挑战”视频,其内容是挑战者吃掉各种高辣度的辣椒并拍下视频,此后吸引大量网民参与该游戏。等网络热点,它们彼此之间构成了复杂的多线性结构。
彩蛋电影超文本结构的原型是电子超文本。电子超文本是用于建构非线性文本网络的互联网语言和技术,它引发了人的思维机制和技术的工具逻辑之间互为掣肘的争议。1945年,美国科学家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在《正如我们思维所至》(AsWeMayThink)一文中呼吁,应在人类思维活动和现存的海量知识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同时提出了超文本的元理论——记忆扩展器(Memex),随着技术的进步布什的概念构想演变为“仙都项目”(Xanadu)、“NLS联机系统”(Non-linear System)、“超文本编辑系统”(Hypertext Editing System)和“白杨镇电影地图”(Aspen Movie Map)等技术实体,甚至形成了基于万维网(World Wide Web)的覆盖全球的超文本网络。然而,由此产生的一个巨大悖论是,布什高度赞扬人类智识活动的能动性,但随着计算机科学和通信网络的飞速发展,人的这种能动性却完全被电脑所代替。在电子超文本网络中,技术的工具逻辑战胜了人的能动性,人的作用被完全剥夺,人造物将人的主体性排除在外。
相较而言,在艺术领域,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在超文本中仍发挥重要作用。彩蛋电影是典型的艺术超文本网络,它既是罗兰·巴特所说的可供话语扩展的“树状结构”[11]的起点,也是雅克·德里达所说的指向不在场源头的“解中心”(décentrement)[12]。彩蛋电影的超文本结构不像网络页面和游戏界面那样通过数字通路进行字节跳转,而是锚定彩蛋构成的符号或符号组进行“超链接”(hyperlink),然后依靠人的思维进行文本跳转。也就是说,在电子超文本中,假如打开一个电影介绍的网页后想要继续了解这部电影的导演,那么只需要点击带有超链接的导演姓名或是隐藏有超链接的导演照片,然后就能跳转到导演介绍的网页界面中。在这个过程中,人是机械的,仅仅是在思维的停滞中充当了“传感器”(transducer),“在‘构架’的技术化含义中,生命的一切领域普遍地被卷入‘技术化’的潮流……人已无法控制信息交流的过程”[13],人沦为技术的附庸。但是,在彩蛋电影中,人的能动性是文本的决定力量,作为超文本结合点的实体超链接被思维超链接取代,符号以意义互文的灵活方式发挥了超链接的功能,人的思维代替数字通路,以人脑的记忆和想象代替互联网数据库,完成互文本联结。因此,在《头号玩家》《无敌破坏王2:大闹互联网》《死侍2:我爱我家》等彩蛋电影中,超文本的形态是不可见的,文本之间的互文链接存在于接受者的思维之中。
然而,正是由于彩蛋电影高度依赖接受终端,假如观众未发现彩蛋电影中的彩蛋,那么彩蛋电影就会成为一种抽离掉互文意义的“零度文本”,复归文本的初始状态。例如,当在《头号玩家》的“绿洲”大决战中看到混杂在人群间的“猎空”(Tracer)角色时,观众会下意识搜索自己的记忆存储,如果玩过网络游戏《守望先锋》(Overwatch,2016),那么他/她会想到“猎空”正是出自这款游戏中的角色,这时电影文本和游戏文本就通过彩蛋实现了联结。相反,如果观众不了解《守望先锋》这款游戏,那就无法体验到电影和游戏发生互文关联的惊喜和乐趣,观众会将她当作一个普通的电影角色来对待,因为她在叙事功能上与混战人群中其他的龙套角色并无二致,只是一个“零度文本”。因此,彩蛋是彩蛋电影中最基本的结构元素,它是文本网络中具有“总体性和过剩性的双重符号”[14],既在文本内发挥独立的符指作用,同时还在文本外进行互文指涉,建构出超文本的网络结构。
(二)再媒介:彩蛋电影的媒介融合属性
当彩蛋电影被视为文本时,电影文本是故事的载体,包括彩蛋在内的所有电影元素都以叙事和表意为中心进行组织和结构。当彩蛋电影被视作媒介时,彩蛋则可以根据信息源的特性进行组织和融合。彩蛋电影中彩蛋的设置较少受到相应规则的限制,具有较高的自由度与任意性,因此可以说彩蛋是一种没有语言的言语。即使作为无互文性的“零度”情节,彩蛋也本就是负载原始信息的符号媒介,当通过互文链接产生新的信息时,彩蛋就成为融汇其他媒介信息的再媒介(remediation),作为“理想类型”的彩蛋电影也因此成为一种电影再媒介化的新型融合媒介。
巴赞提出的“电影是什么?”是一个持续追问却充满争议、永无定论的永恒命题。电影是“窗户”“画框”“镜子”,电影是商业、艺术、技术,电影也是媒介。1924年,贝拉·巴拉兹(Béla Balázs)在《可见的人——电影文化》中旗帜鲜明地指出电影是一种具有工具性的信息中介,他说:“电影与印刷术一样是大量复制和传播精神产品的工具。”[15]同样在1924年,中国电影人也认识到电影的媒介属性,周剑云和汪煦昌在昌明电影函授学校的授课讲义中呼吁:“影戏虽是民众的娱乐品,但这并不是它的目的……请莫忘影戏宣传之能力!”[16]除了宣传功能之外,两人还讨论了电影的“通俗教育”“增广见闻”“帮助演讲”等功能,这些都是电影媒介的功能体现。正是基于电影固有的这些媒介属性,电影才能实现再度媒介化的媒介融合,而不是成为一种“新媒介”。
大卫·博尔特(David Bolter)和理查德·格鲁辛(Richard Grusin)提出再媒介理论时指出,“再媒介”是具有数字“引得性”(indexicality)的“超媒体应用”(hypermedia application),其作用在于“将较早的媒体导入数字空间以便批评并改造他们”[17],因此“再媒介”是一个由新媒介力量导致的旧媒介改造过程。基于这一理论,当下电影“再媒介”现象普遍集中在数字技术导致的“以像素为基本单位的数字生成方式”[18],这种数字生成方式导致了电影创作方式的改变和新电影形态的形成。数字技术催生的电影再媒介现象本质上是电影的技术更迭和跨媒介互动,彩蛋电影中的再媒介现象则是内容主导的媒介重构,它不借助技术或其他外部因素,而是基于不同媒介的文本链接对电影媒介进行再度激活和塑造。譬如在《盗梦特工队》中,观众的思维跟随街道上没有指针的钟表跳转到伯格曼的电影《野草莓》(Smultronstället/Wildstrawberries,1957),通过房间里倒置在凳子上的车轮跳转到杜尚的艺术作品《现成的自行车轮》(BicycleWheel,1913),通过展馆内墙上的巨幅好莱坞海报跳转到拉斯查的波普艺术作品《好莱坞》(Hollywood,1969),通过栈桥上惊叫的少女跳转到蒙克的画作《呐喊》(Skrik,1893),通过瓶身上印刻的裸体男子跳转到罗丹的雕塑《青铜时代》(AgeofBronze,1877)……可见,具有超文本结构的彩蛋电影所勾连的媒介类型和产生的互文信息都是惊人的,这便是彩蛋电影再媒介化的传播效果。
彩蛋电影再媒介化的特点是,它是完全凭借彩蛋设计者和接受方的思维互洽和游戏互动而实现的媒介融合。在《头号玩家》中,各种人气超高的游戏是影片的叙事主体,同时电影文本还汇集了大量的流行歌曲、电影、动画、电视等其他媒介的彩蛋,这是彩蛋的设计者斯皮尔伯格和深谙游戏与大众文化的观众进行的一场规模庞大的跨媒介互动游戏。电影再媒介诞生的土壤是当代文化场域中已普遍存在的跨媒介实践,正是跨媒介的文化趋向促使彩蛋电影这样的新型融合媒介形态诞生,这是数字技术产生信息流和融媒体后才会出现的结果。与彩蛋电影一样,数据库电影(database cinema)、桌面电影(computer screen film)、交互电影(interactive film)、监控电影(surveillance cinema)、谜题电影(puzzle film)等不断涌现的电影新形态都是基于技术革新而产生的电影变革,技术的决定性力量使得电影的媒介性质愈加凸显,这些电影新形态的媒介工具性远远高于其内容生产和审美功能。克拉考尔说:“电影——我们的同龄者——跟诞生它的那个时代有一种明确的联系;它迎合了我们内心最深藏的需要,这正是因为它可以说是破天荒第一次为我们揭示了外在的现实。”[19]的确,电影与社会现实总是相互映照,技术是一个正在崛起的社会现实,彩蛋电影的超文本结构和再媒介属性反映了技术对电影的影响甚至是控制,电影的工具化、媒介化、功能化、游戏化等现象是技术作用于电影的结果,这也是对包括彩蛋电影在内的诸多电影新形态应保持警惕的原因。
三、彩蛋电影的文化价值:心智游戏与意义再生产
对于技术主导的现代社会,法兰克福学派持激烈的批判立场。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生产和分配的技术装备由于日益增加的自动化因素,不是作为脱离其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的单纯工具的总和,而是作为一个系统来发挥作用的。这个系统不仅先验地决定着装备的产品,而且决定着为产品服务和扩大产品的实施过程。在这一社会中,生产装备趋向于集权性的,它不仅决定着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能和态度,而且还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愿望。”[20]于是,工业社会中的人日趋成为“单向度的人”,人被物质所宰治,失去了主体性。与法兰克福学派相比,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对现代社会的批判立场相对温和,斯图亚特·霍尔把受众的解码行为区分为“支配—霸权”“协商”和“对抗”三种立场,认为受众并非完全被媒介所支配和驱使,而是具有一定的协商甚至反抗的能力。彩蛋电影是典型的大众文化产品,如果说传统电影是基于技术极权主义的单向线性传播,那么彩蛋电影则是具有反馈的双向互动传播,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说,彩蛋电影具有霍尔所说的“协商”和“对抗”的可能。尽管彩蛋电影或许仍然是通过技术控制实施文化霸权的媒介,但是彩蛋电影在电影内容和生产方式上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沿着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思路可以从中发现它的独特文化价值。
(一)提供互动的心智游戏
彩蛋电影在电影内容上的变革和贡献是为观众提供了互动性的心智游戏。互动性强调受众导向,需要激发观众的主动性,因此彩蛋的设置从少量、简单变得大量、不可预测,不可预测的彩蛋极大地提升了观众的观影期待。对彩蛋电影来说,超文本“最有趣的不是其静态属性(如文本中有多少行或它占用了多少字节),而是与电子文本的延展性相关的某些属性。这些属性将不可预测性注入到作品中”[21]。当这种不可预测性与彩蛋电影固有的受众导向相结合,它的文本延展性和吸引力甚至超过了电子超文本。因为数字通路必然遵循共有的理性逻辑和运算规则,这决定了电子超文本的不可预测性必然是有限的,但对彩蛋电影超文本来说,不同观众的经验存储、认知能力和思维能力却千差万别,这决定了彩蛋电影的超文本制造的不可预测性是海量的。例如,《头号玩家》中隐藏了至少有“170个彩蛋”[22],这些彩蛋涵盖游戏、电影和歌曲等各种类别的艺术和媒介文本,这些文本所属时代的时间跨度也很大,个体意义上的观众大多无法完全感知并理解,因此每个观众所接受到的文本数量和组成的超文本网络都有所不同。
彩蛋电影的不可预知性与游戏的魅力相似,彩蛋电影中的彩蛋是一种具有指向性和召唤性的目标,每一个彩蛋都构成一个实现单元,寻找彩蛋就成为持续闯关的游戏。伽达默尔说:游戏就是“不断自我重复着的运动的反复”[23],彩蛋电影正是凭借它可以重复观看且感知益新的复杂超文本而成为一种具有游戏功能和属性的电影。但是,彩蛋电影与交互式的视频游戏(video game)不同,在彩蛋电影中寻找彩蛋是原初意义上的“游戏行为”(play),而非交互式电子媒介中的“游玩行为”(game),它是赫伊津哈所说的“文化中固有的游戏成分”[24],只是在电影中被彩蛋重新激发。其独特之处在于,它保有电影的独立性和封闭性,所以不需要借助电脑、手机等中介辅助进行互动,完全依靠“银幕—观众”的封闭结构完成由观众主动参与的心智游戏。可以说,彩蛋电影不是实在的游戏行为,是观众依靠“意向”(intentio)在头脑中显现的游戏现象,在本质上它仍旧是以电影为中心的、发生在银幕上的符号嬉戏和文本交互。
作为一种心智游戏,彩蛋电影的互动机制与电子游戏也有所不同。电子游戏有两种互动机制:第一种是人际互动,这是网络游戏(online game)和多人联机游戏(muti-player game)的主要互动方式;第二种是人机互动,这是单机游戏(singe-player game)的主要互动方式。电子游戏的两种互动机制都依赖可供身体参与的实体媒介发生作用,游戏玩家与电子游戏媒介的关系符合麦克卢汉的“媒介延伸论”,玩家的思维被媒介的技术逻辑缝合到游戏机器中,将游戏装置的传感部件当作肉体的延伸,将处理器当作意识的中心,最终人的自我在互动架构中被电子媒介所取代。比较而言,彩蛋电影没有将观众投射到媒介中,它甚至是反技术的,因为被发现的彩蛋从文本中脱离出来产生出间离效果,庞大的超文本系统会放大这种间离效果,提醒观众这是心智游戏而非沉浸式游戏。因此不难理解,即使《头号玩家》的3D视效呈现了充满未来感的游戏世界,观众仍旧不会沉迷其中,反而通过对影片中游戏彩蛋的读解保持充分自省,反思游戏是否存在缺陷。此外,彩蛋电影的互动对象只有文本,它不需要人机互动和人际互动,因此观众可免于臣服游戏复杂的技术规则,同时也免于游戏失败所带来的“陷落在极度的无助之中”[25]的挫败感。
彩蛋电影的游戏互动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观众在文本中搜寻彩蛋,第二阶段是观众通过调动认知经验识别并读解彩蛋。对彩蛋电影的搜寻、识别和读解的过程就像解开一道道谜题,谜题设置的难易度和谜底揭示的成就感具有正相关性。即使是位置相对固定的片尾彩蛋也有需要揭开的谜题,彩蛋位置的固定只是简化了寻找环节,读解过程还是需要观众自己完成。彩蛋谜题的读解是具有一定难度的游戏,且不说漫威电影中的片尾彩蛋必须掌握“漫威电影宇宙”(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或漫威漫画史的知识才能完全读解,即使是花絮式的彩蛋,也需要观众在头脑中迅速搜索刚看完的电影主体部分,将花絮与电影中的情节进行关联对照,才能领会到彩蛋的设置意图。
麦克卢汉曾说:“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时代都有它喜欢的感知模式和认知模式,所以它都倾向于为每个人、为每件事规定一些受宠的模式。我们时代的标记,是厌恶强加于人的模式。”[26]彩蛋电影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受宠的模式”,就是因为它完全激发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它设置的游戏不强加给观众,只是等待观众来选择和识别。因此,彩蛋电影所提供的观众参与互动的心智游戏,不是“支配—霸权”式的编码解码模式,人的主体性在游戏中可以得到“协商”式甚至是“反抗”式的呈现,当彩蛋电影能够覆盖足够的电影类别时,观众便能够在游戏互动的过程中对人与社会进行一定的自反性审视。
(二)媒介的意义再生产
除了通过不可预测的心智游戏激发观众的自主性之外,彩蛋电影还具有一个重要的价值,就是通过再媒介进行意义再生产。彩蛋电影的意义再生产是电影文本对其他文本的意义进行关联后的再生产,电影文本融合电影、文学、绘画、音乐、建筑、漫画、游戏、广告、网络(如手机、博客、论坛、社交平台、线上社区)等媒介的文本,从而使得彩蛋电影这种超文本的意义远超于单个文本。譬如在《盗梦特攻队》中,出现的彩蛋包括《维纳斯的诞生》(TheBirthofVenus,1487)、《倒牛奶的女佣人》(TheMilkmaid,1658)、《邮差约瑟夫·鲁林》(PortraitofthePostmanJosephRoulin,1889)、《拿水果的妇女》(WomenHoldingaFruit,1893)、《白底上的白色方块》(White-on-white,1913)、《泉》(Fountain,1917)、《交织字母》(Monogram,1955-1959)、《八部半》(8,1963)、《双面猫王》(DoubleElvis,1963)、《教父》(TheGodfather,1972)、《低俗小说》(PulpFiction,1994)、《雨果》(HugoCabret,2011)等各类艺术和媒介作品,文艺复兴以来的大量艺术经典文本在此被聚合式呈现。如此多样的跨媒介文本融合后形成《盗梦特攻队》这个电影超文本,这个巨型电影文本不但具有巨大的信息量,并且因为聚集大量意义丰富的文化样本而成为当代文化意识形态的拼图。由于再媒介化使“新媒介从旧媒介中获得部分的形式和内容,有时也继承了后者中一种具体的理论特征和意识形态特征”[27],因此彩蛋电影的意义再生产既是内容信息上的互文链接,更是各种文化意识形态的交汇和重新编码。从这个意义上说,彩蛋电影的意义再生产不是阿尔都塞所说的由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支配的“生产关系再生产”[28],而是对既有文化进行梳理归纳和重新编码的“生产条件再生产”。
爱德华·霍尔认为,“文化的功能之一,是在人与外部世界之间提供一个选择性很强的屏障。在许多不同的形态中,文化选定我们要注意什么,要忽略什么。这种筛选功能为世界提供了结构,保护着神经系统,使之免于‘信息超载’(Information Overload)。”[29]既有文化的符号标识勾勒出各自的边界,彩蛋电影中的彩蛋却通过超文本的强行链接打破上述边界,通过重新编码建构出一个新的“符号域”,这无疑是关于当代文化生产条件的再生产。例如,在《十万个冷笑话2》中出现的彩蛋包括《喜羊羊与灰太狼》《熊出没》《大圣归来》《大鱼海棠》《阿拉丁》《蓝精灵》《哆啦A梦》《银河英雄传说》《巴啦啦小魔仙》《美少女战士》等诸多经典动画,打破来自不同时代和地域的文化边界,构筑出一个新的当代动画文化景观。在《缝纫机乐队》中,出现的彩蛋包括“唐朝乐队”“鲍家街43号乐队”“痛仰乐队”“新裤子乐队”“面孔乐队”“黑豹乐队”“二手玫瑰乐队”“麦田守望者乐队”等国内著名乐队,这些乐队的风格横跨“硬摇滚”(Hard Rock)、“重金属”(Heavy Metal)、“雷鬼”(Reggae)、“激流金属”(Thrash Metal)、“新浪潮”(New Waudio-videoe)、“视觉系摇滚”(Visual Rock)、“英式摇滚”(Britpop)等多种风格,共同交织出当代中国摇滚文化的总体性和多样性面貌。此外,前文提到的拼贴了大量互联网文本的《无敌破坏王2:大闹互联网》则是通过重新编码文化热点,呈现出极客文化(geek culture)的审美趣味。
彩蛋电影的意义再生产价值不止于对不同文化的拼贴和重新编码,在上述过程中彩蛋电影还能对所关涉的文化进行审视、肯定或贬抑,这是更为重要的意义生产。以《头号玩家》为例,虽然影片通过丰富多样的彩蛋呈现了一部流行文化史,尤其是游戏文化史,但是影片没有对游戏进行盲目的颂扬。恰恰相反,影片通过对游戏最终目的的反思对游戏进行重新审视,影片中有大量意味深长的情节:在绿洲世界中最终的胜出并不是通过获得游戏(Adventure)的通关,而是找到游戏(Adventure)中的隐藏彩蛋;哈利迪(Halliday)因为游戏而失去友情,他将此视作一生中最大的遗憾;韦德·沃兹(Wade Watts)在接管游戏后,执意在每周的周二和周四关闭游戏服务器,让大家可以回归现实生活……《史诗电影》也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在这部影片里虽然出现了《达芬奇密码》(TheDaVinciCode,2006)、《X战警》(X-Men,2000)、《加比勒海盗》(PiratesoftheCaribbean,2003)等大量来自好莱坞大片的彩蛋,但是影片实际上是以恶搞的方式解构了美国大片文化,对重形式轻内容的大片予以批评。由此可见,彩蛋电影并不是完全受商业意识形态支配和主宰的工业文化,它也是一种可以进行“协商”甚至“对抗”的媒介文化,能够进行自反性审视。
四、结语
在人类传播史上,技术始终是媒介生态变动的关键驱动力,数字时代的技术对媒介的变革更是几近形成垄断态势。从技术进化的角度来说,媒介变革过程中既会选择某些新媒介,也会淘汰某些旧媒介,但是作为人类社会交流渠道的媒介,其更替交迭的复杂性远远高于技术的线性进化。“技术正使我们的世界不断加速并趋于复杂,而我们却没有能力应对这种复杂性……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平衡的共同进化”[30]。各种媒介都面临这样的困境,工业技术催生的电影媒介同样面临着技术进化对媒介生态的冲击,并需要适应新媒介兴起所带来的信息爆炸和传播互动等社会变化,彩蛋电影的兴起就是电影艺术与媒介技术在信息时代共同发展的结果。
电影彩蛋的历史由来已久,百余年来它始终只是电影招揽观众的策略或导演与观众游戏的伎俩。20世纪70年代以来,数字技术开始介入电影,直至21世纪以来数字电影彻底取代胶片电影,技术对电影的影响程度几乎可与电影诞生初期相媲美,正是在技术主导的背景下技巧式的电影彩蛋升级成为彩蛋电影。彩蛋电影是深受技术影响的电影体裁,它的超文本结构、超链接方式、再媒介机制、多媒介文本都严重依赖数字化社会所形成的技术思维和媒介经验。与此同时,彩蛋电影的文本间性也深度依赖电影史、艺术史和当代文化场域,各个时代的艺术和文化支撑着彩蛋文本的互文。可见,技术与艺术的共同作用催生出彩蛋电影,彩蛋电影是“平衡的共同进化”的产物。
彩蛋电影常常被人们贬斥为娱乐花招和赚钱伎俩,电影精英主义者对它持蔑视的态度和拒斥的立场,事实上它不纯然是电影工业或是商业运作的结果,它以提供心智游戏、进行意义再生产等方式成为当代文化场域的一个“单子”。从经济角度来说,相比使用彩蛋涉及的版权投入成本,彩蛋电影的营利性和利润率并不足以驱动这种电影现象的发展,是观众知识结构和审美需求的变化决定着电影创作上的这一偏移。因此,彩蛋电影以艺术形式映射社会的变迁和人的发展,是艺术自主性和媒介能动性的共同体现,彩蛋电影的兴起与远景也取决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