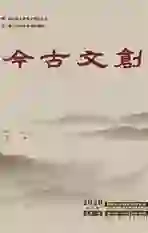滚滚红尘中的复杂人性
2020-08-25潘雨婷
潘雨婷
摘 要: 黑娃作为《白鹿原》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一直以来学界都侧重于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黑娃形象进行解读。本文指出,对作品的分析应当回归文学的本体性:结合具体的时代语境以及作者陈忠实的创作理念来看,对于文学本体性的自觉追求逐渐成为同时代作家创作的主流思想。因此本文结合具体文本,从时代情绪以及人道主义精神两方面对黑娃形象作出分析,着力于还原文学的“人学”特征。
关键词:《 白鹿原》;黑娃形象;创作理念;人性;人道主义精神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264(2020)01-0014-03
在绝大部分已有的研究当中,黑娃是叛逆的代言人,传统文化的皈依者。少年辍学、娶回小蛾、加入农协、成为土匪,这十六个字已然成为黑娃狂暴式反叛的最佳证明。最后被国民党顺利招安,被朱先生纳入门下,立志“学为好人”,理所当然地被归为他屈服于传统文化的重要标识。黑娃被看作一个失败的儒家伦理思想反叛者,他是小说中最有可能向白嘉轩和朱先生所代表的儒家伦理文化进行直接挑战的人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黑娃绕着他的人生转了一圈,又回到了他所憎恶、所反叛的儒家伦理文化中来。“兆谦闯荡半生,混账半生,糊涂半生,现在想念书求知,活得明白,做个好人。”黑娃对朱先生所说的一席话成为他反叛失败的最佳明证,他也因此被打上失败反叛者的标签。但从未受过系统革命理论教育的黑娃为何会自觉反抗封建文化?这种解读是否合理?黑娃到底以怎样的面目存在?我们究竟应该用何种眼光去阐释黑娃形象?要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我们首先要回到作家身处的创作环境以及作家的自觉艺术追求上来。
一、陈忠实创作理念面面观
这一切似乎需要回到作家的创作,作家为何会创作出一个黑娃这般的形象。黑娃并不是一个正直高大、完美无缺的英雄式扁平人物,善与恶、邪与正、忠与奸、淫与直在他身上交织。不同于传统农村题材小说当中一身正气凛然的主人公,陈忠实似乎力图在人性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的层面上折射出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白鹿原》作为上世纪90年代乡土文学的一支,它一方面保持着新中国文学农村题材的基本品格,以现实主义为主调;另一方面则更加注重对历史的讲述与对乡土概念的现代性反思。时代特征之下,乡土叙事的转型视角或许能够成为我们剖析黑娃复杂人性的切入点。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历经各种各样的文学潮流和高潮,表现出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艰难转化的趋势,与一种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时代风气对于成长在这一时代的陈忠实有很大的影响,这一阶段之后他的小说创作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创作诉求当中强烈的政治情结与道德意识逐渐融解在对于文化心理与真实人性的探寻与表现当中,关于人道主义的争论深深地影响到作家群体的创作,英雄人物创作逐渐淡出作家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表现复杂深刻人性的诉求。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浪潮的推进,中国作家、学者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西方文学作品,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强烈地冲击着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对此作出的应战实际上是对文学本体实在性的回归,中国作家开始在文学意义上寻求与西方、与世界对话。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为现代性的激情所推动,在摆脱所谓的极左路线时,文学更加激烈地追求现代化。陈忠实等陕西作家,并未在其中找到中国文学的准确定位,此时出现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给迷惘探索当中的中国作家指出了一条明路。意识形态在文学当中逐渐式微,关于创新的焦虑深深地困扰着作家群体,魔幻现实主义的成功使作家们对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以现实主义的手法书写乡村社会,则将传统与现代和谐地接洽在一起,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范式。
《白鹿原》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自90年代初期之后,中国社会普遍有回归传统的倾向。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下,基于社會信仰缺失的现实以及重构意识形态的需要,对于传统文化的呼唤影响到作家的文学创作,表现为文学观念的逆转,80年代对于传统的反思性批判一夜之间转向对于民族本位文化的认同。《白鹿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持肯定态度,试图以宗法制的传统观念作为中国文化的精髓,作为走向世界的民族性标记。他以传统文化作为民族的立根之本,力图于在传统文化中寻求涵盖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精神价值,黑娃最终转向于“学为好人”,归顺儒家传统体现着作者回归传统的文化理想性。
二、黑娃形象中的时代与人性
(一)时代情绪之身份焦虑
《白鹿原》描写了从清末到新中国建立这段时间里在关中大地上发生的国事、家事,勾勒出一个个形象生动的人物,其中最让人感到痛心的当属黑娃。从外出熬活到参加农协,从加入习旅到落草为寇,从投降归顺到反正起义,最终殒命于白鹿原,他本人的人生经历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史。不同的是,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实现民族独立和现代化方向明确的历史,而黑娃的人生则是在矛盾中挣扎,于茫然中摸索的历史。
他的自卑怯懦、迷惘无助、狭隘自私都极具代表性,反映出农村青年面对动荡时局的身份困惑。他们有着参与革命的满腔热血,却没有高瞻远瞩的政治谋略;他们渴望以一己之力为新中国打开一片天地,却无奈于政党更迭的纷乱时局令他们无所适从;他们希望能够凭借努力奋斗实现阶级的跨越以谋得更好的生活,却在面对复杂党争之时败下马来。黑娃的一生都在时代中踽踽独行,没有坚定的政治理想与目标,没有志同道合的伙伴与朋友,辨不明忠贞伪善,分不清奸佞良正,最终百口莫辩而冤死在白鹿原上。
黑娃的人生最后以失败收尾,他的一切愿景都陨灭在一声枪响当中。他的冤死无可避免地与白孝文的虚伪残忍有关,但仔细深究下去,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他面对人生选择时的窘迫与无助。黑娃一生集国、共、匪、儒多种身份于一身,如此丰富的人生经历背后,实际上是强烈的身份焦虑与信仰缺失。黑娃所作出的决定常常源自于一种盲目的冲动,黑娃对于这场革命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一雪前耻与报仇雪恨之上,真正发动黑娃参加革命的,实际上是黑娃对于提高自己社会地位,以及改变社会阶级的强烈要求与渴望。对于革命的粗鲁理解为黑娃最后选择入山为匪的行为做了铺垫,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理解却又和同时代选择投身革命的无数农民的缘由吻合。
在近代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危亡时刻,无数社会底层的有志青年就是如黑娃一般通过培训而动员起来参加革命的,但这种短暂的培训实际上并不能为黑娃一般没有接受过系统革命知识教育的农村青年指明一条人生发展道路,确定毕生发展的方向与轨迹,黑娃未来所作出的身份探索实际上是他在不断寻求归属感的过程,动荡时局之下强烈不安的心理正是底层人民的典型状态。即使是最后走上“学为好人”的归顺儒家之路,逼迫他作出选择的,也并不是人性的顿悟与传统文化的熏陶,而是毕生反抗对象的衰微与消解所带来的无意义。这种无意义令他感到焦虑与绝望,此时转向为之挣扎了半生的传统儒学成为填补心灵空缺的最佳途径。
(二)人道主义之复杂人性
黑娃作为陈忠实笔下最具反叛精神与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发展历程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最令人不解的也正是矛盾迭起的身份选择,他前后不符的言行成为解读视域中人们争论的焦点。有人提出陈忠实既站在道德主义的角度去思考如何获得救赎,又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表现历史的必然性,道德的衰亡呈现出一种无可挽救的颓势,历史的必然性当中藏纳了无数荒谬与混乱,因此作者写作之时便陷入历史与道德的悖论而无从得解,贯穿黑娃一生的反叛精神成为这一论调的最佳例证。黑娃最初强硬反叛传统伦理道德的姿态与最后自觉选择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行为过渡生硬,难以令人信服,价值观上断崖式的转换表现出作者身份处理上的无力。
然而对于文本作进一步的深究,我们却会发现,黑娃的反叛是一种无意识的不自觉的反叛,黑娃种种不合常理行为背后是生命个体中涌动着的人性,黑娃这一形象的设置实际上是作家急切想要表现的人道主义精神。黑娃有强烈的生命本能冲动与个体意识,他所做出的种种决定更多时候是遵照自己的意愿而不符合封建礼法规范的要求。但這种反叛从人类毕生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更多地应该被归结为青少年的叛逆心理,而并非“五四”传统影响下摧毁旧制度并建立新制度的自觉反抗。
一直以来,黑娃与田小娥的结合都被看成是黑娃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自觉逃离儒家传统文化的义举,但对文本进行研究后发现,首先提出叛逃的是田小娥。黑娃在选择这一段被鹿兆鹏夸赞的自由婚姻时,并不明白这种行为背后蕴含的文化意义。他之所以选择开始这一段关系,根本上来自于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长期性压抑,而不是追求一段自由恋爱;他之所以选择找到老秀才家将田小娥娶回家,实际上源自于内心深处强烈的道德感与责任感,而不是有意挑战封建纲常伦理;他之所以选择在村外买下一口破窑洞拼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更多的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村民的认可,而不是表明自己着意于与白鹿原仁义精神对抗的姿态。
这时的黑娃仍然是白鹿原仁义精神身体力行的践行者。黑娃人生真正的转折从他决意在白鹿原上刮起一场“风搅雪”才正式开始。加入农协策划革命,革命失败仓皇出逃,而后转经鹿兆鹏介绍而加入习旅,跟着军队九死一生,战场上的生死厮杀、手指上沾染的鲜血以及对革命前景感到迷茫都让他怕了、累了、倦了。黑娃曾经由一次培训激发起的革命激情与疾恶如仇的勇敢直率脆弱不堪,在真实而残酷的战争面前轰然崩塌。不同于“十七年”文学当中对于革命英雄人物的全面美化,一系列变故之后,黑娃表现出来的退缩与软弱才真正反映人性中最不堪一击的怯懦。
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陈忠实的作品呈现出不同于“十七年”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他在表现人物时着力破除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并强化文学的本体性,黑娃形象当中的矛盾多疑正体现出作者对此的自觉追求。作为从仁义白鹿原上走出的青年,出逃伊始,黑娃身上依然有着一股仁义劲。进入习旅之时,黑娃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习旅长的安全,不论是职责本能还是兄弟义气他都尽心尽力。但在战争的残酷面前,命悬一线的危机与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让黑娃趋于崩溃,所作所为中开始显露出人性当中潜藏的邪恶。
这种对于生命的漠视与不屑显示出极端的残忍,但黑娃身上的这种邪恶只在情绪处于临界点时才集中爆发,当生活重归平静之后,人性中的善与美又回到本位。虽然做土匪时穷凶极恶,烧杀掠夺无恶不作,但当其正式被保安团招安之后,却又显示出超人的自制力,言行举止中又透出了白鹿原上千百年来滋养出的忠诚仁义风度。反叛意义的消解使黑娃急切地需要寻求新的精神寄托,曾经潜沉的对于儒学的敬意又一次浮上心头。从他选取高玉凤为妻之时开始,他就已经否定了自己之前的一切叛逆行径。“兆谦闯荡半生,混账半生,糊涂半生,现在想念书求知活得明白,做个好人。”他的这句内心独白,正是他回归白鹿原的正式宣言。至此,黑娃已经完成了心路历程中最重要的几次转折,彻底脱离了反叛者的形象。
一直以来,许多的文学评论将黑娃形象解读为失败的封建文化反叛者,但纵观黑娃人生经历的每一处细节,他的一生实际上从未真正自觉地对儒家传统文化发起过反叛,一直以来他都渴望着最终能够得到白鹿原的认同。在欲望的驱使下,他的种种不合礼法的行为有了依据。回到黑娃行为动机的原点,似乎一切都能够落脚于人性,黑娃人生中的各种插曲实际上折射出人性当中复杂与矛盾的一面。
三、结语
陈忠实的创作一直在谋求作品的去意识形态化,那么对于其中人物形象的解读更应该注重文学的本体性,作品当中所展现出的人性发展的复杂历程实际上正彰显了上世纪80年代所兴起的人道主义精神。黑娃在小说中先后充当过小长工、革命者、土匪首领、国民党军官、共产党副县长等差异极大的社会角色。从倔强地叛逆到狂暴地反抗,再到从容地皈依,他逐渐由一个少不经事的愤青成长为沉稳深厚的成熟男性,世事沧桑将黑娃的锐利棱角磨平,也给予了他积淀着人生历练的深厚底蕴。剥离政治的影响,回到文学本体再来看《白鹿原》当中的黑娃形象,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是滚滚红尘中翻腾着的复杂人性。
参考文献:
[1]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2]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吴进.论陈忠实对柳青的“剥离”[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 (5).
[4]赵丛浩.矛盾一生——简析《白鹿原》黑娃形象[J].山东文学(下半月),2011, (4).
[5]傅强.崇拜与反叛——从黑娃形象论《白鹿原》的儒家文化[J].淮海工学院学报,2012, (8).
[6]朱慧娟.灵魂的变异——浅析《白鹿原》中黑娃的形象[J].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10, (7).
[7]杨明巍.失败的剥离——精神分析视角下的黑娃形象[J].青年文学家,2016, (8).
[8]王渭清,代纪东.从鹿三父子的人格悲剧看 《白鹿原》的人格治疗学意义[J].唐都学刊,2005, (4).
[9]李晓卫.现实主义的精髓——陈忠实与柳青创作的倾向观比较[J].兰州学刊,2011,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