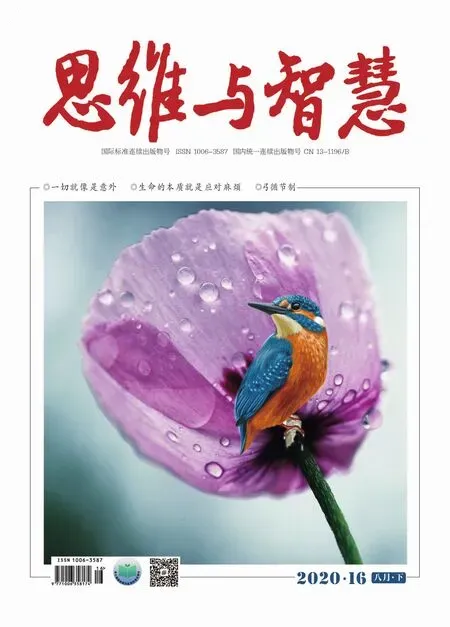记忆中的煤油灯盏
2020-08-22王维胜
●王维胜

最近我在一家民俗馆看到一个展品——一盏煤油灯。我的脑海,立刻浮现出儿时的情景,煤油灯微弱的光芒,勾起我心中柔软而温暖的记忆。
那是小时候的事。村里大部分人家的煤油灯盏都十分简陋,寻一个空墨水瓶或玻璃药瓶子,按照瓶口大小找一块薄薄的铁皮,用剪子剪成圆形瓶盖。盖上钻个差不多筷子头一样大的孔。然后用棉絮搓成一个长长的棉条,也就是灯芯。芯子外面包一截薄铁皮卷的寸把长的小筒子,插进孔中固定。芯子伸进瓶内煤油中。露出瓶盖的那截棉芯子,也被煤油洇湿,用火柴点着,灯焰如豆般摇晃,荧荧的火头跳跃着,闪动着,光芒填满了整个屋子。朦朦胧胧的光线下,屋子里箱柜的影子拉得很长。
每户人家的灯盏都放在固定的地点,或窗台,或炕头,或在墙壁上掏个洞,专门放灯盏。
煤油灯是明火,灯盏长年累月放在同一个地点,灯火烟熏火燎,土墙就变成了墨黑的颜色,灯盏底也是油渍斑斑。尽管灯盏油渍尘积,一副黑黝黝的模样,但它点亮满屋昏黄,照亮了凄清的夜晚。
母亲从生产队干活回家,赶紧生火做饭。待吃了饭,洗了锅,喂完猪,天就黑了,忙碌了一天的母亲爬上炕,划一根火柴,点燃了炕头栏台上的煤油灯。
煤油灯的光芒蹒跚而来,弥散开来,照亮炕头,照亮糊着报纸的墙壁,照亮了屋顶被烟熏得乌黑发亮的椽子,照亮屋子的每个角落。家的温馨与宁静,舒适与温暖,立刻涌入我们心间。
母亲就在如豆的灯光下做针线,粘鞋帮、纳鞋底、缝衣服。我在炕桌上摆好作业本,盘腿坐在暖暖的炕上,趴在煤油灯前歪歪扭扭地写字。但那时没有升学压力,学不好也没啥事,学习都是自己的事。母亲不识字,也不会问学习上的事,老师似乎也没有布置多少作业。我很快写完作业,倒头要睡。
母亲是女人,她怕寂寞,深夜里也会恐惧,但没有大人陪她闲谝。就让我和尕姐陪着她。我不肯,她用满是老茧的手抚摸着我的头说:“你们甭睡,我给你说古今。”说古今就是讲故事。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很会讲故事。深夜里,母亲一边在煤油灯下纳鞋底,一边讲故事。她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生动,鲜活,不但那时候爱听,时隔几十年,还有不少母亲讲的故事在我的心底里涌动,能随时追忆出来。我最喜欢听故事,但过不了多久,就打盹睡着了。
隆冬漫漫寒夜,我半夜醒来,睡眼朦胧睁眼看一下,母亲斜凑在灯前,用针轻挑灯芯。那情景,现在回想起来,特别温暖,特别温馨。
灯芯烧尽,灰烬仍旧在灯芯上,在火焰中会结成花朵般的灯花。灯花一点点增大,煤油灯的光亮就会一点点变得微弱。这时候,母亲拿起剪刀,轻轻剪掉一点灯芯,灰烬随之被剪掉,仿佛灯芯注入了新鲜血液,焕发了青春,瞬间屋子又亮了。
父亲后来从城里买来了一盏罩子灯。高高的灯座,圆圆的肚子,还有一个长长的、透明的玻璃灯罩,灯口有一个旋钮,轻轻地一转,灯芯就上下蠕动。天黑以后点亮灯,放上罩子,黑烟随着罩子向上飘浮,柔和的光线立马四射开来,照耀整个房间。罩子灯的好处是灯芯粗,火焰大,亮度好,不怕风,却费煤油,因此罩子灯只在农忙吃饭时摆在桌上,或者晚上来客、逢过年过节时才舍得用。
那一盏盏发着昏暗光芒的煤油灯盏,如同母亲讲的故事,如今已退出了生活,走进了博物院、民俗馆,可是我忘不掉那萤火虫般微弱的光芒在漆黑的夜里摇曳的情景,它虽然粗糙,却驱散了黑暗,点亮了寂静幽暗的家园,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带来了心灵慰藉,带给童年的我无数的快乐,使我的黑夜不再寂寞。它的灯光虽弱,火焰虽小,但它燃烧的执著却具有穿透一切的力量。
(北方摘自《农民日报》图/槿喑)